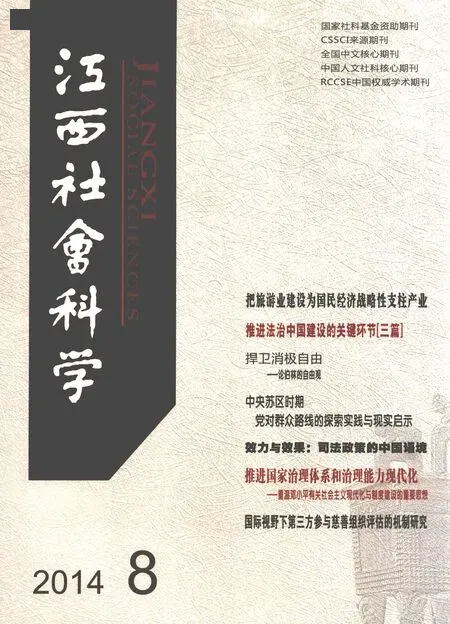地域文學中的后現代主義——以現代嶺南文學為例
■葉從容
后現代(后現代主義、后現代思潮)的由來,大多追溯到20 世紀初,尼采被尊作鼻祖。20 世紀60、70 年代起,歐美后現代思潮風起云涌,興盛一時,至今仍未現衰竭之象。所謂現代嶺南文學,以20 世紀初為起點,延至當下,起始點與前者大體相當。20 世紀,古老中國文明與西方現代思潮多次碰撞,促成了本土文化與后現代主義的博弈與交融。嶺南獨特的地理、人文環境,使其成為東方文明與西方思潮博弈的前沿,現代嶺南文學記錄下了后現代主義在嶺南地區的行進軌跡。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后現代主義的內涵非常豐富,后現代的思想大師們在后現代主義的大纛下詮釋出不同的精彩。自百年前尼采敲起現代性的喪鐘,后起的反現代主義者從不同角度去超越或批判理性主義、本質主義。利奧塔把后現代主義視為與宏大敘事相對立的元敘事,福柯從權力的角度批判無處不在的人的壓抑,德里達在語言與文字中暴露了本質主義的謬見,杰姆遜把后現代主義視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巴赫金推崇狂歡式的民間話語方式。此外,伽達默爾的對話觀、德勒茲和加塔利的視角主義多元論、懷特海的有機論、霍伊的系譜學解釋學、麥克盧漢的電態文化、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賽義德的后殖民主義研究等,無不展現出后現代主義內部的蕪雜與多元。
與此相應,后現代主義在文學上并沒有公認的、整齊劃一的劃分標準,中國文壇亦然。有學者曾經指出,后現代主義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主要表現為后現代性——作為后現代主義的因素存在,而不是一種明確的后現代主義作品。如王朔的反主流、反精英主義,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蘇童、格非的新歷史主義,殘雪的碎片化敘事等等。對于嶺南文學而言,后現代主義主要體現在對形上性的漠視、邊緣化的自足等等,呈現出德勒茲所言的“游牧思維”特征。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嶺南文學的這些特性并不是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產物,從20 世紀初以來,這條線索或隱或現,始終潛行其中,成為嶺南地方性文學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現代嶺南個性的文學生成與后現代意識的萌生(20 世紀初—1949)
嶺南,古稱嶺表、嶺外、嶺嶠、嶺海等,泛指五嶺以南的地區。本文所涉及的嶺南,主要包括廣東、廣西、香港、澳門以及江西、湖南部分地區。
19 世紀前的嶺南文化應當劃歸中原文化的大范疇。文學方面,嶺南素有“雄直”之風,從張九齡到陳白沙、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等莫不如此。然而,作為“化外之地”的南粵大地所受的中原文化輻射畢竟有限,對儒家文化的推崇遠不及內地,有利于生成獨特的文學個性和異質思想。同時,作為一種世俗文化,嶺南文化追求世俗的享樂而遠離意識形態的規范,表現出“地域性與超越性,時空性與超前性,個性與時代趨向性結合”[1](P169)的基本特征;它務實靈活,善于變通,是一種“利益驅動人心思變”、“俗世自樂輕言規范”、“平民心態疏于王權”[2]的文化形態。世俗、包容、務實的嶺南世態民風成為接納、傳播后現代主義之類外來思潮的有利背景。
后現代主義在嶺南地區的早期發生還有其外部因素。19 世紀末以來的激蕩風雷豐富了嶺南文化內涵,有利于現代、后現代主義元素在這片土地上率先萌發。首先,獨特的地緣優勢帶來更加開放的視界。19 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的戰船轟開中國的大門,也帶來國人空間意識的劇變。大量嶺南人漂洋過海帶回異國他鄉的新奇體驗,更貢獻了諸如容閎的《西學東漸記》、梁啟超的《夏威夷游記》、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等睜眼看世界的名篇,給讀者帶來天朝帝國之外的世界印象,播下了多元化思想的種子。同時,長期以來廣州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商埠,外來思潮與本土文化持續不斷地碰撞、交融,利于催生有別于以鄉村經驗為主體的黃土文明的異質思潮。此外,現代傳媒的萌芽和發展促進了現代、后現代元素的孕育、萌芽。作為中國現代報業的先行者,嶺南更早步入了現代傳媒的發展征程。史料顯示,中國近代的第一張報紙,是1858 年在香港創刊的《中外新報》,1833 年在廣州由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創辦和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則是在我國本土上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在現代報刊的影響下,廣東出現了各種文學性、新聞性結合的文本,如《古靈精怪》之類的民間刊物,通過唱詞、民謠的形式寫時事,形成了一種地方色彩鮮明的新聞形態,也對嶺南的世態民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嶺南文化、地域等諸方面的獨特背景為后現代思潮的萌生和發展提供了便利,嶺南文學的后現代性得以在地方性、商業性、多元性的語境中萌生。它低調卻頑強地貫穿了20 世紀的嶺南文學世界,成就了地方文學面向世界與面向自身相結合的典范,成就了現代嶺南文學的獨特經驗。
現代嶺南文學是鄉村經驗與城市經驗、地方經驗與主流經驗、本土經驗和海外經驗糅合的產物。從共時性角度看,嶺南文學還有海洋文化、殖民地敘事、海外敘事的內涵,欲望、肉體、消費是其常見符指,構成了現代嶺南文學個性的基本內容。現代嶺南文學個性的生成與后現代思潮有內在關聯,其生成過程與嶺南后現代意識萌生與發展歷程大致同步。綜觀話語模式、題材特點不難發現本階段嶺南文學后現代性的主要特點。
(一)多元化的表現形態和話語內涵
后現代倡導多元論,信仰“本體論的平等”,主張接受和包容差異。嶺南地區的文學文本大多雅俗參差,既無統一形態,亦不分優劣尊卑,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各得其樂。
梁啟超、黃遵憲等嶺南先行者的文學主張和創作集廟堂與民間的雙重特點,余韻流傳,經久不衰。梁啟超倡導解放文學表現力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黃遵憲則身體力行打破文體等級觀念,積極向民間學習。除了汲取客家山歌經驗,他還建議用非母語民間文藝形式的廣府粵謳書寫時政,在當時文壇產生很大影響,也為后世留下可資借鑒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
嶺南文學在話語內涵上也表現出很大的自由度。以20世紀初留學生的海外敘事為例,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的留日文學與家國有關,而以張資平、李金發為代表的嶺南海外敘事更顯平和、包容,少了身世感慨,多了幾分對異質文化的認同。又如左翼文學方面,早期陳殘云的創作如《風砂的城》、《小團圓》、《受難牛》等,雖然有鮮明的左翼政治色彩,但作者已能有意識地寫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和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塑造了一批具有“流氓性”、“小市民氣習”的農民形象。這些并不完美、高大的革命人群,卻讓我們讀到比一般左翼文學更多的鮮活人性,也為文壇填補了為大寫的工農兵形象所遮蔽的更廣泛、真實的社會人生。香港作家的創作更為靈活,他們有的開創了香港城市底層敘事的文學世界,如侶倫的《窮巷》;有的則以華僑故事開辟了新的題材領域,如司馬文森的《南洋淘金記》、杜埃的小說集《在呂宋平原》等。
總體而言,20世紀上半葉的嶺南文壇群雄并起卻各不相擾:李金發的象征主義、張資平的市民小說、黃谷柳的都市底層傳奇、陳殘云的嶺南水鄉故事等各有精彩,貌似沒有龍頭、缺乏主流,卻折射出文學生態的自由、舒展,體現出有別于等級森嚴的主流文壇的所謂本體論平等。
(二)言語模式凸顯地方性特征
方言不僅是工具,更是文化、思維方式,是嶺南文學地方性的重要表征。嶺南文學的方言寫作現象十分突出。除了木魚歌、粵謳、客家山歌等以民間形式表現民間悲歡,還有《古靈精怪》之類民間形式、新聞性質的早期傳媒文學,它們之間最大的共同點是方言寫作。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與方言結合的創作在嶺南長盛不衰。20世紀30 年代,歐陽山以《廣州文藝》為陣地倡導粵語寫作,并帶頭創作粵語小說《單眼虎》等;陳殘云的作品中也遍布了各色粵語,如話頭醒尾、知慳識儉之類的方言土語,傳遞出嶺南人特有的思維方式、文化氣息。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被譽為20 世紀40 年代末華南地區最受讀者歡迎小說的《蝦球傳》(黃谷柳),這部作品的大眾化、地域化努力效果明顯,通過大量的粵港方言突出地域特點,即在總體規范的基礎上融入地方俗語、民謠、土話、外語等等,既不影響不同地域讀者的閱讀理解,又為作品打上“嶺南制造”的烙印。這種多語言元素混搭的表達方式影響久遠,至今盛行不衰,傳遞出嶺南人獨特的認知方式、思維習慣,彰顯了鮮明的地域性特征。
(三)異質性的商業化寫作
商品化寫作是后現代主義社會的特征之一。馬爾庫塞指出,發達工業社會中,藝術發生日常生活化,進而發生俗化,這使文學失去批判立場;阿多諾也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生產進行嚴厲的批判。在他看來,發達工業社會(后現代社會)的文藝狀態是娛樂化、市場化的,作家為了市場而寫作,他們孜孜不倦追求的只是作品的商業價值。
務實重商的嶺南人對文學商業化有較高的包容度。尤其是作為西方殖民地的港澳地區,它們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最終形成與內地主流文學發展道路迥異的商業化發展風貌。這類帶有異質文化性質的文學經驗反過來又參與了對大陸嶺南文學的形塑,刺激、推動了嶺南文學與主流文學的若即若離以及對商業文化的天然親近。
嶺南地區最早與市場大規模結盟的著名作家當屬張資平。張資平善寫現代人的婚戀故事,以三角戀、畸戀之類題材迎合普通讀者閱讀趣味,作品暢銷一時。沈從文指出:“所以張資平也仍然是成功了的:他‘懂大眾’,把握‘大眾’,且知道‘大眾要什么’,比提倡大眾文藝的郁達夫似乎還高明。”[3]比照馬爾庫塞、阿多諾等的后現代觀,我們不難發現張資平小說另一種解讀路徑:他的情愛小說堪稱中國本土最早、最世俗化的現代文化工業產品之一,已經基本具備了今天市場化寫作的主要特征。從個體“作坊”到雇傭幾名窮學生寫手,更借助現代傳媒的發展,他站在了那個時代文化商品生產的前沿,不僅紅極一時,更以生活化、類型化、商品化、消費化、世俗化的小說創作奠定其在現代都市言情類通俗文學史上的地位。
綜觀20世紀上半葉的嶺南文學創作,我們不難從中梳理出一條有別于主流思潮的文學發展線索。其中對大眾化、商業化、世俗化等等元素的強調使這一時期文學呈現出接近于后現代主義的一些特征,這是不容忽視的。
二、同一性語境下地方性策略的建構(1949—1989)
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方向早在“延安時期”便已確立下來,解放區文藝經驗被全國推廣,力倡文學政治功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成為全體作家的創作指南。同樣奉“延安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圭臬的嶺南文學與各地文壇一起經歷了政治的考驗。與眾不同的是,即便在極端政治環境下,嶺南個性仍通過地方性策略頑強地表現出來。
“地方性”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研究的重要命題。在其代表作《地方性知識》中,吉爾茲通過地方性知識的強調揭示了邊緣的獨特意義。吉爾茲的地方性與以往倡導的民族文化不同。啟蒙時期的文學家們如伏爾泰、萊辛、赫爾德、歌德等曾大力倡導民族文學;斯達爾夫人在《論文學》中提到過南北方審美取向的不同;泰納指出文藝發展取決于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這些學者雖然倡導關注地方的個性,但大多通過對文化的反思解釋其獨特意義。對比而言,吉爾茲的思想無疑更具超越性、啟發性。“地方在此處不只是指空間、時間、階級和各種問題,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對所發生的事件的本地認識與對可能發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聯系在一起。”[4](P126)通過對地方的強調,吉爾茲抹去了中心與邊緣、自我與他者、西方與非西方等的對立性,倡導多元視角與立場,表現出超越性的后現代主義眼光。
地方性與后現代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后現代的特征之一就是通過地方性展示出“求異性”,地方性經驗與后現代意識共生,通過對地方性的認可肯定文化的多樣性,從而對普世性所遮蔽的各種區域性文化中獨特的精神價值進行了祛蔽。因此,強調“地方”是全球化浪潮中的另類,是對席卷地球村的同一化思想觀念、思維模式、生活形態的拒斥。地方元素在文學中的出現不僅是保留傳統的、地方的記憶,同時也是對文化多元化、文學生態系統多元化的捍衛,對地方文化的生產、繁榮、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見,地方性的強調是后現代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地方性不僅是對現代化、理性主義的拒斥,也是對全球化、普世性背景下自我個性的堅守。從新中國成立到20 世紀80 年代,成功的嶺南文學創作大多以地方性取勝,地方性策略在靈活、圓融之中消解同一化文學思潮壓力,為文學個性的生存爭得寶貴空間。陳殘云、秦牧等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陳殘云的創作體現出嶺南特有的包容、寬厚、實在、不走極端的文化特征。有學者指出:“廣東小說至今形成不同于北方文學的南國風格特點,可以溯源于陳殘云,而且,由于他的作品的成就,廣東小說逐漸走向獨立,成為新文學小說領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5](P135)陳殘云小說的地方性策略是全方位的,不僅表現在常見的內容、題材、語言、風格等具體層面。如曾有批評者指責《金沙洲》中黨支書劉柏和婦女干部梁甜等基層干部形象不典范,沒能反映這一群體的先進性、典型性。但打動人心的恰恰是這些所謂不完美的形象,他們身上的弱點或不足拉近了作品人物與讀者的距離,流露出同時期高大全式英雄典型所普遍缺乏的親切感、真實感。
同時期另一位重要作家秦牧的散文被譽為思想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統一的典范。他既注意迎合主流,又常常另辟蹊徑,含蓄說理。秦牧強調文章的真善美統一,這使他的散文在那個高揚同一性的時代呈現出獨特的文學趣味和真性情。
如果說老一輩的作家大多只能含蓄、謹慎地傳達地方性立場,新一代嶺南人則更灑脫、自信。20 世紀80 年代,橫空出世的《雅馬哈魚檔》、《你不可改變我》等本地佳作帶給人們新的驚喜。
章以武、黃錦鴻的中篇小說《雅馬哈魚檔》堪稱中國改革文學先驅之一,啟蒙意義顯而易見。但小說最成功之處在于塑造了當代主流文學長廊長期缺席的新一代市民形象。改革開放背景下的一群都市小人物,“沒有發現新大陸,沒有發明原子彈,沒有得過金牌,沒有得過獎章,甚至還沒有做過什么值得記下來的好事”[6](P102),卻組合成市場經濟下蕓蕓眾生的生動速寫,展示了消費社會帶來的欲望躁動與思考。
如果說《雅馬哈魚檔》更多是以題材和人物創新取勝,《你不可改變我》則開始表現出嶺南青年從骨子里流露的后現代意識。主人公孔令凱的我行我素、特立獨行,既可以解讀為現代性的主體意識的覺醒,也可以歸入后現代主義的范疇去解讀,如后現代主義解構一切,反主流、反傳統,肯定個體欲望等特征,都能從主人公與眾不同的言行中找到對應。
本階段的港澳作家既無太大的意識形態壓力,也沒有崇高的作家光環,商業氣息濃重的現代都市對曲高和寡的現代主義文本表情冷淡,卻熱烈歡迎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大眾化作品,金庸、衛斯理等的小說由此廣受追捧,風光無限。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大多數香港作家的后現代意識是潛行、內在的,主要表現在商業化意識和大眾化形態等方面,也有一批作家直接對現代西方思潮做出回應,其中最主要代表是劉以鬯、黃碧云。從20 世紀60 年代的《酒徒》開始,劉以鬯一直沒有停下實驗的腳步,其中廣受關注的《打錯了》成為反思現代性的絕佳隱喻:一切因果并非必然,偶然才是命運的終極裁決者。個體如此,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發展的進程亦然。女作家黃碧云受法國新小說派影響較大,她贊賞小說的無情節、無人物,喜好超越傳統的零度情感敘事、暴力血腥的情節和符號化人物形象。對照20 世紀80 年代國內先鋒作家的創作,我們可以發現以劉以鬯、黃碧云等為代表的香港作家在先鋒路上起步更早,他們對各色形式主義的操練爛熟于心,碎片化敘事、符號化人物、隨意的拼貼等手法運用嫻熟,堪稱先鋒中的先行者。從市場化、大眾化的敘事選擇到后現代手法的靈活運用,香港文壇的后現代先行者既有內在精神的契合也有文學觀念的自覺追求,邁出了中國文學走向后現代主義的堅實步伐。
三、后現代語境中嶺南文學經驗的賡續及發展(1989—21 世紀初)
劉西鴻《你不可改變我》中張揚的個性,已然預示著嶺南文壇個人時代的到來。進入多元化社會的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嶺南文壇群雄并起,張欣式的新都市寫作,黃茵、黃愛東等的小女人散文,木子美的身體寫作,鄭小瓊、王十月等的打工文學以及形形色色的商界敘事等等,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異彩紛呈的多元化景觀。20 世紀末以來,嶺南文學的后現代特征愈發明顯,大致有以下表現:
(一)以游牧思維對抗整一思維
德勒茲曾經用游牧式思維來解構整一思維,并由此闡述后現代主義思想的特點。整一思維呈現總體性、同一性、層級性特點,游牧式思維則重個體性、多元性和反層級性。前者試圖控制、一致,后者則更多呈現出自由、游走的特征,它總是試圖擺脫整一掌控和設計。德勒茲進一步解釋道:“游牧者并不一定是遷移者……相反,它們不動,它們不過是待在同一位置上,不停地躲避定居者的編碼。”[7](P167)
反觀這一時期嶺南文學的發展,不難發現其既有對傳統文化、主流話語的認同,同時也表現出較以往更為靈活、務實的品格,呈現開放、游走、個體化的特質。嶺南文壇向來少有號令群雄的野心,亦不喜拉幫結派,乃至形成了類似于洋蔥式的無中心的內部結構。近年來,雖有第三種批評、嶺南學、珠江文學等號召的發起,大多只是小范圍的回應或實踐。嶺南作家習慣獨步文壇,不喜盲目跟風,早前主流文壇紅極一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等潮流盛宴基本上沒有太多嶺南作家的身影。20 世紀末嶺南文壇雖好戲連臺,但大多只是孤軍作戰,如:張欣的都市傳奇、鄭小瓊的打工詩歌、黃詠梅的嶺南市民故事、錢石昌和歐偉雄的商界敘事、林賢治的在場散文、楊文豐的科學散文,等等。作家們不結盟,不重復,正可謂一個蘿卜一個坑,各有各精彩。
香港的文學隊伍則更加“散漫”:亦舒、岑凱倫、李碧華、林燕妮的言情,倪匡、黃易、張君默的科幻,梁鳳儀的財經,南宮博、唐人的歷史,張宇、余過的靈異,林燕妮的香水文學,張小嫻的隨筆,無不呈現出自在、自為的游牧品格。
(二)以紅塵瑣事取代宏大敘事
宏大敘事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其背后是西方源遠流長、深入人心的本質主義思維方式。自利奧塔以宏大敘事為靶,對現代性發射出致命的一箭后,宏大敘事在很多時候已經成為后現代主義的對立面而招致各方詬病。
嶺南文學向來欠缺“宏大”情結,幾至所有優秀作品都力爭回避“宏大”之重。20 世紀末以來嶺南的都市敘事是最引人注目的,但風頭最盛的廣州作家幾乎都不涉足宏大敘事:張欣的都市言情重在好看,情節跌宕起伏,人物命運富有戲劇性;小女人散文抒發都市女子的小牢騷、小體驗,精致得幾乎沒有質感;早慧的黃詠梅也無指點江山的野心,筆端始終撇不開珠江兩岸的市民悲歡。其他如珠海蔣麗萍、王海玲,深圳劉學強、黎珍宇等的都市文學也都不以宏大奪人眼球。總體而言,嶺南文學重于人間煙火而輕于形上玄思,樂于紅塵瑣事的吟哦而疏于史詩品格追求,甚至自動放棄了精英階層的批判、反思立場而走向對現實的諸多認同,呈現出馬爾庫塞所批判的缺乏批判與超越的“俗化”傾向。
(三)以肉身體驗消解主流話語
20 世紀末以來興起的網絡文學為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也為文學這種私人性極強的活動提供了聚眾狂歡的平臺。木子美、竹影青瞳正是其中代表。
不同于《北京娃娃》(春樹)的殘酷青春敘事、《上海寶貝》(衛慧)大都市俏嬌娃情與欲不可得兼的兩難,木子美,這個地道的嶺南人扯下青春肉體的最后一點遮羞布,以全裸的姿態殺入文壇,帶給文壇一片驚呼。其《遺情書》中沒有愛之纏綿和生之無奈,只有大膽、瘋狂、全無羈絆的性愛敘事。《遺情書》以欲望敘事、肉體敘事對抗主流社會所張揚的現代性、理性主義的同時,宣示了對無處不在的權力話語的反窺視、反控制:“忠貞教育是原始的性懲罰,它以占有欲代替自主權,鼓勵人們完整占有對方,并限制自我。當你奉為美德時,可又看到它是統治手段的延伸罷了。而我們反對統治的方式是,不以性自由為羞恥,不以性丑聞為淪喪,把‘懲罰’當作娛樂。”[8]就這樣,木子美式肉體狂歡的書寫將那些因張揚女性立場而略顯沉重的陳染、林白們拋在身后,以決絕的反權威、反傳統、反理性、反道德、反主流形象成為新世紀以來多元化嶺南社會一個鮮活符號。
杰姆遜指出:“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烏托邦式的設想,而后現代主義卻是和商品化緊緊聯系在一起的。”[9](P166)當下社會的商品化大潮,裹挾著地域文學在后現代主義道路上愈行愈遠。20世紀末以來,嶺南文學的多元化、邊緣化、商品化傾向進一步凸顯,從周星馳的無厘頭式電影走紅到木子美肉體書寫的轟動效應,以及質疑不斷卻綿綿播出的《喜羊羊與灰太狼》系列等等,無不彰顯后現代主義的強大影響力。
應該指出的是,嶺南文學在文化精神上與后現代主義思潮存在內在的相通,但大多數情況下這只是潛行于地表之下的暗流,而且后現代主義思潮在接受、傳播過程中也悄然發生了一些本土化轉換,任何過度的解讀都是有失客觀的。例如黃谷柳的《蝦球傳》,盡管文學史上占一席之位,也為嶺南文學的市民化、多元化、世俗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囿于作者自身的學養和視界,缺憾也是明顯的,如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展示不足,人物性格的單一和現代意識的缺失等,使我們無法將其與試圖超越現代性的后現代主義思潮相提并論。即便是時下的嶺南文學也尚未跨入成熟、純粹的后現代主義文學行列:一方面,嶺南文化固有的包容、平和有助安撫、軟化各種激越的思潮,后現代主義的反叛性由此變得更加溫和甚至曖昧,失去超拔與決絕的批判、反思與超越姿態;另一方面,嶺南文學的后現代性并不是對西方后現代主義理論的亦步亦趨,各種各樣的傳統思想與現代、后現代觀念交織混雜,導致了其內部的豐富性、復雜性,呈現出斑駁參差的特征。這是百年來嶺南文學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解讀現代嶺南文學的一個向度,將有助理解嶺南為代表的地域文學的獨特價值。20世紀以來的嶺南文學以其傳統與現代、后現代有機糅合的獨特書寫為文壇提供了一份可資借鑒的走向后現代主義的地方性文學經驗,也為其他地域文學提供了一份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發展樣本。
[1]謝望新.南方文化論綱[A].廣東省作家協會五十年文選·文學評論卷[C].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
[2]張紅娟,吳重慶.嶺南文化的靈活善變與廣東經驗[J].現代哲學,2000,(1).
[3]沈從文.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J].新月,1930,(1).
[4](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A].法律的文化解釋(增訂本)[C].北京:三聯書店,1998.
[5]鄧國偉.陳殘云小說略論[A].廣東省作家協會五十年文選·文學評論卷[C].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
[6]章以武,黃錦鴻.“雅馬哈”魚檔[A].紅棉花開:廣州市改革開放25年優秀文學作品精選(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
[7](法)德勒茲.游牧思想[A].尼采的幽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8]木子美.性的懲罰[J].時代人物,2013,(10).
[9](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