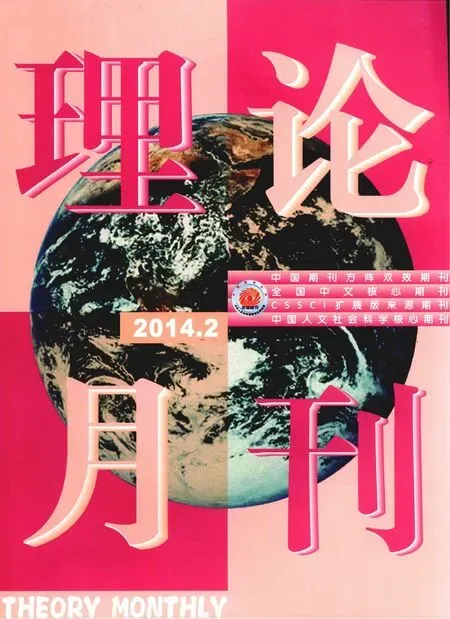社會權與社會階層作用機制再探*
李文祥,吳德帥
(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一、社會權與社會階層關系的現實考證
社會權概念是舶來品,最早提出社會權的是英國社會學家T·H 馬歇爾。馬歇爾將公民資格分為三個部分或構成元素,即民事權、政治權和社會權。“民事元素是由個人自由所必須的權利組成的:個人自由,言論、思想和信仰自由,擁有財產和簽署有效契約的權利以及法律的權利……絕大多數直接與民事權相連的機構是法院。關于政治構成元素,我意指參與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相對應的機構是議會和地方政府的委員會。關于社會構成的元素我意指從少量的經濟福利和保障權利,到完全分享社會遺產,并且依據社會中流行標準過一種文明生活權利的所有范圍,與社會權最密切相關的機構是教育制度和社會服務”。[1]馬歇爾所言的社會構成要素就是指社會權,也即是其一直所倡導的公民資格社會權,簡稱社會權。
社會權一方面作為個人獲得社會福利的依據,保障個人的生存與發展,進而實現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作為抵抗市場力量的另外一種反向力量,社會權也會對市場機制進行修正,進而形塑社會分層結構。然而,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福利困境導致了社會權的危機。上世紀上半葉社會權觀念的興起催生了福利國家制度。隨著非商品化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社會權不斷擴展,水平大幅度提高,福利國家在社會權基礎上亦不斷發展。正是因為社會權對福利國家的這種決定作用,當福利國家出現問題甚至走入困境時,便引發了人們對福利國家的改革和對社會權的重構。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福利國家之所以陷入危機,正是由于國家過分強調社會權,提供個人高水平的社會福利,損害了個人自由,助長了懶惰心理,并最終降低經濟效率,影響經濟的發展。因此,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市場在個人福利服務中的主導作用,主張個人在市場中憑借個人努力獲得福利,強調公民履行福利責任。新自由主義在強調個人責任的同時,否定了國家在社會福利服務中的責任主體地位,與福利國家單純強調國家責任反向而行,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市場再次成為個人獲得福利的唯一途徑的后果是人們再次被市場奴役而成為商品,這完全違背了社會權宗旨——勞動力去商品化。正如戰建華所言:“這種繼續擴張市場的做法與其說是對福利國家進行改革,不如說是對福利國家進行取締,新自由主義福利改革沒有緩解社會權危機,反而走到了社會權的對立面。”[2]
社會權的這種惡化狀況進一步影響了改革后的福利國家階層關系狀況。以剩余式、選擇式的社會救濟取代社會福利,必須存在不同的社會階層群體,社會救濟就是將受助對象即目標群體定位在處于社會最弱勢地位的社會底層群體,這種做法無疑會強化底層的邊界,無形中在底層與其他階層之間構筑了一條屏障,這種顯性化的標簽不但會給接受救助的群體帶來不同程度的屈辱感,還會對他們未來的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層析出底層群體同時,也阻礙底層群體向上流動,進而固化了這種分層結構。[3]
我國社會權及其與階層關系狀況同樣存在問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我國的社會分層機制逐漸由傳統的再分配體制向市場機制轉變。人們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更多是靠自治性因素獲得。由于市場機制本身對結果平等并不關注,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階層差距隨之加大。既然社會權是作為抵抗市場力量的另外一種反向力量,對市場機制進行修正,進而形塑社會分層結構,那么,我國社會權亦理應減小市場機制的副作用。但現實是我國社會權非但沒有很好的形塑社會階層結構,相反,不均等的社會權固化了我國階層結構。郁建興、樓蘇萍認為,我國社會權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我國公民的社會權并沒有建立在公民資格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身份、職業、收入等基礎上。也因此,社會權在促進社會公正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差別化的社會權本身就是社會不公正的重要來源之一。[4]孫立平直言,斷裂的社會源于權利的失衡。根本的意義上說,目前中國社會形成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格局,以及在這兩個群體之間形成的深深的裂痕,就是社會權不均衡的必然結果。[5]
二、社會權與社會階層關系的理論追索
以上是現實存在的問題。針對社會權及其與階層關系問題,人們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論回應。T·H·馬歇爾是研究社會權與階層關系的第一人。馬歇爾將公民權分為三個部分或構成元素,即民事權、政治權和社會權,馬歇爾正是從這三個元素出發,論述公民權是如何影響社會階級不平等體系的。“它不再滿足縮小提高社會殿堂基礎的層面,而留下上層建筑原樣不動。它開始重建整個建筑,而且它甚至通過將一座摩天大樓轉變為一間平房而告終”。[6]可以說公民權中社會權的融入和發展極大地縮小了階級、階層之間的差距,重塑了原有的社會階層結構,使之更加趨于合理。T·H·馬歇爾的《公民權與社會階級》是迄今為止論述現代公民權問題的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二戰后的福利國家就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建成的。
即便如此,馬歇爾的社會權與階層關系理論亦有其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首先表現在他對社會權的闡述上。馬歇爾提供的主要是一種有關公民權演化的“歷史描述”,[7]同樣,社會權亦是作為歷史演化的結果而自然而然的出現,即基于英國本身的歷史狀況,做出的描述性分析,這必然降低其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如果他國的社會權與英國的社會權特質有很大差別,那么,其對社會階層的影響還會如馬歇爾所論述的那樣,會縮小階層差距,緩和階級矛盾嗎? 除此之外,馬歇爾在論述社會權與階層關系時,只注重分析社會權對階層結構的影響。然而分析有關社會階層問題,除了對如階層結構等主題的把握外,還應從階層團結與整合,階層流動等動態把握;除了對如階層距離的客觀要素把握,還有階層情感(階層的心理認同,階層怨憤)等主觀要素的分析。馬歇爾并沒有在這些方面展開二者的關系研究。最后,正如馬歇爾自己所言,他主要關注的是公民權對社會階級的影響,實質就是社會權對社會階級的影響,而在社會階級對社會權的作用上著墨不多。
馬歇爾之后,安德森以社會權為分析原點提出去商品化的概念,進而分析基于不同去商品化能力的三種福利國家與社會階層的關系。安德森是以去商品化能力為中介,來分析不同社會權對社會階層的不同影響。埃斯平-安德森認為不同福利國家的去商品化的社會權發展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輕易的找到蘊含在不同福利國家的不同分層體系。“福利國家不只是一個干預,也可能是修正不平等結構的機制;其本身即是一個分層體系”。[8]自由主義者崇尚自由和效率,認為普遍的社會權和國家干預會限制自由和效率。因此,自由主義的福利國家主要以社會救助為主導,有效的控制了社會權的范圍,市場得到了強化,通過懲罰與丑化接受救助者,促進了社會的二元分化,建立了一個分層的秩序。保守主義福利國家是一種階級政治形式。社會權的賦予并不是以公民權利或者公民身份為基礎,而是以既有的特殊社會身份地位為基礎,社會權是附屬于既存的階層和地位之上,以維護不同地位之間的差異。所以,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權并沒有如馬歇爾所論述的那樣,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權利基礎上,改變整個社會不平等模式,重塑整個社會結構的大廈;相反,作為特殊權利和特權的附屬品,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權固化了原有的階級階層結構。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認為市場提供基本的福利無法保證公民的社會權和社會公平,因此,應該由福利國家提供基本福利,而非市場。這樣的國家,由于社會權擴展到新中產階級,因此是高水平平等的福利國家。[9]由于社會權擴展到新中產階級,避免了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的二元分化,有利于兩個階級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在穩固中產階級地位的同時使工人階級更容易向上流動,從而擴大中產階級的隊伍,形成穩定的社會結構。
安德森的這種分析,一定程度上發展了馬歇爾的社會權理論,然而安德森給出三種參照模型,仍然是一種描述分析,是結合具體國家背景,做出一種經驗性歸類。所不同是后者考察的背景由馬歇爾的英國擴展到歐洲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由馬歇爾的一種權利狀況,變成三種權利參照。只要安德森沒有在經驗分析的基礎上抽象出所有可能類型,他的理論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釋福利資本主義國家之外的社會權對社會階層結構的影響。此外,安德森也如馬歇爾一樣,主要分析公民權對社會階層的客觀結構的影響,沒有進一步分析公民權對階層團結、階層心理的影響,亦沒有進一步分析社會階層對社會權的影響。
一個社會就是在公民資格體系所追求的平等,與市場經濟體系和社會階級體系所形成的不平等這種結構性沖突中不斷走向進步。[10]那么,社會權與社會階層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社會權如何在自我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與社會階層的良性互動?回答此類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究二者間具體影響機制。
三、社會權與社會階層作用機制分析
社會權與社會階層的關系并非簡單的單向、線性作用關系,而是通過復雜的交互作用機制實現雙向互動。為了能更深入的分析二者這種交互作用,采取的策略是先拆解,再還原。即將復雜的雙向作用機制先拆解為單向作用機制,分別分析社會權對社會階層的作用機制、社會階層對社會權的作用機制。在此基礎上,通過我國的社會權與階層關系的分析,還原二者雙向互動的關系。
(一)社會權對社會階層的作用機制
社會權對社會分層的作用性質和作用力度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社會權充分度和社會權均等化程度。社會權充分度:筆者用總體社會權的去商品化程度或能力來表征社會權的充分度。社會權的充分度與社會權的依賴模式即主要依賴于市場還是非市場力量密切相關。社會權獲得主要依賴于市場,社會權在這樣的國家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抑制,社會權充分度低;若社會權的提供由非市場力量主導,社會權充分度高。社會權均等化程度:指社會權在社會共同體內所有成員之間分配的均等化程度。社會權均等化程度取決于賦予社會權的依據或標準是什么。若社會權的獲得主要依據既有的特殊社會身份地位,則社會權均等化程度低;若社會權的獲得依據是平等公民權(公民身份或公民資格),社會權的均等化程度就高。根據充分度和均等化程度,可將社會權分為四種類型:充分度低,均等化程度低型;充分度低,均等化程度高型;充分度高,均等化程度低型;充分度高,均等化程度高型。四種類型的社會權因為對階層產生不同作用而形成不同作用機制。
1.階層分化與整合的動力機制。此種機制在階層結構沒有定型、正在變動時發生作用。當社會權均等化程度較低時,即社會權的分配以差別身份為依據,社會權與市場同向作用,成為階層分化的動力機制;當社會權均等化程度較高時,即社會權的分配以平等公民身份為依據,社會權與市場逆向作用,成為階層整合的動力機制。
2.階層結構形塑機制。此種機制發生在階層結構相對穩定定型時,且只有當社會權充分度較高時,才能起到有力的形塑作用。當社會權充分度高,均等化程度低時,社會權固化現有階層結構或進一步擴大階層差距;當社會權充分度高,均等化程度高時,社會權會縮小階層差距。
3.階層心理認同機制。社會權對階層的這種機制能否發揮積極功能,主要取決于能否公平分配社會權,即社會權均等化程度如何。當社會權均等化程度較高時,即使充分度不高,社會權也可發揮正功能,提高人們的階層心理認同感;相反,如果均等化程度較低,則會降低人們的階層心理認同。通過社會權在階層之間的均衡分配,可以改變人們尤其是下層群體對社會不平等和階層不平等的感覺,減小階層怨憤感。由于平等社會權意味著平等的權利主體地位,這會降低人們的“相對剝奪”感,進而提高其階層心理認同。
(二)社會階層對社會權的影響
1.分層的階層結構決定了差序的社會權。①本研究的差序社會權借鑒了郝鐵川的權利實現的差序格局,其權利實現的差序格局包含兩層意思:第一,現實中的權利主體是逐步擴大的,即一部分人先享有法定權利,然后推而廣之及于其他人;第二,現實中不同種類權利,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權利等的法律化及其實現是循序漸進而非一蹴而就的。本研究社會權的差序在第一層意思上與郝鐵川的權利差序是一致的,即主體逐步擴展;但第二層意思上則完全不同,是指社會權的充分度自社會階層的上層往下逐漸降低。差序社會權有兩層意思:第一,指社會權的實現順序,是由階層結構的上層向下層逐漸實現;第二,社會權充分度自社會階層的上層向下降低。由于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差異,使得社會權首先存在于社會的上層,而后隨著社會權的發展而不同程度的向下層擴展。
2.下層(權利受損或無權階層)索權。下層索權有利于社會權的擴展。底層政治、意識形態、底層主體性、底層的公共性等要素有利于弱勢群體形成一個階層,使底層成為自為的階層,通過底層積極抗爭、索權,使其自身進一步去商品化,促進社會權的發展。
3.上層(權利既得階層)護權。上層護權有可能促使社會權內卷化。社會權逐漸在上層內部聚集很少甚至不再向其他階層擴展,最終導致社會權內卷化,內卷化的社會權進一步固化階層結構。②我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中間階層力量還十分弱小,更主要的是通過依附于上層或下層而發揮作用。中間階層有可能與下層聯合從而一起構成下層力量索權,也有可能與上層聯合共同構成上層力量維護權利,當然,不排除將來中間階層作為獨立階層維護自身權利,但這不是本研究目前的重點。因此,本研究主要依據權利的狀況進行二分,從而將階層劃分為無權或者權利受損的下層以及權利既得者的上層。
不同階層之間較量可能導致以下幾種結果:第一種結果也是比較理想的一種結果,即上層維護既得權利同時,社會權不斷向下層擴展,最終實現不同階層間的社會權均衡;第二種結果是社會權更主要的在上層積聚,很少向下層擴展,導致社會權在權利既得者的上層內卷化;最后一種結果也是當代社會最不可能出現的一種結果,即社會權的顛覆,社會權由上層向下大量轉移,最終形成新的權利失衡。
上述兩種作用機制,在我國的社會權與階層關系的分析中可以還原為雙向互動的關系。我國分層的階層結構決定了差序的社會權。由于資源稀缺性,社會權的實現可以是逐步漸進的,這是現實的選擇,但公民資格的公平性又決定了社會權最終應實現均衡化分配與發展。我國社會權發展過程中,社會權的分配沒有逐步向均衡化方向發展,而是仍然按照差別化的身份為依據,致使社會權沒能實現向下層擴展,而是在上層內部不斷積聚,內卷化。不同階層群體的社會權差距越來越大,形成社會權層級結構,最終導致下層權益被嚴重剝奪繼而造成權利失衡。失衡的社會權更主要的成為市場的同向力量而作用于社會階層,固化市場主導的社會階層結構。
我國在市場化機制逐漸成為社會分層主要機制的同時,出現了貧富分化嚴重、社會階層差距不斷拉大甚至階層斷裂等問題,但問題不能完全歸咎于市場機制本身。在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市場經濟體制成為配置社會資源基本手段的一種經濟體制不可改變,市場機制也必然會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機制。市場帶來的不平等、貧富差距擴大的后果只能由市場以外的再分配等機制化解。而問題就在于,我國的再分配機制沒能很好的解決市場帶來的后果。社會權作為再分配機制,其功能并非固化甚至擴大階層差距,而應該是縮小階層差距,應該在自我可持續發展中實現與社會階層的良性互動。要想實現社會權與社會階層的良性互動,需要徹底改變社會權的以差異身份為依據的獲得機制,真正做到以平等的公民身份為權利獲得依據。要想實現這種權利公正,需各個主體充分發揮各自能動性:既需要國家積極承擔責任,自上而下建構平等社會權;也需要社會階層群體發揮自身主體性,增進階層間的社會合作,實現權利自下而上的自我調配、自主生長;而公民個人獲得社會權的同時必須履行相應的責任,實現權責對等。
[1][6]T·H·馬歇爾.公民權與社會階級[M].劉繼同譯.北京:國外社會學雜志社,2003.
[2]戰建華.福利國家改革與公民社會權利重構[J].湖北社會科學,2010,(6).
[3]李艷艷.固化與形塑——我國社會福利制度與社會分層的關系研究[D].吉林:吉林大學,2010.
[4]郁建興,樓蘇萍.公民社會權利在中國:回顧、現狀與政策建議[J].教學與研究,2008,(12).
[5]孫立平.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7]陳鵬.公民權社會學的先聲—讀T·H·馬歇爾《公民權與社會階級》[J].社會學研究,2008,(4).
[8][9]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M].苗正民,滕玉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0]王元華.社會公民資格權利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