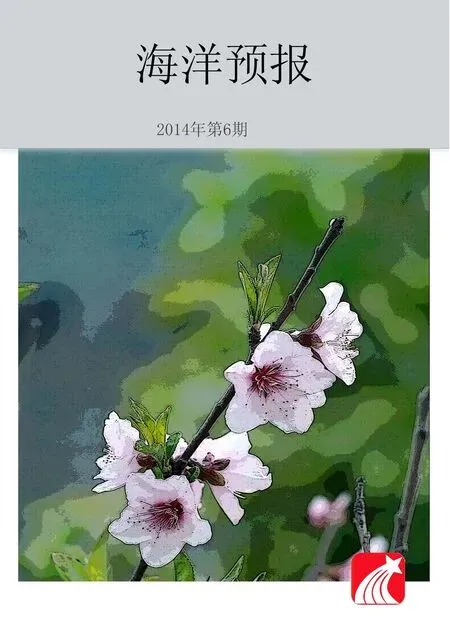基于高低潮的風暴增水人工神經網絡預報模型
王如云,雷磊,占飛,周鈞
(1.河海大學港口海岸與近海工程學院,江蘇南京210098;2.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學院,江蘇南京210098)
1 引言
風暴潮是由強風或氣壓引起的海面水位異常波動的現象,如果遭遇天文高潮,往往使海域水位暴漲,甚至造成防波堤毀壞,引起海水淹沒等破壞作用。因此對風暴潮增水進行準確預報,對沿海防災減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風暴增水的預報,除了基于動力學的可進行大范圍的數值預報模型外,國內外還開展了基于統計學和人工神經網絡的針對有海洋觀測站的局部海域的單站點[1-7]、多站點聯合[8-9]風暴潮預報模型的研究。
BP 人工神經網絡是種基于誤差反向傳播算法的多層前向神經網絡,是對人腦的一種簡單的抽象和模仿,具有非常強的非線性表達能力,比較適合多因子、多目標的擬合問題研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有人把人工神經網絡方法應用到風暴潮的研究當中。1994年蔡煜東[1]以廣東海門測站為例,考慮了測站的最大增水過程,用BP 人工神經網絡探索了臺風暴潮極值的方法;2003年陳希等[2]探討了BP 人工神經網絡在臺風浪預報中的應用,并對模型輸入因子的重要性進行了檢驗;2005年薛彥廣等[3]以湛江站為例,建立了預報風暴增水的BP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并用貝葉斯算法提高了模型的預報能力;Tsung-lin lee[4-5]分別于2006年、2008年建立了臺灣將軍站灣和蘇澳灣的風暴潮BP人工神經網絡預報模型,在將軍站建立的模型得到了比較精確的預報結果,在蘇澳灣利用人工神經網絡和潮汐調和分析并用的方法,預報誤差得到比較大的改進,并對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和其他模型進行了對比;2003年波蘭Marzenna Sztobryn[6]用人工神經網絡模型模擬了波蘭西部海岸一段時間內的水位變化和臺風期間的純風暴增水;日本的Sanin 海岸人工神經網絡模型也有應用,并討論了各個輸入因子對模型的靈敏度的影響[7];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Wenrui Huang 等利用Naples 站(1965年建)的水位數據和Cedar Key(1914年建,NOVV 水位站)站的水位數據建立了BP 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用這兩個站1999年的水位資料進行訓練,2002年水位資料進行模型驗證,為Naples 站補充了1914—1965年的水位資料,得到了利用ANN模型和NOVV水位站資料求得南佛羅里達海岸各個測站水位資料的一種方法[8];2006年李未等[9]利用BP人工神經網絡建立了燈籠山和黃埔兩測站臺風暴潮和天文潮的綜合增水效應預報模型,利用臺風期間燈籠山的實測水位對黃埔站的綜合增水進行了預報,并針對不同預報時段對計算結果和潮位極值的準確程度進行了相應的討論。我們發現上述工作都是基于潮位站具有較長歷史整點潮位資料展開的,這對于某些只有高低潮的潮時和潮位資料的潮位站就無法進行風暴增水的預報了。針對只有高低潮的潮時和潮位數據這種情況,本文借助BP人工神經網絡,給出了一種建立預報當前(或預報)臺風時刻后的第一個高潮時的風暴增水模型的方法。
2 BP人工神經網絡簡介
一般的BP 人工神經網絡包括輸入層、中間層和輸出層,三層之間進行全連接(見圖1)。模型的輸入向量為:


實際輸出向量為:

希望輸出向量為:
一組輸入向量和對應的希望輸出向量構成模型的一個訓練模式對。
輸入層和中間層的連接權為:

中間層和輸出層的連接權為:

人工神經網絡的目標函數為:

式中,n 為輸入層單元數,p 中間層單元數,q輸出層單元數,m 為訓練模式對總數,θj,γt為中間層和輸出層各單元的閾值,f 為激活函數。
3 風暴增水預報模型的建立
3.1 輸入輸出因子和網絡結構的確定
對于某一站點而言,在影響其的一定范圍內的臺風的強度和臺風位置對于預報該站點的風暴增水非常重要,這里把臺風在某一時刻、某一地點時的特征量叫做臺風因子,比較重要的特征量有臺風中心的經度、緯度,最大風速和中心氣壓等等。
通常情況下未來某時刻的風暴增水與當前時刻的風暴增水,以及未來臺風因子之間存在著重要的非線性關系,這里嘗試用人工神經網絡來建立它們之間的對應關系模型。
選取臺風在當前時刻、前6 h、前12 h、前18 h的中心經度、緯度、最大風速和中心氣壓作為輸入因子,希望通過人工神經網絡的信息特征提取能力,提取出臺風因子隨時間變化的特征,隱含給出未來時刻的臺風因子的作用,這樣人工神經網絡就有了16個輸入因子。另外,針對只有高低潮的潮時和潮位數據這種情況,我們取當前時刻前(后)第一個高潮時刻的風暴增水值(此數據由高低潮潮位觀測值減去利用王如云[10]等人建立的高低潮的優化保形調和分析模型(OCTHM)方法計算得到的潮位給出),作為人工神經網絡一個重要的輸入(輸出)因子。至此,人工神經網絡共選取了17 個輸入因子,也即輸入單元個數為17 個。1 個輸出因子,即輸出單元個數為1。
因目前尚無成熟的關于中間層個數選取理論[11],一般依靠經驗而定,這里準備用模型后報結果來確定中間層個數。
3.2 模式對的規范化
這里取人工神經網絡的激活函數為:

式中,當 ||x 較大時,f(x)非常接近0 和1,從而引起f′(x)=f(x)(1-f(x))值非常接近0,導致人工神經網絡訓練時收斂過慢,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這里把輸入單元的數據規范在0.01至0.99之間,并要求模型連接權的初始值在(-1,1)之間隨機產生;因為激活函數f(x)∈(0,1),所以輸出單元的數據要規范化到(0,1)之間,考慮到輸出層規范化是在已有的數據基礎上進行的,為了顧及模型檢驗和用于未來預報時出現比訓練時更大的輸出數據,這里把輸出單元的數據規范在0.01至0.99之間,具體做法如下:


3.3 人工神經網絡臺風因子預報模型
選取臺風在當前時刻、前6 h、前12 h、前18 h的中心經度、緯度、最大風速和中心氣壓作為輸入因子,分別取未來6 h、12 h 等的中心經度、緯度、最大風速和中心氣壓作為輸出因子,可分別建立未來6 h、12 h 等的人工神經網絡臺風因子預報模型,根據此思想我們已對東中國海建立了臺風因子預報模型[12](另文發表)。利用此模型對本文檢驗所用到的臺風因子進行了預報,并和實測值進行了比較,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6 h臺風因子預報結果
對臺風(“Sinlaku”森拉克,2008年9月8 號至9月21號)的臺風因子預報結果如表2所示。
3.4 風暴增水預報模型
首先根據歷史臺風因子、高低潮以及由高低潮分離出來的風暴增水資料,形成若干模式對進行人工神經網絡的訓練。

表2 森拉克的6 h臺風因子預報結果
在人工神經網絡訓練成功后,就得到了風暴增水預報模型。可利用臺風在當前時刻、前6 h、前12 h、前18 h 的中心經度、緯度、最大風速、中心氣壓、當前時刻前第一個高潮時刻的風暴增水值作為輸入因子,可對當前時刻后第一個高潮時刻的風暴增水值進行預報。
在此基礎上,把當前時刻、前6 h、前12 h,看成前6 h、前12 h 和前18 h,把6 h 后作為當前時刻,利用過去時刻相應的臺風因子和利用6 h臺風因子預報模型給出當前時刻的臺風因子,并把前面剛預報的風暴增水值作為當前時刻前第一個高潮時刻的風暴增水,這樣就可由風暴增水預報模型預報未來6 h后的第一個高潮時刻的風暴增水值。如此遞進,可對未來12 h、18 h 等時刻后的第一個高潮時的增水值進行預報。
4 模式檢驗
根據我們已有的1965年、1967年、1971年、1972年、1973年、1975年、1976年、1977年、1979年、1981年、1983年、1985年、1987年、2006年、2008年的高橋站的高低潮潮位和相應年份臺風數據資料,選取臺風路徑經過以高橋站(31.33°N,121.56°E)為中心的方圓300 km 范圍內的有關數據進行分析計算。
符合上述有關條件的臺風共有13 場,共建立了96 個模式對,將其分為模型訓練和模型檢驗兩部分,其中選取70 組為訓練模式對,26 組為檢驗模型的模式對。模型的學習率降低到小于10-6時退出訓練,用所求得的模型連接權、閾值進行預報。
對于不同的中間層個數,模型的后報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3 不同的中間層個數對應的模型檢驗結果
在選定中間層單元數為9時,模型檢驗的所有結果誤差情況見表4。
對于不同的中間層個數,森拉克的模型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表4 中間層單元數為9時模型檢驗結果誤差

表5 森拉克的模型檢驗結果
5 結果與討論
由1965年高橋站的高低潮數據,利用王如云[10]等人給出的建立高低潮的優化保形調和分析模型(OCTHM)方法,首先建立高橋站的天文潮預報模型。把所有各年份的高低潮數據減去天文潮預報模型的預報值得到的余潮位記為{ΔHi},其均方差記作Δη1。選取臺風當前時刻前第一個高潮期間的余潮位作為形成訓練模式對因子的高潮時刻的增水記為(余潮位{ΔHi}的子集),其均方差記作Δη2。在人工神經網絡訓練結束后,利用此網絡后報訓練模式對中的高潮時刻增水值記為{ΔHi*(1)},計算再計算的均方值,從而得到人工神經網絡后報后的結果的均方差(記為Δη3)。選取臺風期間的余潮位作為形成后報檢驗模式對因子的高潮時刻的增水記為(余潮位{ΔHi}的子集),其均方差記作Δη4。在人工神經網絡訓練結束后,利用此網絡后報檢驗模式對中的高潮時刻增水值記為計算再計算的均方值,從而得到人工神經網絡后報后的結果的均方差(記為Δη5)。有關計算結果見表3。

表6 均方差的比較(單位:cm)
有關結果分析討論如下:
(1)Δη1是所有高低潮處的余潮位的均方值,它反映了潮位在去除了主要天文周期潮后的變化總體情況,其中含有臺風、徑流等非周期因素的影響。Δη2、Δη4是臺風期間高低潮處的余潮位的均方值,主要含有臺風的影響。因此表3 中的Δη1<Δη2、Δη4是正確的;
(2)Δη2是所選取的訓練模式對的余潮位均方值,Δη3是在人工神經網絡模型提取了訓練模式對中余潮位所含風暴潮影響后的均方差,所以表3 中Δη3<Δη2是正確的,說明神經網絡模型確實提取出了臺風對潮位的影響效應;
(3)Δη4是檢驗模式對的余潮位均方值,Δη5是在人工神經網絡模型提取了檢驗模式對中余潮位所含風暴潮影響后的均方差,所以表3 中Δη5<Δη4是正確的,說明神經網絡模型確實具有預報臺風對潮位的影響效應的能力,且具有比較好的預報精度。
[1]蔡煜東,姚林聲.預報臺風風暴潮極值的人工神經網絡方法[J].海洋預報,1994,11(1):77-81.
[2]陳希,李妍,沙文鈺,等.人工神經網絡技術在臺風浪預報中的應用[J].海洋科學,2003,27(2):63-67.
[3]薛彥廣,沙文鈺,徐海斌,等.人工神經網絡在風暴潮增水預報中的應用[J].海洋預報,2005,22(2):33-37.
[4]Lee T L. Neural network prediction of a storm surge[J]. Ocean Engineering,2006,33(3-4):483-494.
[5]Lee T L. Prediction of Storm Surge and Surge Deviation Using a Neural Network[J].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2008,24(4A):76-82.
[6]Sztobryn M. Forecast of storm surge by means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J].Journal of Sea Research,2003,49(4):317-322.
[7]Kim S Y,Shiozaki S,Matsumi Y,et al.A study of a real-time storm surge forecast system using a neural network at the Sanin Coast,Japan[C]//Oceans.Hampton Road,VA:IEEE,2012:1-7.
[8]Xu S D, Huang W R.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odel Application on Long Term Water Level Predictions of South Florida Coastal Waters[C]//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Wuhan:IEEE,2010:1-4.
[9]李未,王如云,盧長娜,等.神經網絡在珠江口風暴潮預報中的應用[J].熱帶海洋學報,2006,25(3):10-13.
[10]王如云,占飛,周鈞,等.基于高低潮的優化保形調和分析模型(OCTHM)及算法[J].水運工程,2014,(8):15-19.
[11]高建華,何琴.人工神經網絡方法在苯類衍生物常壓沸點預測中的應用[J].鄭州大學學報,2005,37(1):61-63.
[12]張鑫.臺風參數預報模型及風暴潮增水預報檢驗[D].南京:河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