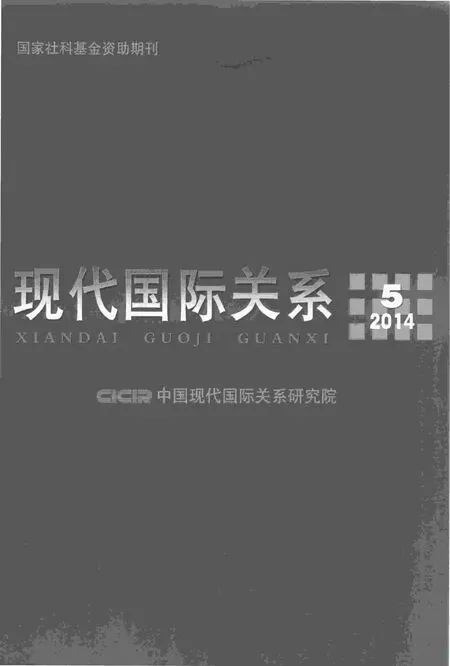奧巴馬政府網絡空間戰略面臨的挑戰及其調整
魯傳穎
2014年3月14日,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宣布將放棄對“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的控制權,并在移交聲明中指出,將由ICANN管理層組織全球“多利益攸關方”(Multi-stakeholder)討論接收問題,但明確拒絕由聯合國或其他政府間組織接管。①The NTIA,“NTIA Announces Intent to Transition Key Internet Domain Name Functions”,http://www.ntia.doc.gov/press-release/2014/ntia-announces-intent-transition-key-internet-domainname-functions.(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鑒于ICANN在國際互聯網管理中的戰略地位及其特殊的移交方案設計,美國此舉的深層含義表明,奧巴馬政府正著手對網絡空間戰略進行重新調整布局。本文首先對奧巴馬政府的網絡空間戰略進行梳理,對“棱鏡事件”后其面臨的挑戰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討美國網絡空間戰略的調整及其對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影響。
一、奧巴馬政府的網絡空間戰略
美國政府歷來重視網絡空間戰略。早在克林頓時期,美就通過實施《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行動計劃》(NII)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發展網絡經濟戰略。“9·11”后,小布什政府將網絡戰略重點轉向網絡安全,并先后于2003年和2008年出臺了《確保網絡空間安全國家戰略》和《綜合國家網絡安全倡議》(CNCI)兩份重要文件,強調發展保衛國家網絡安全的能力。②沈逸:《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時事出版社,2013年,第153-163頁。奧巴馬政府則將網絡空間戰略列為重中之重,試圖構建一個包含網絡安全、網絡經濟、網絡監控、網絡自由等在內的全方位戰略,主導國際網絡空間的權力、資源和財富分配。在美國國務院、國防部、情報部門、國土安全部等各部門的積極配合下,奧巴馬政府集戰略思想、政策舉措和行動策略三位一體的網絡空間戰略逐漸浮出水面。
奧巴馬政府分別于2009年和2011年發布《網絡空間政策評估》和《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兩份政策報告,對外公布美國在網絡空間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目標。③劉興華:“奧巴馬政府對外網絡干涉政策評析”,《現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12期,第53-55頁。2012年12月,奧巴馬總統簽署絕密的《第20號總統政策指令:美國網絡行動政策》,詳細規定了美國在網絡空間采取進攻性和防御性政策的原則、目標和方案;明確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利益包括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國家經濟安全、“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可靠運行、“關鍵資源”的控制權等;詳細制定了“進攻性網絡效應行動”(OCEO)和“防御性網絡效應行動”(DCEO)兩個行動方案,規定在必要時可以對他國網絡空間的數據、信息以及關鍵基礎設施采取控制、運行中斷、拒絕執行指令、性能降級、甚至完全破壞。①The White House,“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 20”,http://www.fas.org/irp/offdocs/ppd/ppd-20.pdf.(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第20號總統政策指令》暴露了美國在網絡空間建立霸權的實質,并對美國整個網絡政策體系導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白宮戰略思想的指引下,美國國務院、國防部、情報部門、國土安全部等各部門紛紛提出各自的網絡空間政策規劃。美國國務院作為《網絡空間國際戰略》主要執行部門,積極推動在網絡空間的價值觀外交,強化盟友之間的價值觀同盟,并通過在網絡空間“建章立制”,試圖建立起一套符合美國利益的網絡空間規則;②Margaret P.Karns& Karen A.Mings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Politics and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0,pp.258-262.國防部發布了《網絡空間行動戰略》,宣布成立網絡司令部,加速發展網絡部隊,③US Department of Defense,“DOD Strategy for Operating in Cyberspace”,http://www.defense.gov/news/d20110714cyber.pdf.(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并通過網絡軍演、軍事交流等方式加強盟友之間在網絡戰領域的合作;國家安全局(NSA)、中央情報局(CIA)等情報部門加大了網絡情報搜集力度和廣度,并且將大數據技術引入網絡情報分析,為美國政府提供大量有價值的情報,一舉成為美國網絡空間戰略的核心部門。除此之外,各部門之間還開展了一系列協調與合作,如國防部與國土安全部簽訂“2010協議備忘錄”,增加在政策法規、任務成效和預算等三方面的合作;國土安全部、司法部、國家安全局等部門通過加強協作,制定網絡安全框架、指南和程序維護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④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Improv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ybersecurity”,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2/12/executive-order-improving-critical-infrastructure-cybersecurity.(上網時間:2014年4月8日)
美國政府網絡空間政策主要通過國際和國內兩個行動策略來實施。在國際層面,美國主要是推行一種“去政府化”的網絡空間治理模式,一方面從理論上把網絡空間描述為“全球公域”,否認網絡主權;另一方面推行“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以企業、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為網絡空間治理主體,限制國家及政府間組織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發揮作用。美國之所以采取如此策略,是因為其壟斷負責互聯網運營的國際機構和企業,⑤NazliChoucri,Cyber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IT Press,2012,pp.208-216.如負責互聯網IP地址分配、域名注冊和域名解析服務的ICANN和負責網絡協議和標準制定的IETF等都位于美國,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12-2013)》,時事出版社,2013 年,第120 頁。美國IT企業則基本上壟斷了全球市場的網絡設備、操作系統、數據庫、搜索引擎、社交網絡、云計算等領域。因此,無論是強調網絡空間的“全球公域”屬性還是“多利益攸關方”治理模式,無非都是借此抹殺他國網絡主權,給美國創造在網絡空間“全球介入”(Global Access)的能力。此外,為進一步搶占網絡空間治理領域的話語權,美國務院牽頭搭建名為“倫敦進程”(London Agenda)的網絡空間治理平臺,向其他國家兜售美國的思想和價值觀;國防部也通過開展網絡軍演,打造網絡軍事盟友體系;情報部門則通過“五只眼”國際情報聯盟、北約情報共享機制、盟友間情報共享機制等各個層級的網絡情報分享行動,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情報體系。
在國內層面,奧巴馬政府積極推動公-私(Public-Private)合作。美國的網絡資源大多分布在政府之外的企業、非政府組織和社會當中,推動公-私合作是為了整合這些資源并將其轉化為美國的網絡權力。2013年2月奧巴馬總統簽署《關于提高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的行政命令》,授權相關政府部門制定安全標準和實施指南,通過監督、協商、合作等手段加強對關鍵基礎設施所有者和運營商的安全檢查,讓其參與政府制定和執行標準的決策,促使其主動與政府分享機密信息。⑦Larry Clinton,“A Relationship on the Rocks:Industry-Government Partnership for Cyber Defense”,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Issue 2,2011,pp.104-106.奧巴馬政府還積極推動對于美國具有戰略意義的網絡技術發展,如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大數據通過對海量數據的挖掘和整合,可以掌握原先只有政府才能掌握的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敏感信息。掌握了先進的大數據技術,即意味著可以輕易突破其他國家的數據主權。對此,奧巴馬政府特別責成白宮科技政策委員會成立大數據高層指導小組,要求聯邦政府各個部門積極支持“大數據研發計劃”。①The White House,“Big Data Initiative”,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big_data_press_release_final_2.pdf.(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美國政府不僅在每年龐大的IT采購預算中優先采購云計算服務,還建立聯邦云計算示范工程,并通過一攬子計劃鼓勵亞馬遜、谷歌、微軟、IBM等企業在全球獲得領先地位,②The White House,“Federal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assets/egov_docs/vivek-kundra-federal-cloud-computing-strategy-02142011.pdf.(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把美國打造成全球數據的存儲、交換中心。這樣一來,美國政府無需進入他國即可獲得網絡數據的“全球介入”能力。
綜而言之,奧巴馬政府的網絡空間戰略具有三大特點。一是全局性和戰略性。奧巴馬政府將網絡空間視為權力、財富、資源不斷聚集的,與陸、海、空、天同等重要的第五戰略空間,并將網絡空間“建章立制”視為與二戰后建立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同等重要。二是繼承性和延續性。在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國已經開始探索在網絡空間建立霸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奧林匹克計劃”和“棱鏡計劃”正是這一時期開始執行,奧巴馬上臺后延續了上述項目并加大投入。此外,小布什政府在任期結束之前,曾委托分別來自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兩位眾議員引領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制訂《致第44屆總統網絡安全報告》。該報告建議在小布什時期網絡安全戰略基礎之上建立一個包括外交、情報、軍事、經濟的綜合性網絡安全戰略。③James A.Lewis,Securing Cyberspace for the 44thPresidency,December 2008,p.1,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81208_securingcyberspace_44.pdf.(上網時間:2014年3月20日)奧巴馬對此照單全收,其后來發布的多項網絡空間戰略都源自該報告的思想。三是控制性和進攻性。因受“9·11”影響,小布什時期的網絡空間戰略主要強調發展保衛網絡安全能力,特別是防范網絡恐怖分子對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奧巴馬時期的網絡空間戰略則更強調控制性和進攻性,無論是積極發展網絡軍事力量,開展網絡監控,還是推動網絡空間的“建章立制”,都是采取進攻性手段實行對網絡空間權力、資源、財富的控制。
二、奧巴馬政府網絡空間戰略面臨的挑戰
奧巴馬政府的網絡空間戰略是一個復雜而矛盾的體系,體現在:戰略思想存在內在矛盾,既要維護網絡空間開放、透明、可操作性,又要建立美國的網絡霸權;協調機制不暢,導致國務院、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及情報部門的政策相互抵觸;國際和國內層面的行動策略彼此沖突。“棱鏡門”事件更加速了矛盾的爆發,暴露出奧巴馬政府過度推進進攻性網絡政策、開展網絡監控、干涉他國主權和壟斷互聯網管理權,把網絡空間推向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和軍事化的困境。
由于各種因素影響,美國的網絡空間戰略面臨國際和國內多重挑戰。首先,在國際上陷入信任危機。美國一直把建立國際網絡空間的“行為規范”標榜為其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的主要目標之一。“規范”(Norms)一詞在《韋氏新國際英語詞典》中的多項解釋暗含著“正確的”、“正面的”、“廣為認可”等褒義。言下之意,美國要樹立網絡空間行為準則的典范,并對其他國家不符合規范的行為進行約束和懲罰。自2013年6月起,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持續不斷向媒體披露“棱鏡計劃”的具體細節,揭露美國政府竊取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文件、對巴西總統羅塞夫的私人手機、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辦公室,甚至到訪的中國前國家領導人的通訊進行監聽。④“Prism”,The Guardian,June 11,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prism.(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雖然奧巴馬辯稱,情報收集是每個國家的正常工作,“棱鏡計劃”主要針對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等特定對象,但正如《紐約時報》所指出的,提前竊取潘基文與奧巴馬會晤中的談話要點,監聽默克爾的私人通話等既與防止網絡犯罪無關,也與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無關。⑤“Obama Weighing Security and Privacy in Deciding on Spy Program Limits”,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0,2013.美國在網絡空間的行為與自己所標榜的“行為規范”相去甚遠,在國際上廣受指責;盟友之間在網絡政策上的協調被中斷,默克爾總理不僅要求徹底審查美國在歐洲的監控行動,甚至提議建立歐洲自己的互聯網。①“Angela Merkel Rebukes US and Britain over NSA Surveillance”,Telegraph,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germany/10604664/Angela-Merkel-rebukes-US-and-Britain-over-NSA-surveillance.html.(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在羅塞夫總統的提議下,2014年4月在巴西召開全球互聯網峰會,打算討論美國“棱鏡計劃”對網絡空間秩序的負面影響。雖然在美國政府的強烈要求下最終取消了相關議題,但在會場上下依舊有很多參會者就“棱鏡計劃”對美國政府提出了強烈批評。②Veridiana Alimont,i“Privacy and Surveillance”,http://content.netmundial.br/contribution/privacy-and-surveillance/273.(上網時間:2014年5月7日)
其次,國內基礎分化。美國政府一直采取諸多策略尋求國內對于網絡空間戰略的支持,如在網絡空間推廣美式價值觀以迎合國會和民眾;在網絡安全問題上高調批評中國,以外部威脅為由迫使企業和民眾支持政府的網絡戰略;在網絡安全防范等領域推動公-私合作,將非政府組織、企業、社會納入政府的網絡政策框架內等。“棱鏡門”事件消解了美國政府在推動國會、非政府組織、企業、公民社會在網絡戰略上形成共識的努力,斯諾登揭露了一個包括“棱鏡”、“X關鍵分”(X-Keyscore)、“美景”(Fairview)、“核心”(Main core)等近10個監控項目在內的監控體系。③“List of Government Mass Surveillance Projects”,April 1,2014,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List_of_government_mass_surveillance_projects&oldid=602236932.(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該監控體系由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等多個情報機構參與,幾乎覆蓋了網絡空間的社交網絡、郵件、即時通訊、網頁、影片、照片等所有信息。美國政府不僅要求微軟、谷歌、臉譜等9家主要全球互聯網企業向監控項目開放數據庫,甚至在所有經過美國境內的洲際光纖上攔截數據。“棱鏡計劃”破壞了法律對民眾隱私的保護,激起了國會、企業和全社會對美國政府的聲討。在參議員艾爾·弗蘭肯的提議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向國會提交了《監聽透明法2013》(Surveillance Transparency Act of 2013),要求對《愛國者法》第214、215條款進行修改,限制情報機構對互聯網和電話元數據的收集;對《外國情報收集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第702條款進行修改,重新審查“棱鏡”項目對互聯網信息的收集。④“Surveillance Transparency Act of 2013”,S.1452,113th Congress(2013).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范斯坦對中央情報局監控國會議員電腦大為光火,態度強硬地指責其涉嫌違反憲法、破壞三權分立原則。為了挽回“棱鏡門”給企業聲譽造成的負面影響,涉及監控項目的企業紛紛與政府劃清界限。蘋果、微軟、雅虎等8家全球著名的互聯網企業發表公開信,要求政府改革監控體系。⑤“Apple,Facebook,Google Call for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Reform”,Los Angeles Times,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technology/la-fi-tn-apple-facebook-google-call-for-governmentsurveillance-reform-20131209,0,1482369.story#ixzz2zLRIpKQV.(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微軟和谷歌甚至向法院訴訟聯邦政府。美國民眾對于政府打著反恐旗號開展無孔不入的監控表示不滿。據媒體報道,有85%的民眾反對政府監聽項目,并有超過一半的民眾視斯諾登為英雄。美國公民社會聯盟在網上發起“停止監視我們”(Stop Watch Us)行動,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得到數以萬計網民在網站上的簽名、留言,以及數百個公民團體的響應,他們通過組織游行示威、向國會請愿、發起網絡倡議等方式配合該行動。⑥“Stop Watching Us”,https://optin.stopwatching.us/.(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
第三,網絡空間分裂風險加大。美國強行推廣“互聯網自由”戰略,把廣大發展中國家推向對立面,使當前網絡空間面臨著巨大的分裂風險。美國務院是推進美國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的主要部門,在希拉里國務卿主政時期,曾多次就“互聯網自由”發表演講。美國政府將“互聯網自由”定義為“包括網絡空間保護個人自由表達其觀點的權利、向領導人請愿的權利、基于信仰進行禮拜的權利”。圍繞“互聯網自由”這一新概念,美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一是在價值觀引導下,形成國際、國內網絡價值觀同盟,排斥他國的網絡價值觀。二是通過強調互聯網信息的自由流通,反對其他國家的互聯網公共政策,阻止他國在網絡空間行使主權,進而把美國的權力和利益拓展到他國網絡空間。在伊朗、突尼斯、埃及、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的政治動蕩中,美國的推特、臉譜、優兔等社交網絡媒體發揮了重要作用,是當地反政府勢力號召、組織、宣傳推翻政府活動的主要平臺。美國政府借所謂“互聯網自由”,力挺西方通訊服務商拒絕所在國政府關閉網站的要求,還鼓動開放注冊波斯語、阿拉伯語賬號為反對派推波助瀾,樹立在社交網絡積極支持反對派的形象。三是以“互聯網自由”為借口,要求其他國家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把美國的互聯網企業推向全球。美國通過給對美國企業造成競爭壓力的他國企業貼上違反“互聯網自由”標簽,在道德上進行抹黑從而影響國際市場對其產品的采用。美國的“互聯網自由”政策引起越來越多國家的反對,在2012年迪拜國際電信聯盟大會上,共有89個信息發展中國家提出要將“成員國擁有接入國際電信業務的權力和國家對于信息內容的管理權”寫入《國際電信規則》,落實信息社會世界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突尼斯議程中提出的“互聯網政策是一國主權”的共識,并不顧美國的強烈抵制強制表決通過了決議。雖然因最終投票的國家沒有達到法定數量導致該條款無法生效,但發展中國家依舊借此向美國展示了強硬立場。此外,發展中國家為了抵制美國的“互聯網自由”戰略,必將出臺更多互聯網管理措施,以犧牲網絡空間的開放性、透明性來維護網絡主權,從而進一步加劇網絡空間分裂的風險。網絡空間的統一、開放、透明、可操作是美國網絡國際戰略的前提,也是網絡空間的價值所在,一個分裂的網絡空間顯然不利于奧巴馬政府推行其網絡空間戰略。
第四,網絡安全形勢惡化。奧巴馬政府大肆渲染美國面臨的網絡安全威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發展網絡軍事力量,把網絡空間推向了軍事化。①Adam Segal,“Chinese Computer Games:Keeping Safe in Cyberspac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2,pp.16-17.2009年6月,美國成立網絡司令部,并開始組建網絡作戰部隊。不僅如此,美國還將網絡戰運用到實踐中,通過震網病毒(Stuxnet)破壞伊朗的核設施;秘密開發火焰病毒(Flame),在全球感染難以計數的計算機,搜集他國的軍事情報。美國的進攻性網絡軍事政策打開了網絡戰的“潘多拉魔盒”。②Mark D.Young,“National Cyber Doctrine:The Missing Link in the Application of American Cyber Power”,Journal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 Policy,Vol.4:1732010,pp.173-176.表面上,美國希望通過威懾方式增加網絡安全,卻加劇了網絡空間的軍事化,反而惡化了美國的網絡安全形勢。一是在美國大力發展網絡軍事力量的刺激下,各國紛紛成立網絡部隊,加大了研發網絡武器的力度,以挑戰美國在網絡軍事方面的優勢,迫使奧巴馬政府不斷加大在網絡軍事領域的投資,從而陷入網絡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之中。二是在缺乏有效網絡軍控機制下,網絡武器開始泛濫并逐步向非國家行為體擴散。網絡武器只是一些復雜代碼所構成的病毒程序,可以輕易地通過便攜式存儲設備復制、轉移,恐怖分子獲得網絡武器的機會將由此大大上升,而美國是網絡恐怖主義主要攻擊目標之一。三是由于網絡空間的匿名性,在“歸因”(即科學地尋找發起攻擊的源頭)方面難以做到客觀、公正,各種誤判將會引起國家間的網絡軍事沖突,并將影響到整體網絡安全。網絡空間的互聯性使得美國的高網絡依存度成為其在安全領域的“阿喀琉斯之踵”。③Panayotis Yannakogeorgos& Adam Lowther,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Cyberspace,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3,pp.50-66.
三、奧巴馬政府對網絡空間戰略的調整
面對諸多挑戰,奧巴馬政府不僅重新審查了“棱鏡計劃”,更重要的是對整個網絡空間戰略的戰略思想、政策舉措和行動策略進行了調整,旨在構建一個更加均衡的網絡空間戰略,包括戰略目標上調整網絡空間治理觀念,解決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國際層面上在進攻性網絡政策與防御性網絡政策之間采取平衡,以避免網絡空間的“巴爾干化”;國內層面上對企業和民眾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在保障網絡安全和保護公眾隱私之間尋找平衡,避免網絡戰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支持。此外,還大力加強與網絡新興大國之間建立信任措施,為在網絡空間“建章立制”創造有利環境。
在具體貫徹過程中,奧巴馬政府采取了四大措施。第一,調整對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認知,正視網絡空間的主權屬性,緩和網絡空間治理困境。奧巴馬政府一直視網絡空間為“全球公域”,否定“網絡主權”,并將這種認知延伸到網絡空間全球治理進程當中。當前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有三大主要平臺,分別是聯合國下設的互聯網治理論壇(IGF)、國際電信聯盟(ITU)以及“倫敦進程”。①Margaret P.Karns& Karen A.Mings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Politics and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0,pp.540-541.奧巴馬政府認為,在互聯網治理論壇和國際電信聯盟這兩個平臺中發展中國家數量占優,它們更支持“網絡主權”,于是采取各種措施抵制其發揮作用,并于2011年創立“倫敦進程”,試圖以此主導國際網絡空間治理進程。網絡發達國家與網絡發展中國家在網絡主權問題上相互對立,加劇了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困境。2013年6月,由包括美國在內的15國代表組成的聯合國專家組發表了一份報告,首次明確“國家主權和源自主權的國際規范和原則適用于國家進行的通信技術活動,以及國家在其領土內對通信技術基礎設施的管轄權”。報告進一步認可“聯合國憲章在網絡空間的適用性”。②United Nations,General Assembly,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A/68/98,June 24,2013.與2010年版聯合國專家組報告相比,這是一個巨大進步,為尋找網絡空間治理共識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表明美國正在調整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觀念。
第二,調整在網絡空間全球治理上的策略,理順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矛盾,避免網絡空間分裂。一直以來,美國政府理論上支持“多利益攸關方”模式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并主張限制政府和政府間組織發揮作用。③Roger Hurwitz,“Depleted Trust in the Cyber Commons”,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Fall,2012,pp.21-23.但實際上,美國卻控制著ICANN這樣掌握互聯網戰略資源的國際機構不肯放手。ICANN壟斷了互聯網的IP地址分配、域名注冊和域名解析服務等關鍵性資源,美國通過控制ICANN掌握了互聯網的封疆權和路由權。④楊劍:《數字邊疆的權利與財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7-215頁。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美國就通過ICANN停止對伊、阿兩國的互聯網域名解析服務,切斷兩國與國際互聯網的聯系,給兩國造成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沖擊,為美國取得軍事勝利創造了條件。因此,奧巴馬政府一直視其為國家戰略資產,拒絕放權。2014年3月,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家通信管理局突然宣布將放棄ICANN的控制權,將其移交給全球“多利益攸關方”。此舉的深層原因在于,奧巴馬政府將網絡空間戰略的重心轉移到國際戰略中,旨在加快網絡空間的“建章立制”進程。在戰略目標上,向國際社會表明美國無意在網絡空間謀求霸權,以恢復美國在網絡空間“建章立制”上的道德形象和合法性,繼續主導網絡空間治理進程。在策略上,對內可以拉攏在網絡空間擁有強大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互聯網公司、學術界和輿論界,對外可以盡快修復網絡空間戰略的盟友體系。“棱鏡門”事件后,美國先是對憤怒的歐洲領導人進行安撫,隨后又積極支持歐洲制定的《布達佩斯網絡犯罪公約》成為國際標準。放棄ICANN的控制權是進一步向歐洲做出讓步的姿態。⑤“U.S.to Relinquish Remaining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5,2014.當然,奧巴馬政府不會放棄對ICANN的影響力。只要能保證ICANN在國際化進程中其功能、總部、人員構成、決策程序等不發生改變,美國政府依舊可以通過在ICANN董事會、支持組織和咨詢委員會中的絕對話語權,發揮重大影響力。此外,此次移交并不包括具有域名解析功能的13臺根服務器。為了控制整個移交過程和結果,美國政府還通過與國會之間“互動”,向國際社會施加壓力。如近期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持續審視域名公開事務法案2014”(Domain Openness Through Continued Oversight Matters Act of 2014),提出要對政府“移交ICANN”的行為進行研究和評估,并要求政府確保“多利益攸關方”不受其他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影響。⑥“Domain Openness through Continued Oversight Matters Act of 2014”,H.R.4342,113th Congress 2nd Session(2014).一旦該法案獲得通過,相關的審計和調研將至少需要1年時間,從而大大放緩移交進程。
第三,加強在網絡空間的行為規范建設,重塑道德形象。美國長期以來過度追求發展網絡空間的技術能力和行動能力,卻忽視了網絡空間的倫理道德,這是導致其網絡空間戰略受阻的主要原因。鑒此,奧巴馬政府一是加強了對相關政策的網絡倫理審查。“棱鏡門”之后,奧巴馬總統任命了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對政府的情報監控活動進行審查。2013年12月,該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名為《變動世界中的自由與安全》(Liberty an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的報告,認為“國家安全局存在一些嚴重和持續地違反隱私及相關規定的行為,引發了人們對國家安全局有效、合法管理自己職權能力的擔憂”。報告還指出,“監控計劃破壞了網絡空間的開放、統一,應當對國家安全局進行改革,建議下一任國安局局長由平民擔任,網絡司令部與國家安全局的長官不能由同一人擔任。”①The White House, “Liberty an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3-12-12_rg_final_report.pdf.(上網時間:2014年4月19日)奧巴馬政府進一步承諾,政府將與國會一道就《愛國者法案》旨在允許政府收集民眾電話元數據的第215條款進行修改。二是基于《外國情報監聽法》加強公眾監督,避免類似“棱鏡計劃”的監聽行動超出法律允許范圍。三是要求情報部門加強公開和透明,盡可能多地向公眾提供關于網絡監控的信息,并責成司法部出臺對《愛國者法案》第215條款的司法解釋。四是責成深處漩渦中心的國家安全局通過參加國會聽證、公開材料等形式回應民眾訴求。2013年8月,國家安全局公布了一份關于其任務、職責、合法性來源以及關于監控項目一些細節的報告,以增加民眾的知情權。但與此同時,審查報告中對國家安全局進行組織改革的提議并沒有得到落實。2013年4月,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思·亞歷山大宣布辭職,繼任的麥克·魯杰不僅是軍隊少將,而且身兼國家安全局與網絡司令部兩職。在美國軍費縮減的背景下,國家安全局的財政撥款依舊保持增長。事實表明,盡管美國政府加強了對網絡監控的監管,但網絡監控依舊是美國網絡空間戰略的核心支柱。
第四,加大建立信任措施(CBMs)力度,緩和網絡空間的政治化、軍事化趨勢。美國與新興大國在網絡空間“建章立制”上的立場差異以及溝通機制的缺乏,導致雙方互信缺失,加劇了網絡軍備競賽和網絡安全形勢惡化。因此,奧巴馬政府借鑒在核安全領域的合作模式,加大了與網絡新興大國在網絡空間建立信任措施的力度。②Meyer Paul,“Diplomatic Alternatives to Cyber-Warfare”,The RUSI Journal,Volume 157,Issue 1,2012,pp.14-19.2013年6月,美俄之間達成了一項在網絡空間建立信任措施的協議,內容包括:建立軍事熱線,雙方的網絡協調員可以就網絡安全危機直接對話;建立雙方計算機應急響應機構(CERT)之間的聯系,加強技術、數據等領域交換;成立網絡工作組,討論網絡空間威脅,尋找合作領域;加強雙方政策文件的交換,增加網絡軍事發展的透明度。③“U.S.and Russia Sign Pact to Create Communication Link on Cyber Security”,The Washington Post,June 17,2013.同年7月,在網絡安全領域一直相互指責的中美兩國也在網絡問題上取得共識。雙方在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之前的戰略與安全對話(SSD)框架下設立了中美網絡安全工作組,就網絡安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展開了討論。雙方提出要建立經常性交流機制,加大在維護網絡安全與打擊網絡犯罪領域的合作。此后,雙方停止了網絡安全領域的相互指責。工作組于2013年12月在北京又召開了一次會間會,雙方對于落實網絡工作組第一次會議達成的共識表示滿意,并將進一步加強各個領域的合作。2014年4月,曼迪昂特公司再次發布《中國網絡間諜的報告》,但與上一次相比,沒有了美國政府的造勢,因而報告并沒有掀起任何波瀾。
建立信任措施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國際網絡空間軍事化趨勢,但可以避免由誤判導致的軍事沖突,從而降低網絡空間軍備競賽的速度,為國際網絡空間的“建章立制”創造有利環境。
結語
奧巴馬政府調整網絡空間戰略首先是要紓緩國際、國內壓力,其次是要在進攻與防御之間尋找均衡的策略,最后還要落實到網絡空間的規章制度、行為規范,但其調整不會改變美國以網絡軍事力量建立網絡霸權、以發展進攻性網絡能力維護安全,并主導網絡空間秩序的戰略思想。美國在戰略思想和政策上的調整,緩和了各方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的對立情緒,有助于國際網絡空間“建章立制”朝著有利于美國主導的方向發展,并壓縮網絡主權與政府主導模式的國際空間。新的形勢下,網絡空間治理理論創新關系到網絡空間未來的發展,也是各個網絡新興大國面臨的首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