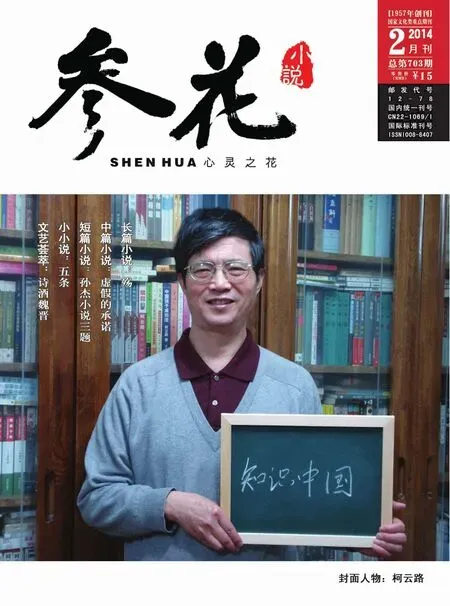夕陽下的那片綠
◎李克利
夕陽下的那片綠
◎李克利
小學校址遷了。遷了遷了吧,日子還是像以往一樣平常,該怎么過還怎么過,但對于張老卻無異于一個打擊。因為再也聽不到孩子們的歡歌笑語、朗朗讀書聲了,再也看不到孩子們做操、跑步、打籃球那活潑的身影了。不過校園門口的大槐樹是遷不走的,這多多少少給了張老一些安慰。
黃昏了,張老提著馬扎到門前坐下,眼睛癡癡地望著槐樹。槐樹老了,能有三百多年了,很高,有白云在樹頂纏繞,有鳥雀在上面做巢。它的主干足有三抱粗,皺巴巴的樹皮是老人嶙峋的脊背,布滿了風雨侵蝕的疤痕。樹根扎得很深,有些根須裸露在地面,交錯盤結(jié),失去了扎向泥土的欲望。風來了,狂風,紋絲不動。槐樹下是黑磚砌就的圍墻,長滿了小草和青苔。在離地面大約四米高的地方,樹干分成兩岔。側(cè)枝上面吊著一座銅鐘,也有百余年了,生了很重的銅銹。銅圈箍入樹肉里,與槐樹融成一體。
槐樹的頂端枯了,是讓雷劈的。張老曾經(jīng)是這所學校的校長,教語文,還教自然和美術(shù)等副科。由于種種原因,張老決定給槐樹安裝避雷針。他和自己最得意的一個學生去了,也是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安裝成。過了幾年,側(cè)枝中間部分還光禿禿的,頂端卻奇跡般生出一片綠來。主枝至今還是老樣子,只不過比側(cè)枝細了。大概側(cè)枝身上負有銅鐘,只有猛力吸取營養(yǎng),長粗長壯,才能承受得住銅鐘的重量。由此張老便驚異于這棵槐樹,懷疑它有某種神靈附體。他領(lǐng)著那個他很得意的學生一起畫過槐樹,但總覺得缺了點什么。離休后又專門畫過,還是缺點什么,于是只能作罷,卻成了心事。
張老熟悉槐樹的一切。他忘不了在槐樹下領(lǐng)著學生們玩耍,忘不了自己年幼時聽父母講槐樹的歷史和傳說,當然也忘不了在槐樹下挨過的批斗。美好的回憶是春風,讓人溫暖和愉悅。糟糕的回憶不能去想,會影響心情,就當作陳芝麻爛谷子,一定要丟棄的。但是對于校園,對于槐樹,張老丟棄不了,割舍不了。
夕陽西下,火紅的光輪在下沉,平穩(wěn)地、緩緩地在西方的天邊旋轉(zhuǎn)著,射出它的全部光輝,燃燒著槐樹,燃燒著張老,并且鍍上一層赤色的光芒。暮色漸漸加濃,槐樹越來越模糊了,終于失盡了蒼青和碧翠,變成黑如烏云般巨大的一團,沉默地凝然不動地迎接黑夜。可是樹頂卻突然亮了,尤其側(cè)枝的頂端,更亮,亮得逼人——夕陽把她最后一抹光線投射過來,射向側(cè)枝頂端被雷火劈掉復(fù)又生出來的那片綠。在夕陽下,它已不是綠色,是紅色,是赤色,成了一朵瑰麗的霞,一團燃燒的火,閃耀著奇異的光輝,像金屬,那般燦爛輝煌,在黑暗即將到來之際,顯示出說不出的驚人的美來!
這時候,張老在贊美,在驚嘆,雙眼閃出的光也像火,像霞。只是剎那間,火就熄滅了,霞也消失了,黑夜開始了。
張老提起馬扎回到屋里,開始吃晚飯。吃罷飯,打開電視,看了陣子,沒啥好節(jié)目,關(guān)了。說說話,三個女兒都大了,嫁人了,和老伴都老夫老妻的了,沒啥好說的。家里也沒裝電腦,就是裝了,張老也不愿意搗鼓那玩意兒,總覺得那是年輕人的事情。只能熄燈躺下。
翻來覆去睡不著,胸口憋得慌,很悶。恍恍惚惚地,張老穿衣,下地,走出去,來到槐樹底下。
槐樹無風自搖。張老抬頭望去,樹冠和夜空融為一體,讓人覺得樹冠也是夜空。樹干搖晃著,銅鐘也跟著晃。漆黑的寂靜的夜里,張老聽到說話的聲音。循聲找去,卻是槐樹和銅鐘的聲音。張老驚異地張大了嘴巴,忘記了合攏。
張老聽槐樹說,孩子,你該下去了,你在這我身上吊了好多年,我老了,承受不住了。銅鐘說,不,我不愿意下去,我也下不去了。槐樹說,孩子,聽話,下去吧,不要逼我。學校遷了,卻沒有把你遷走,人家用不上你了,聽說現(xiàn)在都換成電子鐘了。銅鐘說,我不愿離去,我愿意每天望著校園,你讓我離開,我會難受死的。槐樹說,孩子,這里不是校園了,你每天看到的只是一片空房子。對不住了,我要毀斷自己叫你下去。銅鐘說,求求你了,別這樣。槐樹說,我老了,你也老了,現(xiàn)在提倡年輕化、科技化,再說你整天沉湎于過去也不好。
銅鐘不再說話。夜色沉默得讓人窒息。過了一會兒,張老就聽到“咔”的一聲巨響,槐樹的側(cè)枝斷了。銅鐘撲然落地,無一絲聲息。銅鐘是自愿離開的。槐樹也不搖了,安靜地矗立著,有風吹來,不搖不晃。
這時候,張老醒了,睜開眼,看到天花板影影綽綽的,耳畔是老伴熟睡的鼾聲,槐樹和銅鐘的對話在張老的腦海里越來越清晰。張老悵然若失的心似乎有了依靠,那些煩躁和憋悶也像銅鐘落地般離開了。倦意襲來,張老沉沉地睡了。
初秋的一個黃昏,小學舊址來了一位中年人,瘦瘦的,弱不禁風的樣子,穿戴很樸素,來看望張老。不湊巧張老和老伴去了小女兒家小住。那個中年人敲開張老鄰居家的門,和鄰居聊了幾句,問了問張老的日常起居、身體狀況,并且拿出紙筆,記下了張老的通訊地址和聯(lián)系電話。中年人走到槐樹下,仰頭望了望聳入云天的樹冠,然后用手輕輕地拍著樹干,耳朵緊緊地貼著樹干聆聽。過了好久才走開,走一步回頭望一眼,一直走出很遠。夕陽西下,最后一抹光線射向老樹,射向老樹側(cè)枝頂端被雷火劈掉復(fù)又生出來的那片綠。中年人的雙眼驀地亮了,目光里含著贊美、驚異、深情。天完全黑了,中年人才一步三回頭地離開,再也沒有回來。
張老從女兒家回來后,聽鄰居說起了中年人。張老打開記憶的閘門進行搜索,想起中年人應(yīng)該是那個自己最得意的學生,是那個曾經(jīng)和他一起去畫槐樹、給槐樹安裝避雷針的學生。
日子如水般一天天流淌,張老盼望中年人能夠來電話,每天盼來的都是失望。小學舊址成了村辦紙箱廠,機器整天轟隆隆響。老樹底下成了紙箱廠的停車棚,停滿了自行車、電動車、摩托車。銅鐘也派上了用場,鐘聲第一遍敲響,張老知道工人上午下班了,該吃午飯了;鐘聲第二遍敲響,那是工人下午下班了,該吃晚飯了。銅鐘只在紙箱廠下班時敲響,上班時從來不敲。
轉(zhuǎn)眼間天涼了,槐樹的葉子黃了,落了,光禿禿的枝干伸向高遠的天空。張老又端起畫夾畫槐樹,還是缺了些什么。張老感到很累,老了,的確老了,心中更珍惜那片綠。
深冬的一個上午,天陰沉沉的,像要下雪的樣子。郵遞員送來一個包裹,撕開外包裝,里面裝著一幅畫。張老展開畫,畫面上:一棵老槐樹,離地面很高的地方分成兩岔,側(cè)枝上吊一銅鐘,枝干無葉,頂端碧綠。夕陽的最后一抹光抹在那片綠上,閃著神圣的光,耀眼。樹的不遠處,一位老人望著槐樹,如癡如醉。畫的落款和印章就是張老那個得意學生的名字。
張老后來才聽說,學生是位很有名氣的畫家,不久前因病去世。這幅畫是他的遺作,臨終前囑咐家里人一定要寄給張老。曾經(jīng)有人出大價錢購買這幅畫,學生的家人都沒有賣。
張老到書畫店把畫裝裱了,掛在家里客廳迎門的墻上。張老每天都看畫,看畫上的槐樹、銅鐘、老人,看夕陽和夕陽下的那片綠。看著看著,張老的眼淚就會無聲地流下來。
(責任編輯 姜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