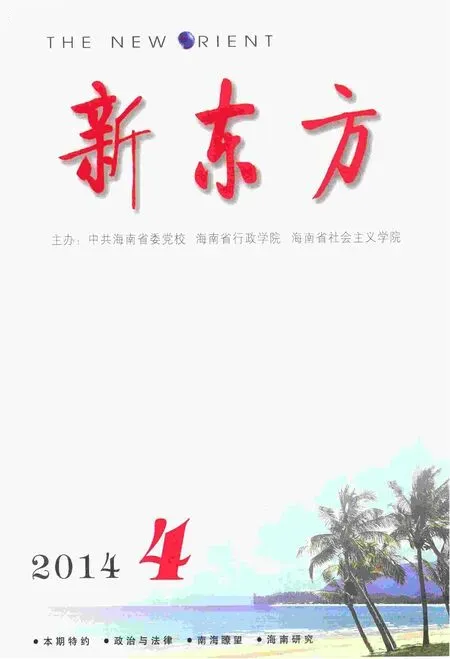民族主義:歷史沿革與前景展望
1774年德國哲學家赫德爾最早提出“民族主義”一詞,隨后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和費希特《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說》的發表,標志著民族主義的正式形成。盡管如此,學術界對于民族主義的內涵至今沒有一個公認和普適的定義。
一、關于民族主義的基本觀點
什么是民族主義?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其一,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予以理解。安東尼·吉登斯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指一種心理學的現象,即個人在心理上從屬于那些強調政治秩序中人們的共同性的符號和信仰。”其二,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予以理解。保爾·布拉斯認為,“民族主義是政治精英創造的文化理論,最終目的是讓其政治行為和權力更加合法化”。其三,從政治合法性的角度來予以理解。埃內斯特·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關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在某一個國家中,族裔的疆界不應該將掌權者與其他人分割開”。其四,從民族與民族主義關系的角度來予以理解。安東尼·吉登斯認為,民族若沒有形成,就絕不可能會有民族主義,至少絕不會有現代形式的民族主義。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民族。相反,蓋內爾認為,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孕育了民族主義。法國思想家吉爾·德拉諾瓦則認為,在現實的世界上這兩種說法都成立,民族主義可以創造民族,如近代所出現的民族國家,民族當然更可以孕育民族主義,如由古老文化民族發展而來的近代民族國家內的民族主義。兩者可以互為因果,簡單的界定往往會留于片面。因此,“不要先驗地認為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或相反,民族一定會創造出民族主義”,民族和民族主義實際上處于一種相互制約、相互激勵,既互為條件又對未來開放的變遷與互動之中。其五,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予以理解。赫伯特·吉本斯認為:“民族主義可以被看作是顯示民族精神(如歷史、傳統和語言)的特定的方式;而抽象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是制約一個民族的生活和行動的觀念。”我國學者也將民族主義理解為一種社會運動和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
盡管學者們對民族主義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一般認為民族主義最早興起于近代西歐,后逐漸擴散到整個世界,其基本內容包括強調本民族的同質,強調本民族的具體文化傳統,認為國家是政治忠誠和政治行動的最終目標,要求建立民族國家,以此保護和捍衛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傳統和疆界的完整與獨立。
二、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
中世紀的西歐,建立在莊園農奴制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等級制度將人們禁錮在人身依附網絡之中,而基督教神學支配著人們的觀念,為封建制度蒙上神圣的靈光。自14世紀開始,資本主義萌芽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共和國中滋長,隨后擴展到法國、英國、尼德蘭、德意志等國家和地區。于是,隨著城市的勃興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西歐人逐漸走出中世紀小生產的狹小田地,突破了傳統的人身依附關系的網絡。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由交換的經濟形態,而現實的神學禁欲思想阻礙了人們的思想交流,阻礙了經濟發展,人們必然要求擺脫封建等級觀念與神學思想的束縛。于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便水到渠成,風起云涌了。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把人們從宗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世俗權力特別是王權得到加強,宗教共同體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體的地位上升。在這一社會變革過程中,逐漸崛起的新興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反對封建割據,主張國家的政治統一。在新興階層的支持下,西歐各國的君主們打擊地方分裂勢力,不斷加強王權,從而把居民置于國家的直接管轄之下,確保政治上的統一。于是,“在16世紀,西方出現了絕對主義國家。法國、英國和西班牙集權化君主是與金字塔式的四分五裂君主制及其領地制、封臣制這一整套中世紀社會結構的決裂”。
隨著絕對主義國家的發展,國家主權概念在《威斯敏斯特條約》中得到確認,國家具有了明確的人口和疆界,便于民族共同體的確定。絕對主義國家確立了民族共同體的基本框架,大體明確了本國與其他國家的基本區別。不過,由于王權高居于民族之上,并不是真正的民族和國家的代表,因此絕對主義國家僅僅是形式上的民族國家。
一旦主權觀被確立為政府原則,那么它就開始同公民權關聯起來。公民權的適用范圍指向總體上的國家政治共同體。法國啟蒙運動批判君主專制制度,發出了“專制之下無祖國”的呼聲。基于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相結合,啟蒙運動提出了系統的民族主義思想,從而催生了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摧毀了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宣布了主權在民原則,國家成為共有的家園。可以這樣說,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并在革命中得到普及,并且在世界范圍內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覺醒。法國大革命因其大眾性與自覺意識而成為近代政治民族的開端,同時也是民族主義形成的重要標志。
民族主義形成后,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迅速向外擴散。
在西歐,工業革命形成了國民經濟,凸顯了民族國家的重要性;摧毀了農業社會的鄉村、行會等等各種共同體,民族共同體成為新的寄托;帶來城市化,人口越來越集中在城市中,生活方式趨于同質化;新興交通工具的興起促進了人員流動,加深了人們對自身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區別認識;教育的逐漸普及與現代傳播手段興起,有利于民族主義的傳播。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以建立民族國家為首要目標的民族主義不斷擴展。到19世紀70年代,隨著德國、意大利實現了國家統一,西歐民族國家建立的任務基本完成。
19世紀70年代以后,西歐民族主義進入到追求民族國家富強的新階段,民族主義的性質隨之發生變化。在西歐范圍內,西歐各國之間展開爭奪霸權和殖民地的激烈斗爭,民族主義轉化為狹隘民族主義甚至極端民族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西歐各國以“文明民族”自居,侵略掠奪其他民族。可以這樣說,民族主義是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西歐和北美以外的廣大亞、非、拉地區,其民族意識在遭到侵略后得以覺醒,從而使民族主義被迫啟動,導致民族主義從西歐北美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
20世紀以來,世界上出現了三次大的民族主義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多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擺脫了西方殖民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是第一次民族主義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至20世紀60、70年代,更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中取得了勝利,建立了新興國家,是第二次民族主義浪潮。在1991——1993年期間,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個社會主義聯邦制國家相繼解體,導致在東歐、中亞地區一時間涌現出了20多個民族獨立國家,是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
總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體系“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因此,建立民族國家是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根本前提,而民族主義則是伴隨民族國家的建立所產生的一種現代性觀念形態。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等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就是這樣迅速而無情地遍及全球的。
三、民族主義的作用
“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是工業革命的產物”,而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歷史范疇,它一方面是指工業革命開始以來歐美社會的轉變,另一方面是指歐美現代化在世界范圍內的擴散。隨著現代化的產生及擴散,民族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廣泛興起。因此,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是同步發展的,它日益被整個世界所接受的過程,也是人類逐步實現現代化的過程。
一定的價值觀往往成為社會變革的先導。啟蒙運動為現代化奠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價值觀基礎。因為“啟蒙運動是歐洲文化和歷史的現代時期的開端和基礎,……是對一切文化領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顛覆,帶來了世界關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歐洲的完全更改”,它把近代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現代原則充分表達出來。
民族主義是一種建立在對本民族文化、傳統和利益等認同基礎之上的民族情感,民族情感往往是以一種分散的方式被體驗和表達的,當它們在某種環境里被強烈地喚起的時候,需要政治領袖人物以某種方式集中表達并付諸實施。
民族主義具有如下作用。
(一)民族主義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
在西方國家,從工場手工業、產業革命到自由資本主義的形成,民族主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民族主義喚醒了民族覺醒、促進了民族統一,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意識形態支持。
(二)民族主義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
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原因在于:其一,由于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集體主義價值觀,在其作用下導致對國民財富的理解得到升華,并以民族國家為競爭主體形成了各國相互競爭的局面,從而塑造了現代經濟發展的競爭結構和激勵機制;其二,由于對民族威望的評價是相比較于其他民族的,因此民族主義也就意味著國際競爭,于是基于民族威望所帶來的自豪感是激勵民族成員努力奮斗的重要動力;其三,由于民族主義本質上來說是精神層面的推動力,有利于本民族共同致力于整個民族國家的繁榮與進步,因此民族主義還可以避免由于本民族內部客觀存在的各種對立而阻礙經濟發展。總之,“民族主義是現代經濟發展背后的倫理動力。”
(三)民族主義可以推動世界多元現代化的進程
現代化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在全球范圍發生的大轉型。正是由于民族主義的興起,為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提供了可能性。但具體到各國而言,現代化進程則呈現出豐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模式,使得世界各國在現代化實踐中必然呈現為一體化與多元性的對立統一,從而導致某些國家在歷史轉型期出現程度不一的認同危機和社會陣痛。而以民族文化傳統認同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有可能為現代化大潮沖擊下的社會提供一個有凝聚力的新認同,從而保持社會統一與穩定,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弭或緩和這些國家常見的傳統和現代二元結構沖突,并進而推動世界的多元現代化的進程。
(四)民族主義往往阻礙后發國家現代化的進程
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先經濟,后文化、政治、社會的自然進程。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則是伴隨著西方殖民入侵作出的被動選擇,因此其現代化進程首先是一個政治進程,后表現為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進程。這種現代化進程的時序倒置,容易使后發國家建設走上偏離現代化目標的歧路。不僅如此,西方發達國家在實現現代化之后,往往把自己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強加給后發國家,增加了其從容改造傳統文化、吸收先進文化而獲得現代性的艱巨性。于是,后發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民族主義在認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帶上厭惡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強烈色彩,從而阻礙了以現代化為取向的變革。
(五)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往往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
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指不惜損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來滿足自身的貪欲,主要表現為:一是大民族主義或民族沙文主義,其特點是自視本民族優越于其他民族,并對其他民族加以歧視、壓迫、控制,直到征討、奴役。二是民族極端主義,其特點是與相鄰或相關民族視同水火,絕不相容妥協,主張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甚至采用恐怖手段。三是民族分裂主義或分離主義,其特點是從多民族國家或大民族體系中分離出來,追求獨立建國。這些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往往使公民的國家轉變為民族的國家,不僅埋下了種族主義的種子,而且也鏟除了愛國主義的根基。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是采用意識形態手段對愛國主義進行分解的產物,是組成恐懼與仇恨的重要因素。
總之,民族主義在現代化的不同歷史階段起著非常復雜的作用。它既可以成為一面凝聚力量的“旗幟”,也可能成為一件遮丑的“外衣”。
四、民族主義的前景展望
冷戰結束不久,民族主義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歷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全球化浪潮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全球化是人類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而出現的一個新階段。二戰后,世界經濟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以跨國公司為載體,各種生產要素的利用和配置大大超越民族國家的疆界,世界市場不斷整合和一體化,使得全球的產品、服務和資本通過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國際投資高速度、大容量地依據既定的規則跨國界流動。于是,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日趨密切,導致民族國家間相互依存的不可逆性,人類所生活的地球日益成為一個狹小的“地球村”,不同國家、民族、種族的公民日益融合為世界公民。傳統的國際政治行為主體民族國家逐步失去其針對市場的主導性的控制力,不僅弱化了民族國家的主權性,同時還帶給民族國家地位與利益的不均衡性。
當今全球交往達到空前深度與廣度,這對于民族主義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全球化邁出的每一步都會加強民族主義的反抗力量。盡管民族主義為政治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然而,民族主義理論的不系統性與其過分突出的情緒性二者的結合所隱含的暴力與戰爭傾向早在民族主義社會動員的初始階段即已顯露,這也是民族主義的痼疾。對民族主義必須謹慎以待。必須看到民族主義可能從左右兩極都走向極端的危險,將民族主義看作是拯救民族的靈丹妙藥,會將民族引向癲狂的深淵;而將民族主義看作是洪水猛獸,無情鞭笞,很可能既會傷害民族主義借以依憑的民族感情,又會使民族主義獲得發展動力而適得其反。
我們應該提倡一種有限度的民族主義:一個民族不能僅僅以民族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而且每個民族都有民族自豪感,都渴望富強,因此必須承認其他民族存在優點,承認其他民族渴望富強的訴求,不能把本民族凌駕于其他民族之上。
在全球化時代,尊重多元與開放,積極進行各民族文化與經濟的整合,增強民族凝聚力,這也許是民族主義保持生機與活力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