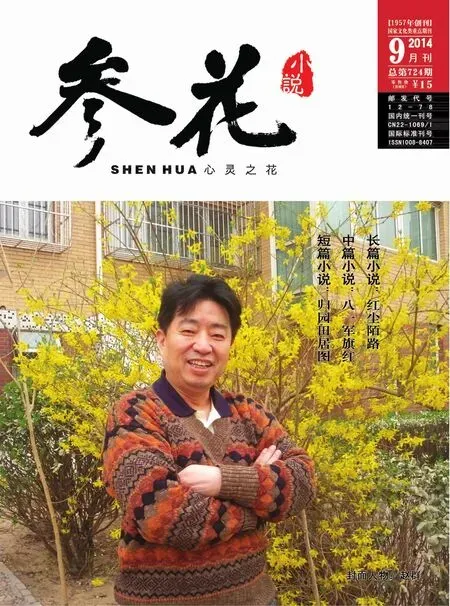阿城小說《孩子王》文本的音樂性闡釋
◎陳 雍
阿城小說《孩子王》文本的音樂性闡釋
◎陳 雍
本是音樂術語的“復調”被巴赫金借用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后,“復調小說”的理論成為二十世紀重要的文本分析理論。從復調理論來闡釋中國現代作家阿城的《孩子王》,我們可以看到文本的復調結構與敘述的旋律與節拍讓文本呈現出音樂性的特征。在文本里音樂性不只是文本的形式問題,內容也統一于其中,從這個理論角度來看,《孩子王》的“尋根性”更上升為一種文化哲學意味。
《孩子王》 復調 敘述 音樂性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提出了“復調小說”的理論,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眾聲喧嘩的對話特征,進而讓作者本人的價值傾向得以回避,讓小說自成一體得到無窮的闡釋。受此理論的啟發,阿城《孩子王》中四個人物的故事交織并存又互相獨立,線索明顯,有一種四重奏的多聲部效果,四種樂器構成了和聲,從而形成小說的統一體,敘述的節奏與節拍更是體現了小說文本的音樂性,在這種闡釋當中,我們對小說《孩子王》有了更新的認識。
一、文本結構的復調式
“復調”本是音樂術語,在作曲法中是指不同聲部的旋律不同,但不是多旋律的混雜,而是通過和聲對位,結構成多聲部的交響式的“織體”,改變了以往多聲部單旋律的線性結構。[1]進而,巴赫金借用“復調”的術語來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具有復調性:“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2]接著,米蘭·昆德拉更為具體地說明小說復調:試圖避開單線性,在一個故事的持續敘述中打開缺口。[3]昆德拉理解的復調有以下特征:小說是多線索的,各個線索間的關系是平等的,總體上交織成一個整體,在文體上則可以是各種文體同時并存。依以上小說復調理論來看阿城小說《孩子王》,同樣能體會出其韻味無窮的音樂性。
《孩子王》的文本層面,四個人物故事線索同時敘述,齊頭并進又彼此交織。第一部分,孩子王“我”勞動生活的結束和教師生活的開始上路,但同時伴隨著來娣的出場及其對音樂教師夢想向往;第二部分講“我”教書的經過同時以回憶的方式從中穿插王七桶的故事,講“我”回隊聚友的過程并穿插來娣為夢想而贈字典進而提出“老子寫詞,老娘編曲”;第三部分,學生習作的開端又穿插進“我”寫詞的心緒;第四部分,“我”帶學生進山勞動與“我”和學生王福的賭約齊頭并進,而“我”將會被教育科整頓的預兆也出現了;第五部分海納百川地囊括了四個人物的故事,“我”教書生活的結束、來娣唱出了“老子寫詞,老娘編曲”的歌,王福識字及習作的大為進步,而王七桶的形象在王福的作文中更加鮮明。四個人物的故事交織并存又互相獨立,線索明顯,有一種四重奏的多聲部效果,四種樂器構成了和聲,從而形成小說的統一體。
在文體上,把整部小說當做完整的樂章來看,學生稚嫩到成熟的作文和來娣的歌曲則是其中的插曲,粗略地來說,小說文本由三種不同的文體構成,小說成了雜燴的文體。而學生作文是小說關鍵性的情節,是孩子王“我”教書生涯的高潮,同時也促成了最后的“被撤”結局,是小說最深刻的主題。來娣的曲和“我”的詞成了歌曲被唱了出來在一定意義上,完成了她的心意也完成了她形象的轉變,滿足了讀者期待視野。更重要的是,在聲音上,來娣的曲是“泉水叮咚”,與來娣自出場以來的“老娘”不停的率直和粗狂形成
張力,飽滿了人物形象。在這個整體里面,小說的主題、人物的語言以及人物性格等都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顯示出濃重的生活氣息的同時把知青的意識形態與時代的悲劇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
二、敘述的旋律與節拍
從敘述的角度看,阿城《孩子王》的敘述呈現出樂章的旋律,節拍感明顯。米蘭·昆德拉曾把小說比作音樂,他說:“一個部分也就是一個樂章。每個章節就好比每個節拍。這些節拍或長或短,或者長度非常不規則。這就將我們引向速度的問題。我小說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標上一種音樂標記:中速,急板,柔板,等等。”[5]這種音樂性標志到底是小說的內在形式還是一種外在的東西?到底是作家自覺而成,抑或“無心插柳柳成蔭”?盡管昆德拉承認是有意為之,并與其自身從事過音樂事業相關,而從伊塞爾的接受美學站在讀者闡釋的角度,問題的答案也無關緊要了。
阿城小說《孩子王》共五個部分,每個部分的敘述速度因內容以及氛圍的不同而不一,呈現音樂的旋律和節拍。依篇幅和段落設置用音樂來標志如下:
第一部分:十九個段落三千六百多字;快板
第二部分:四十六個段落一萬一千多字;中速
第三部分:十個段落兩千五百多字;小柔板
第四個部分:十三個段落三千四百多字;柔板
第五個部分:二十一個段落四千四百多字;小快板
依據上述復調結構的四重奏敘述,第一部分用快板來敘述孩子王“我”勞動生活的結束和教師生活的開始上路以及來娣的音樂教師夢想,無疑符合敘述口吻和人物心理活動的輕快和寬松,更多地體現對新生活的向往。第二部分顯然是小說的最大樂章,講“我”的教書生涯、王七桶的故事、回隊聚友和來娣為夢想而贈字典,而中速的敘述使得故事不緊不慢,娓娓道來,傳遞出人物的從容氣魄。第三部分,學生習作的開端又穿插進“我”寫詞的心緒,小說寫到此是一個轉折:學生從識字轉到了習作,接下來的第四部分同樣是習作。從習作的成績來看,第四部分顯然是學生突飛猛進的進步,從小柔板到柔板的敘述是漸漸減慢了敘述速度,讀者漸漸把握的是故事的細節,特別是師生賭約更明顯的是“我”的教師生涯擺脫了一開始的生疏。所有的故事人物發展到此,都基本成熟。第五部分回到小快板,“我”教書生活的結束、來娣唱出了“老子寫詞,老娘編曲”的歌,王福識字及習作的大為進步,而王七桶的形象在王福的作文中更加鮮明,小快板的敘述傳達出人物在苦中的樂觀主義。以快板開始以小快板結束,中間從中速到小柔板到柔板,基本上是回旋的節奏,樂章也自成和諧一體。作為知青一代,阿城是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的根的作家,而自成樂章《孩子王》不愧是他長期從最底層的深處吸取生活的營養后的發韌之作。
結語
從文本結構的復調到敘述的旋律和節拍,音樂性成為了《孩子王》文本的重要特征。“復調”既讓小說經得起多重闡釋,又讓小說成多聲部的一體,這也正是小說文本生命得以源源不息的原因。值得探究的是,音樂性的特征是一種內置節奏還是外在的東西?
在西方文論史上,二十世紀是文本分析理論形成多元格局。自從俄國形式主義信誓旦旦要擺脫傳統的批評理論(傳統批評理論側重于對作家、世界等被形式主義者認為是作品以外的因素)而提出“陌生化”理論,打開了文學“內部研究”的理路,于是對之前的“傳統”文論批評的重大反撥和發展的文本分析理論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沿著俄國形式主義者的語言的陌生化理論,布拉格學派和英美“新批評”的眾多理論家更是提出了“含混”“張力”“反諷”等理論來研究作品的語言,這個理路一直發展到了法國結構主義的尋找作品語言所形成的“深層結構”。而在對“深沉結構”的追究和闡釋時又必然涉及文學的“外部”——社會、文化、歷史等領域。進而當 “兩級符號”“互文性”“文本之外無一物”“話語-權力”等后結構主義理念風行起來。“讀者論”或“文化論”轉向引發的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空間理論”“身份認同”等各式方法流派中,文學批評又同政治、文化、社會、語言、意識形態等眾多領域和問題交織互滲起來。這說明了一個問題: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截然分開的兩個問題,而是具有暗合和統一的問題。
據以上理論,我們可以看到,從文本結構的復調到敘述的旋律和節拍,音樂性成為了《孩子王》文本的重要特征。“復調”既讓小說經得起多重闡釋,又讓小說成多聲部的一體,這也正是小說文本生命得以源源不息的原因。在文本里音樂性不僅只是文本的形式問題,內容也統一于其中,從而讓我們對小說文本《孩子王》有了更高的闡釋視野。陳凱歌陳述過《孩子王》的思想內涵:“它通過對教育狀況的描寫,深刻地表現了文化和人之間的關系,追溯了中國出現諸種社會災難的文化背景”。在音樂性的文本里盡情地演繹人物命運與時代悲劇,歷史與民族的沉重感在阿城筆下跳躍成一曲樂章,從這個理論角度來看,《孩子王》的“尋根性”更上升為一種文化哲學意味。
[1]馬新國:《西方文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2頁
[2][俄]《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3][捷]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頁
[4]吳曉東:《從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45頁
[5][捷]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頁
(作者單位: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天河學院)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