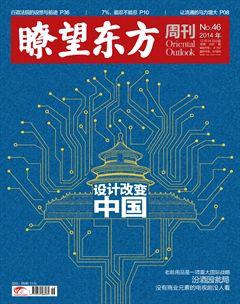工業設計三人談
姚瑋潔+徐穎
拉夫·威格曼
全球工業設計著名推手,iF國際設計論壇總裁,歐洲設計管理獎評委會主席。他曾為多項世界知名設計獎擔任評委,如INTEL 設計獎,愛爾蘭Glen Dimplex設計獎等。
《瞭望東方周刊》:為何選擇深圳作為國際上第一個展示iF設計大獎的地方?
拉夫·威格曼:中國對好的設計如饑似渴,希望吸引世界頂尖的設計獎項;而深圳又是中國設計師聚集的重要城市,因為這里有大量的客戶。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2014年深圳工業設計論壇的參加者,你對深圳以及中國工業設計的印象如何?
拉夫·威格曼:工業設計在這里大量存在,是論壇舉辦的重要原因——當地需要設計,設計師也需要挑戰和工作。當地政府也意識到,創意工業是從產品導向轉型為品牌導向的核心手段。會議以及相關論壇活動不僅吸引了設計領域的人,也能讓普通大眾接觸到。這是一種低投入、高回報的投資。未來的挑戰在于,如何設計并提供高水平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中國品牌的需求。
《瞭望東方周刊》:你最早接觸到中國的工業設計是什么時候?這些年來,對于中國工業設計的變化,你怎么看?
拉夫·威格曼:20年前,在中國,設計還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當認識到設計能使產品具有國際競爭力時,人們的意識變強了,來自政府的支持變多了。
當然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中國頂級經理人的認識。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依然認為工業設計只是產品形狀的修正,這意味著他們沒有明白設計師的戰略價值。
另外,不少中國設計師必須學習如何為他們最好的“解決方案”而戰斗。他們被教育要遵從客戶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好的設計師會堅持保留最好的——也許正是客戶不看好的!
如果設計師需要支持,他們可以試著尋求iF國際設計論壇的幫助,這是一個擁有獨立意見的平臺,也許對設計師來說,這里的專家更能幫助他們,也更有說服力。
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開始獲得國際大獎。但你必須了解,在申請和獲獎之間有一個比率。也許一個設計工業成熟的國家,全部參評作品有50%可以獲獎,但工業設計剛剛起步的國家可能只有3%的獲獎率。
中國工業設計行業有很高的積極性、雄心并愿意參與競爭,而且中國有廣大的市場等待著他們。如果申請iF設計大獎,必須高于平均水平,并且每年都要申請。一次的成功并不夠。設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一個品牌的信任是建立在持續的基礎上的。
《瞭望東方周刊》:很多設計師認為,設計的成功不在于獲獎,也不在于客戶滿意,而在于市場是否認可。你對此怎么看?什么樣的設計最吸引你?能否舉例說明?
拉夫·威格曼:客戶只關注一點,就是市場的成功。但你很難搞清楚一個產品究竟為何失敗。 是因為不好的設計?是因為錯誤策劃、市場策略還是惡劣的銷售服務?很多公司都把失敗歸結于設計而把成功歸結于策劃,這非常錯誤而且不公平。
我本人特別喜歡以環境和社會為導向的產品和項目。
《瞭望東方周刊》:你是國際最為著名的工業設計產品推手,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動一個工業產品價值的實現?如何借助設計展這樣的平臺來推動工業設計能力的提升?
拉夫·威格曼:這一行的追隨者而非創新者,越來越多,因為獨特性非常稀缺。所以,如果某一產品想要長久地吸引注意力,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品牌戰略。對于企業來說,這意味著一定要真正尋找到滿足公司“哲學”并能幫助提升這一“哲學”的設計師。而設計師一定要足夠優秀。設計推動者就需要知識、經驗以及國際視野,必須理解行業的需求、設計師的能力和競爭力,并且敏銳地意識到市場的方向在哪里。
光說“設計是重要的”是沒用的,我們必須證明它的重要性。
《瞭望東方周刊》: 在你看來,工業設計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很多人認為它增加了制造業的附加值,也有人認為它就是產品的核心價值所在,你怎么看?
拉夫·威格曼:工業設計最重要的角色,簡單來說,就是解決問題,提高環境質量,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
今天我們多次提及“工業4.0”是下一個工業革命。產品和人類彼此之間將獨立交流、自行優化流程、降低成本、提高質量。設計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發揮作用,是當前最大的挑戰。
《瞭望東方周刊》:你在深圳有什么合作計劃?與中國工業設計界有怎樣的合作計劃?
拉夫·威格曼:深圳有望成為我們在中國市場的樞紐。我們甚至想在這里開設辦公室。不過,要真正創建信任和高效的合作,中國設計界需要明白,成功是需要時間的。我們的中國朋友始終傾向于快速地跟著變化走,這讓長期的成功變得艱難。但我希望他們知道,iF總是在他們身邊,我們時刻準備著為他們提供幫助和服務。
凱瑞姆·瑞席
當代設計師中最多產的大師,曾獲300多個獎項,有3000多項作品投入生產,覆蓋全球35個國家。他很重視人性化體驗,代表作有Umbra公司的嘉寶垃圾桶、Alessi公司的Kaj手表,及為森本餐廳、費城酒店所作的室內設計等。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2014年深圳工業設計論壇的參加者,你對深圳以及中國工業設計的印象如何?有哪些優點或缺陷?
凱瑞姆·瑞席:這個世界正在不斷地被重新設計,中國在這種設計變革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思維嚴謹,很有自律性,也很聰明。
深圳的優勢已經不再是行業本身,而是其與制造者和其他國家的直接關系。標準和追求完美都是做出好的設計的必要條件,對于詩歌、情感和人性的尊重,也是好的設計所不可或缺的。
深圳的機場和出口處都充滿著創意設計,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根據仿生學原理設計的長長的通風通道,之后是機場里的光線和空間設計,給人一種人性化的現代體驗。
《瞭望東方周刊》:你2014年開始擔任這一論壇的評審會主席,作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師,你對中國的工業設計怎么看?endprint
凱瑞姆·瑞席:工業設計是一個與社會緊密相連的過程,其價值遠遠超越設計產品本身。光有創造力和高科技創造不出好的設計,還要考慮實用性、市場營銷、行為學、美學、制造技術、材料選擇、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問題。
過去20年中,中國的生產質量實現了從較差到最好的巨大飛越,這種提升離不開工業設計的發展。但是,我認為中國還缺少一個非常清晰的計劃,中國企業還沒有足夠的品牌意識,幾乎沒有世界知名品牌。中國需要理解怎樣培養原創性,并將其發揚光大。
《瞭望東方周刊》:很多人認為,中國目前強烈的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動力,推動著工業設計近年來的蓬勃發展,對這你怎么看?在世界范圍內,推動工業設計發展的核心動力是什么?
凱瑞姆·瑞席:視覺產業和信息產業越來越專業化,人的精力和時間都在極度膨脹,消費者不斷地被周圍的環境刺激,我們正處在數字時代,所有的東西都要被重新設計。
設計的發展正遵循著一套復雜的標準——人性化體驗、社會、政治、經濟、國際事務、物質與精神上的交流,形態視覺以及對現代文化的全面理解。然而,制造卻遵循著另一套標準——投資、市場份額、生產管理、配置、服務、產品表現、質量、生態環境以及可持續性。所有這些因素正在影響著室內設計、審美觀、文化和人性化的體驗,同時也在定位公司品牌和塑造品牌價值。
《瞭望東方周刊》:一些設計師認為,設計的成功不在于獲獎,也不在于客戶的滿意,而在于市場是否認可。你是當代最多產的工業設計師之一,如何做到這一點?
凱瑞姆·瑞席:對于產品所產生的成就感可以是多個層面的。我設計的動力一直在于,設計是一種人性的體驗。我的信念是通過設計去激勵其他人。我能夠從宏觀到微觀,全面地將人的體驗融入任何我設計的產品之中,小到開關、門把手。
《瞭望東方周刊》:有不少中國設計師認為,除了為客戶提供優良的設計方案,還需要提供整套的產品設計系統,包括產品定位、營銷策略等,你怎么看?提供更豐富全面的服務,是否工業設計企業的唯一出路?
凱瑞姆·瑞席:當然!我相信很多中國優秀的設計產品,并不是完全出自美國和歐洲的公司。中國需要有自己的品牌并打破世界工廠的形象。我時常想到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國家,比如瑞典,雖然只有700萬人口,但卻擁有宜家、沃爾沃等國際知名品牌。中國有14億人口,但除了阿里巴巴,我竟然說不出別的品牌了。
如果中國想要創造具有影響力的世界品牌,就必須回答幾個問題:公司是否對人性和文化感興趣?制造業是否經常討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家庭的幸福感、愛情的密碼、人的自我表達方式、人的自由等?你的產品能否將這些元素體現出來?
《瞭望東方周刊》:為什么選擇工業設計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聽說你在33歲前的經歷很坎坷,到紐約后才獲得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二次生命,能否分享你的奮斗故事?
凱瑞姆·瑞席:從我有記憶開始就喜歡上設計了。七歲時,我的房間里有一個橙色的勃朗鬧鐘,還有非常具有未來感的白色音響。很小的時候,我就想設計周圍的環境。1982年我獲得了工業設計的本科學位。之后的兩年我在意大利米蘭的設計工作室繼續學習。那段經歷讓我以后想設計既有美觀性又有實用價值的產品。
但是從1985年到1991年回到加拿大的這段時間,我做了很多機械、醫療器械、電動工具、激光測量儀器、雪橇、火車的室內設計,還為加拿大郵局設計郵箱。我領悟到很多東西,我覺得意大利是唯一一個意識到必須將美學融入工業設計的國家。
那時,北美的公司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我辭掉工作專心學術,有近兩年的時間沒有設計。之后我身無分文地來到紐約開始畫身邊的物體,美化我一直想要塑造的理想世界。
《瞭望東方周刊》:聽說你可能入駐中芬設計園,接下來在深圳有什么合作計劃?
凱瑞姆·瑞席:六個月前我在深圳設立了一個辦公室,希望能夠促進中國辦公室和紐約辦公室之間的設計與文化的交流。我現在和很多的中國制造商都有合作。但我更想在中國設計室內裝飾,還想開辦一個國際設計項目。我喜歡中國,我想見證中國的發展并參與其中。
黃智恒
IDEO中國區設計總監。IDEO 公司由一群斯坦福大學畢業生創立于 1991 年,是全球頂尖的設計咨詢公司,曾為蘋果公司設計出第一只鼠標,設計出了全世界第一臺筆記本電腦。黃智恒曾獲得包括iF和紅點在內的多項國際設計大獎,曾為美的、三星、TCL、方太等國內外知名企業提供設計服務。
《瞭望東方周刊》:不少以代工生產(OEM)為主的中國制造企業,目前正期待通過工業設計打造自己的品牌,你對此有何建議?
黃智恒:我們在中國有不少制造業客戶,他們經驗豐富, 擅長生成消費者反饋和洞察, 但是在如何把這些洞察轉化成利于營銷的創新型產品方面,還比較欠缺。
關鍵并不在于這些企業缺乏轉化能力, 而是在于思維理念上的轉變。要成功經營一家OEM企業, 通常的理念就是要求員工盡可能地高效工作。然而, 要使推出的產品或服務有卓越的用戶體驗, 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要鼓勵員工在嘗試中學習,并且要具有擁抱未知領域的開放心態。
一件好產品的誕生, 不只是關系到專業設計師的工作。要培養設計師對目標用戶的同理心,依據明確的用戶需求來指導技術和商業決策。
《瞭望東方周刊》:你的中國客戶一般有何特點,比如企業規模、對工業設計的認識、對于價格的看法等?你了解到的中國政府官員對工業設計態度如何?
黃智恒:我們與各類中國客戶開展合作, 其中既有跨國公司, 也有初創企業。這些客戶通常都有宏偉的發展愿景, 公司的領導人也不乏樂觀精神和好奇心。正是這些特質驅動著設計創新。
在我看來, 中國政府對工業設計重要性的認識以及大力扶持顯而易見。特別是在中國政府立足于進一步做實擴大內需戰略來支持經濟增長,以及中國開始失去低成本生產制造優勢的大環境下,這一點尤為明顯。endprint
盡管如此, 我仍然認為需要進一步加大對工業設計行業和教育的投資力度。因為只有懂得如何從真正了解人的需求出發來做設計,而不是為了設計而設計,以及懂得如何與跨專業團隊通力協作,而不是自我封閉在單一的工業設計團隊里,才能應對當今世界的各種復雜挑戰。
《瞭望東方周刊》:從2008年第一屆國際工業設計節開始,深圳工業設計協會就與IDEO有合作和交流,你認為這6年來,工業設計在深圳、在中國的發展有何特點和趨勢?
黃智恒:深圳可以說是世界制造中心,累積了豐富的專業經驗,不斷推動著工業設計邁向世界一流品質。MIT媒體實驗室的伊藤穰一教授最近分享了他對深圳這種獨特的硬件生態系統的看法,并把它與硅谷的創業運動作了類似比較。對于工業設計師來說, 如今的深圳已然是一個催生著各種可能和新機遇的地方。
《瞭望東方周刊》: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你認為,未來數年中國的工業設計會在哪些產業有更大的空間和作為?
黃智恒:中國正在邁入老齡化社會,“4-2-1”家庭結構日益普遍,我認為老齡化領域將是工業設計未來數年、在全球范圍內可以有更大空間和作為的領域。
根據IDEO今年推出的全球創意設計平臺“Designs On:Aging”預計,到2050年中國將有約三分之一的人口超過60歲。針對這個老齡化趨勢,我們的中國設計團隊提出一個名為“故事盒”的設計概念,用于連接真實可見的個人物品和虛擬的記憶。此外,IDEO 新加坡團隊開發的“停靠點”概念,旨在幫助老年人和行動緩慢群體在繁忙的都市中找到歇腳的地方。就像在十字路口這類城市中常見的停靠點設置一些類似拐杖的設施, 供老人在路上獲得片刻休息,在等紅綠燈或找公交系統的時候,他們也可以把購物袋掛在停靠點上。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設計能在解決老齡化相關挑戰上發揮積極強大的作用,不僅滿足用戶的情感及功能需求, 而且能滿足企業的商業需求。
《瞭望東方周刊》:工業設計行業未來的模式會是怎樣的?很多中國設計公司正向整個鏈條延伸,包括營銷等等,你如何看這些趨勢?
黃智恒:對于中國的工業設計行業來說, 我希望設計思維的應用可以超越外觀、功能、可用性、生產及營銷本身,來幫助解決社會面臨的一些系統性挑戰,比如教育、健康和環境。
這絕不是空想,IDEO的發展歷程就是最好的證明:從最初一家開創世界諸多第一款產品的工業設計公司,到如今運用設計來幫助企業和組織探尋核心問題,開創價值新領地——我們積極幫助應對埃博拉病毒;推動像The North Face這樣的全球知名品牌深入中國市場;幫助美的電器等企業勾勒新的未來愿景,并為新西蘭航空打造更卓越的空乘體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