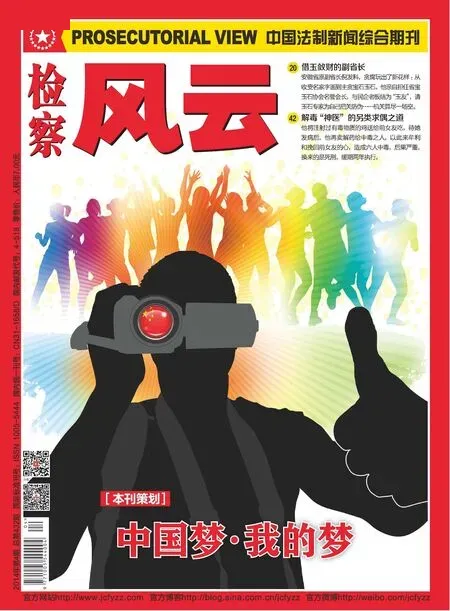繁體字復興之爭
文/胡潔人
繁體字復興之爭
文/胡潔人
自中國大陸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推行簡體字以來,恢復繁體字的聲音一直存在。廢繁用簡還是廢簡復繁,大家對此莫衷一是。無論是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提出恢復繁體字,還是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在兩會正式遞交有關繁體字的提案,或是馬英九先生倡導“識繁書簡”,都讓人們爭論不休,形成所謂“繁簡之爭”。究竟簡體字的歷史如何?為何現在有人提倡重新使用繁體字?繁體字復興又有何意義?
漢字簡化運動逾時30年
中文字體經歷了上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國古代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最初是甲骨文,筆畫粗細大致相同,并且用圖畫來表達事物。文字的筆勢(筆畫的形態)一直在發生著變化,主要的趨勢是筆畫由圓變方,圖畫感減少,符號性增強。漢字的字體主要分為古文字(商代至秦代,主要字體有:甲骨文、金文、六國古文、大篆、小篆)和今文字(漢代至現代,主要字體有:隸書、草書、楷書、行書)。
漢字與文化的關系非常密切,無論是其內部結構還是外部形體,都反映著它所依存的民族文化。從漢字的內部來說,漢字構意反映著漢民族的文化認識,漢字構意變化的背后是其所依存的文化內容的變化。從外部來說,社會文化事件往往成為漢字字體演變的推動力。中國漢字的每個字都蘊涵著特定含義,每個字都是一個生命,它的筆畫不能隨便改動,一改動意義就變了。
中國漢字以往都是繁體的,又稱正體字,為何到現代會成為簡體字?這是何時開始,由誰提倡的呢?當今的簡化字是現代中文的一種標準化寫法,主要由傳承字以及1950年代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在中國大陸地區推行的簡化字所組成。
追溯其歷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1952年2月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收集民間及民國以來主張漢字簡化的學者們之建議,于1954年底提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并于1955年2月公布于《人民日報》。7月,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由董必武為主委,郭沫若及作家老舍都是該會成員。該會于1956年1月28日通過簡化字515字及簡化偏旁54個。在1964年國務院又公告了《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是352個不作偏旁使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類推的1754字,共2236字,這就是今天通行大陸的簡體字。
應該說,推廣簡化字在建國初期對文化的普及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解放初期,我國的文盲占全國人口的80%。用繁體字掃盲十分困難,學來學去,認識的還是那幾個筆畫少的字。農民說:“政府年年辦冬學,我們年年從頭學。”這種現象直到推行簡化字后才有了改變。1964年,我國在進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13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漢字簡化對掃除文盲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1967年-1969年文化大革命火熱時期,各地方紅衛兵都曾推出不同程度過分簡化的字體,“文革”后明令禁止使用。到了1977年,文化大革命剛結束,隨即公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的草案。1986年由“國務院”廢止“二簡方案”。同年,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組成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而且和文化部、教育部同時發表“關于簡化字的聯合通知”,一致表示: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應當保持穩定,以利應用。至此,大陸漢字簡化運動暫告一段落。
書寫快速VS文化傳承
中國在1971年進入聯合國后,就全面推動中文簡體字,幾乎停止使用繁體字。聯合國有關一個國家使用的語言文字相關條例也規定,所有社區語言文字和語言文字來源國所使用的現代語言,應保持一致。目前繁體字主要用于臺灣、香港、澳門和北美的華人圈中,使用人數約為3000多萬。簡體字用于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東南亞的華人小區,使用人數超過13億。
另外,像日本、韓國原也有一些漢字,近年已陸續出現簡體字。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差異就在于,一個漢字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形體,這幾個形體筆畫多的叫繁體字,筆畫少的叫簡體字。那么究竟是繁體字好還是簡體字好呢?
贊成漢字簡化的學者認為,簡體字令部首簡化,書寫快速,字體清晰,保持結構,和原字前后連貫性較高,是相當不錯的簡化方法。支持繁體字的一派則認為,簡體字雖然書寫起來沒有那么多筆畫,看似簡單,但是實際上卻從很大程度上丟失了漢字的形體所表現出來的內涵和意義。
韓國學者張喜久先生認為,中國簡化文字筆畫,在跟上時代潮流和提高文字使用效率方面,確實取得了成功;但另一方面,丟掉了原來的繁體字,使現代人對中國古籍的認知能力大大削弱,這不能不說是個極大損失。臺灣也有學者認為,簡化字雖然方便快捷,但會阻礙文化的傳承,文字簡化不可一刀切,簡化字若成單一標準,將使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出現斷層。而繁體字像一條紐帶一樣連接了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是語言的“活化石”,文脈嚴謹,比較清晰地體現了造字原理,既便于現實應用,又便于歷史研究,不應該摒棄。
反對將漢字簡化的人們常常從傳統文化角度去闡釋簡化的弊端:比如把工廠的“廠”字改成“廠”字,結果現在大陸國營的“廠”真的大多倒閉,很多人下崗,什么都沒有了。“車輪”的“輪”改成“輪”,人字下面加上“匕首”,所以大陸車禍比同樣使用漢字的香港、臺灣多得多。把“愛”改為“愛”,沒有了“心”,使人們不再用心去愛了。又如“義”字,上面是個“羊”,羊溫馴又善良,這么吉祥美好的東西,正好用來祭祀天地神明當供品。簡體的“義”,一個大叉叉,再加上斜斜的一點,叉叉已經不是好東西,再加上三畫都是斜的,真是邪之又邪。所以現在還有幾個人有正義和信義?人人爭發不義之財,處處驚曝貪污丑聞!諸如此類雖帶有點迷信色彩的解釋,也反映了人們對簡化字缺失了某種文化傳承的不滿和批評。
特別地,當今社會處于信息時代,相比過往人們大大減少了手寫漢字的機會,取而代之的是計算機輸入文字,在這種情況下,對文字的傳承和文化的保留顯得更為重要。另一方面,繁體字多數是看而不是寫,因此在多為通過視覺辨認文字時,使用繁體字比簡體字更適合。臺灣學者杜學知在其《漢字三論》中指出,12畫的字比3畫至6畫的字更容易學習,而14畫至19畫的漢字最容易學習。這說明,繁體字比簡體字更容易學,這雖是一家之說,但值得我們研究。
別用錯誤手段改正錯誤
近年來,社會上有學者開始提出要恢復繁體字的呼聲,引發正反兩方的爭論。反對者認為繁體字太難寫,也不好記,恢復繁體字就是開歷史的倒車。而且,簡化的字體有利于中國和鄰邦的交流合作,有利于外國人學習漢字,也有利于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然而也有很多贊成的聲音,批評簡化漢字的步伐走得太急。他們認為,繁體字是中國文化的根,知曉繁體字,就是知曉中國漢字的由來、知曉中國文化的由來。而漢字的簡化雖是一種進步的表現,但同時也造成了中國文化的一種隔斷。其次,漢字所包含的東方思維方式——具象、隱喻(象征)和會意(指事),是中國文化及其傳承的核心。這種思維形態被熔鑄在漢字里,令其成為種族靈魂的載體。
其實,膠著于哪種字體更加優秀并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和意義。有人擔心的是,恢復繁體字是否在“試圖用錯誤的手段改正錯誤”。中青報記者張偉指出:“用粗暴的方式推行改革,用激烈而不是漸進的方式改造文化乃至社會,是這個錯誤的核心之處。正是在這種邏輯的指導下,50多年前,在我國大部分地區,通行的繁體字系統被摧毀,現行的簡化字取而代之。用同樣簡單和激進的方式,將一個社會已經習慣的文字全盤否定——這樣的做法,和50多年前并沒有分別。”
確實,對于幾十年開展簡體字教育和使用的中國大陸,要復興繁體字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朱大可在《文化復蘇當從漢字起步》中提出要恢復繁體字對于中國文明和文化的“密碼”作用,結合現狀提出三點:
一、倡導繁簡共存,公共空間與字典,輸入法采用繁簡加漢語拼音;
二、小學教育開始“書簡認繁”,大學部分專業掌握兩種書寫;
三、重申簡化字方案,對錯誤簡化局部修正,但在漢語教學和各種文字標識中可以更多地實行簡繁并用,讓人們做到識繁用簡,是大有好處的。
北大百年校慶時,饒宗頤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國當前應有“文藝復興”。他的意思是中國要發展,只靠經濟不行,還應有新的“文化復興”。“文化復興”不等同于否定現在,也不是重復歷史,而是要以當下的視野對傳統文化作新的詮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是,任何一種文明的發展都是有周期性的,而中華文化,當前也到了一個需要向前推進的新周期。真正意義上的“復興”是核心倫理觀、價值觀的弘揚,這也是文化軟實力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別是在今天,當社會出現某種意義上道德迷失的時候,這更是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今天,中國國力大幅度提升,但怎樣來構建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比較好的辦法就是從傳統優秀文化中提煉出最精粹、影響力最大、接受程度最廣的倫理道德觀念,并加以發揚光大,而文字就是很好的切入點。
編輯:鄭賓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