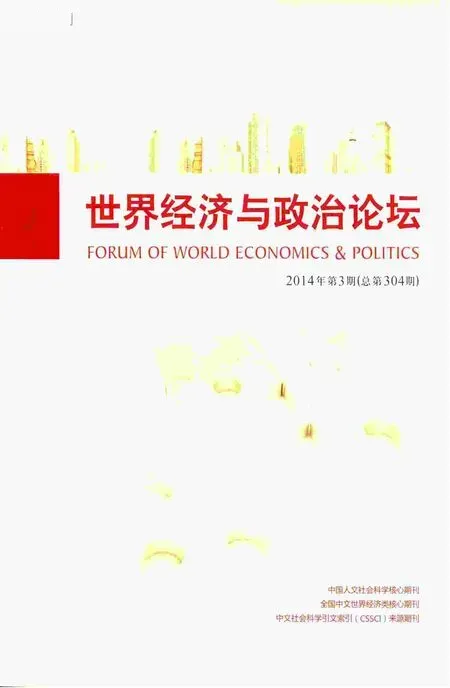從同化政策到尊重差異——美國印第安人政策演變的思考
張 駿
美國印第安人在美國西進運動和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遭受剝奪限制及其爭取自治權的歷史也是美國構建白人文化霸權和建設多元文化社會的歷史。本文中的文化既包括人們外顯的生產生活方式及其載體,也包括內在的思想觀念。文化的沖突也是異質文化在影響力和領導力上的較量,不僅涉及文化資源吸引力的傳播,也涉及思想觀念和制度的對抗。本文擬簡要回顧19和20世紀美國印第安人政策的發展,分析白人文化和印第安文化沖突的實質,及其對協調國家內部族群關系和處理不同民族國家關系的啟示。
一、19世紀的美國印第安人政策
“印第安人問題”不僅涉及剛剛誕生的美國社會的政治穩定,也是推進西部開發的經濟問題。因此,這一百年間美國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積極服務于維護邊疆的穩定,創造一個安全的政治環境,同時在軍事、經濟的優勢下,軟硬兼施積極推進印第安部落的“文明開化”,以實現文化的征服。總體看,強制同化是19世紀美國政府解決“印第安人問題”的主導政策。
政治上,聯邦政府承認印第安部落的主權地位,談判、締約是聯邦政府解決與印第安部落糾紛和沖突的主要手段。早期邦聯國會通過的《西北法令》中就明文規定,在對印第安人交往中應守誠信之道;不經印第安人同意,不得奪取其土地和財產;不得隨意侵犯印第安人的財產、權利和自由;應制定公正、人道的法律,防止對印第安人的虐待,努力保持與印第安人的和平與友誼。①Henry Steel Commager ed.,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NY:Meredith Corporation,1973,p.129.經修訂后,這一法案在聯邦政府第一屆國會上又得到通過。《美國憲法》中則將對印第安部落的貿易管理權與對外國、州與州之間的貿易管理權并列,統一歸屬國會,在法律上確認了印第安部落作為美國以外的主權實體地位。西進運動中,印第安部落土地的流失絕大部分都是通過締約出讓完成的,條約的簽署意味著部落的一部分或全部土地及主權的出讓,而聯邦政府的條約義務則是保護部落的安全,維護部落成員的利益。1830年代實施遷移政策和設立印第安領地、1850年后開始的保留地政策在形式上都基本得到部落的同意,通過雙邊條約完成,而條約背后往往伴隨著利誘、欺詐甚至暴力。但是伴隨國家實力的增長以及白人對部落土地和礦藏資源的無限覬覦,美國政府相應對保留地加以調整和改組乃至撤銷,并頒布法令中止印第安部落與美國政府的締約關系,實施保留地份地分配制,鼓勵定居和開發。最終,在19世紀末美國政府正式宣布邊疆消失,美國向西開拓殖民的時代結束時,也是部落的獨立和自主權被剝奪殆盡之時。
經濟上,鼓勵印第安人擺脫傳統生活方式,學習白人定居生產,實現經濟的自給自足是聯邦政府一貫目標。為此,通過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美國政府對于保留地內的部落以培訓和配給形式提供援助。而早在18世紀末,為促進和規范印第安部落與白人的貿易往來,聯邦政府曾依據國會1796年通過的《貿易和往來法令》(先后在1799和1802年經過修訂)在印第安人中建立起由國家經營的印第安人貿易商行系統。1834年又重新通過類似法令,但最終都因管理不力不敵私營公司的競爭先后告敗。而印第安人滿足于傳統生產方式,習慣用獸皮換取烈酒、火藥,也往往在白人蠱惑下用土地進行交易。在邊疆不斷推進的紛爭中,通過各種條約、法令,美國政府未能改變印第安人的經濟生活模式,事實上促成了印第安部落的大片土地易主白人。
文化上,同化始終是這個世紀美國政府針對土著居民一以貫之的政策。杰弗遜等老一輩領袖就真誠相信通過傳教士和文明教化可以同化印第安人,并積極推動幫助印第安人學習定居和農耕,成為美國農民。但即便杰弗遜這樣富于人道理想的人也曾表示,有必要把頑固不化的印第安人向西驅逐。①Richard A.Bartlett,The New Country,A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1776-189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31.美國政府在與印第安部落簽署的條約中往往加入學習白人生活方式的條款。②Garrick A.Bailey,Changes in Osage Social Organization:1673-1903,Oregon University,1973,p.68.但是否接受這種同化最初完全是自治的印第安部落的自主選擇。1850年后,通過實施保留地制度,美國政府公開而系統地展開了對印第安人的強制同化和改造。對于在印第安部落中組織傳教,開辦學校的宗教團體,政府還贈予土地加以鼓勵。在保留地內實施“美國化”改造的措施不僅包括強制青少年接受白人教育、禁止印第安人宗教信仰、強制學習白人的定居生產方式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造,而且還輔以土地制度改革以期加速從根本上的同化。拒絕遷居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或部落則會受到聯邦軍隊的清剿。保留地內不予合作者則被扣發保留地配給,甚至被處監禁。如1880年頒布的《印第安人學校規則》規定,教會和政府開辦的學校一律用英語教學,禁用印第安語,禁止印第安傳統服飾和發式,如有違反則停止政府的撥款。著名的卡萊爾印第安兒童寄宿學校的辦學口號就是“消滅印第安人,造就一個新人”。③“Kill the Indian in him and save the man,”See Wayne Moquin,et al.,ed.,Great Document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New York,1973.p.110.到1900年,保留地內外各種印第安人學校達307所,在校生達21 568人,約占當時印第安總人口的1/9。④Francis P.Prucha,The Great Father: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American Indians,Nebraska University Press,1984,p.816.按1887年通過的《道斯法案》,通過對部落土地實行私有化份地分配制,打破傳統的部落集體生活方式,強制印第安人接受土地私有制和經濟獨立,聯邦政府計劃在25年內將印第安人一舉改造為定居的農民。
盡管美國政府竭力推進同化政策,一些印第安部落甚至在西遷和抵抗白人同化過程中瀕于滅絕,但“印第安人問題”沒有消失。作為一個整體看,美國印第安文化傳統在白人文化的殖民主義征服中飽受壓制和剝奪。19世紀美國白人社會發展的每一頁歷史都是以犧牲印第安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寫就的。
二、20世紀的美國印第安人政策
進入20世紀,美國社會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開始反思社會公正、民權及社會經濟和政府改革問題。尤其是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社會主流觀念逐步向包容和尊重差異,接納并倡導文化多元主義發展。鼓勵多元,倡導自決成為印第安人和其他社會各界的共同呼聲。
政治上,20世紀是印第安人開始真正介入美國社會的時代。19世紀末的一系列聯邦法案打破部落制度、剝奪印第安部落主權后,印第安人從美國體系之外的特殊族群置身為美國政府的監護對象。為加速對印第安人的美國化改造,國會于1924年通過《美國印第安人公民權法》,授予美國境內全體印第安人以美國公民資格。但公民權不僅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公民義務。在許多州,他們并沒有獲得相應的選舉資格。1965年,國會又通過《投票權利法》,從法律上來保障包括印第安人、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的選舉權。但脫離印第安人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要求,空談公民權無法根本解決印第安人問題。20世紀美國印第安人政策的特征在于突破文化差異的阻隔與強制同化要求的狹隘。
在保留地制度去留問題上的反復演繹了美國印第安人政策從強制同化向開放自決的歷史轉折。印第安人保留地土地改革失敗后,美國印第安人政策經歷了恢復保留地—終止保留地—重新恢復保留地的變化。1934年,美國國會通過《印第安人重組法》,停止份地分配,恢復部落制,幫助印第安部落按白人的模式重建部落政府。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針對白人和聯邦政府背信違約而組織的印第安人“訴訟運動”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政治思潮影響下,聯邦政府于1953年實施了終止政策,廢除保留地,解除對大批印第安部落地位的認可。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和多元文化潮流的影響下,印第安人的自決成為印第安部落和聯邦政府印第安人政策改革的共識。1968年通過的《印第安人民權法》,恢復保留地,擴大了保留地內印第安人的權利,對印第安人擬就的各部落法律予以承認。此前一批被解除認可的部落地位得到恢復,而且保留地印第安人的自決權得到承認。截至20世紀末,歷屆美國總統都先后公開支持印第安人自決。目前,美國政府承認的印第安人部落已有564個。各部落的自決權體現在對保留地的自治權上,包括對部落成員行使刑事和民事訴訟等職能。盡管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仍待改善,通過自決自治,印第安人的政治權利的行使無疑達到了歷史新水平。
經濟上看,19世紀末開始實施的保留地土地制度改革沒有給得到土地的印第安人帶來經濟獨立,許多人因無意農耕而出租土地。即便國會在1906年通過《1887年法案修正案》,對部落成員無力開發的份地延長托管期,但白人土地投機商最終總能設法將大片份地據為己有。20世紀50年代,作為撤銷聯邦政府對保留地服務計劃的一部分,聯邦政府推行了“印第安人城市化”政策,即將保留地貧困印第安人重新安置,使其成為城市居民。1956年國會又通過法案規定為定居城市的印第安人提供職業培訓,幫助他們實現獨立、適應城市、融入白人社會。與此同時,在終止政策期間,當初保留地的聯邦機構“經濟事務辦公室”工作改由印第安人具體參與;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恢復保留地和部落制,鼓勵印第安人自覺自治的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印第安人獨立自主改善經濟生活的積極性。
文化上,20世紀的美國印第安人生活的改觀首先從印第安人教育政策的改革開始。根據1926年對印第安人寄宿學校進行的一項調查,1928年出版了《梅利亞姆報告》。報告指出,印第安人教育的當務之急在于改變政府的態度。以往的教育理念是把印第安兒童從家庭環境中剝離出來,而現代教育觀念應該是在有家庭氛圍的自然環境中培養人。報告認為,印第安寄宿學校扼殺了學生的創造性和獨立性。此后,聯邦政府開始關注社區學校和美國印第安人的文化生活。①Joel Spring,The American School:1642-2000,Boston:McGraw-Hill,2001,p.176.如1934年通過的《印第安人重組法》撤銷了對印第安人使用傳統語言、信仰傳統宗教的禁令。1968年,聯邦政府頒布的《雙語教育法》首次承認英語以外的其他少數族裔的語言在公立學校擁有合法地位,把包括印第安人在內的少數族裔爭取教育機會平等的努力轉變為了法律。到20世紀末,先后通過1972年的《印第安人教育法》、1975年的《印第安人自決和教育援助法案》、1978年的《美國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1994年部落自治法》等一系列法案,印第安人文化生活的自決權得到鼓勵和保護。
20世紀,美國印第安人政策雖然充滿矛盾和反復,但總體上趨向尊重差異,開始更多考慮印第安人的利益與實際,反映了美國社會多元化發展的現實要求。
三、強制同化政策和尊重差異政策的原因及影響
強制同化所以成為19世紀美國印第安人政策主導原則,原因在于印第安人文化與白人文化對于自由理解的差異以及對于文化差異的不同態度。
首先,自由在兩種文化中有不同的定義。根據17世紀英國人對自由的傳統理解,“自由意味著正式、具體的特權,如自治權、免除服役和稅收權,或王室賦予某些群體或個體從事特定行業的權利、王室詔令或王室的購買等”①[美]埃里克·方納:《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王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 22-23頁。。帶著這樣一種傳統來到北美,殖民地開拓者通過獨立革命成為這片大陸的主人——美國人。對于美國人,自由不再是一套具體的權利,也不再是某個特定條件下的一部分人的特權,而是不受先決條件限制的普遍的權利。美國社會不斷向西擴張的進程成為美國自由和平等觀念的西進過程,但是對于持有獨特自由觀的印第安人,白人從一開始就排除了他們享有自己界定的自由平等權利的資格,用白人的游戲規則主導了北美的征服活動。努力堅持自己的傳統觀念和權利的印第安人盡管頑強勇敢,但最終卻無法遏止白人西進的狂熱。在白人看來,印第安人是沒有“家長權”、“族長權”和“法律”概念的“野蠻人”。正如“黑人被奴役到不能再奴役的地步,印第安人則被放任自由到極限”。印第安人的自由是一種“野蠻的獨立”,是“擺脫社會的一切羈絆,不受任何約束”。②[美]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71頁。顯然,印第安人具有截然不同于歐洲人的“自己的自由觀念”。或者說,“一定意義上,他們是過于自由了,以至于缺乏秩序與紀律這些歐洲人眼中的文明素質”。他們普遍認識到個人自由是受人奴役的對立面,但是更為注重“群體的自主和自決權,以及富于歸屬意義的責任感”。③[美]埃里克·方納:《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王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0頁。印第安人的自由植根于廣闊的草原、山林和季節性游牧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熱愛草原游牧生活,那里才有自由和幸福。一旦定居,注定衰弱死去”。他們熱愛“草原自由的風,自由的陽光。沒有遮攔、無拘無束”,為此甚至“寧愿死在那里,也不想活在院墻之內”。①Dee Brown,The American West,New York:Simon & Shuster,1995,p.112.美國印第安人與美國白人之間的沖突就源于不同的自由觀為基礎的價值觀念的分歧。
其次,面對文化差異,美國白人文化強勢突進,印第安文化招架乏力。有學者指出觀念的力量只有在與經濟和軍事實力相結合時才會產生實效。②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New York:Harper Touchbooks,pp.103-139.建國以后,白人文化或價值觀一直主導著聯邦政府與印第安部落的關系。遵循殖民地時期的傳統,最初聯邦政府與印第安人的關系主要通過彼此締結的條約、聯邦法令和最高法院就相關案件所做的判決加以明確。
一方面,通過發明“發現權原則”(Doctrine of Discovery),白人賦予自身剝奪土著權利的權力。雖然印第安人早于白人在北美大陸定居生活,但歐洲人普遍認為西班牙、法國、英國等在新大陸的探險和拓殖賦予了自身“發現權”,即白人享有發現并擁有新大陸土地的權利,而印第安人則僅僅享有占用土地的權利。由于印第安人世代保存其獨特的自然觀和價值觀,歐洲人堅持認為印第安人從來沒有真正改進和開發過他們居住的土地,因而并不真正擁有土地產權。盡管最初只是這片大陸上的移民,但借“發現”和“拓殖”之名,白人賦予自己自由開拓并成為主人的權力并對此堅信不疑。根據這一原則,美國人“承認印第安民族對其所擁有領土的合法權利,同時也承認入侵者購買領土的合法權利,從而免于擔心這些領土會賣給某個……敵對國家”③Warren I.Cohen,ed.:《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周桂銀、楊海光等譯),第 1、2 卷,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6頁。。這樣,印第安人對其領地的占有權利顯然必須讓位于美國西進移民的發現權以及白人通過締約或購買所獲土地的主權。正是以這種自我賦予的權力加之經濟、軍事上的優勢為基礎,美國人在印第安人問題上占據了居高臨下主導地位。此后,通過創造“顯然天命”論,西部擴張的邏輯成為美國社會謀求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理想的一部分。在偏見和懷疑中,印第安人被長期視為沒有開化的民族,缺乏享受公民權和自治權的能力和資格。隨著邊疆的逐步消失和白人社會的不斷擴張,當印第安人不再構成對白人移民和社會的威脅時,印第安人已經沒有選擇,只有接受被發現和教化的權利。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通過立法和司法對美國印第安人事務實施強制管理,包括聯邦土地政策和州及聯邦法院的判決。馬歇爾擔任首席大法官期間的三大判決清楚表明印第安人如何被“合法”剝奪了社會身份以及在這片世居土地上的自主權。1823年,“約翰遜訴麥金托什”案(Johnson v.M’Intosh,1823)的判決中,馬歇爾訴諸歐洲人創造并普遍認同的“發現權原則”。土著印第安人盡管占有居住的土地,但沒有處置權;發現賦予發現者排他的權利,土地最終所有權歸屬發現它的歐洲國家。印第安部落早于美國人生活在這片土地之上是不爭的事實,但根據該案判決,土地的最終產權屬于合眾國,土著居民被“合法地”剝奪了對土地的支配權。作為印第安部落的自治主權在殖民地時代曾受到英國國王和殖民地議會的承認,但美國建國后,部落的這種主權僅僅被視為部落處置內部事務的權力。1831年,“切羅基部落訴佐治亞州”(Cherokee Nation v.Georgia,1831)案判決中,馬歇爾訴諸歐洲文明賦予的傲慢與偏見,指出:切羅基部落不屬于國家,而是“國內附屬族群”(domestic dependant nations)。印第安部落領地是美國的一部分,印第安人既不是美國公民也不屬獨立的外國。對于美國人而言,印第安人因其獨特的部落自治和文化屬于未開化的異族,尚不具備白人社會的文明素養。在保護的名義下,聯邦政府當仁不讓地將印第安人置于被監護的地位。1832年,“伍斯特訴佐治亞州”案(Worcester v.Georgia,1832)判決,對印第安人的管轄權僅屬于聯邦政府。切羅基等印第安部落是受聯邦政府保護的獨立的政治共同體,合眾國政府承認它們在其領地范圍內擁有排他性的主權;但與印第安部落相關事務及其土地的管轄權屬于聯邦政府,不屬于州。①Henry Steele Commager ed.,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Meredith Corporation,1973,pp.256,259.這樣,在承認印第安部落獨立政治共同體地位同時,又剝奪了土著部落自決自主的獨立性。原本自由獨立的土著部落在這個世代居住的大陸上被置于一種尷尬境地——部落主權需要通過聯邦政府得以認可。
歸根結底,文化的沖突是不同民族不同觀念和選擇的沖突。19世紀,美國白人與印第安人的征服與反征服的斗爭揭示了白人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本質。“強制性同化乃是種族對抗的繼續”。①李劍鳴:《美國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與作用》,載《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73頁。無視文化差異,瓦解部落制度代之以所謂文明的體制,與其說帶給部落成員以權利,不如說是為白人獲取更大的利益。
進入20世紀,印第安人要求自治的斗爭與美國社會尊重差異,倡導多元的主流觀念,共同促進了文化多元主義的發展。20世紀美國印第安人政策的變革就是從聯邦政府和社會大眾兩方面得到積極推動的。
在19世紀的急速擴張和發展中,美國白人社會與印第安人社會的關系為何從最初相遇時的友好演變為兩種文化之間、兩個政府之間和兩個民族之間的激烈沖突,無法擺脫懷疑、貪婪、戰爭和犧牲呢?經過兩個世紀的沖突、磨合,標榜進步的白人文化與被視為落后的印第安文化彼此依然涇渭分明。面對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帶來的社會危機,是否白人文化真正能夠代表人類進步的方向?或是印第安文化能夠給予人類更多反思?站在20世紀的門口,美國社會不得不反思選擇,并采取行動。
早在1881年,海倫·杰克遜就曾發表《百年恥辱》一書,揭露政府對于土著印第安人的虐待,激起人們改革印第安人政策的呼聲。據說,她曾特意將該書寄送國會議員人手一冊。她在書中直言:“欺騙、掠奪、背信棄義——政府對于印第安人的這些行徑必須終止。除此之外,還需要加以制止的就是拒絕給予印第安人財產權、‘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權利’法律上的保護。”②Noy,Gary,Distant Horizon,Documents from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West,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p.300.海斯總統的內務部長卡爾·舒爾茨在同一年就“印第安人的困境”發表演講。他指出,聯邦政府與印第安人的關系史是一部背棄協議、不公正戰爭和殘酷掠奪的歷史;政府應該對多數與印第安人的戰爭負全責,并呼吁政府實施開明的政策。1970年,尼克松也曾呼吁“印第安人的未來取決于他們的行動和決定”。美國社會大眾趨向的共識是:印第安人事務的管理權在于印第安人自己。③[美]J.艾捷爾編:《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趙一凡等譯),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529頁。1831年,土著美國人撰寫的第一本具有影響力的自傳《森林之子》(A Son of Forest)中,作者寫道:“印第安人想要什么?你只需要睜開眼看看那些為他們制定的不公正的法律,然后就會說‘他們想要我想要的東西’。”“如果白人行為舉止能夠像文明人一樣,對每個人給予應有的尊重,事情會比現在好得多。”①[美]埃里克·方納:《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王希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77頁。當印第安部落領地不斷遭受白人的占據,當聯邦政府通過復制白人的社會管理和文化模式,強制印第安部落社會的美國化,印第安人只有一種未來,即美國白人所控制的未來。從部落被剝奪土地支配權、司法權、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權到呼吁部落傳統和文化的復興,印第安人在經濟、政治自由的雙重限制和打擊下最終學會認識并改變自身,認識并積極加入社會變革。從被動地拒絕和回避社會變革發展的挑戰到主動參與到美國體制之中,印第安人通過人權運動、印第安“紅色權利運動”以及爭取自治運動投入捍衛部落自決權活動中,加強了族裔認同和凝聚力。通過參與、合作去贏得自己的未來無疑是歷史的選擇,也是理性的選擇。正是印第安人自身的覺醒以及其他社會改革者們的聲討和行動推動了美國社會主流觀念的變化,并主導了20世紀印第安人政策走向開放多元的變革。
四、美國印第安人政策演變的啟示
根據美國德裔猶太哲學教授霍拉斯·卡倫的見解,任何用“美國化”、“熔爐論”和“盎格魯–撒克遜化”來描述美國社會模式或理想未來的做法都是不妥的,因為寬容差異本身就是“美國思想”的一部分。1924年,他創造了“文化多元主義”一詞,用來描述“一個推崇和欣賞,而不是企圖壓制族裔多元化的社會”。事實上,包括魯斯·本尼迪克特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無論是種族優越論,或是按照由“原始”到“文明”的等級定式來劃分某個社會或種族的想法,都是毫無科學根據的。②[美]埃里克·方納:《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王希譯),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009頁。美國社會白人和印第安人的關系發展證明,文化沖突往往始于對異質文化選擇權的剝奪,文化的優劣高下之分源于種族偏見和利益紛爭。
由于新舊世界文明發展的時空差異,北美大陸的開拓以及美國人西進拓殖過程成為兩個發展階段的較量,并演變為一種觀念對另一種觀念的征服,代表了白人所謂“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后”的二元對立。在長期較量中,白人不僅訴諸經濟、軍事的力量,還訴諸觀念的力量。通過民族國家意識、文明進步理想賦予的神圣感和使命感,邊疆的推進和白人文化的霸權獲得了某種正當性。盡管印第安部落首領悲憤的抗議和浴血奮戰始終伴隨著美國社會擴張的進程,由于北美印第安部落彼此不同、利益分歧,維護部落傳統的斗爭往往難以通過長期的部落聯盟得到維持。而與印第安文化的弱勢相對,白人的價值觀是始終主導這個年輕的民族國家成長的主流價值觀。殖民地時期獨立自治的生產生活實踐以及獨立建國后生存和發展的時代環境逐步塑造了美國文化的特性,即對于發現創造的熱情、教育的理想和自治的傳統。①[美]克拉克·威斯勒:《人與文化》(錢崗南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8-15頁。而部落社會自由不羈、簡樸自然的生產生活習俗塑造了印第安文化特性,即信仰自然和諧的生產方式、珍視部落集體生活的傳統。文化交流的意義在于破除禁錮,取長補短。在偏見和封閉條件下的文化往來必然釀成悲劇和苦難,在平等開放條件下的文化往來則有助于不同族群和國家的和諧進步。美國白人文化與印第安人文化從同化、沖突走向尊重差異、多元共存的發展無疑可以為多元文化社會和國家處理族群關系和文化沖突提供一點啟示。
[1]錢滿素.美國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美]托馬斯·帕特森.美國政治文化.顧肅、呂建高,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3][美]丹尼爾·布爾斯廷.美國人:開拓歷程.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4][美]丹尼爾·布爾斯廷.美國人:建國歷程.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
[5]李劍鳴.美國的奠基時代 1585-1775.美國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美]詹姆斯·布賴斯.現代民主政體.張慰慈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7]李劍鳴.文化接觸與美國印第安人社會文化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1994(3):157-174
[8]Nye J S.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90.
[9]Morris,R B 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New York,1953.
[10]Morison S E,Commager H S,Leuchtenburg W E.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Vol. One.Six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69.
[11]Nichols R F.History in a Self-Governing Cultur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7,72(2).
[12]Beard C A,Beard M.A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Doubleday,Doran& Company,1944.
[13] Nye J.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4]Blake N M.A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Inc.,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