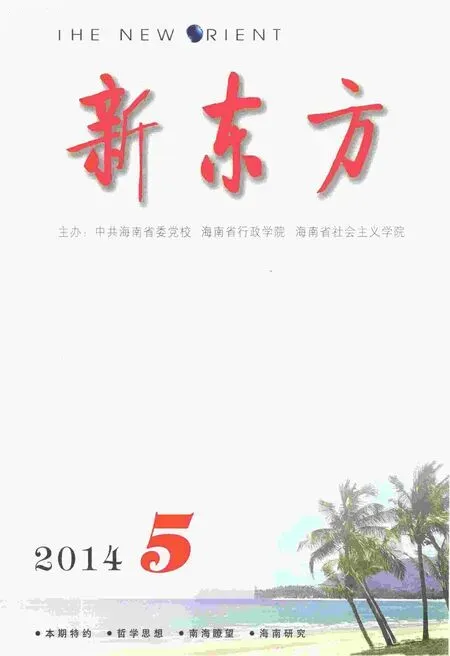辛派詞人學蘇及其詞的“蘇味”
(作者系海南科技職業學院、海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導)
關于南宋詞人學蘇即蘇軾,后人認為從南渡詞人開始,葉夢得、朱敦儒可為代表。學蘇說至辛派詞人更甚,尤其是被后人認為是辛派詞人領袖的辛棄疾,故這里對他們學蘇及詞的“蘇味”作一點探討。
一
南宋范開在《稼軒詞序》里有一番較全面的評價:“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非有意學坡也,自其發于所蓄者言之,則不能不坡若也。坡公嘗自言與其弟子由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且以為得于談笑之間而非勉強之所為。公之于詞亦然;茍不得之于嬉笑,則得之于行樂;不得之于行樂,則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際。揮毫未竟而客爭藏去。或閑中書石,興來寫地,亦或微吟而不錄,漫錄而焚稿,以故多散逸。是亦未嘗有作文之意,其于坡也,是以似之。雖然,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于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故其詞之為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無他,意不在于作詞,而其氣之所充,蓄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1]
范開所論的蘇軾與辛棄疾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認為辛棄疾在創作時與蘇軾一樣,情感積郁,故辛詞似蘇詞。但這一說法很讓人質疑。就兩宋詞人論,從北宋到南宋詞壇,發乎情感積郁的詞人何止蘇、辛,在蘇軾之后的何止辛棄疾,詞因情而生,或喜或愁,或樂或悲,人們為什么獨說辛棄疾呢?辛詞類蘇,關鍵是詞風,而不是創作的基本態度或方式。二是辛棄疾以“氣”為詞與蘇軾也有相似的地方,范開稱之為不能不同。這是為社會形勢的影響及二人不同的遭遇、襟懷決定的。蘇軾之“氣”體現為在北宋的一統江山之下,因宦海浮沉而生的憤激與曠達;辛棄疾之“氣”則是南宋江山淪陷,因報國無門而生的悲憤與強烈的愛國情懷。二人都不主故常,創作走向則不盡相同。因此,辛棄疾終究沒在蘇軾身后亦步亦趨。此外,人或就范開說的“其詞之為體”而稱辛詞為“稼軒體”,同時以范開比擬辛詞的“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為“稼軒體”的基本特征。這一特征相當朦朧,究其意只是表明辛詞長于變化,且變化可觀、風格多樣而已。
辛棄疾與蘇軾都深愛哲人莊子和詩人陶淵明。辛棄疾深知《莊子》,《哨遍·秋水觀》用莊子理論寫成,或說是隱括了莊子的篇章。全詞如下:
蝸角斗爭,左觸右蠻,一戰連千里。君試思、方寸此心微,總虛空、并包無際。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從來天地一稊米。嗟大小相形,鳩鵬自樂,之二蟲又何知。記跖行仁義孔丘非,更殤樂長年老彭悲。炎鼠論寒,冰蠶語熱,定誰同異。 噫,貴賤隨時。連城才換一羊皮。誰與齊萬物,莊周吾夢見之。正商略遺篇,翩然顧笑,空堂夢覺題《秋水》。有客問洪河,百川灌雨,涇流不辨涯涘。于是焉河伯欣然喜,以天下之美盡在己。渺滄溟、望洋東視。逡巡向若驚嘆,謂我非逢子。大方達觀之家未免,長見悠然笑耳。此堂之水幾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
這首詞隱括了《莊子·則陽》的“觸蠻之爭”、《逍遙游》的“鵬鳩故事”、《秋水》“泰山毫末”之說、《盜跖》的跖與孔丘的故事、《齊物論》的莊周夢蝶、《秋水》的河伯與伯海若的對話等,世間萬千事物,果真是“炎鼠論寒,冰蠶語熱,定誰同異”。在詞的下闋中,他化用莊子《秋水》的河伯故事,張揚自己的才學。其理趣也本于莊子《秋水》。河伯先是欣然自喜水勢之大,然后見浩渺大海,則惘然自失,才知道自己的淺薄。辛棄疾以“空堂夢覺題《秋水》”與篇尾的“此堂之水幾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相照應,把空堂一曲清溪借《秋水》藝術化了,有想象與謀篇布局之妙。同詞牌的《哨遍·一壑自專》上闋說陶淵明躬耕田園兼及莊子,下闋的“會我已忘機更忘己,又何曾物我相視。非會濠梁遺意,要是吾非子。但教河伯、休慚海若,大小均為水耳”,又是莊子逍遙與齊物理論的化用。
辛棄疾在《水調歌頭·題永豐楊少游提點一枝堂》中寫道:“萬事幾時足,日月自西東。無窮宇宙,人是一粟太倉中。一葛一裘經歲,一缽一瓶終日,老子舊家風。更著一杯酒,夢覺大槐宮。記當年,嚇腐鼠,嘆冥鴻。衣冠神武門外,驚倒幾兒童。休說須彌芥子,看取鹍鵬斥鷃,小大若為同。君欲論齊物,須訪一枝翁。”雖說這里的“一缽一瓶”“須彌芥子”用佛教思想;“夢覺大槐宮”用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淳于棼夢為南柯太守,終感人生幻滅的故事;但“哧腐鼠”“看取鹍鵬斥鷃,小大若為同”等都化用莊子的寓言故事和理論,表明對名利的輕視和莊子式的“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逍遙游》)式的滿足。
不僅是辛棄疾,辛派詞人的干將陳亮也好莊,雖不及辛,卻也在《水調歌頭·和趙用錫》里用莊子語意,表現人生的不平。如其上闋寫道:“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鯤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旁邊笑,河漢一頭傾。”在這里,莊子《逍遙游》里的鯤鵬與斥鷃被賦予了深厚的政治意蘊,說是大鵬高飛九萬里,實際上只落得斥鷃哂笑。而“事業隨人品”及“萬事盡出汝書生”也只是慰人與自慰之詞。同時,陳亮表白的“雨過風生,也應百事隨緣”(《新荷葉·艷態還幽》),與莊子順應自然的思想相吻合,不是人生的積極兼濟,而是獨善的隨波逐流。之所以如此,根本還是對世俗及人生的通透認知。他曾說“問唐虞禹湯文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云鏟過?”(《洞仙歌·丁未壽朱元晦》)歷史的一幕幕走過之后,先圣前賢的功名在哪里,都若“浮云”,那么現實的人生追求意義何在呢?陳亮對于“功名”的否定,也是在否定或放棄自我意欲進取的人生。
辛棄疾深愛陶淵明及陶詩。他引陶淵明或陶詩入詞是很平常的事,曾隱括陶淵明的詩,如《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閣》《新荷葉·再題悠然閣》《聲聲慢·隱括淵明停云詩》等,不妨將《新荷葉·再題悠然閣》錄如下:
種豆南山,零落一頃為萁。歲晚淵明,也吟草盛苗稀。風流劃地,向尊前、采菊題詩。悠然忽見,此山正繞東籬。 千載襟期,高情想像當時。小閣橫空,朝來翠撲人衣。是中真趣,問騁懷、游目誰知。無心出岫,白云一片孤飛。
這首詞鄧廣銘疑作于慶元六年(1200),辛棄疾60歲。從它所敘的生活及表現的情緒,宜為辛棄疾晚年賦閑于江西鉛山的瓢泉所作。它隱括了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三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飲酒》其五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去來兮辭》的“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等,表明自己與陶淵明相同的生活趣味。而他的《鷓鴣天·晚歲躬耕不怨貧》序中說“讀淵明詩不能去手,戲作小詞以送之”,詞道:“晚歲躬耕不怨貧,只雞斗酒聚比鄰。都無晉宋之間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載后,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上闋是陶淵明生活與心態的描述,下闋則稱道陶淵明詩文的成就,仰慕陶淵明,希望自己像陶淵明那樣,“萬卷有時用,植杖且耘耔”(《水調歌頭·賦傅巖叟悠然閣》)。以讀書和躬耕悠閑度日。他還在《賀新郎·甚矣吾衰矣》的序言中說,“一日,獨坐停云,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仿佛淵明思親友意云。”這些都可見他內心與陶淵明的親近。更有甚者,是辛棄疾同樣作于瓢泉的《水龍吟·老來曾識淵明》,流露出對陶淵明的生活心向往之:
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覺來幽恨,停觴不御,欲歌還止。白發西風,折腰五斗,不應堪此。問北窗高臥,東籬自醉,應別有,歸來意。 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吾儕心事,古今長在,高山流水。富貴他年,直饒未免,也應無味。甚東山何事,當時也道,為蒼生起。
這首詞說自己老來曾識淵明,夢見陶淵明,說他仍凜然有生氣,是對陶淵明生活與精神的高度認同。但他說自己夢覺之后,深感頭發花白的陶淵明不當在秋風中為五斗米折腰。他用陶淵明說過的“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書》),“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結廬在人境》),說陶淵明之意在于歸耕田園。繼而以伯牙與鐘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暗喻自己是陶淵明的知音,對于富貴和“東山”即謝安功業都不以為意了。
二
蘇軾之好莊子和陶淵明,在他的詩文中屢見不鮮,難以盡言。這里可以從下面兩段文字來看。一是蘇轍說過:蘇軾“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2]1126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的散文與辭賦里,也體現在他的詩文與詞中。如蘇軾在《前赤壁賦》記述與客游于黃州赤壁之下,蘇軾說:“客亦知乎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所謂水與月盈虛的卒莫消長,在于萬物的變與不變,與莊子的萬物齊同論相一致。又如前面提到的《行香子·述懷》,那“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與莊子人生短暫、名利傷身的思想吻合。二是蘇軾自己說的:“我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后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2]1110這番陶詩的“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論,一向被視為對陶詩的經典評價,影響深遠。蘇軾好陶且和陶詩,從躬耕于黃州東坡開始,最后到海南儋州,完成了遍和陶詩的宿愿,陶詩也與他相伴隨。當然,他的和陶詩與隱括詩或隱括詞不一樣,所和之作用陶詩之題、步陶詩之韻,而其內容多出己意,成為不同于陶詩的新作。這類似于漢樂府之后,詩人們用樂府舊題寫時事抒己情。隱括之作則多保留或多用原作之言而寄己意于其間,原作之意與詞人之意是同在的。就詞言,蘇軾以《哨遍》隱括過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這在前面已言及。他又在黃州所寫的《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的序言里說自己躬耕東坡,仿佛是陶淵明的斜川之游,其開篇寫道:“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這里雖然小有牢騷,但他對陶淵明生活與趣味的認同感是很強的。而黃庭堅為他的和陶詩作跋時也說:“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詩》)
辛棄疾和蘇軾一樣受莊子和陶淵明的影響,重要的還是體現在精神氣質上。他們都寫過以“歸去來兮”開頭的詞,蘇軾的《滿庭芳·歸去來兮》寫于元豐七年,他正要結束在黃州的謫居生活去汝州。詞中說他要歸于“岷峨”即自己的家鄉,有朋友“相勸老東坡”,不希望他離開黃州,他自己對黃州也依戀難舍。次年他到南都,隨之受命去了陽羨,于是依前韻填了另一首《滿庭芳》,仍以“歸去來兮”開頭。詞中有“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用戰國馮瑗的故事委婉訴說人生的失意,卻從愁苦中走出來,以游仙表現自己超脫世俗,追尋紅塵外的生活。所謂“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縷掛煙蓑”,是以調侃的口吻說明人間不及天上,俗人不及神仙,批評俗世人生。而辛棄疾則有《行香子·歸去來兮》,其詞寫道:
歸去來兮,行樂休遲,命由天、富貴何時。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 名利奔馳,寵辱驚疑。舊家時、都有些兒。而今老矣,識破關機。算不如閑,不如醉,不如癡。
辛棄疾的“歸去來兮”與蘇軾同樣用了陶淵明“歸去來兮”的語意,他們不同于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里傾訴田園之趣及順應自然之樂。蘇軾以游仙說超脫塵世,辛棄疾仍然沉溺在嚴峻的現實中,人生認命,看破紅塵,不再熱衷名利寵辱。所謂的“不如閑,不如醉,不如癡”使人想起蘇軾在黃州寫的戲謔詩《洗兒戲作》,人生諸多的不如意,聰明還不及愚笨的好。辛棄疾的“閑、醉、癡”之說,與蘇軾這首小詩之意相吻合。且蘇軾有《行香子·過七里瀨》:“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鑒,鷺點煙汀。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但遠山長,云山亂,曉山青。”這首詞作于熙寧六年(1073),他路過浙江桐廬縣南錢塘江的七里瀨,舟行江中,見眼前景象,想到曾在此垂釣的嚴子陵以及山色依舊,說出“君臣一夢,今古空名”的話來,也是把塵世看得很透的。
辛派詞人中,并非唯獨辛棄疾懷有這樣的脫世情懷,劉過、劉克莊等人亦然。不妨看劉過的《念奴嬌·留別辛稼軒》:
知音者少,算乾坤許大,著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名相誤,十年枉費辛苦。 不是奏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之語。我自匆忙天未許,贏得衣裾塵土。白璧追歡,黃金買笑,付與君為主。莼鱸江上,浩然明日歸去。
他引辛棄疾為知音,雖說人生趣味的表達有異,但也曾想在乾坤中有安身之處,尋求功成身退,好夢醒來,方知“虛名相誤,十年枉費辛苦”,于是本有兼濟天下之心的劉過表示當“白璧追歡,黃金買笑”,與柳永在落第后說的“且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黃金榜上》)相通。他也說要“歸去”,所謂“莼鱸江上,浩然明日歸去”,暗用西晉張翰因秋風起而思家鄉莼菜和鱸魚,慨嘆人生貴在適志而命駕還鄉的故事,表示要棄名利而去了。他在生活上比辛棄疾恣意任性,如《水調歌頭·春事能幾許》的“人生行樂,且須痛飲莫辭杯。坐則高談風月,醉則恣眠芳草,醒后亦佳哉”。最終還是依戀田園,與辛棄疾、蘇軾也是同道了。
又如劉克莊,他雖然最后官運亨通,但內心還是充滿了矛盾,曾在《念奴嬌·菊》里寫道:“老夫白首,尚兒嬉,廢圃一番料理。餐飲落英并墜露,重把《離騷》拈起。……尚友靈均,定交元亮,結好天隨子。籬邊坡下,一杯聊泛霜蕊。”他這里提及三個人:靈均即屈原、元亮即陶淵明、天隨子即陸龜蒙,彰顯了思想深處的矛盾所在。所謂“尚友靈均”的與屈原交友,還說到屈原的《離騷》。《離騷》是屈原遭讒罹憂之辭,是屈原愛國精神與高潔品格的集中體現。屈原不愿附合流俗,最后在郢都被秦兵攻破之后投江而死,這使劉克莊的“尚友靈均”別有政治的意蘊。不過,他有時從思念屈原中走出來,故有《滿江紅·端午》所吟詠的:“有累臣澤畔,感時惆悵。縱使菖蒲生九節,爭如白發長千丈。但浩然一笑獨醒人,空悲壯。”屈原在《漁父》里行吟澤畔,自稱舉世皆醉而吾獨醒,劉克莊的慨然笑之,使自己又遠離了屈原。而他說的“定交元亮”,是出自對陶淵明的喜愛,他常常流露這種情緒,如說“平生酷愛陶淵明”(《水龍吟·平生酷愛陶淵明》),“晚愛陶詩高妙”(《賀新郎·何必游嵩少》)。甚至說:“吾評晉士,不如歸去來子。”(《念奴嬌·太丘晚節》)所謂“歸去來子”即寫了《歸去來兮辭》的陶淵明。至于“結好天隨子”的天隨子是晚唐詩人陸龜蒙,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赍束書、茶灶、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3]。這番描述在劉克莊晚年寫的《解連環·甲子生日》里也有體現:“買只船兒,穩載取、筆床茶具。便蕓瓜、一生一世,勝侯萬戶。”他想過陸龜蒙那樣自然灑脫的田園生活,是陶淵明式的,也有莊子思想的影子。他愛說莊子的《齊物論》,所謂“老去愛持《齊物論》,誰管彭殤壽夭”(《賀新郎·憶昔俱年少》)。既然萬物齊同,長壽也罷,短命也罷,都是無所謂的。同時又笑屈原道:“殤子彭鏗誰壽夭,靈均漁父爭醉醒。向江天、極目羨禽魚,悠然哉。”(《滿江紅·著破青鞋》)。這里的“極目羨禽魚”,也用莊子典故,一則是逍遙游的大鵬,二則是快樂的濠水之魚,說明人生最好是悠然自得,沒有必要像屈原和漁父那樣去論說世人是醉還是醒。從這些來看,劉克莊在人生的終極意義上,是傾向于陶淵明和莊子的。
三
辛棄疾在紹興元年或二年(1190或1191)50歲或51歲時,用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韻填了三首《念奴嬌》,其一《念奴嬌·瓢泉酒酣,和東坡韻》如下:
倘來軒冕,問還是、今古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藥籠功名,酒壚身世,可惜蒙頭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之杰。 堪嘆黃菊凋零,孤標應也有,梅花爭發。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鴻明滅。世事從教,浮云來去,枉了沖冠發。故人何在,長歌應伴殘月。
辛棄疾步蘇詞韻而為新詞。蘇軾在“赤壁懷古”中,以懷古敘說江山依舊、人事皆非,并借周公瑾大敗曹操事感慨自我人生漸老而功名未成,有難以言說的悲愴。而辛詞的首句“倘來軒冕”用《莊子·繕性》的“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者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莊子強調人生當順應自然,不因高官放縱心志,不因窮困附合流俗,方能有樂而無憂。他曾經做過滁州太守、江西提點刑獄,這時賦閑隱居瓢泉,不禁問古往今來的軒冕是何物,寓有濃郁的故國憂思和人生無奈。“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之杰”所表現的英雄豪氣還在,終究陷于人生浮云的喟嘆之中,其“故人何在,長歌應伴殘月”較之蘇軾的悲愴,卻消沉多了。其后,辛棄疾還有《水調歌頭·我志在寥廓》用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韻,詞前序說:“趙昌父七月望日用東坡韻敘太白、東坡事見寄,過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約。八月十四日,余臥病博山寺中,因用韻為謝,兼寄吳子似。”這序說明其創作緣由,詞則以夢的形式,狀游于天宮的生活,所謂“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間”用《楚辭·九歌·東君》的“援北斗兮酌桂漿”和韓愈《瀧吏篇》的“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的典故,固然是寄身于天宮,卻有以北斗酌酒的豪舉,不像蘇軾“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的輕盈。詞的下闋以鴻鵠高飛仿佛說有志獲騁,卻在欲重歌之際夢覺,想到人事終難全。“有美人可語,秋水隔嬋娟”。其“美人”之說,有屈原以“美人”喻君王之意,然“秋水伊人”的相思終有空間距離的阻隔。這里所說的辛步蘇韻之詞,辛詞的所思所想及情趣盡管與蘇軾有所不同,也是辛學蘇詞的明證。
在辛棄疾身后,許多人論詞者自覺將辛棄疾與蘇軾相比較,或說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論為詞。雖說蘇軾以文為詞也存在“論”的現象,但多為散文式的敘說,而不是散文式的論理。從蘇軾到辛棄疾詞風是不一樣的,明代王世貞說:“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極矣。”[4]所謂詞至辛棄疾而變,其實詞在南渡詞人那兒就發生了變化,辛棄疾詞體現出來的多重風格都可以在南渡詞人的詞中感受到。只是辛棄疾詞更多、更集中地表現了抗戰恢復主題以及自我慷慨悲憤的情懷。王世貞也說辛棄疾的詞源于蘇軾,又順勢涉及劉改之即劉過,主要是詞風的豪放。這基于蘇軾詞的兩點,一是他《江城子·密州出獵》表現出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英雄氣概,盡管它在蘇軾詞中甚少,終究是其詞的一種趨向。二是他《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里表現出來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曠達,以及對名利的淡泊或說超越塵俗的灑脫、對田園山林生活的向往。
辛詞的豪放,清代胡薇元稱之為“雄豪”,他說辛棄疾:“其詞十二卷,慷慨縱橫,不可一世,才氣俊邁,于倚聲家為雄豪一派,世稱蘇、辛。”[5]同為清人的蔣兆蘭稱之為“豪邁”,他說:“宋代詞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約為宗。自東坡以浩翰之氣行之,遂開豪邁一派。南宋辛稼軒,運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蘇、辛并稱。”[6]而蘇、辛說,既有人們關于蘇、辛詞同派的認知,又有辛棄疾“雄豪”詞或“豪放”詞受蘇軾詞影響的意味。不過,論詞的英雄氣,蘇軾不及辛棄疾。辛棄疾的豪放詞風自然會受蘇軾的影響,但他身為失意悲憤的報國英雄和蘇軾身為失意曠達的一介文士畢竟有所不同。這不單純是詞的表現主題,辛棄疾的詞較之于蘇軾詞有了全新的內容。而且,在詞的表現風格上,辛棄疾學蘇詞,情緒昂揚時意氣風發,悲憤填膺時就有了蘇軾詞所缺乏的英雄沉郁,往往意氣與悲憤兼而有之,而辛棄疾把這二者張揚得更加厲害。
后人在評述辛棄疾詞風與蘇軾詞的關聯時,有時也兼及辛派的其他詞人,如清代沈濤在《空清詞館序》里說:“詞以南宋為正宗,北宋諸公猶不免有粗豪處。稼軒、龍洲、后村,流派原本東坡居士,但別有寄托,未可一例視也。”盡管他說辛棄疾、劉過、劉克莊在繼承蘇軾詞風時各有寄托,不能一概視之,但三人之詞“原本東坡居士”畢竟是他說的。在辛派詞人中,姑且不說南宋遺民詞人,最重要的除辛及二劉外,還有上面提到的陳亮。人們常將陳亮與辛棄疾同論,劉熙載說:“陳同甫與稼軒為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7]就“詞亦相似”言,主要指的是抗戰英雄詞的相似,尤以一組同韻的《賀新郎》為代表,它們的豪邁都有蘇軾詞的風味,陳亮的《賀新郎·鏤刻黃金屋》是用蘇軾《賀新郎·乳燕飛華屋》韻的,陳亮詞前有序:“人有見誑以六月六日生者,且言喜唱賀新郎,因用東坡屋字韻追寄。”二者都是相思曲,蘇詞的“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陳詞的“粉生紅、香臍皓腕,藕雙蓮獨。拂掠烏云新妝晚,無奈纖腰似束”,都見萬般柔情,這雖是傳統艷詞風情不屬蘇味詞,但陳亮詞有蘇軾影響則是一定的。還有陳廷焯曾說:“潛夫詞豪宕風流,有獨來獨往之概。”并就其《賀新郎·思遠樓前路》繼續說道:“清麗芊綿。豪宕感激,悲壯風流,是潛夫本色,是蘇、辛流亞。”[8]在這樣的評說中,認同潛夫即劉克莊的詞“是蘇、辛流亞”,那么劉克莊的詞總歸還是有蘇軾詞的味道。劉克莊有《賀新郎·行樂尤宜少》,其序說“讀坡公和陶詩,其九篇為重九作,乃敘坡事而賦之”,詞中說“憶坡公、洞簫聽罷,劃然長嘯。四海共知霜鬢滿,莫問近來何妙”,儼然是蘇軾詞所具的曠放風格。
這里說辛派詞人的學蘇及詞的“蘇味”,并非簡單地從所謂“蘇辛詞派”立論。“蘇辛詞派”的問題,劉揚忠曾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作過全面的評說,他認為混稱“蘇辛詞派”,把“稼軒體”類同于“東坡體”是不妥的,這樣淡化了辛詞的藝術個性與創新。蘇、辛詞的主導風格不同,不能以同派視之。他要肯定辛棄疾在詞壇上開宗立派的地位,因此極力為辛詞辯。但他隨后又說辛詞的確受了蘇軾詞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在眼界與魄力、廣泛開拓題材、盡興披露情感、提高且強化詞的功能與氣格、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變艷科小道為抒情言志等方面。然后說道:辛棄疾“接東坡始啟之端緒,擴東坡初就之軌跡,拓展東坡未創之境界,成就東坡未能想見之大業,以自己的比東坡更霸蠻的‘青兕’才力及獨特的審美方式,集‘言志’詞之大成,將詞的藝術推向新的天地。這是稼軒體對東坡體的最積極的繼承。這種繼承,其中就包含著創新。就稼軒體的包孕宏深、雄渾博大的氣度格局來看,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稼軒體對于東坡體,是絕對地創新多于繼承,所以它才在東坡體之后成為詞壇上另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高峰,而不是只成為東坡體在南宋的一個‘分支’。”[9]這番話對辛棄疾及其詞的高度肯定意在辛詞為獨立一派,其實辛派獨立并不存在問題,辛派詞人獨特的社會環境是蘇軾時代不具備的,因此詞產生新的主題和詞人情感,在這狀態下的詞人創作都會在前代詞人基礎上有所“拓展”或“成就”。劉揚忠認為將辛棄疾與蘇軾相較,顯然辛棄疾更勝蘇軾,所以他才會說辛棄疾“在東坡體之后成為詞壇上另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高峰”。殊不知蘇軾就是蘇軾,他的“東坡體”足以與“稼軒體”相頡頏,不必因“蘇辛詞派”淡化辛棄疾,但也不必揚辛而抑蘇。
[1]辛棄疾.辛棄疾全集[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4:393.
[2]蘇轍.蘇轍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0.
[3]歐陽修.新唐書 [M].北京:中華書局,1975:5613.
[4]王世貞.藝苑卮言[M]//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391.
[5]胡薇元.歲寒居詞話 [M]//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4034.
[6]沈濤.詞說[M]//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4632.
[7]劉熙載.詞概[M]//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3694.
[8]孫克強,等.《云韶集》輯評[J].中國韻文學刊,2010(3):65.
[9]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