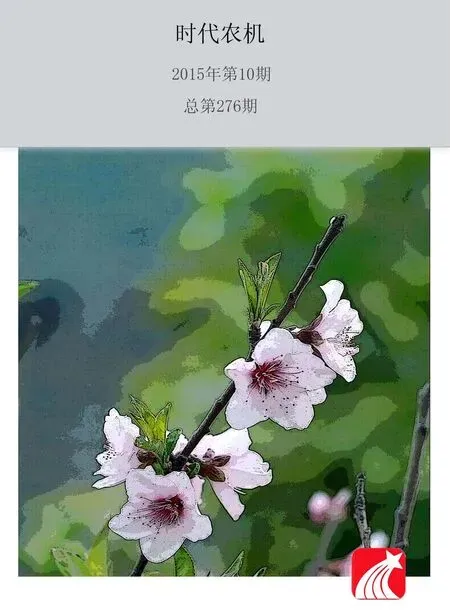加強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懷的有效策略
周玲玲
(湖南財經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湖南 衡陽 421002)
1 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隨著社會市場經濟活動的發展和進步,人類生存的流動性持續增大,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高職院校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與機遇。傳統的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理念已經無法適應新形勢下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實施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因此,新課改背景下的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須打破傳統教學理念的制約和束縛,拓展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理念,不斷提出適應新社會、新發展的教學方法與思路,由此達成為社會培養“以人為本”理念下的優秀人才,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課程教人育人的培養目標。
2 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關懷缺失的原因
(1)教育主體的缺失。目前,作為高職院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沒有真正地將人文關懷工作有效實施到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并未認識到人文關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高職院校管理的基礎上實施的教學方式,能夠促進高職院校管理效率的不斷提高。高職院校管理的本質就是制定符合情理的行為規定指導學生個性化發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其根本目的是管理的有效性,使學生按照制定的行為規范開展活動。正因如此,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施要始終以學生個人根本利益為原則。
(2)教育目標的缺失。在傳統高職學生思想教育教學目標下,很多高職院校開展的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過于注重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經常在教育實施過程中導致高職學生形成逆反心理。目前,部分高職學生在社會道德價值判斷方面出現了偏差,甚至有著隨波逐流的傾向,對老一輩革命家堅持的信仰感到不解和迷茫,難以完全認同社會和諧發展中弘揚的公平工作、團結合作、科學發展、遵紀守法等理念精神,更有甚者無法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尤其是在價值取向方面存在著極度扭曲的問題。
(3)教學方法的缺失。現代高職學生的生活方式和人際交往發展主要以個人興趣為前提,注重的是情感的交流和思想的一致。當前,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關懷工作實施沒有良好的人文環境和關懷分為,大多數情況下的人文關懷工作只是流于形式。因此,針對高職學生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圍繞學生實際生活環境,結合使用正確的教學方法,理論知識是學生的思想實踐,而真實的親身體驗才是生活的具體實際。
3 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關懷實施策略
(1)提高人文關懷教育能力。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關懷要始終堅持落到實處,因此,高職院校需要建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學隊伍,不斷提高教師對學生人文關懷的能力。特別是高職學生輔導員的招聘工作要十分謹慎,輔導員崗位不但要具備教書育人的能力,更要有敏銳的洞察力、良好的溝通交流能力,以及組織協調能力等。
(2)貼近學生的現實生活。首先,作為高職院校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專職教師,其教學活動要貼近高職學生現實生活,尋找學生最真實的生活狀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促進教師與學生交流溝通的和諧開展。其次,教師要使高職學生能夠將自己所學的知識理論與現實生活結合,用于指導其社會實踐發展。對于大部分學生來說,高職院校的教育教學的最終目的是提高學生個人綜合素質水平,在今后步入社會后能夠盡快適應社會發展。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導高職學生自我價值實現的同時,體驗各種生活實踐中的樂趣,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處,最終實現揚長避短,超越自我發展,為社會塑造更完善的自己。
(3)創新課程教學內容設置。在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課程設置上,要不斷增加人文素質的培養內容。首先,作為高職院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要充分考慮高職學生社會發展和個人生存問題,在不斷提高高職學生物質、精神生活的同時,使思想政治教育更貼近學生,將學生內心真實情感、所需所求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起點,結合社會實際案例,在健康發展、生活交友、求職戀愛、遵紀守法等問題方面對高職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內容和培養目標方面,高職院校要始終遵循滿足學生生理、心理需求原則,關心關注高職學生的人際交往訴求,在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基礎上,促進高職學生個人自身價值的實現。其次,在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課堂上采取分組教學模式,教師可以按宿舍將學生分為多個小組,在教學活動中設置多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安排學生采取分組合作討論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樣有助于學生自主掌握知識、解決問題,同時完成了教學計劃的安排。學生良好的課堂氛圍中激發了個人興趣,主動對設置的問題進行探索思考,在課堂上培養了學生積極主動的成長角色。由此,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在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獨立思考、團隊協作能力時,使學生能夠針對問題提出自己的理解層面,對知識的深入探究有利于高職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
4 結語
在開展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不斷增強人文關懷內容的有效實施。這有利于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高,更有利于高職學生對理論知識內容的深化認識,幫助高職學生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提高自身價值水平。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關懷理念的融合,一方面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必然需求,另一方面是衡量教育教學改革發展是否取得成效的真實體現。高職院校高職學生的學科教育都需要跟隨社會的發展變化,以滿足社會對專業人才的需求,高職院校管理者和教育者要積極將學科教育融入到社會實踐生活中,在學生教育中增強人文關懷,為社會培養更全面、更優秀的專業人才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