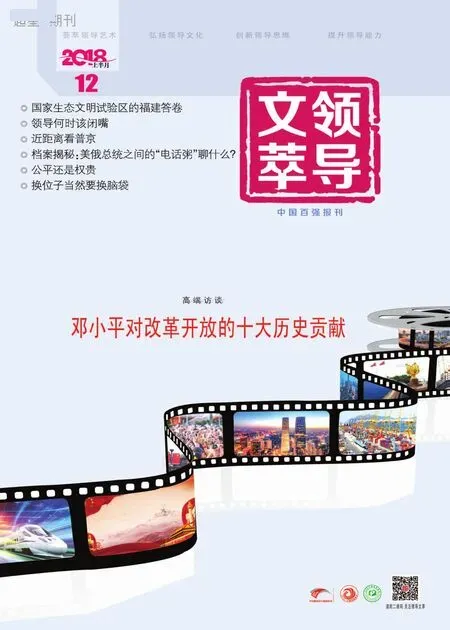不成功是大多數人的命運,這不可怕
阿蘭德·波頓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事業恐慌的時代,就在我們認為自己已經理解我們的人生和事業時,真實便來恐嚇我們。現在或許比以前更容易過上好生活,但卻比以前更難保持冷靜,或不為事業感到焦慮。今天我想要檢視,為何我們會變成事業焦慮的囚徒。
職業的勢利
勢利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它確實存在。勢利是什么?勢利是以一小部分的你,來判別你的全部價值。
今日最主要的勢利,就是對職業的勢利。你在派對中不用一分鐘就能體會到,當你被問到這個21世紀初最有代表性的問題:你是做什么的?你的答案將會決定對方接下來的反應,對方可能對你在場感到榮幸,或是開始看表,然后想個借口離開。
世人所愿意給我們的關愛、尊重,取決于我們的社會地位。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如此在乎事業和成就,以及看重金錢和物質的原因。我并不認為我們特別看重物質,而是活在一個物質能帶來大量情感反饋的時代。下次你看到那些開著法拉利跑車的人,你不要想“這個人很貪婪”,而是“這是一個無比脆弱、急需愛的人”。
對自己的人生過高期待
還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使得我們更難獲得平靜。擁有自己的事業,是一件不錯的事。但同時,人們也從未對自己的短暫一生有過這么高的期待。這個世界用許多方法告訴我們,我們無所不能,我們不再受限于階級,而是只要靠著努力就能攀上我們想到的高度。這是個美麗的理想,出于一種生而平等的精神。
這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嫉妒。嫉妒來自生而平等的精神。越是兩個年齡、背景相近的人,越容易陷入嫉妒的苦海。今日社會的問題是,它把全世界變成了一個學校,每個人都穿著牛仔褲。但并非如此,當生而平等的概念遇上現實中懸殊的不平等,巨大的壓力就出現了。
今日你變得像比爾·蓋茨一樣,有錢又出名的機會,大概就跟你在十七世紀,成為法國貴族一樣困難。但重點是,感覺卻差別很大。今日的雜志和其它媒體讓我們感覺,只要你有沖勁、對科技有一些新穎的想法,再加上一個車庫,你就可以踏上比爾的道路。那些自我勵志類書籍基本上分成兩種,第一種告訴你:“你做得到!你能成功!沒有不可能!”另外一種則教導你如何處理“自信缺乏”,或是“自我感覺極差”。
功績主義
還有一個概念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焦慮,這就是“功績主義”。一個崇尚功績主義的社會相信:如果你有才能、精力和技術,你就會飛黃騰達,沒有什么能阻止你,這是個美好的想法。問題是,如果你打從心里相信,那些在社會頂層的人都是精英。同時你也暗示著,以一種殘忍的方法,相信那些在社會底層的人,天生就該在社會底層。換句話說,你在社會的地位不是偶然,而都是你配得的,這種想法讓失敗變得更殘忍。
在中世紀的英國,當你遇見一個非常窮苦的人,你會認為他“不走運”,或者說是不被幸運之神眷顧的人。而現在,不幸的人——尤其在美國,社會底層的人被刻薄地形容成“失敗者”。這表現了四百年的社會演變,我們對誰該為人生負責看法的改變,神不再掌握我們的命運,我們掌握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干得很好,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相反的話,就很令人沮喪。社會學家Emil Durkheim分析發現,這讓自殺率空前提高。追求個人主義的發達國家的自殺率要高于世界上其它地方,原因是人們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全當作自己的責任。人們享有成功,也就要擁有失敗。
“功績主義”,也就是相信每個人的地位忠實呈現他的能力,這個想法很瘋狂。一個完全徹底以能力決定地位的社會,是個不可能的夢想。每個人的能力都忠實地被分級,好的到頂端,壞的到底端,而且保證過程毫無差錯,這是不可能的。這世上有太多偶然的契機,無法忠實地將人分級。
“失敗者”在古老的西方傳統中僅把他們稱為“悲劇”。悲劇的藝術來自古希臘,這是一個專屬于描繪人類失敗過程的藝術,同時也加入某種程度的同情——在現代生活并不常給予同情時。你不會說哈姆雷特是個失敗者,雖然他失敗了,他卻不是一個失敗者。
輸贏中有太多偶然
我一直在談論成功和失敗。成功的有趣之處是,我們時常以為我們知道成功是什么。你會想,這個人可能很有錢,在某些領域赫赫有名。但實際上,你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成功。所有對成功的想象,必須承認他們同時也失去了一些東西,放棄了一些東西。總是有什么是我們得不到的。
在輸贏的過程中,有太多偶然,今日我們太講求所有事情的正義和公平。政治人物總是在談論正義,我們應該盡力去追求正義,但我們也應該記得,“偶然”總是一個強烈的因素。我們社會需要的模范人物就像你的一位父親,理想的父親是怎樣的?往往是嚴厲又溫和的,不要走極端,不要完全的集權、純粹的紀律;也不要模糊馬虎,亂無規章。
(摘自《職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