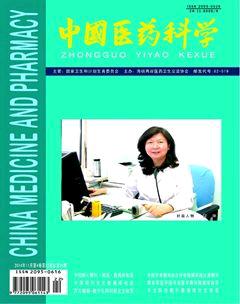新生兒黃疸早期干預的臨床評價
黃金科
[摘要] 目的 對新生兒黃疸早期干預的臨床評價進行探討。 方法 我院產科新生兒黃疸180例,將進行了干預治療的87例分為高膽紅素對照組,只進行動態監測未進行干預治療的93例分為觀察組,對兩組患兒黃疸高峰期、黃疸消退后的NBNA及生后1、3、6、12個月的智能發育隨訪結果進行比較。 結果 兩組患兒治療黃疸高峰期的NBNA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黃疸消退后高膽紅素對照組的NBNA(38.9±1.6)分略高于觀察組(38.0±2.6)分,(P>0.05);生后1個月時高膽紅素對照組的智能發育評分(67.1±13.9)略高于觀察組(66.3±12.7)(P>0.05);生后3、6、12個月時隨訪結果則顯示兩組患兒的評分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膽紅素對照組后遺癥發生率為3.4%(3例),觀察組后遺癥發生率為5.4%(5例),兩組后遺癥發生率比較(x2=1.40, P>0.05)。 結論 如果不存在高危因素,新生兒血清膽紅素值偏高于正常值是安全的,但需密切動態監測膽紅素情況,一但出現異常即時進行對癥處理,而有高危因素的患兒,則一定要積極的干預治療。
[關鍵詞] 新生兒;血清膽紅素;干預治療
[中圖分類號] R722.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4)22-190-03
新生兒黃疸是新生兒時期最常見的癥狀之一。在我國,幾乎所有足月新生兒都會出現暫時性總膽紅素的增高;80%以上的早產兒亦可見黃疸[1]。新生兒黃疸既是新生兒早期的一種生理現象,也是出生后各種病理性疾病的臨床表現之一[2]。目前對新生兒黃疸的治療可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傾向。(1)出于對高膽紅素血癥所導致的膽紅素腦病和核黃疸的擔心及顧慮而出現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的現象。(2)另一相反的情況就是由于某些醫生(包括患兒的家長)對形成高膽紅素腦病的影響因素認識不足,以及對新生兒出生早期膽紅素的監測不足而出現延誤診斷,并因未能得到及時的治療而導致核黃疸的發生,產生嚴重后果[3]。鑒于上述情況,目前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癥的診治方法和隨訪工作等方面均存在著諸多的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去解決和完善。我們結合本地區出生的新生兒黃疸情況作進一步的監測探訪和追蹤,以便為今后能更加正確地、科學地處理本地區的新生兒黃疸提供依據,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抽選本院產科2011年7月~2013年6月期間180例符合《實用新生兒學》中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癥診斷標準[4]的新生兒為研究對象,將未進行干預的93例患兒分為高膽紅素研究組,其中足月兒64例,早產兒29例,男49例,女44例;日齡3~12d,平均(5.4±0.3)d;體重2180~3515g,平均(3083±211)g;顯像時間:生后3~7d 57例,7~11d 36例;血清總膽紅素≥220.1μmol/L 51例,≥342.0μmol/L 30例,≥427.5μmol/L 12例。將轉兒科干預治療的87例分為高膽紅素對照組,其中足月兒61例,早產兒26例,男47例,女40例;日齡3~12d,平均(5.6±0.3)d;體重2178~3510g,平均(3082±213)g;顯像時間:生后3-7d 54例,7~11d 33例;血清總膽紅素≥220.1μmol/L 48例,≥342.0μmol/L 28例,≥427.5μmol/L 11例。兩組患兒在男女比例、日齡、體重、顯像時間及血清總膽紅素方面比較,無統計學差異(P>0.05)。
1.2 方法
研究組:一經發現面部黃染者即開始以皮測膽紅素檢測儀(日本美能達公司出產)進行監測,每天3次(8點~12點~14點)進行動態觀察黃疸進展情況,或者抽血到化驗室采用全自動生化儀(南京神舟英諾華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出產型號為D280)化驗總膽紅素值,并觀察有否出現異常表現,直至黃疸消退至安全范圍之日止。過程中如患兒出現異常表現即轉兒科進行對癥治療。
對照組:參考《中華兒科雜志》編輯委員會及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新生兒學組2009年11月制定的“新生兒黃疸診療原則的專家共識”所推薦的不同出生日齡的足月新生兒黃疸干預推薦標準及不同胎齡/出生體重的早產兒黃疸干預推薦標準進行治療[5],分別給予光療或換血治療。光療的患兒裸身置于藍光治療箱中,照射前將患兒雙眼、會陰、肛門用黑布遮蓋,藍光波長主峰選擇在425~475nm之間,采用多次短時照射,照射8h間隔4h再照射8h,每天共照射16h,至患兒黃疸消退為輕度停止藍光治療,一般治療時間為2d。1例溶血性黃疸患兒行換血治療,采用周圍動靜脈同步換血,選擇一側橈動脈,用24G靜脈留置針穿刺,另一側肢體開放一路外周靜脈,用同樣的24G靜脈留置針穿刺置管。兩人配合換血,一人從動脈以180mL/h速度抽血,另一人使用注射泵將選擇好的血源從靜脈以180mL/h速度注入,換血總量150~180mL/kg。
1.3 觀察指標
本研究中所有患兒出院后均定期隨訪對其生長發育(包括行為及智力)進行監測。新生兒行為神經測定:采用全國新生兒行為神科研協作組制定的NBNA方法,分別在生后黃疸高峰期、黃疸消退后進行檢測。智能測試:于生后1、3、6、12個月時采用由中國科學院中國發展中心心理分中心編制的小兒智能發育量表進行智能發育檢測[6]。
1.4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表示,組間對比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當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NBNA比較
2.2 兩組患兒智能發育評分比較
2.3 兩組患兒預后情況
共3例出現后遺癥,1例聽力輕微受損,2例癲癇,發生率為3.4%;觀察組共5例患兒出現后遺癥,智力低下3例,腦性癱瘓1例,1例死亡,發生病為5.4%;兩組后遺癥發生率比較,觀察組略高于高膽紅素對照組(x2=1.40,P>0.0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觀察組5例出現后遺癥的患兒均為伴有高危因素而家長拒絕進行干預的患兒。
3 討論
雖然高濃度膽紅素對神經、心、腎、肝、消化和免疫等器官有毒性作用,但在生理狀態下,他又是一個抗氧化劑,屬于非酶類抗自由基系統,彌補了新生兒酶類抗自由基的不足。在早產兒生后的最初幾天,膽紅素的存在可增強其抗氧化系統的功能,合并高膽紅素血癥的早產兒其患呼吸窘迫綜合癥及早產兒視網膜病的結局要比低膽紅素者好些[7]。看來,一定量的膽紅素對機體有益,故新生兒黃疸時,掌握好對新生兒高膽紅素的干預指標,避免過早過度干預,從而發揮其抗自由基的作用,會給機體帶來好處[8]。有些兒科醫生由于忽略日齡的影響,只要膽紅素接近或超過220.1μmol/L(12.9mg/dL),認為都要接受各種治療,而缺乏個體化的分析和監測。一些正常足月新生兒血清總膽紅素雖超過生理正常值,但找不到任何病理因素,可能仍屬生理性黃疸[7-8]。國外Newman等[9]于2006年發表過一項中心調查結果,作者認為正常足月新生兒如果不存在高危因素,其血清紅膽素值在342~427.5μmol/L(20~25mg/dL)是安全的,但需密切監測膽紅素,而有高危因素者一定要積極干預。
本研究中我們對180例高膽紅素血癥患兒的臨床治療情況,進行了監測和預后追蹤,從隨訪結果可以看出,只進行了動態監測黃疸進展情況的觀察組,其黃疸高峰期及黃疸消退后的新生兒行為神經測定結果,顯示與進行了治療干預的對照組對比,差異不大(P>0.05)。且兩組患兒生后1、3、6、12個月的智能發育隨訪結果顯示,生后1個月時高膽紅素對照組的評分略高于觀察組,但差異不大(P>0.05),生后3、6、12個月時隨訪結果則顯示兩組患兒的評分均相差不大(P>0.05);說明新生兒如果不存在高危因素,其血清膽紅素值偏高于正常值是安全的,但需密切動態監測膽紅素情況,一但出現異常即時進行對癥處理[10]。在兩組患兒預后情況方面來看,觀察組的后遺癥發生率為5.4%,略高于高膽紅素對照組3.4%,兩組對比差異不具統計學意義(P>0.05)。但值得注意的是,觀察組5例出現后遺癥的患兒均為伴有高危因素而家長拒絕進行干預的患兒。說明有高危因素的高膽紅素患兒,應盡早進行干預治療措施,避免患兒出現不可挽回來的損害。應加強家長對新生兒黃疸危害的認識與重視,以減少后遺癥的發生[11]。
綜上所述,新生兒黃疸啟動治療的標準應該是依據新生兒病史(母孕產史、胎齡、日齡、喂養、大小便等)、體檢和實驗室檢查而制定的策略和開始治療的標準[12],任何干預標準或指南僅僅是從流行病學角度出發,為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癥的治療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范圍,具體到每個患兒應該是依據胎齡、日齡,是否存在高危因素等個體化的標準[13],而有高危因素的患兒,則一定要積極的干預治療。
[參考文獻]
[1] 陳昌輝,李茂軍,吳青,等.新生兒黃疸的診斷和治療[J].現代臨床醫學,2013,39(2):154-160.
[2] 丁玉紅,鄧曉毅.新生兒行為神經測定對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癥預后的評估[J].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2008,29(11):1309-1310.
[3] 陳艷霞,王家勤,許建文.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癥行為神經測定及嬰幼兒期智能發育隨訪[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07,22(14):1079-1080.
[4] 金漢珍,黃德珉,官希吉.實用新生兒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9:217.
[5] 中華兒科雜志編輯委員會,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新生兒學組.新生兒黃疸診療原則的專家共識[J].中華兒科雜志,2010,48(9):685-686.
[6] 鮑秀蘭.新生兒行為和0-3歲教育[M].北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95:240.
[7] 黃誠英.早期干預對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癥智力發育的影響[J].廣西醫科大學學報,2011,28(4):573-574.
[8] 丁國芳.關于新生兒黃疸診療問題的思考及建議[J].中華兒科雜志,2010,48(9):643-645.
[9] Newman TB,Liljestrand P,Jeremy RJ,et al.Outcomes among newborns with total serum bilirubin levels of 25 mg per deciliter or more[J].N Engl J Med,2006,354(18):1889-1990.
[10] 唐紅裝,梁麗清,謝映梅.短時多次藍光療法在新生兒黃疸治療中的效果觀察與護理[J].廣東醫學,2010,31(23):3154-3155.
[11] 顏思璐,寧岑.間隙藍光照射治療新生兒黃疸的可行性分析[J].海南醫學,2013,24(3):361-363.
[12] 鄧慕儀,梅紅,劉應波.新生兒黃疸的相關因素及防治措施探討[J].當代醫學,2014,20(10):4-5.
[13] 胡婭,劉麗.新生兒黃疸膽紅素和總膽汁酸測定的臨床意義[J].中國現代醫生,2013,51(15):117-119.
(收稿日期:2014-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