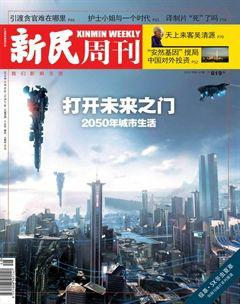離開“綠色”的創新沒有生命
姜浩峰
面對上海2050年建成全球城市的說法,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有不同的看法。 諸大建認為,如果關于上海2050的討論只談“全球城市”,對可持續發展避開不談,這樣的戰略研究,難說有國際眼光與民生關注。諸大建說:“現在討論上海2050,需要有理論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和綠色經濟長波最有啟發力,上海需要成為國際影響、區域包容、綠色宜居的全球城市。”
諸大建認為,研究上海2050,許多學者習慣于從現在推向未來,從紐約等標桿城市,預測35年后上海怎么樣;沒有人倒過來,從2050年世界怎么樣,構想上海的可能情景和應該怎么做。很少有人去想,2050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比1990年減少50%,上海的城市、產業、消費方式是如何。
即使到2010年代,制造業在上海GDP中依然占有較高比重。未來,是否該把制造業的比重減少到25%左右?諸大建認為,如果不減少,上海的工業用地、能耗、二氧化碳排放,與紐約等標桿差距太遠;如果減少,當下的許多規劃就需要修改。
另一方面,全球城市的包容性一直被人所樂道。上海的城市包容性,在中國各大城市中或可排位靠前。事實上,成就1930年代遠東第一大都會的上海,就曾以城市包容性著稱,比如白俄、猶太難民等,都得以在上海安生。美國城市學家Florida基于3T理論(科技、Talent、Tolarence)認為,影響上海登頂全球城市的最大因素是包容性。Florida在其最新著《Great Reset(2013)》中寫道:“沒有更大包容性,上海就不可能像紐約、倫敦那樣吸引幾百萬外國人。”
參與各類上海2050討論,令諸大建不滿意的地方是,一些經濟學家只想擴大城市空間,而不懂得增長管理。“其實上海城市發展已經越來越看不到邊界了:原來中心城區以外環線為界,現在已與寶山、閔行連成一片;郊區新城,本來被農村分隔,現在新城與新城間在填充水泥空間;本來上海與江浙有綠色分界,現在也將被所謂全球城市區域蠶食。”
至于是否能成為頂尖的全球城市,諸大建的看法是:“全球城市上,上海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三第四,但現在看不出超越紐約倫敦的潛力;城市區域上,按照高鐵體系、城市能級、區域文化,上海與長三角可以成為世界翹楚;在城市生活和環境質量上,沒有看到領軍希望,這方面趕超要至少30年積累。”
諸大建提到:“許多人喜歡在四個中心之上,不斷增加新的中心,例如創新中心、文化中心、醫療衛生中心……上海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去當中心,研究上海未來發展,需要有綜合集成概念,可以覆蓋城市發展的眾多維度。”
他認為,綠色創新是個不該忽視的問題。“紐約、倫敦、東京都在爭當全球綠色創新中心城市,上海不應忽視綠色創新。”他對于3T的詳解則是——Technology,上海需要制造業服務業融合和綠色創新,哺育全球影響力本土企業;Talent,上海需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既造血生產本土人才,又輸血引進海外人才;Tolerance,上海需要政府創造愜意舒適的城市物質條件和包容性的思想文化軟環境。
“盡管認識到環境風險是城市發展的主要制約,如資源方面有水資源、能源、土地資源,污染方面有生活垃圾,生態方面有海平面上升,但在討論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時,卻很少有人把節約資源、環境友好的綠色科技作為中心內容。不管創新的口號如何時髦,只要回避綠色問題,任何創新都是脫離上海現實的。”諸大建在《綠色的創新》一書內容提要中寫道:“中國的基本國情和21世紀的世情都決定了,中國的未來發展面臨著生態創新或綠色創新的最嚴重挑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