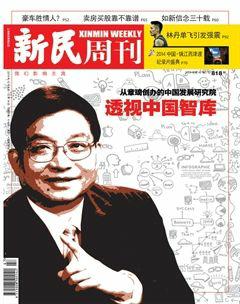董家渡的紅月亮
沈嘉祿
希望老樹佇立在江邊,不管今后董家渡會有怎樣的風采,我們就有重訪的理由了。
前不久,黃浦區董家渡13、15號地塊以“快閃”的方式拍賣成功,據說還以248.5億元的總價成為2014年新的全國總價地王。我家離董家渡一箭之遙,春江水暖鴨先知,小區周邊的房產中介馬上將掛牌房的信息刷新了一下,小漲三個百分點算厚道的。
當天晚上與太太去董家渡散步,一大片舊房拆平之后,視野豁然開朗,走在昏暗的路燈下,望著廢墟中孤立的一兩幢危房,聽見微弱的燈光里傳來陣陣笑聲和嘩嘩洗牌聲,周遭顯出別樣的寂寥。彼此看一眼后問:將來這里起了高檔寫字樓和住宅樓,我們還會來嗎?自問自答的言語里,泛起了留戀與惆悵。
從小生活在盧灣區,也就是如今的新天地一帶,偶爾會去城隍廟軋軋鬧猛,近江的董家渡要等許多年后,騎自行車去那里看望一個朋友,才發現其實也相當有趣,所見多為本地房子,低矮而破舊,沿街小店和路邊攤鱗次櫛比,人聲嘈雜,燈影晃動,人間煙火,唯此為甚。后來在陸家浜路置了新房,這一帶的舊名是“大南門”,故而快去一箭之遙的董家渡熟悉環境。街道、弄堂、舊房,還有從房屋夾縫中探出樹冠的老樹,似乎一切照舊,只是在董家渡路、南倉街以及外倉橋街一帶冒出了許多路邊攤,花花綠綠的布料掛得鋪天蓋地,本地女人、外國女人(以俄羅斯女人居多)大聲喧嚷,眼疾手快地挑三揀四,然后大包小包地走人。裁縫鋪也不少,量身定做西裝禮服、婚紗旗袍,生意很好,七浦路服裝市場的老板也是這里的常客。
這里的路名也極有意思,比如雞毛弄、花衣街、西鉤玉弄、蘆席街,與老城廂的業態有關,而青龍橋街、小普陀街呢,散發著濃郁的農耕文明氣息,再比如萬豫碼頭街、公義碼頭街、王家碼頭路,見證了上海在開埠后快速取代廣州躍升為中國外貿中心的歷史。董家渡路上有一座氣勢不凡的天主堂,資格堪與徐家匯天主堂比肩,不做禮拜的日子,這里一派安謐。往南走幾步是會館碼頭街,一片瓦礫中佇立著一幢中式宮殿式建筑,它就是商船會館,早年沙船業巨頭經常聚會議事的行業協會。幾番風雨,花開花落,兩旁的配殿早已廢圮,只剩下搖搖欲墜的主體建筑,被外來人口占用。董家渡地塊拍賣后,這處老建筑是移建它處還是原地保護,如果原地保護又如何與周邊現代化的建筑相對不沖,相安無事,都將考驗政府部門與開發商的智慧。
七八年前,董家渡就進入動遷倒計時,我和太太也經常去那里散步,空氣中彌漫著些許緊張和躁動,居民圍作一團,在路燈下議論紛紛。簽約一戶,封堵一家門窗,簽約一批,整幢房子立馬推倒,有時拆到一半,百年老屋露出難以轉圜的空間結構,令人唏噓。最后,好像承受了一記加速度,轉眼夷為平地,我們也松了一口氣。
今年八月十五的晚上,據說有個紅月亮會升上天空,于是許多人都來到董家渡的空曠地面上賞月。月亮升起來了,果然如烙鐵般通紅。有年輕人舉著手機轉到天主堂前試圖拍到與建筑物親密接觸的紅月亮,但教堂太低,效果不理想。我想再過若干年,這里會聳起一幢幢現代化的商務樓,屆時再來拍一個中秋節的圓月,一定不會讓人失望。
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我們還會回來嗎?我就跟太太講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向南外灘開發公司的老總建議:董家渡的舊房拆除了,留下許多老樹,請不要隨意處置,可將它們移至濱江綠化帶,給每株老樹做塊銅銘牌,標明出自某路某弄某號某個庭院,原住民有張三李四幾戶。哪一天街坊老鄰居相約而來這里訪舊,這些老樹依然承載他們的感情,延續他們的生活記憶,是他們與這座城市密切關系的證明。公司領導聽了很感興趣,認為這個建議有可操作性,將來也是一個新聞亮點。
是的,我們希望老樹佇立在江邊,不管今后董家渡會有怎樣的風采,我們就有重訪的理由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