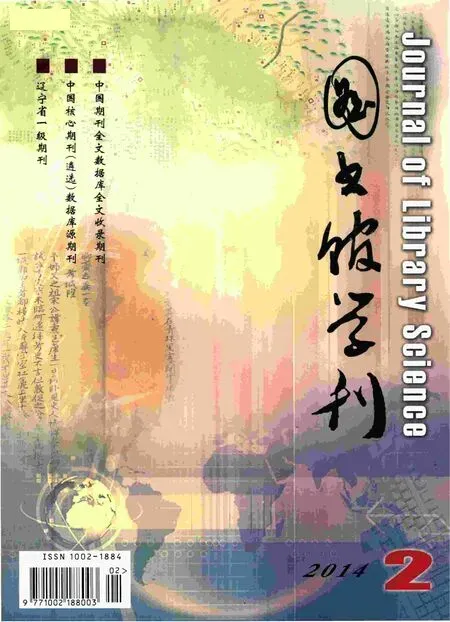四部分類系統的邏輯生成
晁冬梅
(陜西理工學院文學院,陜西 漢中 723000)
1 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系統
我國古代文化輝煌燦爛,早在3000年前的周代,先民就開始對浩繁的圖書典籍進行分類整理。西漢時期,光祿大夫劉向奉旨校理國家藏書,撰成《別錄》一書,后劉歆子承父業,在《別錄》基礎上編制《七略》,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國家圖書目錄,開創我國圖書分類事業之先河。此后,我國古代圖書分類以《七略》為源頭,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逐步于隋唐時期確立了成熟的四部分類體系,并于清代乾隆年間達到鼎盛,出現了集大成的分類著作《四庫全書》,由此完成了我國古代圖書分類事業。
四部分類系統是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的主流,它自劉歆編制《七略》起,經歷幾個時期的發展變化,到唐初編撰《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才得以最終確立,這是學界關于四部分類確立的普遍觀點。目前學界關于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系統的研究,多數集中于對各個時期分類法的歷史陳述,鮮有對整個分類系統的邏輯形成作過程性梳理。筆者把我國古代圖書分類事業看作一個完整的分類系統,即四部分類系統。筆者所討論的四部分類系統的確立,是從源頭《七略》開始,到《隋志》為止,重點討論《七略》《中經新簿》《晉元帝書目》《七志》《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七錄》《隋志》這7部目前有史料記載的目錄著作。
2 “七分法”與“四分法”之爭
目前學界關于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系統的討論存在較多爭議。筆者對視線所及范圍之內的目錄學著作做了梳理,大致分出以下兩種觀點。
2.1 我國古代圖書分類存在兩個分類系統
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即認為我國古代并行著“七分法(或六分)”和“四分法”兩個分類系統,且對于《隋志》的系統歸屬問題,學者觀點不一,各自祖述,各有沿承。概有以下3種情況。
一是認為《隋志》繼承荀勖、李充的四分法。此觀點以張舜徽先生為代表。“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另一個系統,便是今日仍在通行的四部分類法。起源于魏晉之際。”“唐初修《隋書·經籍志》時,便直標經、史、子、集四部之名,來代替甲、乙、丙、丁的稱號。”[1]114“茲就七略分類法和四部分類法,各列一表,以明其因革損益如次”,[1]116張舜徽先生附錄了《歷代采用七略分類法的代表寫作對照表》和《歷代采用四部分類法的代表寫作對照表》,通過表格可以看到張舜徽對于《隋志》之前分類法的基本觀點。
二是認為《隋志》繼承《七錄》《七略》。此觀點以姚名達先生為代表。姚名達在《中國目錄學史》里明確指出:“《隋志》之四部。貌似荀、李而質實劉、阮,遠承《七略》之三十八種,近繼《七錄》之四十六部。嫡脈相傳,間世一現。”[2]66“《隋志》者,固《七錄》之子,《七志》之孫,而《七略》之曾孫也”。[2]76
三是認為《隋志》綜合繼承了“七分法”和“四分法”。此觀點以程千帆、徐有富和高路明先生為代表。程千帆、徐有富認為《七錄》把內篇分為五部,主要根據劉孝標的《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在此已打破了七分四分系統各自的封閉性,他明確指出:“《隋志》分為四部,以經、史、子、集取代甲、乙、丙、丁,是受到魏晉時期目錄的暗示殆無疑問。至于在細部的劃分上,則取資于《七錄》為多。”[3]123高路明在《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一書里也表達了相似觀點。他認為阮孝緒所分七類綜合了《七略》《七志》及劉孝標所編目錄,“《隋書經籍志》吸取荀勖、李充以及《七略》《七志》《七錄》的分類成果,分群書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四大類又分為四十小類”。[4]35
2.2 認為我國古代圖書分類是一個完整系統
學界以余嘉錫先生為代表。余先生在《目錄學發微》里明確指出,“七略之變而為四部,不過因史傳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諸子、兵書、術數、方技之漸少而合之為一部,出術數、方技則為五,益之以佛、道則為七,還術數、方技則為六,并佛、道則復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諸子一部。互相祖述,各有因革。雖似歧出枝分,實則同條共貫也。”[5]161“七略四部,名異而實同,荀勖、李充取六略之書合之為四。王儉、阮孝緒又取四部之書分之為七。觀其分部之性質,實于根本無所改革。”[5]165筆者據此觀點將逐步厘清這個完整分類系統是如何經歷眾多發展與曲折而得以最終確立的。
3 四部分類系統的邏輯生成
從《七略》第一次大規模類分群書開始,到唐初《隋志》的編制完成,我國古代類分圖書的四部分類系統大致成型。縱觀其間出現的各種分類法,都只是四部分類系統各個不同階段的表現而以,筆者通過探究各個分類法之間的內在承繼與發展關系,旨在使我們對四部分類系統的形成產生更直觀清晰的認識。這不僅有助于我們把古代圖書分類看作一個完整的發展完善的系統,還有益于我們正確評價不同時期各個分類法的優劣,以及分類法自身的價值功效問題。
《七略》原書已亡,其分類部次被完整保存在《漢書·藝文志》里,共分六大類三十八小類。《隋志》分為四大類四十小類,另附道、佛二錄。我們把《七略》和《隋志》各自的分類情況列成表格進行比較(見表1)會發現,分類系統從無到有、到發展為《隋志》的四部四十類,大概需要以下7個要素的逐步顯現,即:A大部名稱,B細目名稱,C類序,D四分法部類劃分出現(史部析出、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合為一部),E佛道經附錄(佛、道),F四部類順序固定,G四部類名稱確立(見表2所示)。

表1 ①
在《七略》和《隋志》產生期間,出現了5部代表性的目錄著作,即《中經新簿》《晉元帝書目》《七志》《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和《七錄》。有些原書今已亡佚,但由于其書序或者主要分類部次被載于其他文獻而使其分類情況目前大致可考。《中經新簿》在阮孝緒《七錄》序(《廣弘明集》卷三)和《隋志》序中有記載。李充的《晉元帝書目》可從《晉書》卷九二《李充傳》、《隋志》序和清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序中考證其部次分類。《七志》的體制保存在《隋志》序中。劉孝標的《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記載于《古今書最》和《隋志》中。《廣弘明集》卷三保存有《七錄》序,據此我們可以得知該書的基本體制和成書緣由的大致情況。
縱觀六部書目的分類情況,可清晰看出作為整體的古代圖書分類系統是如何形成的,還可以此來解釋目前學界的一些爭議性觀點。

表2 ②
從每行“√”出現的先后和數量的多少,可以判定各個分類法對于系統生成的貢獻大小,也即各分類法的價值大小。從表格前兩行的“√”來看,7個主要要素的5個都已出現,且《七略》和《中經新簿》功勞各半。此一點即可糾正我們歷來對于《七略》的過分推崇而忽視《中經新簿》的價值,如姚名達先生把魏晉時期的四部分類稱為單純四分法,列于正統四部分類之外。我們應該把各個分類法平等地看作系統形成過程的各個不同階段,分類法有優劣之分,但無尊卑之別。
表格中,每列從上向下,“√”和“×”的交替出現可以看出每個要素在系統形成各個階段的不同狀態,由此可以比較各個分類法分類思想的異同。如史部析出和佛道經附錄兩要素,被《七略》之后多數分類法認同并加以采用。這反映了由當時書籍狀況和學術風貌決定的不可逆轉的分類潮流。
《七志》和《七錄》歷來被學術界并稱,《隋志》言其“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推崇七分法的學者更把它們視作嫡脈相承的關系。我們比較《七志》和《七錄》各行的符號情況,它們都有較前一分法的進步之處,但最大區別在于史部析出,這是王儉分類的退步之處,較于之前的逆潮流之處。沒有史部析出,即可完全退回到《七略》時期。正如余嘉錫先生所言“王、阮二家雖同法《七略》,而王一意返古,阮之類例,則斟酌于古今之間,就書之多少分部,不徒偏重理論,自序言之甚明。后人泛以王、阮并稱者,非也”。[5]158
我們把古代圖書分類事業的發展看作一個完整系統的生成,那么系統的生成和完善主要取決于系統內主要要素的依次出現和要素組合結構的固定。所以表二中,各個行表頭從左到右標出了系統生成的不同階段,結合列表頭,可以表示每個分類法在系統生成過程中所處的階段和位置。由此觀之,我們不僅可以清晰地看出統一完整分類系統的生成過程(所謂的七分法、四分法都只是系統形成中的不同階段而已),還可以看到各個分類法對于系統生成的貢獻大小以及不同分類法之間的繼承和變化情況。據此我們不僅可以正確評價各個分類法的價值大小,還可以解釋學界關于分類法各自祖述的一些爭議性觀點。
4 結語:圖書分類要因時而宜
四部分類系統形成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產生了不同的分類法。在解決了系統作為整體的生成問題之后,怎樣看待和評價各個時期的分類法,便成為當下需要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最重要的評價標準應是看其是否適應于當時的書籍存亡狀況和學術研究風貌。
章學誠先生認為“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6]2余嘉錫先生也曾說:“夫古今作者,時代不同,風尚亦異。古之學術,往往至后世而絕,后之著述,又多為古代所無。四部之法,本不與《七略》同,史出《春秋》,可以自為一部,則凡后人所創作,古人所未有,當別為部類者,亦已多矣。”[5]161黃建國在《試論我國古籍四部分類的形成和發展》一文中指出:“圖書分類與學術文化的變遷、書籍的增多緊密相關。尤其是在我國古代,圖書分類體系往往和社會上存在的圖書變動有關,實際上是:收藏了哪些書,就設立哪些類目。”[7]姚江河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中國古代的目錄都是面向具體文獻的,亦即根據當時實有文獻來建立分類體系和類目設置的。”[8]這些論述都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即圖書分類法應該變化,并且要根據當時的書籍狀況和學術需要做出相應改變。反之,評價分類法的優劣,就要看其是否因時而宜。
魏晉時期四部分類法的出現,是對《七略》分類法的巨大改變。其產生的背景,是魏晉時期書籍學術的發展變化,史書增多,需要從《春秋》中別立一類;文學自覺之后,文集也相應增多;佛教傳入道教興起,使得佛道經文獻也大量出現,需要另立類目,所以就產生了以荀勖為代表的四部分類法。且自荀勖之后,歷代分類法都沿承了這幾個變化。到了劉宋時期王儉意欲返古,棄之不用,以致其分類法并未存在多長時間便被時代所拋棄。
南宋時期,有史學家、目錄學家鄭樵編制《通志》,他在《藝文略》中把古今存亡圖書分為12類,從經部中獨立出禮、樂、小學各成其類,與經部并列,從諸子中分出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各自成類,與諸子并列。鄭樵打破了之前四分法的統一性,對經學的主導地位提出挑戰。但其畢竟處于儒家經學占統帥位置的封建時期,與封建學術面貌所要求的分類思想相異,所以其分類法只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到其幾百年后的清代,仍回歸到唐初既已確立的四部分類系統上來,并將其發展到了頂峰。學術發展的時代潮流對于分類法的篩選,正是因著分類法是否合于當代學術風貌而來。
注釋:
①數字表示其在原書中所處位置的次序。
②(1)表格中,行表頭標示系統形成需要依次出現的7個要素,列表頭標列主要的7部目錄著作。(2)“√”表示相應要素在此分類法中出現,“×”表示之前已出現要素在此分類法中消失。(3)“?”表示目前史料缺乏,有無此類暫不可考,不過不影響整體。(4)空白單元格表示與前者相比沒有變化。(5)為了過程表述清楚,荀勖之后的甲乙丙丁四部分類視為沒有部類名稱,盡管可能只是分類工作不完整。
[1]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M].濟南:齊魯書社,1998.
[4] 高路明.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5]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6] 章學誠.校讎通義·宗劉第二[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7] 黃建國.試論我國古籍四部分類的形成和發展[J].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9):107-115.
[8]姚江河.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古典文獻分類法研究綜述[J].塔里木大學學報,2011(3):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