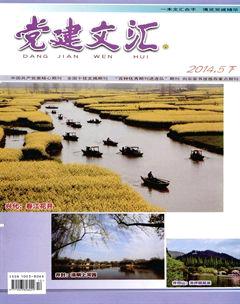盤點官場稱呼上的講究等
舒煒等
“千萬別直稱‘某巡視員”
巡視員一般都是廳級干部,算大領導了,但在現實中,卻很少有人直接稱他們為某某巡視員。
“千萬別這樣喊,人家不樂意聽。更多時候,我們都還是會用他之前的職務來稱呼,比如王局、張廳、李主任等。”多名省級機關干部對記者說,“但是正式行文時,要稱為巡視員。”
曾有一名媒體人回憶,自己剛入行不久時,跟著老記者去采訪某廳的一名副巡視員,很“莽撞”地直接管人家叫“某巡視員”,讓本來“和顏悅色”的對方“臉色陡變”。后來報社領導好幾年內都拿這事給新記者做反面例子,讓自己好不郁悶。
但同為非領導職務,級別為處級的調研員在口頭稱呼上要隨意一些。“徐調、王調可以隨便叫,都不會在意的。”西部某市的一名處級干部王正偉說。“當然,并非所有的調研員或者巡視員都是這樣,但我所打過交道的這類領導有數十名,基本符合這樣的情況。”
“歸根到底,還是一部分干部境界和心態的問題,你本來就是這個職務,人家這樣稱呼你是完全正確的。”王正偉的一名同事表示。
“大市長”和“二市長”
相較上述情況而言,在不少官員看來,對正職和副職稱呼,才更是一門“功課”。
記者之前去東北采訪,聽當地官員在餐桌上聊起“大市長”、“二市長”來。當時是第一次聽到還有這么個稱呼,不解。
細問才明白:一個城市有一個市長,若干個副市長。向客人介紹時,過去不論正副只說蘇市長李市長,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還是副的,于是,為了便于區分,說著方便,就把市長叫大市長,把常務副市長叫二市長。依此類推,可以叫出大縣長、二縣長;大書記、二書記之類。
當地人的解釋是,這個叫法透著東北式幽默,這也是一種創造。不過在軍隊中,對副職的稱呼一定要把“副”字帶上。把副職當做正職稱呼,那是絕對不允許的。比如,張副團長就是張副團長,你就不能叫張團長,團長只有一個。王副政委、丁副參謀長、熊副主任、江副連長,這些是電視劇《父母愛情》中的稱呼。
有時候,也是為了刻意套近乎,甚至可以通過稱呼的變化,來探查親密程度。有官員舉例說,“有的場合,在稱呼上級領導時只叫名不加姓了,如‘××書記批示了什么,××市長才和我吃過飯,顯得自己和上級領導關系‘不一般”。
有名干部曾自述道,自己在某縣委工作,37歲。鄉鎮和縣直單位的同志覺得:稱“老劉”吧,言外之意還有說人老氣橫秋、提拔無望之嫌:喊“小劉”吧,年紀也確實不太小了,好像也有點不夠尊重;最后只好依官場慣例,呼其官稱了。可我就那點官職,加上我知名度偏低,著實給別人帶來不少麻煩。于是,大家便依慣例稱我為“劉主任”、“劉科長”、“劉秘書”、“劉會計”等等,或干脆送頂高帽——“縣委領導”。
姓氏和職務怎么搭配
2003年,上海特別發過一個紅頭文件,要求黨員干部做到對黨內擔任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黨內行文或報送其他書面材料也要照此辦理,曾得到媒體一度好評。
天津師范大學教授譚汝為發表過一篇文章,專門對官場上流行的簡稱作了分析。一般正職以姓氏加職務稱謂的第一個字,偶爾遇到姓氏諧音難題,如“范局”、“戴校”、“季院”、“史科”等,“此時就最好不要用簡稱了”。
同時,官場中人還特別注意上司姓氏與職務的語音搭配,如趕上傅、富、符、付、戴等姓氏的一把手,你叫“傅廳長”和“戴局長”,誤以為他是副職或臨時代辦呢。那咋辦呢?
據記者了解,一些地方的做法是略去其姓氏,直稱官銜“廳長”或“局長”則可。但是有時候,領導只要扭臉出門走不了三步遠,一些下屬剛才的稱呼馬上改口,“張書記”立馬成了“老張”,“李局長”也變成了“李頭”。
曾有個段子是這樣說的。有一次,一個娛樂界的活動在某某鄉舉行,舉辦方的工作人員一口一個“李湘馬上要到了”,搞得觀眾翹首以待。當最后是一個漢子昂然出現時,人們才明白,工作人員說的是李鄉——李鄉長。還有一鎮長姓莫,有次上級打電話給鎮上,問:“你們哪個鎮長在?”接電話的人說:“我們莫鎮長(陜西方言,莫=沒)。”上級疑惑地反問:“怎么沒鎮長?”接電話的回答道:“就是莫鎮長。”
此外,還有一種名字加同志的叫法。有人說,如在干部交接大會上,彼此稱呼上就常常出現“××同志”,會使語氣頓時加重了許多。這種叫法的重心在“同志”上,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使命準備托付了,或是有什么問題要提醒了。“如果有一天上級領導突然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那么,你就要留神了。”
×廳×處之外,官場上還喜歡稱自己的上司為局座、老板。實際上,田家英他們當年即稱毛澤東為老板。如陳巖《往事丹青》說道:他當學徒時所在的悅雅堂有次下戶采購到一套《三希堂法帖》。正趕上田秘書在,他看了看說: “等定了價,給老板送去。”陳巖解釋,他們稱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邊的人都這樣叫。
在民間,對中央領導人的叫法則充滿了時代感和親切感,“小平你好”和“習大大”這種更親切的稱呼,使對領導人的稱呼一下子有了更新的含義,成為普通人心中的一種標志。 (摘自《廉政瞭望》舒煒/文)
公共權益流失。車位價格猛漲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家庭擁有汽車,而小區車位配比不足,一些業主抱怨,“找個停車位比找媳婦還難。”“轉圈1個小時找不到一個可停之處。”
為了愛車有位可停,許多車主不得不購買車位,然而,這個幾平方米的空地并不便宜。“我買車花了15萬,結果一個停車位要20萬。”武漢徐東某小區黃女士最近在小區買了一個地下停車位,總共5平方米左右,算下來每平方米4萬元,“比別墅還賣得貴。”
武漢洪城物業公司劉經理說,車位價格一路上漲,當初三四萬元的車住如今多漲到十幾萬元、數十萬元,高檔小區的車住抵得上一套小戶型房產。“但市場需求強烈,買車位也得搖號、找關系。”endprint
而業主們高價買來或租來的車位,還有不少其實是開發商低價租用的人防工程用地。湖北金衛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宮步坦介紹,法律規定一定規模的小區必須配置人防工程,由人防部門管理,不能出售,產權不能轉讓。但經過人防部門審批同意可以長期租賃,須繳納一定的費用。
宮步坦說,以武漢某小區為例,開發商以低于1角錢每平方米每天的價格與人防部門簽約,又以20萬元的價格賣給業主。如此算來,小區90個人防工程地下車位為開發商帶來1800萬元收入。就這樣,通過低價租高價轉,開發商獲取了相當可觀的收益。
虛設公攤面積。坐吃“維基”利息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有的開發商為了謀取利益,還在公攤費用上做起了“文章”。比如,有的是先將停車位納入公攤,由全體業主“埋單”,而后,又將車位再次賣給業主。
北京的張先生在西客站旁某知名小區購買了一套91平方米的房子,簽訂的合同上寫著“其中公共部位與公用房屋分攤建筑面積19.78平方米”。但他感覺公攤數字偏大,找來專業測量機構后才得知,這一公攤面積不僅包括樓道、電梯間等,還包括地下車庫、游泳池、小學校等。但開發商并未告知他這一信息。
根據《物權法》規定,如果車位是由已經計入公攤的公共設施改造而來,開發商就對其沒有所有權,車位租賃或出售收益為全體業主所有。但在不少小區,業主入住后,開發商又以數十萬元不等的價格將屬于公攤面積的地下停車位向全體業主銷售。“本屬于我們所有的車位二次賣給我們,開發商糊弄業主的把戲太黑了。”
除了虛設公攤面積以謀取利益之外,小區中諸如房屋公共維修基金、綠化養護費、水箱清洗費等費用,也多以“公益”之名進行了“公攤”。但使用情況常常不容樂觀。家住武漢南湖一小區7棟的胡先生,在2013年底發現該棟頂樓內部公共墻面嚴重滲水,墻面大面積脫落。因而,他多次向物業反映,希望能夠用公共維修基金進行維修,但遲遲未見維修工作啟動。
專家指出,盡管公共維修基金是屬于業主集體的錢,但使用時往往門檻高、程序繁瑣,而資金管理部門也很少主動及時向業主告知用途、結余等信息。
數據統計顯示,北京市自從1998年實行公共維修基金制度以來,截至2013年底累計金額約達到350億元,使用額約8億元,使用比例僅為2.3%。大量資金仍在“睡大覺”。
業內人士透露,部分地區存在坐吃“維基”利息的現象。相關的管理部門將結余基金產生的利息,變成了自己的“小金庫”。南京市的一個小區,曾有近300萬元的公共維修基金利息,被當地住建部門挪作他用。
除此之外,綠化養護費、水箱清洗費等種類繁多的收費,也讓不少業主覺得交的不明不白。
侵占業主權益,賬目從不公開
通過走訪,記者了解到,部分城市的小區物業管理用房被計入了公攤面積,但卻被開發商用于租售獲利,天津、鄭州等城市已出臺規定,明確要求物業管理用房由開發建設單位無償提供,不得計入公攤面積,產權歸全體業主所有。
“小區的游泳池、羽毛球場、網球場等,原本是歸業主集體所有的權益,現在卻被開發商長期侵占。”北京市蓮花橋附近一小區業主告訴記者,小區開發商侵占、轉移業主權益獲得了五六百萬元收益,但并未向業主公布資金去向。
利益糾葛之下,小區物業管理收支狀況并不透明。宮步坦認為,小區收取的相關費用應由業主委員會支配,賬戶要接受業主委員會監管,并向全體業主公開。“現在矛盾聚焦點在于各類收費成為一筆糊涂賬,這些資金的使用亟待公開透明。”“一些物業公司與開發商是‘利益共同體。”湖北省物業管理協會副會長王建國指出,這些公司要么是開發商的下屬企業,要么是開發商選定的企業,當然維護開發商利益,也與開發商私底下簽有協議,從各種費用中抽取好處。
“有的社區也與開發商有利益聯系,其辦公用房也是開發商提供的。”王建國說,有些地方還明確提出了“每100戶不低于20平方米辦公用房”的標準。
專家指出,多重利益相互交織,導致一些社區行政和物業管理問題叢生。只有對癥下藥,清理“糊涂賬”,斬斷相關“利益鏈”,才能維護業主權益。(徐海波梁建強)
路橋費收費怪象頻現
記者調查發現,很多路橋由承建企業負責路橋收費、運營,而站點設置與收費標準是由相關政府部門制定并執行。多年來,一直無法澄清的路橋費成為“糊涂賬”,被人質疑為“利益固化的藩籬”。
——“死灰復燃式”收費。隨著4月8日江西省南昌市大橋管理處發送的一條催繳費用的“溫馨提醒”,已經“停收”6年的過橋費重新開征。南昌市有關部門解釋,路橋費從未取消,只是沒有強制性措施,繳費率很低。但這一解釋顯然不足以讓消費者信服:為何重啟?收費依據、收費程序、收費標準和年限到底合不合法?
——超期收費。本為政府還貸公路大橋的鄭州黃河大橋在1996年就還清了銀行貸款,耐人尋味的是,違規超期收費4年后,又以“經營性收費公路大橋”之名繼續收費。盡管這座大橋已于2012年終止收費,但其超期征收的幾十億元費用是否該向公眾交代清楚?
——“打包”收費。不少地方的年票制路橋費也頗受網友抱怨,這樣的“一刀切”強制收取,對于不經常通過路橋的車主來說很不公平,而城市道路管理條例規定征收費用必須限定為“過往車輛”。
——“滾雪球”收費。從4月1日開始,未繳納一年一度的路橋費的長沙車主,將面臨每日千分之二滯納金的處罰。不少當地車主認為此舉缺乏有效依據。
本不該成為一筆“糊涂賬”
“當前對于城市道路、橋梁的收費時限、金額、方式,都是地方自行規定,每條路投資多少、貸款多少不公開,征收費用去向不明,路橋成了政府和企業的‘搖錢樹。”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認為,路橋收費本不該成為一筆“糊涂賬”。
以長沙市為例,曾有市民問詢:收取的這些錢都花到哪去了?能否公布收支明細?但當地路橋征費維護管理部門卻回復“比較困難”。endprint
一些網友表示,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需要大筆資金,在國家和地方財政“錢袋子”不寬裕的情況下,多方籌款、收費還貸等方式可以理解。但基礎設施的收費年限、收費標準應有科學評估,建立透明公開的公共決策機制。隨意延長收費年數、變更公路性質、捆綁收費、去向不明的“糊涂賬”不應再繼續下去。
記者查閱相關材料了解到,貸款建設城市路橋,而后收費還貸的方式源于基礎設施建設比較落后的特定時期,城市道路管理條例中規定,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門對利用貸款或者集資建設的大型橋梁、隧道等,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向過往車輛(軍用車輛除外)收取通行費,用于償還貸款或者集資款,不得挪作他用。
“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范圍的擴大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眾多城市完全具備建設路橋相應的財政實力,繼續采用貸款加收費的方式,就顯得不合適了。”交通運輸部管理干部學院教授張柱庭說,超期收費等亂象的背后,體現了現有收費公路管理政策法規存在滯后和缺失。
因為對路橋費“違規”收費不滿 部分民眾選擇了與相關部門“對簿公堂”。有媒體報道,律師孫農和車主周潤凡曾就珠海路橋通行費年票涉嫌超期征收一事狀告廣東省物價局和省交通廳;在東莞經營一家貨運公司的蔣明亮,曾因質疑東莞實行的路橋費年票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年審是否應該與年票掛鉤”等問題,將收費部門起訴到法庭。
多地市民反映,路橋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產品的運輸成本和生活成本。北京的京通快速路兩公里收費5元錢就頗受詬病,專家指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口分流,沒有起到緩解城市“肥胖病”的作用。一些企業界人士認為,“高額”的路橋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城市發展的障礙,地方政府還應多算“長遠賬”。
改革必須突破“利益的藩籬”
與一些城市仍在變換各種途徑征收路橋費不同,不少城市已經開始算“民生大賬”,在取消收費方面做出了“讓利于民”的探索。
為了城市發展和疏通黃河兩岸交通梗阻,降低市民出行成本,山東濱州市人民政府與山東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協商決定,于今年1月31日起對濱州籍(魯M)載客和載貨機動車輛實行免費通行G205濱州黃河大橋。由此給山東高速集團造成的通行費收入損失,由濱州市政府給予經濟補償。除了濱州,廣西柳州、天津、遼寧撫順等城市也相繼取消了路橋費。
張柱庭認為,城市取消路橋收費應成為一種趨勢,把這當做一項重要的民生問題加以解決。在完全有能力解決的情況下,一些城市之所以繼續選擇收費,不少是因為不愿放棄源源不斷的收入。
“路橋作為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不能從建設到維護全由市民埋單。”張柱庭建議城市路橋的收費賬目實行信息全公開制度,從國家層面出臺相關的法律,用于規范各地路橋收費,同時明確監管主體,及時查處相關問題。“對于有些地方到了限定時間卻繼續征收的情況,這就需要在開展公眾監督的同時,強化相應的審計和自上而下的監管。”朱列玉說。(摘自《新華每日電訊》高潔等/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