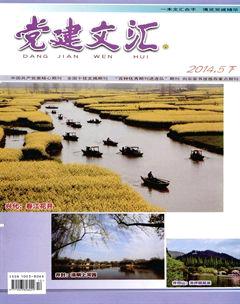傳統文化教育不能“得其形而遺其神”等
晉浩天等
近日,廣東東莞一工程師劉先軍“過勞死”的報道,引發輿論強烈關注。記者追蹤采訪發現,超時加班在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存在普遍性。
當“加班文化”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被奉為企業管理的“先進經驗”,劉先軍的“過勞死”就不會是類似悲劇的終點。實際上,盤點近年來發生的勞動者“過勞死”案例就會發現,超時加班正成為摧殘勞動者生命健康的主要元兇,在多數“過勞死”案例的背后,都能發現勞動者加班或“被加班”的魅影。
那么誰能幫助勞動者從無休止的加班中解脫出來,維護其正當合法的休息休假權益?答案只能寄望于對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完善,以及各項法律法規在現實中的嚴格執行。
比如,根據《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的相關規定,用人單位違反規定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對企業的罰款“按照受侵害的勞動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標準計算”。這意味著,新聞中提到的劉先軍生前供職的東莞市德創實業有限公司,其最終面臨的最大處罰金額也不會超過5.5萬元。可是,幾個企業會把如此輕微的違法代價放在眼里?
現階段必須對相關的法律條款進行完善,加大企業的違法成本,提高對違法企業的懲罰力度,讓其不敢以任何形式強制勞動者加班。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會倡導一種“準時下班文化”,鼓勵企業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向效率要效益,而不是向加班要效益。當“準時下班”成為一種社會共識,成為所有企業領導和管理者的一種法律、制度與道德自覺,勞動者“被加班”問題才會得到解決或緩解。(摘自《重慶商報》苑廣闊/文)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一首《離騷》,讓某高校文藝學專業研究生龍旭回憶起自己的高中生活,“同學們搖頭晃腦,背著《離騷》,很有古風。只可惜,當初背得滾瓜爛熟的課文,現在基本都‘還回去了。”
記者隨后采訪了部分在校大學生和剛剛走出大學的畢業生們,絕大多數受訪者均表示“背不出來”。“早忘了”“不會背”“只記得一點點”是記者聽到最多的回答。
面臨傳統文化日漸遇冷的問題,教育部日前公布了《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詳細闡述了從小學到大學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具體要求,強調逐步落實課程標準修訂和開發,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課程和教材體系中。
對此,專家學者紛紛表示,將傳統文化融入課堂和教育體系迫在眉睫。
那么,傳統文化的傳承究竟遭遇了怎樣的困境?新形勢下,我們又該如何科學合理地將其融入課程?
“伴隨著背完就忘的古詩詞、古文等,中華文化這個‘模糊的概念似乎在我的生活中漸行漸遠。”當被問及“在校學到了多少中華文化”時,龍旭如此回答。
龍旭感嘆道:“除了一些耳熟能詳的‘床前明月光,‘誰知盤中餐外,現在的大學生還有多少能原文背出《出師表》《蘭亭集序》?還有多少能完全理解文章的含義?真的不多。”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劉運峰的親身經歷佐證了龍旭的想法:“十年前我在英國做訪問學者,恰逢中秋,大家在一起聯歡,我書寫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位研究生畢業不久的朋友說,‘你怎么記得那么牢,我當時也背過,但考完就忘了。”
古代文學是傳統文化的主要體現之一。“不進腦”“不走心”,不僅是古代文學教育的困境,也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尷尬處境。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坦言,從小學到高中,語文課程中“古詩詞和文言文的內容大約占課文總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大量的古詩詞和文言文進入語文課堂,為何收效甚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教授認為,當下的教育理論與方法都有反思的空間。“中華文化是道器合一,核心是人格論與價值論,即培養人才首先是做人的根本價值,然后延及知識系統,而我們現在是‘西體中用,即采用西方教育的知識論與工具論來對待中華文化,導致‘得其形而遺其神。”
袁濟喜進一步解釋:“從六藝之學到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都是價值之學與知識體系的結合,而現在文史哲分科的教育體系與傳統文化體系并不相同,因此,采用這種現代分科教育,及其學科體制下的知識論去從事中國古典詩文教育,效果不會太好。”
“現階段,我們主要是通過學校教育來傳承傳統文化。孑L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意思便是根據人生的不同階段從事教育與熏陶,主要應因材施教。”袁濟喜對《綱要》中從課堂人手的分學段文化教育模式深表贊同。
“基礎教育,主要是依據人性的初始階段,應以文學熏陶為主。青少年階段應加強中華經典文化中的思想性與哲理性,以及文明禮儀方面的教育。大學階段。則可以在經典的選擇與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趨于專深。”袁濟喜說。
(摘自《光明日報》晉浩天/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