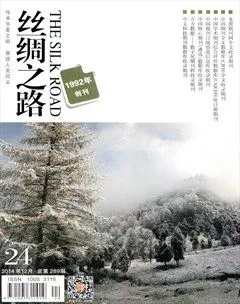蒼龍馱佛度眾生
與門庭若市的漢陽歸元寺相比,武昌寶通寺似乎有些冷清。歸元寺地處偏僻,寶通寺卻身居鬧市。一域之“佛情”如此大相徑庭,這冷清便有點耐人尋味了:是沒落還是堅守?是淡定還是迂腐?是從容還是無能?是不作為還是不屑為……糾結間,游寶通寺的往事便浮上心頭。
寶通寺乃荊楚名剎,位于武昌洪山南麓,其建筑布局有點“寺裹山”意味,殿宇樓臺,依山就勢,層巒疊起,直入云霄,氣勢恢宏,十分壯麗。
更與眾不同的是,它還是一座被蒼龍馱起的佛寺。武漢地理有條寫意龍脈:由漢陽到武昌,自西向東依次有梅子山、龜山、蛇山、洪山、珞珈山、磨山、喻家山。這一連串的峰巒山谷,宛如一條巨龍橫臥大江南北。龍頭為喻家山,龍尾則是月湖之濱的梅子山,而洪山恰好處在巨龍中段,寶通寺便猶如騎在龍背上。蒼龍馱起,普度眾生,很難說當初的選址沒有玄機。
此外,寶通寺還是一座歷史悠久、屢毀屢建的皇家寺院。
此寺始建于南朝劉宋時期,距今約1600年,初名“東山寺”。
唐朝貞觀年間,“鄂國公”尉遲敬德曾奉命在此進行擴建,并監制巨型鐵佛一尊,旋即改寺名為“彌陀寺”。
南宋末年,為避元軍兵燹,宋理宗詔令湖北隨州大洪山靈峰寺南遷至武昌東山,與彌陀寺合并,將東山改稱洪山,賜寺名“崇寧萬壽禪寺”。
元末,萬壽禪寺毀于戰火,明代重建,規模大增,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廷為其更名為“寶通禪寺”。
明末,寶通寺又遭毀壞。清康熙年間重修增制,規模進一步擴大。咸豐末年再度毀于戰火。現存建筑大多是清末保存下來的。
歷史上,寶通寺曾發生過凈土宗、禪宗、密宗等多宗會聚,也曾得到唐文宗等十位皇帝和六位王侯的大力護持,即使唐武宗一手制造的席卷全國的“會昌法難”也沒能毀掉它。寶通寺委實堪稱我國寺廟中罕見的不倒翁。
往事如煙,記得那天是乘公交車去的,一到洪山站即是山門。寶通寺山門面臨武珞路,雖也是傳統的“山”字形結構,但卻是黃墻紅瓦,加上大門兩邊墻上“莊嚴國土,情有利樂”的楹聯,使人一望而知它乃是皇家氣派。門額上的“寶通禪寺”四個鎦金大字,為已故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著名書法家趙樸初先生題寫,雄渾有力,禪意盎然。
步入山門,即見院落寬廣,古樹參天。偌大的庭院內有放生池,池上橫跨一石橋,曰“圣僧橋”,相傳原為木質,后由云游到此的無念祖師改建成石橋。
過橋數十步為彌勒殿,亦稱天王殿或接引殿。殿前立石獅一對,身高丈余,一戲繡球,一抱幼獅,刀法細膩,神態可掬。殿左側有大鐵鐘一口,乃咸豐年間舊物,由城內鐵佛寺遷來,形體莊重,花紋秀麗,四周鑄有自揖性銘文:“皇圖鞏固,帝道假昌,河清海宴,天地承平。”
殿內供奉如常,主尊還是那位豁達樂觀、笑口常開、人緣極佳的彌勒佛。這位未來佛左右,立有觀音和地藏王菩薩塑像,兩壁有高大威猛的四大天王,背后為造像威嚴的佛寺守護神韋馱。
出彌勒殿拾級而上,即是每寺必不可少的大雄寶殿。雖也是格式化建筑,但殿內亦有大鐵鐘一口。此鐘不僅造型古樸,還連著一段傳奇佛緣。鐘身形體龐大,重約萬斤,鑄于南宋末年,四周亦有銘文,曰:“皇帝萬歲,重臣千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時人譽之為“萬斤鐘”。鐘聲雄渾悠揚,銘文可笑堪悲,耳聞目睹,一段700余年前的傳奇佛緣煙云再現。
唐文宗寶歷年(826),洪州(今江西南昌)開元寺和尚善慶云游至隨州大洪山,并在那里建起靈峰寺。九年后(835),善慶和尚圓寂前毅然剁下自己的雙足留于寺內,表示自己升天后仍要繼續為鄉人利益奔走。事跡感天動地,文宗李昂聞訊欽賜法號“慈忍大師”,敕雙足為“佛足”,留鎮山門,還御書了“幽濟禪院”的匾額送給靈峰寺。這雙“佛足”便成了靈峰寺聞名天下的鎮寺之寶。
到了南宋端平年間,金兵不斷南犯,靈峰寺及“佛足”隨時都有可能毀于戰火,時任荊湖制置使的孟珙便奏請宋理宗趙昀頒發帑幣(公費),遷至武昌東山彌陀寺。孟珙乃南宋名將,屢敗金兵,又是將門之后,年輕的趙昀(比孟整整小10歲)豈有不允之理?
嘉熙四年(1240),遷移工作在孟珙主持下宣告完成。為紀念這一“盛世”壯舉,叩謝浩蕩皇恩,歌頌趙昀領導下的殘破河山“國泰民安”,孟珙特鑄“萬斤鐘”立此存照。
誰料,“佛足”遷到“萬壽禪寺”后,終未躲過掠劫,顛沛流離,以致永無歸期。
事因元世祖忽必烈的搶班奪權而起。
相傳,當年驅虎狼百萬南犯的忽必烈曾駐扎武昌元興寺。一天,他登高東望,遙見洪山山頂華光籠罩,以為天降祥瑞,預示真龍出世。詢問左右,始知那里是存放慈忍大師“佛足”的崇寧萬壽禪寺。其時,忽必烈正在所謂“潛邸”期間,不禁驚喜萬分。
1260年,忽必烈長兄元文宗去世。為了搶在四弟阿里不哥之前奪取大位,星夜由武昌趕往京師的忽必烈,命令萬壽禪寺方丈則翁實禪師函封“佛足”扈從至京師,特命安置于秘宇,嚴加供奉,企圖利用“佛足”達到目的。
等其登上九五之尊,成為元世祖后,便下旨護送“佛足”完璧歸趙,美其名曰“還山”。不料途經許州(今河南許昌)時,“佛足”突然變得重如千斤,抬都抬不動,似乎再也不愿往前走了。于是,則翁實禪師派人向元世祖匯報,忽必烈大驚,即令在許州原地建寺,供奉“佛足”。
凡事有因緣,無巧不成書。戰亂使“佛足”南遷北徙,最終也未能回歸萬壽禪寺,但卻成就了一段歷史傳奇,為佛教在中原大地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繼隨州之后,中原地區先后產生了武昌、許昌兩座洪山,客觀上也為中國人文地理增添了一段佳話。
除“萬斤鐘”外,寶通寺大雄寶殿與天下佛寺正殿并無二致。金碧輝煌的殿堂供著三位主尊,分別是釋迦牟尼和文殊、普賢菩薩。佛祖居中,文殊、普賢列身后左右,兩廂有十八羅漢。殿中有歸元寺住持昌明法師所書楹聯一副:
古今來宗教幾何自由平等無如我佛;
東西國文明進化言行高尚獨讓法王。
法師所云通俗易懂,而今細品,怎不感慨萬千?想那俗男俗女,求神拜佛,所為何來?升斗小民,螻蟻眾生,無非祈福消災,求個平安,我佛豈不慈悲為懷?而那權奸巨貪,惡吏碩鼠,也希冀菩薩保佑,何異于癡心妄想?
出大雄寶殿后門登山,原有“鐵佛殿”,蓋因殿內有鐵佛二座而得名。此殿原為方丈講經說法處,據說,殿下石砌暗道曾發現過方丈說法所用的錫杖。此外,殿中還有銀質舍利塔一座,高8寸,寬3寸,仿緬甸大金塔式樣制成。只可惜此殿在新中國誕生前夕毀于大火,有遺址廢墟,無文物法寶。
再往上即是著名的法界宮,它是本埠唯一一座佛教密宗建筑物。此宮建于20世紀30年代初,為寶通寺前住持持松日本留學歸來,依唐密金剛部“五曼荼羅”形式建造,旨在恢復中國密宗。殿內原設木質密宗壇城,雕刻鏤空,玲瓏別致,可惜已遭破壞。現屋面覆以黃琉璃瓦,并以五亭結頂以示東、西、南、北、中五佛方位。各亭均為鏤空大屋脊,飛檐蟠爪,富有民族特色。殿前廊柱,刻有法輪十字羯摩杵,殿基四周刻有雙層蓮瓣,殿前階下為三孔拱橋,橋外雙亭侍立,亭、殿、橋格局別致,相映成趣。
殿右側有華嚴洞,深丈余,洞上建有華嚴亭,供游人休憩。
離開法界宮,我們爬上了山頂。一座高聳入云的雄偉古塔隨即出現在眼前,它就是我少年時代仰慕已久的洪山寶塔。
洪山寶塔原名臨濟塔,又稱寶通塔,乃元代住持贈緣寇為紀念開山祖師慈忍法師所募建,至元十七年(1274)動工,至元二十八(1285)年竣工,歷時11年。此塔為七級八方,磚石疊成,身高13丈3尺,基寬11丈2尺,頂高1丈3尺,以其雄偉秀麗飲譽天下。
據志書記載:原建時每層外圍均有木質飛檐和護欄,塔下周圍為磚木結構的圍廊,每層八角,墜以風鈴,設計之精巧,工程之浩大,堪稱荊楚第一。雖經多年風雨侵蝕,但歷代累有修補。僅清朝同治十年(1871)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重修,工程至1874年才完成。當時為了長久之計,易木欄為鐵欄,塔下圍廊改為八方石階,塔頂則依原樣增高5尺,且用文筆峰式鑄銅結頂,工穩大氣,愈加宏偉。然而,解放前,此塔早已損壞不堪,新中國成立后,武漢市政府于1953年對其進行了全面維修,上下內外,整修一新,使千年古塔再次煥發青春。可是,“文革”十年中,寶塔又橫遭人為破壞,塔身被劃得傷痕累累,基座條石亦有脫落,各窗鐵欄更是大部分銹損。
我們由底層拱門而入。沒想到,一股十分難聞的尿臊味迎面撲來,再拾級盤旋而上,又不時踩到人屎鳥糞,看來已是很久無人清掃了。心中不禁起疑,難道這就是自己渴望一游的地方?
寶塔雖是舶來建筑形式,但融于本土文化后便產生了某種圖騰意義,有人甚至認為除了鎮邪之外,它還象征陽元崇拜。不管是古印度的原始本義,還是故國神州的延伸別義,有一個共同點則是沒有疑問的,那就是對它理應有敬畏之情。然而,眼前之景象卻令人格外痛心,我們的敬畏之情哪里去了呢?
我們掩口捂鼻,好不容易爬到頂層。“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憑窗遠眺,煙波浩淼的萬里長江,波平如鏡的千頃東湖,層巒疊翠的迤邐群山,長虹臥波的巍巍大橋,南維高拱的天下名樓,鱗次櫛比的三鎮城區……一望無際的楚天風光,無不盡收眼底。面對如此大好河山,你怎能無動于衷?
當年寶通寺之游以在洪山寶塔頂上飽覽湖光山色作結,仿佛一篇搖曳多姿的文章卻差一個滿意的結尾,總是那么意猶未盡,如今多少年過去,偶爾想起仍不免感慨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