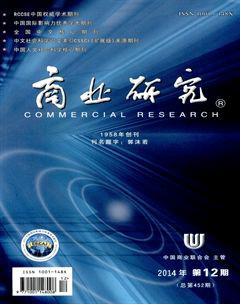人口密度、產業結構與城鎮化質量
李少林
摘要:如何突破資源環境的雙重約束是推動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質量提升的當務之急。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中國30個省會城市的面板數據,將衡量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和衡量生態環境的城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作為反映城鎮化質量的指標,利用靜態和動態面板計量回歸模型實證研究了城市人口密度、產業結構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總體上城市人口密度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呈現“U”型關系;城鎮化質量內生于地區產業結構;市場化改革對城市生態環境的影響顯著為正。
關鍵詞:人口密度;產業結構;城鎮化質量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自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從179%增至537%,年均增速為102%,但城鎮空間分布與規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的出現,使得新型城鎮化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匹配,城鎮化質量的提升成為當務之急。2013年3月,《中國經濟周刊》和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聯合發布的《中國城鎮化質量報告》認為,城鎮化除了重點實現人口城鎮化以外,還須突出空間、土地、經濟、產業以及生活質量的城鎮化。城鎮化應和資源環境承載力、人口就業能力等相匹配。
城鎮化的最顯著特征是農業人口市民化帶來的城市人口密度的變化,以及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之間的結構水平隨之出現調整,亦即產業結構的變遷。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不僅需要對人口分布、產業結構調整的經濟影響進行評估,而且還需考慮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等資源環境約束問題。因此,新型城鎮化是在多重約束下推進的,其質量提升依賴于要素流動、資源供求和環境治理的協同發展,反映在經濟與環境指標上,城鎮化質量通常體現在收入差距和碳排放等方面。陳明(2012)從內涵、研究對象、評價模型等方面對城鎮化質量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系統梳理,認為對勞動力資源的“二次開發”和農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提高是解決城鎮化引致的深層次矛盾的基礎。徐林、曹紅華(2014)認為新型城鎮化更應當注重城市生態的可持續性、宜居性等,并提出“星系模型”,構建了一整套評價體系,實現了新型城鎮化相關概念的關聯分析和可操作性。
在相關文獻中,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收入差距成為國內學者重點研究的領域之一。刑春冰(2008)基于2005年人口普查數據研究了農民工和城鎮職工的收入差距原因,認為兩者的教育水平是最主要的因素。溫興祥(2014)基于2008年城鄉勞動力流動數據,采用無條件分位數回歸和RIF回歸分解方法研究了外來居民和本地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在整個收入分布上,兩者的差距一直存在,且隨著收入的增加逐步擴大;人力資本與行業分布的差異是導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學術界刻畫城市環境一般使用城市碳排放的總量指標——“碳足跡”,其包括企業機構、產品或者個人通過交通運輸、生產消費及各類的生產過程所引起的溫室氣體的總和。在研究城鎮化質量影響因素的國內外文獻中,通過核算碳足跡來量化城市環境的方法被廣泛采用(羅運闊等,2010;張兵等,2011)。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員認為,居住在人口密集城市的家庭碳足跡遠小于全美的平均值,意味著提高人口密度并不能有效降低碳排放①。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陸銘(2014)認為重點關注的是要不要限制大城市的發展,是就地城鎮化還是促進人口進入大城市?其觀點是中國的大城市人口規模還將進一步提高,需著力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在人口密度與城市環境治理的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主要關注的是人口密度和碳排放的關系。Norman等(2006)和Ishii等(2010)的研究結論認為,城市密度對碳排放的影響呈現“U”型,中等密度能夠最大限度地利于碳減排。柴志賢(2013)基于1999-2008年中國30個省會城市的面板數據研究了人口密度、發展水平等變量對人均碳排放的影響,結果發現隨著人口密度的上升,人均碳排放先降后升,而收入水平和人均碳排放的關系符合“環境庫茨涅茨曲線”的“倒U型”特征。研究還發現上述變量的關系存在著區域差異,因此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應區別對待。
通過以上文獻分析可以看出,現有文獻具有以下的某種局限性:一是研究城鎮化質量僅單獨考慮了經濟指標或環境指標;二是對于制度性因素分析不足;三是對于人口、產業的分析未能置于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下。區別于以往研究文獻,本文擬將城鎮化質量界定為經濟質量和環境質量兩個方面,前者指的是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反映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后者指的是城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反映城市生態環境水平。基于此,本文以城市全年用電總量作為能源消耗的代表,在資源環境的雙重約束下,探討城鎮化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著重研究人口密度、產業結構和能耗、市場化改革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并基于研究結論提煉出推動城鎮化質量提升的政策意涵。
二、模型設定、變量說明與描述統計
為探討城鎮化質量的影響因素,本部分擬從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兩個方面對其進行計量模型設定,構造城鎮化質量的衡量指標和變量說明,并對變量間的相關性進行簡單觀測,為實證研究奠定理論模型和數據基礎。
(一)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靜態和動態面板估計方法對資源環境約束下的城鎮化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以此找出推動城鎮化質量提升的政策工具。由于居民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棘輪效應”,我們將恩格爾系數影響因素回歸方程設定為動態面板形式,以考察其可能存在的滯后因變量的影響;而對于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而言則不存在類似的滯后關系,因此我們采用普通的面板回歸模型。本文所需估計的具體計量模型設定如式(1)和式(2)所示:
ECi,t=α0+α1ECi,t-1+α2lndensityi,t+α3structurei,t+α4lnenergyi,t+α5lnmarketizationi,t+σi+εi,t(1)endprint
greeningi,t=β0+β1lndensityi,t+β2structurei,t+β3lnenergyi,t+β4lnmarketizationi,t+ηi+τi,t(2)
其中,i表示省會標識,t表示年份;EC和greening分別是被解釋變量,即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用來衡量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和城市生態環境,代表城鎮化質量;lndensity和structure是本文主要關注的解釋變量,分別代表城市市轄區人口密度和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其它控制變量包括:城市市轄區全社會全年用電總量,代表能源消耗量(lnenergy);市場化改革指數,代表制度變量(lnmarketization)。σ和η分別表示對應回歸方程的城際固定效應、ε和τ分別代表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1)恩格爾系數。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表示城鎮居民人均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生活性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能夠反映出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從經濟層面體現出城鎮化的質量高低。恩格爾系數越大,表明收入水平較低,意味著該城市居民較為貧窮。本文的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的數據是根據《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30個省會城市2001-2012年的城鎮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和人均生活消費性支出的數據計算得到,其中2002年數據是2001年和2003年數據的加權平均數,其余年份個別缺失數據是依據前后兩年數據的加權平均而得。(2)城市市轄區的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城市綠化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生態環境狀況,因此本文將其作為生態環境指標的代表,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數據采集區間為2001-2012年。
解釋變量:(1)人口密度。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轉移農民工市民化后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將會對城市的資源環境帶來一定程度的壓力,因此將首當其沖地影響到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質量。為突出大城市的典型性,本文選取中國30個省會城市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同花順iFinD金融數據庫》,單位是人/平方公里,數據區間為2001-2012年。(2)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對于城市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具有重要影響,本文采用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表示各城市產業結構變動狀況,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控制變量:(1)能源消耗。在分析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林伯強(2003)認為電力消費更能夠準確衡量能源消費情況,王火根、沈利生(2007)也采用此方法衡量了能源消費量,故本文沿用這一做法,將中國30個省會城市全年用電總量作為城市能源消耗的代表,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單位換算為億千瓦時;(2)市場化指數。市場化改革有利于促進要素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有利于提高城鎮化質量。由于數據可得性及省會城市在全省的核心地位,本文將各省市的市場化指數近似作為省會城市的市場化指數,并將其視為影響城鎮化質量的制度變量。其中,2001-2010年數據直接取自樊綱、王小魯和朱恒鵬主編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2011-2012年市場化指數的數據則是依據前兩年數據的移動加權平均近似得到。
(三)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根據上述指標構建和數據來源,為便于回歸結果的解釋,我們對絕對量指標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并從均值、標準誤、最小值和最大值等特征對研究數據進行了簡單描述統計,樣本為2001-2012年中國30個省會城市,共計360個樣本的平衡面板數據。
(四)城鎮化質量與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的散點圖
在進行實證研究之前,有必要對核心變量的相關關系進行簡單透視。我們分別畫出了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與人口密度、產業結構的散點圖(參見圖1(a)、圖1(b)、圖2(a)和圖2(b))。從圖1(a)的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與人口密度的散點圖能夠看出,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大,恩格爾系數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表明人口密度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同理,從圖1(b)可以看出,隨著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上升,意味著兩者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從圖2(a)可以看出人口密度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無明顯的相關性;從圖2(b)則可以看出,隨著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呈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兩者存在較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表明隨著工業在產業結構中比重的上升,工業發展對城市生態環境造成了負面影響。
三、計量回歸結果與分析
根據本文關于城鎮化質量的界定,本部分將采用動態面板估計與靜態面板估計兩種方法分別對城鎮化的經濟質量和生態環境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
(一)動態面板系統GMM估計方法
由于非觀測的城市區域固定效應或者存在聯立的內生性等問題,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很可能是內生的,除此之外的諸如能源消費量、市場化指數等變量也有可能與被解釋變量存在著聯立內生性的問題。表2和表3給出了待估計模型的各變量的皮爾遜積差相關系數矩陣,從中可以看出各個變量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相關性。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所提出的系統GMM方法,可以克服模型(1)和模型(2)中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能夠獲得解釋變量的一致性估計結果。
(二)恩格爾系數影響因素的動態面板系統GMM估計
為便于對動態面板估計方法進行對比,我們還對計量模型(1)進行了混合OLS與固定效應的估計,估計結果參見表4的第2列和第3列。由系統GMM估計結果的α1(08015、07825)恰好在混合OLS估計值(08805)與固定效應估計值(06441)的區間內。根據表4的動態面板系統GMM具體估計結果,我們認為第5列的估計結果較為穩健,我們將按照該回歸結果進行分析和解釋。endprint
首先,從系統GMM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當期城市市轄區人口密度提高10%,會使得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提高2%,意味著當期人口越密集的城市,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水平將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這表明城市規模并非越大越好,當城市人口超越了城市承載力,將導致城鎮化質量下降;上一期城市人口密度增大10%將導致恩格爾系數下降169%,表明上期農民工流入城市,將對當期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產生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城鎮化進程使得農民工能夠在短期獲得比農村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可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但隨著當期人口密度的增大,可能由于人才、資源和房價的競爭性壓力等原因,導致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導致“規模報酬遞減”的效應。總體來看,人口密度并非越大越好,應當適度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切實降低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該結論印證了城市具有最優規模的結論(王俊,2014)。
其次,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與恩格爾系數呈現出正相關關系,但是這種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欠發達城市的第二產業可能為經濟增長和居民生活質量提高貢獻較大,而發達城市則是以第三產業為主,恩格爾系數可能較低。因此,各地區第二產業比重對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沒有顯著的影響。
最后,控制變量方面,能源消耗對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影響為負,但是在統計上并不顯著,表明高能耗的發展方式并不能夠提高城鎮化質量;市場化改革對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影響同樣不顯著,意味著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對于促進人口和生產要素流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城鎮化質量具有重要作用。
(三)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影響因素的靜態面板估計
由于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不具有動態特征,且研究對象為中國30個省會城市,因此我們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估計人口密度、產業結構等因素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的影響,所使用的是EVIEWS60軟件。估計結果參見式(3),括號內數字為相應估計系數的標準差。從式(3)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均具有負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顯著;全社會用電總量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具有正向影響,意味著能耗越大,城市越應注重保護生態環境;市場化改革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省會城市的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運行已初步顯現效果。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在資源環境雙重約束的分析框架下,將人口密度、產業結構、能源消耗、市場化改革等變量納入城鎮化質量的影響因素體系,并將城鎮化質量界定為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兩個層面,分別構建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變量作為城鎮化質量衡量指標的回歸方程,對2001-2012中國30個省會城市的數面板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1)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具有棘輪效應。總體來看,恩格爾系數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亦即食品支出在生活性消費支出中的比重逐年降低,且城市人口密度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呈現“U”型關系;上一期城市人口密度降低了本期恩格爾系數,而本期人口密度則提高了恩格爾系數,表明為達到理想的城鎮化質量,人口密度過小或過大都是不可取的,適中的人口密度可使得城鎮居民具有較高的生活水平。(2)產業結構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不顯著,表明不同地區的城鎮化質量內生于該地區的產業結構,主導產業的不同是引起居民生活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3)市場化改革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的影響顯著為正,顯示出城市環保產業的市場機制運行已初見成效。
根據上述實證研究結論,為促進以恩格爾系數為代表的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以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為代表的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提升,本文建議:(1)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人口的自由流動。(2)根據不同區域的產業結構特征推行差異化的城鎮化發展戰略,推行高效節能的經濟發展模式。(3)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力推動環保產業發展和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提升工作,構建環境宜居城市。(4)著力推行以人為本、資源節約的環境友好型的城鎮化思路,優化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布局,穩步提高城鎮化質量,避免盲目追求速度的城鎮化,使得城鎮化不僅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陣地,更是破解資源環境瓶頸的有力抓手,進而實現人類生存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注釋:
① 資料來源:http://env.people.com.cn/n/2014/0113/c1010-24100312.html。
參考文獻:
[1] 魏后凱,王業強,蘇紅鍵.中國城鎮化質量報告[J].中國經濟周刊,2013(3).
[2] 陳明.中國城鎮化發展質量研究評述[J].規劃師,2012(7):5-10.
[3] 徐林,曹紅華.從測度到引導:新型城鎮化的“星系”模型及其評價體系[J].公共管理學報,2014(1):65-74.
[4] 陸銘.中國的城市化應謹防“歐洲化”[N/OL].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4-05-06/114155424.html.
[5] 羅運闊,周亮梅,朱英美.碳足跡解析[J]. 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123-127.
[6] 張兵,王正,朱超.城市碳足跡定義與計算方法研究[J].山西建筑,2011,37(32):185-186.
[7] Norman, J., H. L. MacLean.Comparing High and Low Residential Density: Life-cycle Analysis of Energy Use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2006,132(1):10-21.
[8] Ishii S, Tabushi S, Aramaki T. Impact of Future Urban Form on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Utsunomiya, Japan[J].Energy Policy,2010,38(9): 4888-4896.
[9] 溫興祥. 城鎮化進程中外來居民和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J].人口研究,2014,38(2):61-70.
[10]林伯強.電力消費與中國經濟增長:基于生產函數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11):18-27.
[11]王火根,沈利生.中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空間面板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12):98-107.
[12]Arellano, M. and O. Bover.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1): 29-51.
[13]Blundell, R. and S. Bond.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 115-143.
[14]劉修巖,殷醒民.空間外部性與地區工資差異: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學(季刊),2008,8(1):77-98.
[15]王俊.擁擠效應、經濟增長與城市規模[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4,12(1):46-52.endprint
首先,從系統GMM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當期城市市轄區人口密度提高10%,會使得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提高2%,意味著當期人口越密集的城市,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水平將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這表明城市規模并非越大越好,當城市人口超越了城市承載力,將導致城鎮化質量下降;上一期城市人口密度增大10%將導致恩格爾系數下降169%,表明上期農民工流入城市,將對當期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產生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城鎮化進程使得農民工能夠在短期獲得比農村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可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但隨著當期人口密度的增大,可能由于人才、資源和房價的競爭性壓力等原因,導致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導致“規模報酬遞減”的效應。總體來看,人口密度并非越大越好,應當適度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切實降低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該結論印證了城市具有最優規模的結論(王俊,2014)。
其次,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與恩格爾系數呈現出正相關關系,但是這種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欠發達城市的第二產業可能為經濟增長和居民生活質量提高貢獻較大,而發達城市則是以第三產業為主,恩格爾系數可能較低。因此,各地區第二產業比重對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沒有顯著的影響。
最后,控制變量方面,能源消耗對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影響為負,但是在統計上并不顯著,表明高能耗的發展方式并不能夠提高城鎮化質量;市場化改革對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影響同樣不顯著,意味著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對于促進人口和生產要素流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城鎮化質量具有重要作用。
(三)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影響因素的靜態面板估計
由于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不具有動態特征,且研究對象為中國30個省會城市,因此我們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估計人口密度、產業結構等因素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的影響,所使用的是EVIEWS60軟件。估計結果參見式(3),括號內數字為相應估計系數的標準差。從式(3)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均具有負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顯著;全社會用電總量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具有正向影響,意味著能耗越大,城市越應注重保護生態環境;市場化改革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省會城市的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運行已初步顯現效果。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在資源環境雙重約束的分析框架下,將人口密度、產業結構、能源消耗、市場化改革等變量納入城鎮化質量的影響因素體系,并將城鎮化質量界定為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兩個層面,分別構建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變量作為城鎮化質量衡量指標的回歸方程,對2001-2012中國30個省會城市的數面板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1)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具有棘輪效應。總體來看,恩格爾系數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亦即食品支出在生活性消費支出中的比重逐年降低,且城市人口密度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呈現“U”型關系;上一期城市人口密度降低了本期恩格爾系數,而本期人口密度則提高了恩格爾系數,表明為達到理想的城鎮化質量,人口密度過小或過大都是不可取的,適中的人口密度可使得城鎮居民具有較高的生活水平。(2)產業結構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不顯著,表明不同地區的城鎮化質量內生于該地區的產業結構,主導產業的不同是引起居民生活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3)市場化改革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的影響顯著為正,顯示出城市環保產業的市場機制運行已初見成效。
根據上述實證研究結論,為促進以恩格爾系數為代表的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以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為代表的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提升,本文建議:(1)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人口的自由流動。(2)根據不同區域的產業結構特征推行差異化的城鎮化發展戰略,推行高效節能的經濟發展模式。(3)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力推動環保產業發展和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提升工作,構建環境宜居城市。(4)著力推行以人為本、資源節約的環境友好型的城鎮化思路,優化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布局,穩步提高城鎮化質量,避免盲目追求速度的城鎮化,使得城鎮化不僅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陣地,更是破解資源環境瓶頸的有力抓手,進而實現人類生存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注釋:
① 資料來源:http://env.people.com.cn/n/2014/0113/c1010-24100312.html。
參考文獻:
[1] 魏后凱,王業強,蘇紅鍵.中國城鎮化質量報告[J].中國經濟周刊,2013(3).
[2] 陳明.中國城鎮化發展質量研究評述[J].規劃師,2012(7):5-10.
[3] 徐林,曹紅華.從測度到引導:新型城鎮化的“星系”模型及其評價體系[J].公共管理學報,2014(1):65-74.
[4] 陸銘.中國的城市化應謹防“歐洲化”[N/OL].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4-05-06/114155424.html.
[5] 羅運闊,周亮梅,朱英美.碳足跡解析[J]. 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123-127.
[6] 張兵,王正,朱超.城市碳足跡定義與計算方法研究[J].山西建筑,2011,37(32):185-186.
[7] Norman, J., H. L. MacLean.Comparing High and Low Residential Density: Life-cycle Analysis of Energy Use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2006,132(1):10-21.
[8] Ishii S, Tabushi S, Aramaki T. Impact of Future Urban Form on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Utsunomiya, Japan[J].Energy Policy,2010,38(9): 4888-4896.
[9] 溫興祥. 城鎮化進程中外來居民和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J].人口研究,2014,38(2):61-70.
[10]林伯強.電力消費與中國經濟增長:基于生產函數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11):18-27.
[11]王火根,沈利生.中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空間面板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12):98-107.
[12]Arellano, M. and O. Bover.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1): 29-51.
[13]Blundell, R. and S. Bond.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 115-143.
[14]劉修巖,殷醒民.空間外部性與地區工資差異: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學(季刊),2008,8(1):77-98.
[15]王俊.擁擠效應、經濟增長與城市規模[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4,12(1):46-52.endprint
首先,從系統GMM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當期城市市轄區人口密度提高10%,會使得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提高2%,意味著當期人口越密集的城市,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水平將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這表明城市規模并非越大越好,當城市人口超越了城市承載力,將導致城鎮化質量下降;上一期城市人口密度增大10%將導致恩格爾系數下降169%,表明上期農民工流入城市,將對當期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產生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城鎮化進程使得農民工能夠在短期獲得比農村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可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但隨著當期人口密度的增大,可能由于人才、資源和房價的競爭性壓力等原因,導致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導致“規模報酬遞減”的效應。總體來看,人口密度并非越大越好,應當適度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切實降低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該結論印證了城市具有最優規模的結論(王俊,2014)。
其次,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與恩格爾系數呈現出正相關關系,但是這種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欠發達城市的第二產業可能為經濟增長和居民生活質量提高貢獻較大,而發達城市則是以第三產業為主,恩格爾系數可能較低。因此,各地區第二產業比重對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沒有顯著的影響。
最后,控制變量方面,能源消耗對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影響為負,但是在統計上并不顯著,表明高能耗的發展方式并不能夠提高城鎮化質量;市場化改革對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影響同樣不顯著,意味著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對于促進人口和生產要素流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城鎮化質量具有重要作用。
(三)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影響因素的靜態面板估計
由于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不具有動態特征,且研究對象為中國30個省會城市,因此我們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估計人口密度、產業結構等因素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的影響,所使用的是EVIEWS60軟件。估計結果參見式(3),括號內數字為相應估計系數的標準差。從式(3)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均具有負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顯著;全社會用電總量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具有正向影響,意味著能耗越大,城市越應注重保護生態環境;市場化改革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省會城市的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運行已初步顯現效果。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在資源環境雙重約束的分析框架下,將人口密度、產業結構、能源消耗、市場化改革等變量納入城鎮化質量的影響因素體系,并將城鎮化質量界定為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兩個層面,分別構建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變量作為城鎮化質量衡量指標的回歸方程,對2001-2012中國30個省會城市的數面板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1)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具有棘輪效應。總體來看,恩格爾系數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亦即食品支出在生活性消費支出中的比重逐年降低,且城市人口密度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呈現“U”型關系;上一期城市人口密度降低了本期恩格爾系數,而本期人口密度則提高了恩格爾系數,表明為達到理想的城鎮化質量,人口密度過小或過大都是不可取的,適中的人口密度可使得城鎮居民具有較高的生活水平。(2)產業結構對城鎮化質量的影響不顯著,表明不同地區的城鎮化質量內生于該地區的產業結構,主導產業的不同是引起居民生活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3)市場化改革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的影響顯著為正,顯示出城市環保產業的市場機制運行已初見成效。
根據上述實證研究結論,為促進以恩格爾系數為代表的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以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為代表的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提升,本文建議:(1)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人口的自由流動。(2)根據不同區域的產業結構特征推行差異化的城鎮化發展戰略,推行高效節能的經濟發展模式。(3)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力推動環保產業發展和城市生態環境質量提升工作,構建環境宜居城市。(4)著力推行以人為本、資源節約的環境友好型的城鎮化思路,優化人口密度和產業結構布局,穩步提高城鎮化質量,避免盲目追求速度的城鎮化,使得城鎮化不僅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陣地,更是破解資源環境瓶頸的有力抓手,進而實現人類生存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注釋:
① 資料來源:http://env.people.com.cn/n/2014/0113/c1010-24100312.html。
參考文獻:
[1] 魏后凱,王業強,蘇紅鍵.中國城鎮化質量報告[J].中國經濟周刊,2013(3).
[2] 陳明.中國城鎮化發展質量研究評述[J].規劃師,2012(7):5-10.
[3] 徐林,曹紅華.從測度到引導:新型城鎮化的“星系”模型及其評價體系[J].公共管理學報,2014(1):65-74.
[4] 陸銘.中國的城市化應謹防“歐洲化”[N/OL].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4-05-06/114155424.html.
[5] 羅運闊,周亮梅,朱英美.碳足跡解析[J]. 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123-127.
[6] 張兵,王正,朱超.城市碳足跡定義與計算方法研究[J].山西建筑,2011,37(32):185-186.
[7] Norman, J., H. L. MacLean.Comparing High and Low Residential Density: Life-cycle Analysis of Energy Use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2006,132(1):10-21.
[8] Ishii S, Tabushi S, Aramaki T. Impact of Future Urban Form on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Utsunomiya, Japan[J].Energy Policy,2010,38(9): 4888-4896.
[9] 溫興祥. 城鎮化進程中外來居民和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J].人口研究,2014,38(2):61-70.
[10]林伯強.電力消費與中國經濟增長:基于生產函數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11):18-27.
[11]王火根,沈利生.中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空間面板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12):98-107.
[12]Arellano, M. and O. Bover.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1): 29-51.
[13]Blundell, R. and S. Bond.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 115-143.
[14]劉修巖,殷醒民.空間外部性與地區工資差異: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學(季刊),2008,8(1):77-98.
[15]王俊.擁擠效應、經濟增長與城市規模[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4,12(1):46-5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