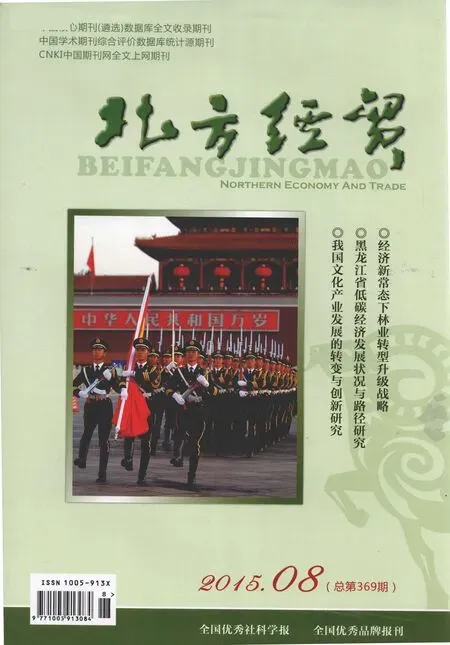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與啟示
胡 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武漢 430073)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一重大轉折點之后,中國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世界貿易和國際分工,在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同時,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和影響力也大不同于往日。在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的大環境下,中國逐漸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企業。早在2000年,中國政府就意識到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用國家發展戰略高度的重視和優惠政策的實際行動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2014年 11月在北京召開的 APEC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取得了很多振奮人心的成果,其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中國正式開啟了“資本輸出時代”。在這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企業應抓住機遇,大顯身手。時至今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相當大一部分企業的海外投資處于虧損的狀態。
與中國改革開放一樣,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增長也曾同樣地引人矚目。尤其在1969年以后,日本逐漸擺脫了國際收支赤字的影響,政府也不再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行嚴格的管制。日本借助承接歐美先進工業國產業轉移的契機,大力發展自身經濟,優化自身產業結構,與周邊亞洲國家相比,日本逐漸積累了明顯的技術優勢和資本優勢。作為一個資源嚴重匱乏的島國,日本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帶動經濟持續騰飛的強大動力,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達到了鼎盛時期。
雖然時下的中國和上世紀60至80年代的日本經濟狀況存在很大差異,國際經濟的形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兩者依然在很多方面都驚人地相似,比如人均資源的日益匱乏、勞動力優勢的逐漸喪失、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來自外界的貨幣升值壓力等等,中國現在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從日本過去的發展經驗中找到借鑒,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從與日本的比較中得到新的啟示。
一、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發展歷程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穩步增長,從無到有,由少及多。2003至2012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尤為迅猛,200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為28.6億美元,而2012年該數值已經達到了878.0億美元,增長了三十余倍,年均增長率高達46.3%。截至2012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6283.9億美元,其中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964.5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5319.4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的6.3%,排名躍居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二戰以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這個時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加之國際收支的拖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尚小且發展緩慢;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隨著日元的升值和日本與歐美國家貿易矛盾的升級,日本逐漸將重心轉移到海外投資建廠,在這一階段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得以高速增長;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90年代中期經濟泡沫的破滅使日本經濟走下神壇,逐漸衰退,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也隨之規模縮小,進入調整期。
二、中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整體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涉及地區廣泛,但分布嚴重不均。截至2012年末,中國有1.6萬家企業在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2萬家,覆蓋率達76.8%,但從對各國家(地區)投資規模占比上我們發現,中國企業的投資范圍主要局限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投資量分別占到整個對外直接投資的68%和13%,其中,單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就占到了整體的58%。較為發達的歐洲和北美洲相比之下略顯冷清。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是動態變化的,中國企業對各大洲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基本都呈持續上升的態勢,其中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長尤為突出,這也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布越發不均的原因所在。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中國有明顯的區別,其區位的選擇與國家的經濟形勢和戰略選擇關系甚密。在20世紀五6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是獲取資源,故其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隨后,日本國內的生產水平和資本積累已經形成一定的優勢,日本企業迫切的需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勢開拓海外市場,此時的投資對象已經擴大到歐美等地。
(三)中日區位選擇的比較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受企業自身生產率和技術水平的限制,同時也會反過來影響企業“走出去”的收益和得利。整體來看,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存在較大差異。雖然兩國對亞洲的直接投資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國對亞洲的依賴性更強,其次是拉丁美洲,中國對這兩個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占到了總額的81%。相比之下,日本的區位分布更為均勻,且更多地集中在發達國家。一方面,由于日本企業在技術和資本的積累逐漸強勢,其投資對象可以從先前的發展中國家轉向歐美等發達地區,動機由最初的尋求資源,開拓市場逐漸偏向技術的學習和獲取;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在各個地區的分散投資有效地避免了本國企業的相互競爭,這樣相對寬松的競爭環境賦予了日本的投資企業更大的生存機會和利潤空間。
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從2012年末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企業在各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5319億美元,涉及產業種類已涵蓋經濟活動中的各個行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是幾個主要的投資領域,而住宿餐飲、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和文化、體育娛樂業等產業投資存量所占份額極小。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具有很強的慣性,2004年發展至今依然保持了穩定的存量分布特征,而各個產業每年的投資流量卻發生著細微的變化,比較發現,大部分產業,如農、林、牧、漁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房地產業等,投資流量在2008年或2009年出現回落后都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而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在近幾年的變化趨勢不甚明朗,甚至在2010年后有下降的趨勢。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同區位選擇一樣,日本的產業選擇也是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戰略目標的轉移而變化。第一階段,國內資源的匱乏決定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相關產業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在獲取資源相關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到了整體投資的44.6%,其次是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分別占整體投資份額的36.3%和19.1%;進入第二階段后,日本國內技術和資本積累已經初顯優勢,同時加上日本同其他國家貿易摩擦等問題的不斷深化和70年代的石油危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重心逐漸偏向以拓展市場為目標的商務服務業和制造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微電子等高科技產業的興起,第三產業逐漸替代傳統的制造業,成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寵兒,1985年,第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占到整體投資的55.3%,資源獲取型產業和制造業的份額和地位越來越不重要。
(三)中日產業選擇的比較
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路徑大相徑庭,這是兩國不一樣的經濟發展軌跡決定的。日本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更像是完成了一個由興起、發展、成熟、產業轉移的階段分明的周期,中國的經濟情況更為復雜。所以表現在產業選擇上,日本經歷了由資源獲取型產業轉向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再轉向第三產業的進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則一直保持著以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的產業格局。在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中,中國制造業的重要性遠遠不及日本,因為中國的制造業還未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不能從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中獲利。
四、中日對外投資主體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根據中國商務部發布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2013》數據統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由2000年的104家增加到2013年的19705家,其中央企或下屬企業661家,地方企業19044家。由此可見,在數量意義上,地方企業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絕對主力,但是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截至2012年末,中國中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3114.4億美元,占整體投資存量的71.5%,而地方企業的該指標僅為1240.6億美元。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角色將會由央企逐漸轉移到地方企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主要構成是大型跨國公司,同時,中小企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綜合商社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是日本經濟社會的支柱,在國際上也有很強的競爭力。據統計,1974年日本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占整體投資的5.4%,而1978年該指標上升為8.3%,到了1984年更是上升到了16%。
(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
中日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構成和功能較為一致,都是數量較少的大型企業作為中流砥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貢獻的對外直接投資占的比重較少,但這一不可缺少的角色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地位也在逐漸上升。不同的是,中國企業在區分央企和地方企業時,指的并不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區別,地方企業中同樣包括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事實上,中國大型民營企業并不多見,所以在中國對外投資直接的企業名錄中,民營企業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的主體構成更加健康合理,一方面,日本中小企業有較強的技術優勢,極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比大型企業更靈活,對于經濟風向的變動更容易做出調整。
五、中日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方式的比較
有一些企業調查結果認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的融資來源并不是銀行的大額貸款,而是自身的未分配利潤。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2013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調查報告顯示,僅有21%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52%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的未分配利潤。
對于日本企業而言,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是對外直接投資貸款的主要來源,它代表了日本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政策支持并為企業提供堅實后盾。同時期的中國,企業通過銀行貸款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也大約是一千四百億美元,占到GDP的0.31%,但是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總規模卻占到了58.0%,遠高于日本。如果考慮日本1971-1984年的數據,企業通過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貸款融資的規模是84億美元,占GDP的0.08%,是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2%。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更依賴于銀行貸款。
通過對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分析,從區位選擇上看,日本的區位分布更為均勻,且更多地集中在發達國家,而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過分集中在亞洲,尤其是中國香港;從產業選擇上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經歷了由資源獲取型產業轉向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再轉向第三產業的進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則一直保持著以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的產業格局;從投資主體上看,中國主要是由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中央企業來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參與度不夠;從融資方式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多地依賴銀行融資,貸款比例占總體投資比例太高。
針對以上結論,認為中國的政府和企業首先應該意識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中的問題和不足之處,看到中國與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模式和盈利水平的差距,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經驗和成功案例。具體而言,第一,中國企業的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國時應該更多地考慮歐美等發達地區,更加重視先進技術獲取的重要性;第二,企業應加大技術研發力度,在促進國內產業優化升級之余,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第三,政府應該積極出臺相關的激勵政策,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較低的利息和稅收優惠,著重培育第三產業。
[1]李 新.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障礙及對策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4.
[2]湯建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特點比較及其啟示[J].當代財經,2007(11).
[3]王文舉,王三星.中日對外直接投資比較研究[J].財貿研究,2002(1).
[4]武 強.中日對外直接投資比較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2.
[5]趙鳳彬,孫才仁,杜笑巖.日本對外經濟關系[M].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