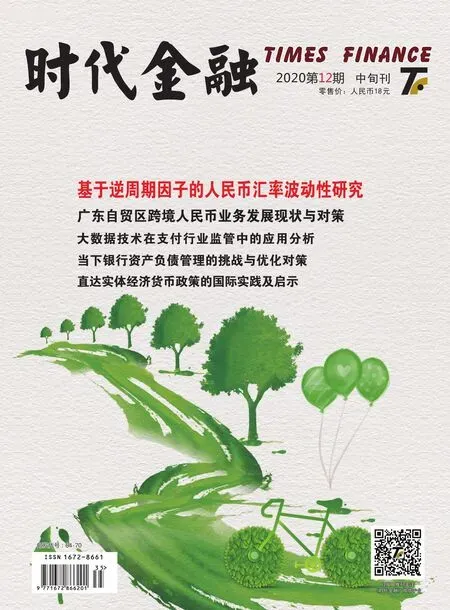中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及其制度分析
孟麗曼
貧富差距拉大引起個人收入分配的不公。經(jīng)濟轉(zhuǎn)型期出現(xiàn)的必然現(xiàn)象是貧富差距。在我國,貧富差距現(xiàn)象顯著,人們把視線更多的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這一方面。分配不公對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它既會對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消極的影響,也會損害中國經(jīng)濟的長期發(fā)展,所以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已經(jīng)提上了我國的議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進行,我國經(jīng)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隨之而來的是收入分配的愈加不公平。
2013年兩會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近日推出的2013年“十大熱點問題調(diào)查”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和“反腐倡廉”名列前三。目前我國正處于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zhuǎn)型的關鍵時期,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成為國家轉(zhuǎn)型能否成功的重要關口。收入分配問題涉及到收入在居民之間的分配以及在居民、企業(yè)和政府之間的合理選擇。人們對收入分配的關注越來越多。收入分配不公對社會的發(fā)展、經(jīng)濟的繁榮、文化的傳播起到了負面的、消極的作用。收入分配不公阻礙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進程,使人們感受不到社會的公平與公正,從而危害社會治安、危害人們安全。基尼系數(shù)用來衡量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2011年1月,我國內(nèi)地GDP和人均GDP均迅猛發(fā)展,我國經(jīng)濟實力日益增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但隨之而來的,我國的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現(xiàn)象日益嚴重。有關經(jīng)濟專家指出,我國的基尼系數(shù)一路攀升,改革開放前我國基尼系數(shù)僅為0.16,然而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shù)已經(jīng)超過了世界上很多發(fā)達國家的基尼系數(shù)。國際上標準的基尼系數(shù)是0.4,然而我國今年來的基尼系數(shù)要遠遠高于標準水平。高基尼系數(shù)反映了我國收入稅分配愈加不公的狀態(tài),我國收入分配問題急需得到改革。
我國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城鄉(xiāng)分配不公、行業(yè)分配不公、地區(qū)分配不公、群體分配不公。地區(qū)差距和城鄉(xiāng)差距是四個問題中的顯著差距,是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關鍵領域。在重慶市城鄉(xiāng)收入調(diào)查中,1985年的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比2.50∶1,而 2010年的比例已增加到3.32∶1,期間2006年,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比值更是達到了20多年來的最高點4.02∶1。
首先我們看一下城鄉(xiāng)差距。近10年來,我國居民家庭收入構(gòu)成發(fā)生了較大變化:收入來源不再單一而變得越來越多元化;城鎮(zhèn)居民家庭工資性收入的比例在不斷下降;農(nóng)村居民家庭工資性收入、經(jīng)常轉(zhuǎn)移性收入在總收入的比例卻呈現(xiàn)不斷上升的趨勢,我國居民收入的來源愈加穩(wěn)定,人們生活有了更多的保障;財產(chǎn)性收入由無到有,由少到多,近年來以兩位數(shù)的速度快速增長。在城鎮(zhèn)居民家庭收入統(tǒng)計中,工資性收入占比從2000年的71%下降到2010年的65%,轉(zhuǎn)移性收入從23%提高到24%,經(jīng)營凈收入占比從3.9%提高到8.1%,財產(chǎn)性收入占比從2%提高2.5%;而在農(nóng)村居民家庭純收入研究中,工資性收入占比從31%提高到41%,經(jīng)營純收入占比從63%下降到48%,財產(chǎn)性收入從2%提高到3.4%,轉(zhuǎn)移性收入占比從3.5%提高到7.7%。其次,我們分析一下地區(qū)收入差距。伴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國各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不斷發(fā)展,人均GDP不斷增加,但各地區(qū)之間收入差距也日益明顯。據(jù)1981年統(tǒng)計分析,我國最高的省份人均收入637元,最低的省份369元;而1999年研究指出,最高的省份人均收入為10932元,最低的省份人均收入僅為4342元。最高和最低省份的人均收入差距由1980年的1.73倍擴大到2001年的2.52倍,相差的數(shù)額也從1980年的268元上升到2001年的6590元,2005年相差的數(shù)額達到了萬元以上,到2010年二者相差倍數(shù)也在2.4倍左右徘徊。我國的地區(qū)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亟須政府的重視和改革。據(jù)統(tǒng)計資料分析,我國東、中、西部的人均收入比由1978年的1.37∶1.18∶1,擴大為2000年的2.42∶1.2∶1。2008年,我國東、中、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人均年收入比達到1.51∶1.01∶1,農(nóng)民居民全年純收入比1.88∶1.27∶1。另有學者指出,2000年,東部地區(qū)人均GDP值是中部地區(qū)人均GDP的1.98倍,西部地區(qū)是中部地區(qū)人均GDP的77%。到2010年,東部地區(qū)人均GDP是中部地區(qū)人均GDP的1.74倍,西部地區(qū)是中部地區(qū)的80%,差距雖有所縮小,但仍然較大。地區(qū)差距的產(chǎn)生原因多樣,歷史、地理、社會政策、我國資源狀況均會影響我國地區(qū)收入分配。地區(qū)之間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成為近期我國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過程中面臨的新挑戰(zhàn)。再次,研究崗位收入差距。北京的某家大型網(wǎng)絡門戶網(wǎng)站,新入職的員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萬元以上,收入差距達20倍。中關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層普通員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數(shù)十萬到幾百萬元不等,收入差距達到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從整體考慮,現(xiàn)今我國在企業(yè)工資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和問題仍然層出不窮,主要問題是政府對企業(yè)工資收入分配調(diào)節(jié)力度不夠,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xù)下降,行業(yè)之間、部分職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zhuǎn),分配秩序不夠規(guī)范,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從合肥市最近發(fā)布的部分職位(工種)人力資源市場工資指導價位上來看,企業(yè)董事、經(jīng)理、廠長等職位平均年薪高位在30萬元左右,企業(yè)董事則可達到32萬元;而包裝人員、浴池服務員、小型家用電器裝配工等職位平均年薪低位不到13000元,如包裝人員年薪少的僅為12600元。如此算來,因從事具體職位不同,在合肥的收入差距達到25倍之多。最后,我們看一下行業(yè)收入差距。2011年研究分析,我國城市國營企業(yè)職工平均工資最低行業(yè)與最高行業(yè)之比為1:4.5,而在私營單位的比例為1:3,這個比例要遠遠大于發(fā)達國家的比例,而與某些新興國家的程度相當。目前我國不同行業(yè)職工收入差距明顯偏大。我市新興行業(yè)如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yè)2010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41770元,而傳統(tǒng)行業(yè)如紡織業(yè)為14739元,食品制造業(yè)更低,僅為12200元。壟斷行業(yè)如煙草制品業(yè),2010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高達47232元,電力、熱力的生產(chǎn)和供應業(yè)2010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更是高達51031元。
是什么導致中國收入分配陷入如今的境地?我們應從下面幾個方面分析:我國自身的狀況及發(fā)展、制度的影響、社會保障體制的缺失等。除了以上三種造成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現(xiàn)在的原因外,我們還可以從制度經(jīng)濟學的層面對其進行研究。我國在經(jīng)濟改革的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忽略了制度的同步發(fā)展,造成了部分制度的缺失,沒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中國收入分配便失去了依靠。那如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么?首先,我國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國應在堅持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完善和豐富各行業(yè)的制度,給予每個層次的勞動人員最基本的保障。其次,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農(nóng)民收入、縮小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我國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重點在農(nóng)村、最大的難點也在農(nóng)村。增加農(nóng)民收入是當前經(jīng)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應推進城市化,使農(nóng)民向城市轉(zhuǎn)移,從根本上解決農(nóng)民收入問題。第三、大力營造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鼓勵人才創(chuàng)新,對于做出貢獻的人予以獎勵。第四、轉(zhuǎn)移發(fā)展重點,縮小收入差距。將重點產(chǎn)業(yè)由東部逐漸向中西部轉(zhuǎn)移,用東部先進經(jīng)驗帶動中西部的發(fā)展。最后,強化制度約束,避免生產(chǎn)條件在社會成員之間的過度非均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