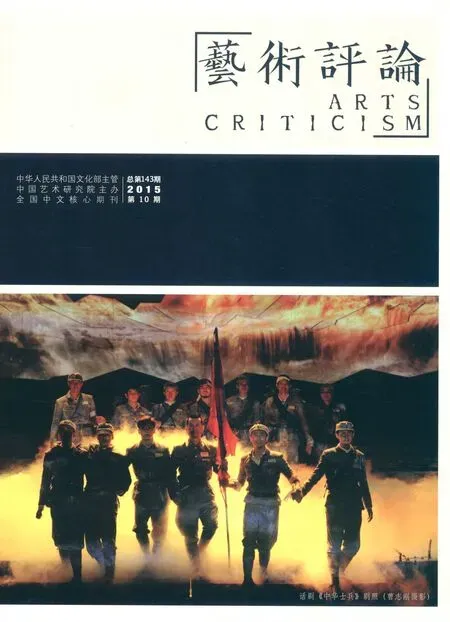論抗戰戲劇的民族化道路
田本相
論抗戰戲劇的民族化道路
田本相
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回顧抗戰戲劇的偉大成就,其主要業績和歷史經驗,是在民族大奮起和民族大覺醒的時代,適應著民族的需要,走了一條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這一點對當代戲劇的發展仍然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啟示。
學界有一種反對民族化提法的主張;但是,對于話劇來說,沒有民族化,也就不可能有中國話劇的生存和發展。百年來中國話劇就是中國人以自己的智慧,將它創造性地轉化為民族話劇的歷史過程。在民族的獨創中,把這個“舶來品”改造成為為中國老百姓歡迎的一大劇種。
抗戰戲劇的民族化,使它無論在劇作的題材、劇作的思想內涵、話劇的藝術形式、藝術風格,直到演出的體制和演出的組織等方面,無不打上民族性的烙印,無不展現出民族的氣派。正是這樣的民族化道路,將中國的現代話劇推向一個高峰,涌現出一批戲劇藝術家,一批優秀的劇團,一批杰出的劇作。
一、以戲劇的形式英勇地發出民族的怒吼
中國話劇的民族化精神,在抗戰時期首先體現在中國話劇工作者英勇抗敵的精神上。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標志,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全國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熱潮。中國話劇工作者走在最前面,以話劇為武器,發出民族的怒吼。
上海的戲劇界打響了抗戰戲劇的第一槍。“七七事變”之后第八天,1937年7月15日,上海劇作者協會召開全體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國劇作者協會。會議決定創作《保衛盧溝橋》,并由辛漢文、陳白塵、瞿白音、阿英、于伶等七人組成籌備演出委員會,推定洪深、唐槐秋、袁牧之、凌鶴、金山、宋之的等十九人組成導演團;協會還決定委托于伶、馬彥祥負責組織戰時移動演劇隊;劇本創作組成了以崔嵬、張季純、馬彥祥、王震之、阿英、于伶、宋之的、姚時曉、舒非(袁文殊)等十七人參加的寫作集體,由夏衍、鄭伯奇、張庚、孫師毅四人整理,不到半個月即拿出《保衛盧溝橋》的定稿。8月7日,《保衛盧溝橋》即在上海南市蓬萊大戲院演出。劇中發出了“保衛祖國,一切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的吼聲。近百名主要演員以滿腔熱情投入演出和劇務工作,演出氣勢磅礴,“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怒吼,聲震山河,轟動了大上海,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他們日夜演出,有時還要另外加演還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一直演出到“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
《保衛盧溝橋》的演出,在中國話劇史上是一次標志性的事件。
繼之,以“七七事變”為題材的劇本蜂擁而來,如田漢的《盧溝橋》,張季純的《血灑盧溝橋》,陳白塵的《盧溝橋之戰》等。1937年8月9日,南京新聞界聯合大華、國民、新都、首都四大劇院,演出田漢的四幕話劇《盧溝橋》(洪深、馬彥祥導演),國民黨當局雖百般阻撓,仍然勝利演出,激起南京廣大群眾的抗日浪潮。
很快,抗敵話劇的大浪,在全國各地洶涌而來,如北京、天津、廣州、桂林、武漢、昆明、貴陽、西安等地話劇工作者,也發動、 組織起來,成立各種各樣的演劇隊和抗日演出團體,掀起全國戲劇界抗敵浪潮。
二、演劇隊:演劇體制的民族創舉
“演劇隊”是中國話劇民族化演劇體制的偉大創舉。
在八年的抗戰中,為了適應抗戰形勢而涌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演劇隊,劇宣隊、救亡演劇隊等,不但是一種適合戰時要求的演劇體制,而且是抗戰戲劇的有生力量。他們長途跋涉,深入部隊、農村、工廠、學校,在宣傳抗日、動員抗日,宣傳民主進步,啟迪民族覺醒上,起到偉大的歷史作用。他們歷盡艱辛,不惜犧牲,寫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抗戰時期的演劇隊在世界話劇史上都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1937年8月,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決定,成立1 2支救亡演劇隊。在這里,幾乎集中了中國話劇的大部分精英:第一隊隊長為馬彥祥、宋之的,隊員有鄭伯奇、崔嵬、丁里、王震之、賀綠汀、塞克、周伯勛、歐陽山尊、王蘋、葉子、王余杞、劉白羽等人。第二隊隊長為洪深、金山,隊員有冼星海、黃治、張季純、田方、田烈、賀路、鄒雷、金子兼、白露、王瑩、歐陽紅纓、熊塞聲、顏一煙等人(四十年代劇社成員主要由一、二隊成員組成)。第三、第四隊總隊長為應云衛,成員原屬上海業余實驗劇團。第三隊隊長為鄭君里、豫韜,隊員有魏曼青、劉群、王為一、沙蒙,顧而已、呂班、俞佩珊、舒非、趙丹、伊明、葉露茜、朱今明,金乃華、蘇丹、海濤、田蔚等。第四隊隊長為陳鯉庭、瞿白音,隊員有趙明、魏鶴齡、陶金、呂復、汪洋、舒強、張客、嚴恭、吳曉邦、趙慧深、李琳(孫維世)、吳衡、吳考等人。第五隊隊長為左明,隊員有艾葉、艾琳、仉平、宗由等人,該隊原為上海先鋒演劇隊。第六隊隊長為李實。第七隊隊長為丁洋。第八隊隊長為劉斐章,隊員有石聯星、王逸、許秉鐸、許之喬、朱琳等人。第九隊因故未能建成。第十隊隊長為辛漢文、王惕予。第十一隊隊長為侯楓。第十二隊隊長為凌鶴、尤競。第十三隊隊長為陳鏗然。救亡演劇隊的骨干力量大多是在左翼文藝運動中鍛煉成長起來的進步的戲劇、音樂、美術工作者,以及一些熱愛文藝的愛國學生。

《保衛蘆溝橋》之一幕

《屈原》之一幕
救亡演劇隊足跡遍布于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陜西、湖北等地,深入群眾之中,主要演出一些短小靈活的街頭劇、活報劇、獨幕劇等,受到民眾普遍的贊賞。
演劇隊不但是編演抗日戲劇的演出團體,也是抗日的宣傳隊、工作隊。他們一邊演出,一邊進行宣傳動員,一邊為抗戰募款。還采取各種藝術形式,如歌詠、美術、講演、辦壁報等進行宣傳工作。演劇隊也是工作隊,參加看護傷員、組織民工運輸軍需品、挖戰壕、調查戶口、家庭訪問等工作。
第三廳成立后,設立了藝術處,并于1938年8月宣布成立抗敵演劇隊、抗敵宣傳隊等組織。上海救亡演劇隊也列入抗敵演劇隊,并將上海救亡演劇隊的業務民主、生活民主、經濟民主等管理方式和民主作風延續下去,有條件的演劇隊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這十個抗敵演劇隊分赴各地,為前線戰士演出,為醫院傷兵演出,在城鎮、工礦、學校進行宣傳演出和輔導工作。從流動演出的地域之廣,歷時之久,演出劇目影響之大等方面看,第三廳領導的抗敵演劇隊始終是抗日劇運的骨干隊伍。
另外,還有各省市抗敵后援會移動演劇隊、軍隊的士兵劇團和地方上的群眾演出團體以及教育部組織的巡回演出隊、軍委會政治部直屬的教導劇團。國民政府教育部也曾組織兩支巡回戲劇教育隊。
演劇隊是在抗戰戲劇運動中產生、發展的一支戰斗的話劇隊伍,這是世界戲劇史所罕見的戲劇現象。它是演劇隊,也是宣傳隊,也是工作隊。它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不但為中國話劇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而且在中國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斗爭中完成了中國話劇的歷史使命。它培育了整整一代革命的優秀的話劇工作者,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話劇藝術家,并且堅持和締造了中國話劇的戰斗傳統。

《國家至上》第一幕

《飛將軍》之一幕(國立戲劇學校)
三、演劇方式的創新:創造了獨特的民族話劇新形式
夏衍在抗戰初期曾經指出,抗戰將會給話劇帶來新的生機和新的創造。他說:“二十年來束縛著中國新戲劇運動之開展的枷銬,終于在抗戰爆發的那一瞬間粉碎了,我將這一次神圣的抗日戰爭譬喻做摧毀一切舊秩序舊體制,和發源于這秩序體制的觀念上的束縛阻礙的雷雨……敵人的炮火與炸彈不僅轟毀了溫室的花棚,那些嬌嫩的野草接觸到了中國的土壤和空氣,同時也還炸破了僵硬荒廢的地殼,而使那些拋棄在中國之原野上的植物有了生根和滋長的機會。”
在艱苦的抗戰環境中,無論是報紙還是廣播都受到物質條件的限制,因此受眾很少。而話劇此刻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大眾傳媒的作用。面對大眾的戲劇,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應滿足他們的需要,貼近他們的生活。夏衍則提出要“創造各種形式,產生各種內容的便于上演的劇本。像不要舞臺布景,燈光等,一些火把就可以在廣場或者農場上上演,甚至于不要劇本,像活報,時事報告,手勢啞劇等等。”[1]
演劇隊適應演出的需要,充分利用當地的環境,創造出了多種新穎的演出方式,如街頭劇、廣場劇、茶館劇、游行劇、活報劇、諧劇等。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戰時期出版、發行的一千兩百余部劇作中,街頭劇就有近百部。《放下你的鞭子》(崔嵬等)、《三江好》(呂復等)、《八百壯士》(王震之、崔嵬)、《流寇隊長》(王震之)等都幾乎演遍了各戰區與大后方的廣大城鎮以及農村。其中,流傳最廣最受人們歡迎的是由崔嵬改編的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
活報劇,意即“活的報紙”,它以速寫手法和喜劇的手法迅速反映時事。“茶館劇”則是根據西南地區百姓有到茶館喝茶的習慣,演員扮作茶客,分別入座,造成故事,引起其他茶客的注意,很自然的進入角色。“游行劇”是采取化裝游行進行宣傳的戲劇形式:1938年10月中國首屆戲劇節期間,上海業余劇人協會在重慶大街上,在成千上萬的觀眾的簇擁下,演出了《漢奸和十字舞》《爭取最后的勝利》《大家一條心》等劇目,轟動整個山城。
這些廣場劇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一是突破劇場演出的局限,推倒了“第四堵墻”,使戲劇更貼近觀眾;二是打破舞臺的局限,使演員忘了是演戲,觀眾忘了是在看戲,演員、觀眾的思想感情融為一體,演員與觀眾之間,觀眾與觀眾之間,形成多向的心靈互動和情感的交流。三是廣場戲劇演出效果,具有狂歡節的特色,它把戲劇的宣傳功能與宣泄功能統一起來。
四、根據地的戲劇民族化、大眾化成就
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根據地的戲劇民族化走向自覺發展的階段,以新秧歌劇、新歌劇運動和舊劇改革為重心,構成根據地戲劇民族化、大眾化的靚麗景觀。
秧歌原本是在我國北方廣大農村流行的一種群眾性藝術形式。延安的戲劇工作者利用和改造了這一民族藝術形式,從題材選擇、人物刻畫、情節安排、語言運用,到音樂設計、表演方法等方面,進行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加工,創作出了既有民族風格又有時代色彩的秧歌劇。在1943年春節的延安秧歌集會上,涌現出《向勞動英雄學習》《擁軍花鼓》《擁軍愛民》《紅軍萬歲》等明顯具有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性質的新的秧歌劇。尤其是“魯藝”創作的《兄妹開荒》,唱出根據地生活的新氣象,唱出了“邊區的人民吃得好來,穿也穿得暖,豐衣足食,趕走了日本鬼呀,建設新中國”。轟動了延安,演遍了根據地,并興起了新秧歌劇運動。這一期間涌現出像《夫妻識字》《一朵紅花》《牛永貴掛彩》《趙富貴自新》《劉二起家》等新秧歌劇。由于秧歌本來就廣泛流傳于民間,這些新編劇目在內容上又通俗易懂、貼近現實,形式上載歌載舞、熱鬧歡快,顯示出“所有中國過去的戲劇所沒有過的一種愉快、活潑、健康、新生的氣氛”。所以,廣大人民群眾對其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和熱情。周揚當時曾撰文指出:“創作者、劇中人和觀眾三者從來沒有像在秧歌中結合得這么密切。這就是秧歌的廣大群眾性的特點,它的力量就在這里。”[2]
正是這些群眾性的秧歌劇運動,給了戲劇工作者極大的啟示,引導他們在改造舊秧歌的基礎上,創造出了民族新歌劇。“魯藝”在繼大型秧歌劇《慣匪周子山》的成功探索之后,于1945年1月創作演出了新歌劇《白毛女》,成為解放區戲劇中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優秀作品,也成為五十年來戲劇舞臺上經久不衰的藝術經典。它的成功經驗,也促成了解放戰爭時期的《無敵民兵》《王秀鸞》《劉胡蘭》《赤葉河》等一批新歌劇的誕生。
在延安的文藝運動中,還掀起了一股舊劇改革的浪潮。早在1939年,張庚就在當時的《理論與實踐》上發表了《話劇民族化和舊劇現代化》的文章。1942年,解放區開始了改革舊劇的實踐。1942年9月,一二師戰斗平劇社到延安演出了新編平劇《嵩山星火》之后,與“魯藝”平劇團及膠東平劇團等合并成立了延安平劇院,而后陸續演出過新編的和傳統的劇目《岳飛》《梁紅玉》等。1944年元旦,中央黨校首次演出了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這是對舊劇進行的一次大膽的革新嘗試。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看了《逼上梁山》之后寫了著名的《致楊紹萱、齊燕銘》的信,提出了“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以此為開端,繼《逼上梁山》之后,延安平劇院又編演了《三打祝家莊》(任桂林、魏晨旭、李綸執筆)。此外,其他各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也改變了以往輕視傳統戲曲的觀念,投入到各種地方戲曲的改編中去,創作了一批新編的秦腔、山西梆子、山東梆子、淮劇、揚劇等新編劇目。晉西北根據地成立了晉西民間戲劇研究會,山東成立了國劇研究會,并提出了“改造舊形式,團結舊藝人”的口號。
話劇的民族化、大眾化,表現在話劇在面向工農兵的生活中,寫出一批新的題材、新的主題、新的人物。如《李國瑞》《同志,你走錯了路》等。根據地戲劇的民族化大眾化,引領了新中國戲劇的發展,
五、歷史劇——民族精神的載體
中華民族素有“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英勇氣概。面對日寇的侵略,劇作家從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中尋找民族英雄和民族傳統,以“發揮其更大的力量,作民族的怒吼”。在全民族的抗戰中,劇作家把目光轉向歷史,轉向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轉向英勇抗敵的歷史事件,從歷史中汲取力量,從歷史中汲取民族精神,涌現出歷史劇創作的浪潮。例如,以郭沫若的《屈原》《堂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為代表的戰國史劇;以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國春秋》,歐陽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陳白塵的《翼王石達開》(又名《大渡河》)為代表的太平天國史劇;還有以阿英的《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于伶的《大明英烈傳》、郭沫若的《南冠草》、歐陽予倩的《桃花扇》等為代表的南明史劇。這些劇目,以古喻今,借古諷今,宣傳團結對敵,暴露黑暗統治,謳歌愛國主義,鞭撻投降變節,演出效果十分強烈。
在眾多的歷史劇中,以郭沫若的5幕話劇《屈原》最為著名。屈原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詩人,其詩作《離騷》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經典,郭沫若首次將其形象塑造于舞臺之上。他以神來之筆,在從清晨到午夜這段非常有限的舞臺時空里,概括了這位詩人一生的悲劇。于此,郭沫若塑造了一位“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橫遭陷害,處境艱難,“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愛國者的形象。他浪漫的詩情,高潔的心靈,偉岸的人格,光照千古。史劇譜寫了一曲屈原的頌歌。 根據《離騷》的詩意,郭沫若在《屈原》中,虛構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美麗的女性形象,即少女嬋娟。作為侍者,她一直守護在屈原身旁,至真至純,蔑視權貴,是道義美的化身,最后飲下南后加害屈原的毒酒,含笑身亡。《屈原》于1942年首演于重慶,轟動山城。
陽翰笙的《天國春秋》取材于太平天國運動,選取導致其由盛而衰的關鍵性事件——楊韋內訌,作為中心內容。由此,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走向衰頹、困頓。面對慘烈的事態結局,洪宣嬌痛悔不已。她驚呼:“大敵當前,我們不該自相殘殺!”陽翰笙的歷史劇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在其另一部史劇《草莽英雄》中,他塑造了一個只講義氣,盲目自信,對兇險的敵人放松警惕的農民革命者羅選清的形象,最后,此人為清兵所殺。陽翰笙的歷史劇波瀾壯闊,沖突激烈,人物形象鮮明生動。他透過歷史悲劇警示世人,弘揚正義。
顯然,歷史劇的興盛,是抗戰戲劇民族化的體現,也是民族化的輝煌成就。
六、現代民族話劇的高峰
抗戰戲劇的民族化,絕非是狹隘的民粹主義,也不是家有敝帚的閉關主義。民族化,一是“化”中國藝術的傳統于話劇之中,二是“化”外國戲劇的精華于中國話劇之中。
中國話劇的現實主義,經由五四時期的濫觴,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已然成為浩蕩之勢。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優秀的劇作家和高水平的劇作,開啟了話劇民族化的進程。曹禺、夏衍等人的劇作,因其具有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而受到觀眾的歡迎。而在抗戰時期,中國的話劇工作者,憑著話劇民族化的自覺,把中國的現實主義推向一個高峰,并最終構筑了中國話劇的詩化現實主義的藝術傳統。
曹禺在30年代初一鳴驚人之后,在抗戰中又大顯身手,寫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總動員》,與宋之的合作),獨幕劇《正在想》、多幕劇《蛻變》《北京人》,并將巴金的小說《家》成功地改編為話劇。
《北京人》是曹禺創作的高峰。它雖然不是直接描寫抗戰,卻透過一個曾經顯赫而漸趨衰敗的官宦家庭,對中國的社會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曹禺的創作藝術也更加成熟了,人物的性格和復雜的心理,都在十分自然的生活狀態下演進著,而深刻的主題和文化內涵就潛藏在其中。在《北京人》中,契訶夫戲劇的神韻融合在曹禺的個性的創造之中。
30年代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已經是優秀的詩化現實主義劇作,而1942-1945年間,他創作的《水鄉吟》《離離草》《法西斯細菌》《芳草天崖》等多部話劇,更是將平凡的現實生活戲劇化,描寫普通人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在人生的艱難中,所顯示出的細膩的心理波動,含蓄的情感狀態以及靈感的復雜性。
在抗戰中,一位年青的劇作家嶄露頭角,并顯示了濃郁的詩情和雄健的筆力,他就是吳祖光。從1937年到1947年,他創作了《鳳凰城》《正氣歌》《風雪夜歸人》《少年游》《捉鬼傳》等一批話劇劇本。《風雪夜歸人》表面上寫的是愛情悲劇,實際上張揚的是人文思想。劇中的感情戲,寫得深婉動人,充滿著濃郁的詩意。
宋之的的《霧重慶》創作于1940年,上演后獲得了很大的聲名。它描寫的是,戰時重慶的社會現實漸漸消磨了一群年輕人的熱情與斗志,使他們卷入碌碌無為的生活之中,在為衣食奔忙中掙扎,沉淪。這些原本應當年青有為的大學生,卻蹈入了理想被毀滅,情感受挫折的可悲處境。劇作以此揭露了社會現實的腐朽和黑暗,同時,也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與妥協性。顯然,這樣現實主義的杰作,對現實的觀察和揭示是更加深化了。
此間,李健吾、于伶等都有佳作問世。
抗戰以后,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由于其政治黑暗,官僚腐敗,激起人民群眾的不滿,掀起一股諷刺喜劇創作的浪潮。
陳白塵是喜劇創作的先鋒,1940年,他出版了喜劇集《后方小喜劇》。1942年創作了《結婚進行曲》,寫一對年輕人既要追求人身權利,又要反抗庸俗的社會積習,由此陷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尷尬境地。政治諷刺喜劇《升官圖》,更代表著中國現代諷刺喜劇的最高成就。它借鑒了《欽差大臣》的喜劇構思和中國傳統戲曲中的丑角造型,該劇的中心內容是夢境,但故事本身卻相當完整。它對吏制腐敗、惡人橫行、庸俗無恥的社會現實做了淋漓盡致的暴露和嘲諷。
老舍在抗戰時期寫了大量的話劇,他的四幕話劇《殘霧》寫于1939年,取材于重慶的社會現實,劇中的冼局長道貌岸然,一面高喊抗戰,一面貪財、好色、弄權。他不僅利用職權玩弄女性,還與漢奸勾結,為其竊取情報,后來事敗被俘,身陷囹圄,不得已供出了女漢奸,而此時這位神通廣大的女子,卻公然到一位政府要員家中赴宴去了。老舍的喜劇,意在拂去籠罩在抗戰形勢下的“殘霧”,把諷刺的鋒芒直刺腐朽的統治。劇中人物性格鮮明,語言生動、俏皮。1939年11月,該劇由怒吼劇團在重慶首演。
正是在艱苦的抗戰中,劇作家將中國話劇的現實主義精神推向一個高峰。
當前,中國話劇又遇到了一個節點,尤其是最近兩三年,成批的形形色色的外國劇目以空前的規模被引進,掀起一陣一陣的浪潮。在這種時候,我們在放眼世界的同時,更要回顧我們民族戲劇發展的歷史,特別是要回顧和總結我們抗戰戲劇的歷史,提升民族化的自覺,激發民族獨創的意志,堅定地走話劇民族化的道路。抗戰戲劇就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走了一條民族化的道路,因而使抗戰戲劇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歷史證明,中國話劇只有適應民族的需要,時代的需要和大眾的需要,走民族化的道路,實現具有民族獨創性的創造,中國話劇才能發展和繁榮。
注釋:
[1]夏衍.戲劇抗戰三年間——祝三屆戲劇節并答蘇聯友人[J].戲劇春秋,1940年創刊號.
[2]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看了春節秧歌以后[N].解放日報,1944-3-21.
田本相: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郭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