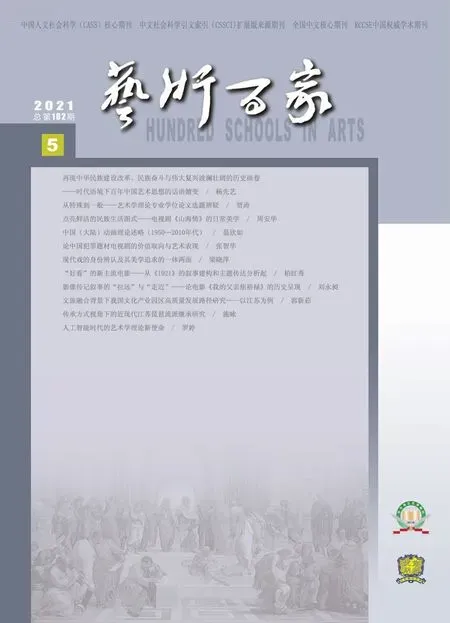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結(jié)構(gòu)
夏東榮
摘要:藝術(shù)問題是一個(gè)最具爭論的文化話題: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性的認(rèn)識,是天才們與生俱來的創(chuàng)造,還是需要漫長刻苦的訓(xùn)練?何為藝術(shù)革命的動(dòng)因?等等,而每一個(gè)問題都在藝術(shù)史上引起過無數(shù)次的爭議,并且還會永遠(yuǎn)進(jìn)行下去。此文對這些問題作一點(diǎn)初步的探索。
關(guān)鍵詞:藝術(shù)學(xué)理論;藝術(shù)創(chuàng)作;藝術(shù)特性;藝術(shù)繼承;創(chuàng)作傾向;藝術(shù)范式;藝術(shù)革命
中圖分類號:J20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藝術(shù),一個(gè)人人都喜愛,又具有爭論的文化載體。它的爭論至今不休,甚至永遠(yuǎn)也不會停止,它的問題是永恒的文化話題,包括: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是否具有一些基本特征;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那些天才們與生俱來的創(chuàng)造,還是需要經(jīng)歷一個(gè)漫長而艱苦的傳統(tǒng)訓(xùn)練;藝術(shù)的創(chuàng)新或革命與科學(xué)革命相類比,范式又如何起作用,是線性的邏輯累積效應(yīng),還是多元的、非持續(xù)性的變革;革命的緣由是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臆想、信手拈來,還是有歷史、社會、文化和創(chuàng)作者個(gè)體特性等根源,如此等等,而每一個(gè)問題都在藝術(shù)史上引起過無限爭議,此論文只是對這些作一點(diǎn)初步的探索。
一、藝術(shù)的基本特性
藝術(shù)自它誕生以來,人們就被“什么是藝術(shù)”這樣的問題困擾著。而這一問題也隨著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本身而備受關(guān)注,特別是各種新的藝術(shù)流派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式不斷受到人們的質(zhì)疑,也挑戰(zhàn)著人們對藝術(shù)的理解。而真正的藝術(shù)又是什么呢?是人們的界定嗎?然而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看法,美國學(xué)者托馬斯·E.沃特伯格(Thomas E.Wartenberg)編著了一本書《什么是藝術(shù)》①,列出了從柏拉圖、康德、黑格爾、本雅明、丹托到沃頓共28位藝術(shù)家和哲學(xué)家的觀點(diǎn),如藝術(shù)即模仿、認(rèn)識、展現(xiàn)、理想、表現(xiàn)、自由、習(xí)俗、假扮,等等,這些觀點(diǎn)一方面給人們許多啟迪,而另一方面也給人們帶來了一些困惑,什么才是藝術(shù)的真正本質(zhì)?而本人認(rèn)為,藝術(shù)之所以成為藝術(shù),應(yīng)該具有一些基本特性,離開了這些基本特性,就失去了作為藝術(shù)的本質(zhì),而這些特性是藝術(shù)所共有的。一般說來,藝術(shù)具有四大特性:創(chuàng)造性、技藝性、審美性和持久性。
1.人的創(chuàng)造性
創(chuàng)造性是藝術(shù)的第一要素,這是因?yàn)樗囆g(shù)首先是人類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不是自然生成的,自然的,就是再美,再所謂的“藝術(shù)”——即使是鬼斧神工,如人們所稱贊的蜜蜂作品——蜂巢,也不是藝術(shù)品。正如康德所說:“藝術(shù)與自然不同,正如動(dòng)作或一般活動(dòng)不同,以及前者作為工作其產(chǎn)品或成果與后者作為作用不同一樣。我們出于正當(dāng)?shù)睦碛芍粦?yīng)當(dāng)把通過自由而生產(chǎn)、也就是把通過以理性為其行動(dòng)的基礎(chǔ)的某種任意性而進(jìn)行的生產(chǎn),稱之為藝術(shù)。……而一個(gè)產(chǎn)品作為藝術(shù)只應(yīng)被歸之于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者。……如果我們把某物絕對地稱之為一個(gè)藝術(shù)品,以便把它與自然的結(jié)果區(qū)別開來,那么我們就總是把它理解為一件人的作品。”②黑格爾在巨著《美學(xué)》中也開宗明義指出:“根據(jù)‘藝術(shù)的哲學(xué)這個(gè)名稱,我們就把自然美除開了。”對此,他還進(jìn)一步進(jìn)行了闡釋,他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固然常說美的顏色,美的天空,美的河流,以及美的花卉,美的動(dòng)物,尤其常說的美的人。我們在這里姑且不去爭辯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把美的性質(zhì)加到這些對象上去,以及自然美是否可以和藝術(shù)美相提并論,不過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藝術(shù)美高于自然。因?yàn)樗囆g(shù)美是由心靈產(chǎn)生和再生的美,心靈和它的產(chǎn)品比自然和它的現(xiàn)象高多少,藝術(shù)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③也就是說,任何藝術(shù)都是由人去創(chuàng)造的,而且只有人的心靈活動(dòng)才能創(chuàng)造的,是一種意識的產(chǎn)物,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蘊(yùn)含著人的主觀意識和思想情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一個(gè)無聊甚至荒唐的幻想,也比那任何一個(gè)美妙的自然美要高些,因?yàn)樗?jīng)過了人的心靈活動(dòng)的創(chuàng)造。所以黑格爾說:“心靈和它的藝術(shù)美‘高于自然,這里的‘高于卻不僅是一種相對的或量的分別。只有心靈才是真實(shí)的,只有心靈才涵蓋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這較高境界而且由這較高境界產(chǎn)生出來時(shí),才真正是美的。”④ 以中國的書畫來說,那出色的筆墨,必須通過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來表達(dá)出美與愉悅,這不僅僅包括藝術(shù)家的手指、手腕以及手臂的肌肉行為動(dòng)作,而且還包含著藝術(shù)家的精神、情感與身體狀態(tài)。在中國,書畫藝術(shù)通常被看成是一個(gè)人內(nèi)心深處的表白,因而中國人將書畫稱之為“心印”。⑤而作為心靈的印記或者形象,一件書畫作品必然反映出藝術(shù)家——這一個(gè)人,他的觀念,他的思想及其自我修養(yǎng)。
雖然現(xiàn)在人們普遍認(rèn)為,藝術(shù)是由人所創(chuàng)造的,正如美國學(xué)者愛米·托馬森在他的《藝術(shù)本體論》中所說:“我們通常認(rèn)為藝術(shù)作品是通過藝術(shù)家、作曲家或作家的想象性、創(chuàng)造性活動(dòng),在某一時(shí)間內(nèi)和特定的文化及歷史環(huán)境中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⑥但是,人們對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理解卻有著不同的闡釋。因?yàn)閷τ谝恍┧囆g(shù)作品來說,有一些是原創(chuàng)的,而另一些卻是可以再度創(chuàng)作的,還有一些仿真品,即所謂的贗品,更有一些是原作品由于損壞需要修補(bǔ)。而對于這些,人們認(rèn)為,只是由于它們藝術(shù)的本體不同,創(chuàng)造的層次或視角就有所不同,但作為人對藝術(shù)作品的創(chuàng)造性這一特性卻不能否認(rèn)。
2.表現(xiàn)的技藝性
任何藝術(shù)的完成都需要有一定的技法或工藝,也就是具有一定的技藝性,有時(shí)稱為“藝術(shù)的技巧”,它是藝術(shù)表現(xiàn)的一種重要手段和方式,比如戲曲的唱念做打、書畫的筆墨功力、文學(xué)作品的文字功底,甚至包括對所用材料的技術(shù)處理等,都屬于技藝性或工藝性的重要方面。如果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沒有一定的技藝作為依托,也只是頭腦中的一個(gè)藝術(shù)構(gòu)想;如果工藝不夠熟練和準(zhǔn)確,那么所展示的藝術(shù)水平也勢必不夠高超或精湛。康德說:“藝術(shù)作為人的熟巧也與科學(xué)不同,它作為實(shí)踐能力與理論能力不同,作為技術(shù)則與理論不同。于是就連那種只要我們知道應(yīng)當(dāng)做什么、因而只要所欲求的結(jié)果充分被知悉,我們就能夠做到的事,我們也不大稱之為藝術(shù)。只有那種我們即使最完備地知道但卻還并不因此就立刻有去做的熟巧的事,才在這種意義上屬于藝術(shù)。”⑦由此可見,所謂技藝性是具有一定的技巧、標(biāo)準(zhǔn)和難度的,它需要通過反復(fù)的、不斷的甚至強(qiáng)制性的練習(xí)才能熟練掌握。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卻不以為然,認(rèn)為這種技藝性與藝術(shù)無關(guān),殊不知任何藝術(shù)都需要技藝的支撐。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樣:“在一切自由的藝術(shù)中卻都要求有某種強(qiáng)制性的東西,或如人們所說,要求有某種機(jī)械作用,沒有它,在藝術(shù)中必須是自由的并且惟一地給作品以生命的那個(gè)精神就會根本不具形體并完全枯萎,這是不能不提醒人們注意的。”⑧而這種強(qiáng)制性的東西或具有機(jī)械作用的東西,正是它的技藝性。美國哲學(xué)家杜威在他的《藝術(shù)即經(jīng)驗(yàn)》中,對技法表現(xiàn)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的作用進(jìn)行了充分論述,認(rèn)為具有重大意義的技法與表現(xiàn)某些獨(dú)特的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密切相關(guān),特別是作為藝術(shù)家對技法的掌握的重要意義。他指出:“藝術(shù)家在說他們必須說的東西時(shí),從技法上講,比其他人所能做的要更好。對我們來說是迷人的天真爛漫,對他們來說,是對所感到的題材用簡單而直接的方法去表現(xiàn)。”⑨特別是,在藝術(shù)發(fā)展中,技藝可作為一種藝術(shù)范式,它的變革同樣會引起藝術(shù)革命和流派的產(chǎn)生。
就中國的書畫來說,需要強(qiáng)有力的筆墨功夫。大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根據(jù)自己的體會,曾寫過多篇關(guān)于書法的文章,論述了如何用筆的技法,如執(zhí)筆五字法、四字撥鐙法、如何運(yùn)腕行筆等,他認(rèn)為只有這樣,才能寫出書法的筆意和筆勢。他形象地說道:“寫字必須先學(xué)會執(zhí)筆,好比吃飯必須先學(xué)會拿筷子一樣,如果筷子拿得不得法,就會發(fā)生搛菜不方便的現(xiàn)象。”同時(shí)他進(jìn)一步論述了書法的執(zhí)筆技法是書法產(chǎn)生藝術(shù)美的重要基礎(chǔ),也是書法家所必須遵循的。他說:“寫字何以要講究筆法?為的要把每個(gè)字寫好,寫得美觀。要字的形體美觀,首先要求構(gòu)成形體的一點(diǎn)一畫的美觀。人人都知道,凡是美觀的東西,必定通體圓滿,有一缺陷,便不耐看了。”⑩而“點(diǎn)畫用講筆法,為的是‘筆筆中鋒,因而這個(gè)法是不可變易的法,凡是書家都應(yīng)該遵守的法。”而對于中國畫而言,技法也同樣重要,如對傳統(tǒng)畫譜的反復(fù)練習(xí),或?qū)Ξ?dāng)今的素描技術(shù)的熟練掌握等,都是最基本的技藝,它甚至影響到畫風(fēng)的形成。正如方聞先生所說:“一幅畫在能夠模擬自然或者表達(dá)含義、反映某種社會片段與物質(zhì)內(nèi)容之前,它必須首先理解造形技法,并且具有其自身發(fā)展歷史常規(guī)的視象結(jié)構(gòu)。”推而廣之,作為任何一門藝術(shù),都有它獨(dú)特的技藝,或者說基本功,而只有熟練掌握了這個(gè)技藝,才能真正掌握這門藝術(shù)的基礎(chǔ),從而也才能進(jìn)一步深入這門藝術(shù)的精髓。
3.藝術(shù)的審美性
任何藝術(shù)都有它的審美性,如果不能引起人們的美感,就談不上藝術(shù),更談不上藝術(shù)的感染力。美國當(dāng)代著名哲學(xué)家、美學(xué)家門羅·C.比爾茲利認(rèn)為藝術(shù)就是美感制作,他說:“藝術(shù)品是帶著賦予它滿足美感旨趣的能力的意圖而制作出來的物件。……美感意圖不一定得是唯一的意圖,甚至不一定得是支配性的意圖;但是,它必須得存在,且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效的意圖——也就是說,在作品的一些特性方面,美感意圖扮演了因果關(guān)系和解釋性質(zhì)的角色。”我國著名美學(xué)家王朝聞先生也認(rèn)為:“美雖不是藝術(shù)的唯一屬性,卻是藝術(shù)的一個(gè)區(qū)別于某種教義的重要屬性。”而什么是藝術(shù)的美呢?這就像什么是藝術(shù)一樣,它所引起人們的爭議也從沒有停止過。這可能因?yàn)閷徝朗且粋€(gè)復(fù)雜的過程,不同的主體對藝術(shù)有著不同的審美情感,也就有著不同的審美判斷,因此,有學(xué)者論述了藝術(shù)評價(jià)的審美原則和審美屬性。
雖則如此,但對于大多數(shù)哲學(xué)家和美學(xué)家來說,他們都有著共同的基本審美理念,那就是任何藝術(shù)都應(yīng)該體現(xiàn)出一種自然美,即從自然美中汲取營養(yǎng),而不是那種嬌柔造作、故弄玄虛的東西。正如康德所說:“美的藝術(shù)是一種當(dāng)它同時(shí)顯得像是自然時(shí)的藝術(shù)……在它的形式中合目的性卻必須看起來像是擺脫了有意規(guī)則的一切強(qiáng)制,以至于它好像只是自然的一個(gè)產(chǎn)物。……藝術(shù)只有當(dāng)我們意識到它是藝術(shù)而在我們看來它卻又像自然時(shí),才能被稱為美的。”黑格爾也認(rèn)為:“理想的藝術(shù)與所謂由人任意設(shè)立的符號誠然是毫不相干的。如果摹仿上述古代藝術(shù)的理想形式和拋棄正確的自然形式,導(dǎo)致虛偽空洞的抽象化,呂莫爾那樣尖銳地攻擊它,當(dāng)然就是正確的。”
當(dāng)然他們所說的自然美,那是從自然中抽象出來的一種美,化作人的一種心靈意蘊(yùn),使其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來,而不是對自然機(jī)械的模仿,或生搬硬套。對此,黑格爾進(jìn)行過精辟的闡述。他認(rèn)為:“具有心靈意蘊(yùn)的自然形式在事實(shí)上應(yīng)該了解為具有一般意義的象征性,這就是說,這些自然形式并不因?yàn)樗鼈儽旧矶幸饬x,而只是它們所表現(xiàn)的那種內(nèi)在心靈因素的一種外觀。就是這種心靈因素使這些自然形式還在現(xiàn)實(shí)狀態(tài)而尚未進(jìn)入藝術(shù)領(lǐng)域之前就已具有觀念性,不同于不表現(xiàn)心靈的單純自然。”
黑格爾對當(dāng)時(shí)德國流行的“追求理想”和“妙肖自然”兩派的對立觀點(diǎn)進(jìn)行了批判,而認(rèn)為藝術(shù)的意蘊(yùn)應(yīng)與自然之美相吻合,是自然美在人的心靈消化后從而在藝術(shù)中進(jìn)行表現(xiàn),正如他在論述古典藝術(shù)的形成過程時(shí)說:“古典型藝術(shù)的對象并不是單純的自然而是已由精神意義滲透了的自然。所以要揚(yáng)棄的就是象征型藝術(shù)用直接的自然形體去表達(dá)絕對的那種表達(dá)方式。”我國著名美學(xué)家朱光潛先生在他翻譯黑格爾《美學(xué)》的注釋里說得好:“在藝術(shù)里的自然是經(jīng)過觀念化的自然,不是生糙的自然。所謂‘觀念化的就是自然納入心靈,受到心靈的滲透和影響,在心靈里轉(zhuǎn)化為觀念或思想,于是成為表現(xiàn)心靈的材料。這種自然是經(jīng)過提練和提高,具有更高的普遍性。”
對于中國許多書畫藝術(shù)家來說,他們經(jīng)常喜愛游覽在美麗的大自然間,并對自然進(jìn)行觀察、欣賞,甚至模寫。他們用毫穎,畫出那感悟的優(yōu)美動(dòng)感的線條,同時(shí)又蘸飽著墨色,進(jìn)行渲染,以不可勝數(shù)的點(diǎn)與線、線與面、骨與肉、淡與濃、柔與剛,以及干與濕等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那萬物宇宙的一切斑斕。特別是作為抽象藝術(shù)的中國書法來說,也有著與自然現(xiàn)象的美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正如沈尹默所說:“雖然字的造形是在紙上,但是它的神情意趣,卻與紙墨以外的,自然環(huán)境中的一切動(dòng)態(tài)有自相契合之處。所以有人看見挑擔(dān)的彼此爭路、船工撐上水船、樂伎的舞蹈、草蛇、灰線,甚至于聽見了江流洶涌的響聲,都會使善于寫字的人,得到很大的幫助。”而古今許多書論家都曾論述過書法與自然美的關(guān)系,如孫過庭在《書譜》中稱之為“同自然之妙有”。因此,自然之美,從某種意義上講,應(yīng)該是美的最高表現(xiàn),也是審美的參照物。
4.留存的持久性
每當(dāng)一個(gè)藝術(shù)或藝術(shù)品被炒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時(shí)候,人們對藝術(shù)審美的這種喧囂總會表示出無奈,“讓歷史來證明”就是一種無奈的評語。其實(shí)真正的藝術(shù)應(yīng)該是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yàn)的,因?yàn)闅v史是無情的,時(shí)間是無情的,它可以把一切非藝術(shù)的東西蕩滌掉,也可以把被人們遺漏的藝術(shù)撿回來。這是由于藝術(shù)美是一種歷史,美是由歷史形成的。自從有了人類文明,人們就有了審美觀,審美過程就是一種歷史性的比較。因此,審美觀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而發(fā)展,使審美觀得到不斷的深入和豐富。人類在原始時(shí)期審美及美的創(chuàng)造是低級的,在當(dāng)時(shí)的歷史背景下認(rèn)為是最美的,而有的在今天看來也許并不美,甚至是笨拙的。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人們的審美觀不斷提高,也不斷創(chuàng)造出更美的東西。人們在歷史性的審美比較中,逐漸累積形成了一種基本的審美經(jīng)驗(yàn),也是一種“審美共識”或“審美準(zhǔn)則”。貢布里希勛爵把這種“歷史審美比較”比作藝術(shù)競賽,通過競賽,競出藝術(shù)的大師、作品和規(guī)則。他說:“往昔的大師有點(diǎn)像文化英雄,他們的藝術(shù)成就不僅被傳說提及,而且也被社會保存,成了對后人的不斷挑戰(zhàn)。……藝術(shù)不僅僅是一種競賽,但是我們可以滿不在乎地使用這個(gè)比喻,這可能是由于競賽的優(yōu)點(diǎn)是依靠精通去探討問題,因?yàn)楦傎惻c藝術(shù)一樣,也需要社會氣氛和傳統(tǒng)以使其達(dá)到和真正的精通相一致的有素養(yǎng)的高級水平。……藝術(shù)不是一種具有固定規(guī)則的競賽,而是在前進(jìn)當(dāng)中制定規(guī)則。”可見,這種審美共識或規(guī)則是發(fā)展的,而且對于評判藝術(shù)價(jià)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yàn)椤八峁┮恍┖饬康臉?biāo)準(zhǔn),即衡量卓越水平的標(biāo)準(zhǔn),鏟平了這些標(biāo)準(zhǔn),我們就不可能不迷失方向。”
人們在歷史性比較中形成了不同時(shí)期和不同地區(qū)的“審美共識或準(zhǔn)則”,然后通過這種審美觀,對流傳下來的傳統(tǒng)藝術(shù)進(jìn)行重新審視,再次評判它的藝術(shù)性或?qū)徝佬浴R恍﹥?yōu)秀的藝術(shù)作品在千百年來的不斷比較和審美中經(jīng)久不衰,成為經(jīng)典之作,成為藝術(shù)奧林匹克山上的神明,既可用來崇拜,也可作為一種標(biāo)準(zhǔn)或規(guī)則。而有些藝術(shù)在當(dāng)時(shí)能夠?yàn)榇蠹宜邮埽皇窃诋?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下,人們的審美觀念與傳統(tǒng)守舊發(fā)生了沖突,但并不是它的本身具有多少審美性,當(dāng)然它也不會留存久遠(yuǎn)。而另有一些藝術(shù),在當(dāng)時(shí)并不被人們所看好,但在其后的比較審美中發(fā)現(xiàn)了它的藝術(shù)價(jià)值,逐漸被人們所重視,當(dāng)然也不斷受到歷史的挑戰(zhàn)。正如英國著名藝術(shù)史家柯律格教授所說:“一些作品早在制作的當(dāng)時(shí)就被視為藝術(shù)品,并且在隨后的記載中繼續(xù)被認(rèn)為是杰出的作品,一直延續(xù)到當(dāng)下,而其他一些作品的藝術(shù)身份則是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強(qiáng)加的。有一些作品恰好不屬于傳統(tǒng)而經(jīng)典的‘重要藝術(shù)品,它們因未能符合品質(zhì)需求的標(biāo)準(zhǔn)而在這類介紹性著作中面臨著挑戰(zhàn)。”由此,具有真正審美價(jià)值的藝術(shù),都是經(jīng)過歷史考驗(yàn)的,因?yàn)椤皟r(jià)值已經(jīng)在歷史中實(shí)現(xiàn)”。
而對于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審美又該如何呢?貢布里希也曾困惑:“越走近我們自己的時(shí)代,就越難以分辨什么是持久的成就,什么是短暫的成就。”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因?yàn)楫?dāng)代的藝術(shù)還沒有經(jīng)過歷史性的檢驗(yàn),它的審美價(jià)值如何評判呢?對此我們只能用歷史觀。歷史學(xué)家、美學(xué)家克羅齊有句眾所周知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這是以當(dāng)代的觀點(diǎn)審視歷史、評價(jià)歷史或解釋歷史,但同樣也可以以歷史的觀點(diǎn)審視當(dāng)代、評價(jià)當(dāng)代或解釋當(dāng)代,所謂的“以史為鑒”。歷史的觀點(diǎn)既是一種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也是一種發(fā)展的觀點(diǎn),是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在藝術(shù)審美上,歷史的觀點(diǎn)就是一種“審美準(zhǔn)則”,這樣的準(zhǔn)則是歷史賦予的。正如布爾迪厄所說:“建構(gòu)美學(xué)判斷的對立并不是先天賦予的,而是被歷史地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因此它們與使用的歷史條件密不可分。”隨之,他進(jìn)一步指出:“美學(xué)稟賦,把被社會指定運(yùn)用這種稟賦的物品變成藝術(shù)作品,同時(shí)把它的力量,連同它的范疇、概念、分類分配給審美能力,因此它是整個(gè)歷史的一種產(chǎn)物。”而這種產(chǎn)物就是在歷史性的比較審美中流傳下來的藝術(shù)成就,它是人們建立審美理念的一個(gè)重要依據(jù)和支撐,也是審美判斷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準(zhǔn)。貢布里希說:“任何發(fā)達(dá)的文化都有在傳統(tǒng)中流傳下來的成就以充當(dāng)檢驗(yàn)卓越程度的標(biāo)準(zhǔn),盡管各種文化在它們對精通種類的估價(jià)上各自不同。”因此,藝術(shù)要留存持久性,就是要經(jīng)得起歷史性的比較和審美,即使是當(dāng)代藝術(shù),如果用歷史的準(zhǔn)則來審視,它是否具有真正的藝術(shù)價(jià)值終究會彰顯出來。
二、藝術(shù)傳承是一個(gè)漫長而艱難的歷程
藝術(shù)既是一種重要的文化、思想和精神載體,也是一種特殊的構(gòu)造物;它既具有高難度的技藝性,也具有深刻而豐富的思想性。藝術(shù)的發(fā)展伴隨著藝術(shù)的繼承,一部藝術(shù)發(fā)展史也是一部藝術(shù)繼承史,在發(fā)展中繼承,也在繼承中發(fā)展,從來沒有一種藝術(shù)憑空從天而降,也從沒有天才不經(jīng)過艱苦的學(xué)習(xí)和傳承與生俱來創(chuàng)造出傳世名作。千百年來,藝術(shù)名家群星璀璨,藝術(shù)思想礦藏深厚,藝術(shù)作品無以計(jì)數(shù),因此,藝術(shù)的傳承需要一個(gè)相當(dāng)長且艱難的過程,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綿延不斷的過程,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的持續(xù)努力。從藝術(shù)的整體來說,是如此,從一門藝術(shù)甚至其中的一個(gè)流派或一種風(fēng)格來說,也是如此。
1.藝術(shù)的技藝性需要艱苦的練習(xí)才能達(dá)到
任何種類的藝術(shù)表現(xiàn)都需要技藝性,或稱藝術(shù)技巧,這是藝術(shù)的一個(gè)重要特征,它的熟練掌握需要經(jīng)過長期而刻苦的訓(xùn)練,人們常說的“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而藝術(shù)技藝是前人一代一代不斷進(jìn)行總結(jié)、提練和創(chuàng)新出來的,對它們的嚴(yán)格而熟練掌握既是一個(gè)學(xué)習(xí)的過程,也是一個(gè)傳承的過程。正如書法大家沈尹默論述書法技藝——筆法所說:“不知經(jīng)過了幾多歲月,費(fèi)去了幾何人仔細(xì)傳習(xí)的精力,才創(chuàng)造性地被發(fā)現(xiàn)了,成為書家所公認(rèn)的規(guī)律,即筆法,……而這不可恪遵的唯一根本大法,只有遵循著它去做,書學(xué)才有成就和發(fā)展的可能。”
就中國的書畫藝術(shù)而言,著名書畫家和鑒賞大師王時(shí)遷先生曾對中國書畫的筆墨功夫有過精辟的論斷:“中國的筆墨就像聲音訓(xùn)練般,必須經(jīng)過極多練習(xí),耗費(fèi)許多功夫,才能達(dá)到精通的地步。”可想而知,前人花費(fèi)很大精力經(jīng)過傳統(tǒng)積累發(fā)展了一門藝術(shù)的技藝,如果后人學(xué)習(xí)與繼承,必然也需要花費(fèi)一定的功夫加以臨摹訓(xùn)練才可以掌握。大書法家米芾在他的《群玉帖》里提到他對古人書帖的反復(fù)練習(xí):“余初學(xué)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jié),乃學(xué)柳《金剛經(jīng)》。久之,知出于歐。久之如印極排,乃慕褚,而學(xué)最久。又學(xué)段季轉(zhuǎn)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并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鐘方而師《師宜官》《劉寬碑》是也。篆便愛《詛楚》《石鼓文》,又悟竹筆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由此可見,藝術(shù)的傳承并非輕而易舉,而是需要勤奮而刻苦地反復(fù)練習(xí)前人的技法。而當(dāng)今一些人無視傳統(tǒng)的積累,只想獨(dú)創(chuàng)技法,卻違反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而另有一些人,卻不愿花苦功夫熟習(xí)前人的技法,只是有個(gè)皮毛的掌握,結(jié)果卻顯功力不夠。對此,著名畫家潘天壽有過精辟論述:“在學(xué)習(xí)繪畫上,是一種不秘的寶貴樞紐,必須以勤懇學(xué)習(xí)的態(tài)度,學(xué)習(xí)古人的傳統(tǒng)技法,打好熟練的基礎(chǔ),……中國畫系的同學(xué)在校學(xué)習(xí)期間,主要還是一個(gè)打基礎(chǔ)的階段,通過寫生和臨摹的訓(xùn)練,學(xué)習(xí)寫生的技能和體會民族繪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尚未到獨(dú)創(chuàng)風(fēng)格的階段,這是要加以注意的。否則,在缺乏基礎(chǔ)訓(xùn)練的情況下,一入手就亂創(chuàng)風(fēng)格,必然會徒費(fèi)時(shí)間精力而無所成功。”
而西方藝術(shù)也同樣需要技藝性的掌握,甚至曾有把技法等同于藝術(shù)的時(shí)代,那時(shí)藝術(shù)、技藝和技術(shù)這三個(gè)名詞的區(qū)別始終不甚明顯。他們認(rèn)為,“任何工藝品的制作都依賴于技藝與技術(shù)的知識。一個(gè)陶瓶、一個(gè)提籃,或一件刺繡與一座寺廟、一幅畫或一件雕塑一樣需要上述二者。唯有形式概念的精妙處理與能留住永恒的技術(shù)掌握這二者合作無間,才可能誕生完美的作品。”因此,在特別重視藝術(shù)技法傳統(tǒng)的西方藝術(shù)史上,許多卓有成效的藝術(shù)家都曾在作坊里當(dāng)過學(xué)徒,進(jìn)行過基本技法的學(xué)習(xí)和鍛煉。據(jù)傳,達(dá)·芬奇曾在佛羅倫薩一個(gè)一流的作坊里當(dāng)過學(xué)徒,作坊的主人是當(dāng)時(shí)著名的畫家兼雕刻家韋羅基奧,在這個(gè)制作各種杰作的作坊里,年輕的達(dá)·芬奇無疑學(xué)到了許多東西。他學(xué)會了根據(jù)裸體和穿衣的模特兒習(xí)作來細(xì)心地為繪畫和雕像做準(zhǔn)備,學(xué)會了畫植物和珍奇的動(dòng)物習(xí)作,而且他在透視光學(xué)和用色方面接受了全面的基礎(chǔ)訓(xùn)練。貢布里希說:“對于其他任何有才華的孩子來說,這種訓(xùn)練就足以使他成為高明的藝術(shù)家,而且事實(shí)上也有許多優(yōu)秀的畫家和雕刻家的確出自韋羅基奧的興旺的作坊。”而米開朗琪羅也一樣,年輕時(shí)進(jìn)入吉蘭達(dá)約(當(dāng)時(shí)著名的藝術(shù)家之一)繁忙的作坊,當(dāng)了3年學(xué)徒,在作坊里,他學(xué)到了雕刻家所具有的技術(shù)手法、畫濕壁畫的扎實(shí)技巧和全面的素描基礎(chǔ)。拉斐爾也同樣如此,他跟隨當(dāng)時(shí)名家之一的佩魯吉諾學(xué)習(xí),學(xué)會了老師傳承的“漸隱法”、“透視縮短法”等,同時(shí)他還努力學(xué)習(xí)了前兩位巨人及其更前人的一些藝術(shù)技法,如利用大型素描草圖來制作大型壁畫等。特別指出的是,藝術(shù)大師們在創(chuàng)作中,他們對技法的輕松諳練,并非一些人所認(rèn)為它是簡易之事,而是長期練就的深厚功底。正如貢布里希對拉斐爾的評價(jià)所說:“拉斐爾最偉大的作品好像絲毫不費(fèi)力氣,以致人們往往想不到那是慘淡經(jīng)營,精勤不懈的結(jié)果。”由此可見,對藝術(shù)技法的熟練掌握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反映了對藝術(shù)的傳承并非易事。
2.藝術(shù)思想和藝術(shù)精神的繼承需要長期的學(xué)習(xí)和吸收
歷史的傳承離不開思想和精神的學(xué)習(xí)、吸收和發(fā)展,它的過程更為艱難而漫長。自古至今,人類留下了大量而豐富的藝術(shù)思想并蘊(yùn)含著藝術(shù)精神。它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是對藝術(shù)進(jìn)行哲學(xué)思考,形成美學(xué)理論,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劉載熙的《藝概》等,康德的《判斷力批判》、黑格爾的《美學(xué)》、克羅齊的《美學(xué)原理》、丹納的《藝術(shù)哲學(xué)》等等;二是藝術(shù)家們關(guān)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體會和經(jīng)驗(yàn),有的呈零碎狀,有的進(jìn)行了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如中國歷代的書論和畫論。也有兩者相結(jié)合的,如孫過庭的《書譜》、張彥遠(yuǎn)的《歷代名畫記》、達(dá)·芬奇的《論繪畫》等。
而藝術(shù)思想和精神的傳承,不僅需要刻苦的研讀,更需要對它的領(lǐng)略。自古至今,藝術(shù)大師們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大家,不僅得助于他們精湛的畫法畫技,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們對藝術(shù)思想的精心研讀和對前人藝術(shù)精神的發(fā)揚(yáng),使藝術(shù)意識和藝術(shù)修養(yǎng)不斷得到提升。雖然有一些畫家,其技法非常精練,但終究難成大家,因?yàn)樗囆g(shù)風(fēng)格需要思想和精神去支撐。人們常說,藝術(shù)思想和藝術(shù)精神就像一盞明燈,它照亮的范圍決定你能走多遠(yuǎn)。國畫大家黃賓虹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畫稱藝術(shù),藝本樹藝,術(shù)是道路,道形而上,藝成而下。畫之創(chuàng)造,古人經(jīng)過之路,學(xué)者當(dāng)知有以采擇之,務(wù)研究其精神,不徒師法其面貌,以自成家,要有內(nèi)心之微妙。”特別是他在論述中國畫學(xué)之人格時(shí),首先強(qiáng)調(diào)要多讀書,他說:“何謂多讀書?甲、古今論畫之書;乙、金石碑帖;丙、古人詩歌;丁、筆記小說。”由此看出,這些書中蘊(yùn)含著豐富的藝術(shù)思想,只有經(jīng)過不斷的學(xué)習(xí),才能掌握藝術(shù)的真諦,也才能提高自己的藝術(shù)修養(yǎng)。
中國自先秦始,就有系統(tǒng)的藝術(shù)思想,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藝術(shù)精神。孔子尊崇音樂,以音樂教化人。孟子對美下了“充實(shí)之謂美,充實(shí)而有光輝之謂大”(《孟子·盡心下》)的定義。而第一部具有系統(tǒng)藝術(shù)理論的《樂論》是荀子所著,他最著名的“不全不粹不足以謂之美”(《荀子·勸學(xué)》),被藝術(shù)家所尊崇。特別是老莊的美學(xué)思想和藝術(shù)精神,一直為后世美學(xué)家和藝術(shù)家所繼承和發(fā)展。老莊提出的“道”、“氣”、“有”、“無”、“虛”、“實(shí)”“味”、“妙”、“虛靜”、“自然”等一系列概念對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美學(xué)家葉朗先生所言:“不研究老子和莊子的美學(xué),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國古典藝術(shù)的意境的秘密。”到了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藝術(shù)走到了“藝術(shù)自覺”的新時(shí)代,它造就了藝術(shù)思想的成熟和藝術(shù)精神的豐碑,出現(xiàn)了劉勰的審美意象分析論、顧愷之的傳神論、謝赫的六法論等萬古不移的精論。他們提出了“得意忘象”、“傳神寫照”、“澄懷味象”、“氣韻生動(dòng)”等命題,承繼了老莊的“氣”、“妙”、“神”、“意象”,同時(shí)在藝術(shù)實(shí)踐上發(fā)展了“風(fēng)骨”、“隱秀”、“神思”等新的美學(xué)范疇,而書學(xué)開始藝術(shù)總結(jié)并理論化。唐五代后,藝術(shù)思想已上升為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唐太宗李世民親自撰寫論文《王羲之傳論》《論書》。尤其張彥遠(yuǎn)把繪畫藝術(shù)看作儒家典籍一樣,具有成教化、助人倫的作用。他在《歷代名畫記》中開篇言道:“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shí)并運(yùn)。”因此,方聞先生說:“世界上沒有哪一種文明像在中國這樣,藝術(shù)在社會和文化中,被有意識地賦予如此重要的地位。帝王貴胄不僅熱心于贊助扶植藝術(shù),而且往往本人還是出色的藝術(shù)家。皇家翰林院的藝術(shù),不僅是詩與美的藝術(shù),而且還是道德和政治理想的藝術(shù)——其基于新儒學(xué)‘文以載道的主張,然而其附加的指令,即這個(gè)‘道,必須是由國家來代表。”在藝術(shù)大繁榮大發(fā)展的背景下,出現(xiàn)了張彥遠(yuǎn)的《歷代名畫記》、荊浩的《筆法記》、張懷瓘的《畫品》和《書斷》、孫過庭的《書譜》等一大批藝術(shù)理論著作,并提出了“同自然之妙有”、“意存筆先”、“外師造化”、“度物象而取真”等重要命題,形成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體現(xiàn)了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精神。到了宋元時(shí)代,也是所謂的文人藝術(shù)時(shí)代,大批文人直接參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以主體心性的宣泄凌駕于客觀物象的造形之上,使文人畫達(dá)到“好、曉、能”。并且他們結(jié)合自己的藝術(shù)實(shí)踐對以前的藝術(shù)思想進(jìn)一步進(jìn)行審視,出現(xiàn)了一大批具有影響的藝術(shù)理論論著,如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宣和畫譜》等,以及以蘇軾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有關(guān)書畫的論述。在這些論著中,既有對唐五代乃至更前的老莊藝術(shù)思想的繼承,也有對藝術(shù)思想的發(fā)展,都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郭熙的“身即山川而取之”和“三遠(yuǎn)”之論,對山水畫創(chuàng)作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總結(jié);蘇軾的“成竹在胸,身與竹化”,反映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黃休復(fù)的“四格論”,確立了逸格的地位;黃庭堅(jiān)則把佛道思想融入到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之中,等等,藝術(shù)思想十分豐厚。正如人們所說,這個(gè)時(shí)期的美術(shù)著述“由于大批帝王貴胄、文人士夫、優(yōu)秀畫家的參與,對文化藝術(shù)的各個(gè)領(lǐng)域既能觸類旁通,對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與史論關(guān)系亦能水乳交融,再加上整個(gè)社會崇文的時(shí)代氛圍熏染,遂使它在質(zhì)量上達(dá)到了歷史的最高經(jīng)典水準(zhǔn),與美術(shù)創(chuàng)作的實(shí)踐成果交相輝映,共同體認(rèn)了中國美術(shù)史由政教、宗教菁華向人文精神轉(zhuǎn)捩的特色。迄今被認(rèn)為足以代表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菁華的美學(xué)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這一時(shí)期獲得確立的——前人的工作,不過是為它作了準(zhǔn)備和鋪墊;而后世的努力,則大都是對它加以進(jìn)一步的闡釋、發(fā)揚(yáng)而已。”而到了明代,文人創(chuàng)作成為主流,同時(shí)創(chuàng)作進(jìn)入了“復(fù)古”時(shí)期。一方面,文人們的人文修養(yǎng)為創(chuàng)作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力追尋遠(yuǎn)古的藝術(shù)形式。在藝術(shù)思想上,他們提出了要達(dá)到“氣韻生動(dòng)”,必須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加強(qiáng)人文知識之修養(yǎng),而人文的修養(yǎng)越深,藝術(shù)心靈的表現(xiàn)也就深厚寬廣。正如徐復(fù)觀先生所說:“學(xué)問教養(yǎng)之功,通過人格、性情,而依然成為藝術(shù)絕不可少的培養(yǎng)、開辟力量。”而這些藝術(shù)思想的最終根源之一,正是也來自老莊的“虛、靜、明”藝術(shù)觀。作為中國古典藝術(shù)思想的終結(jié)時(shí)期——清代,是傳統(tǒng)藝術(shù)集大成的時(shí)代。由于集大成,藝術(shù)追求在藝術(shù)語言、技巧等方面都融匯了前代的經(jīng)驗(yàn)并涵蓋整個(gè)清代美術(shù),同時(shí),藝術(shù)作為創(chuàng)新方面,又往往囿于古人的成規(guī),有一種保守理念。因此,在藝術(shù)思想方面,表現(xiàn)出創(chuàng)新與繼承的爭論,其最具影響的莫過于石濤的《畫語錄》和劉熙載的《藝概》。而特別指出的是,自元明以來,具有創(chuàng)新的民間藝術(shù)思想不斷漫延和壯大,與主流藝術(shù)思想相互滲透和影響,也已成為中國藝術(shù)思想和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文化藝術(shù)的民族性,西方藝術(shù)思想和藝術(shù)精神不完全同于中國的藝術(shù)思想和精神,但是,作為人類精神文化遺產(chǎn),足有許多可借鑒、參考和學(xué)習(xí)之處。自古希臘羅馬以來,西方數(shù)以百計(jì)的哲學(xué)家、美學(xué)家和藝術(shù)家都有在藝術(shù)上進(jìn)行探索的歷程,為人類留下了十分豐富的藝術(shù)思想和獨(dú)創(chuàng)的藝術(shù)精神。在古希臘的藝術(shù)思想中,模仿學(xué)說在闡明藝術(shù)對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都對“模仿”進(jìn)行過論述,以致于有的藝術(shù)史學(xué)家認(rèn)為,西方藝術(shù)思想的歷史自模仿學(xué)說開始。到了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一個(gè)藝術(shù)成為風(fēng)尚的時(shí)代,藝術(shù)名家眾多,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昌盛,藝術(shù)思想蘊(yùn)厚。就繪畫來說,首先是佛羅倫薩藝術(shù)家阿爾貝蒂的《論繪畫》,它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的個(gè)性特征,突現(xiàn)科學(xué)與理性,并認(rèn)為藝術(shù)應(yīng)該模仿自然,而終歸于美,而這種藝術(shù)美超越自然之美的藝術(shù)精神覆蓋了整個(g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這時(shí)期三大藝術(shù)巨匠之首的達(dá)·芬奇,也有一部傳世畫論名作《論繪畫》,他的藝術(shù)思想“鏡子說”主要反映在其中。他發(fā)展了的模仿自然說,認(rèn)為藝術(shù)不僅要忠實(shí)于并再現(xiàn)自然,而且藝術(shù)需要有創(chuàng)造性和神性,要以人的內(nèi)心去體會自然。他說:“畫家的心應(yīng)該像一面鏡子,永遠(yuǎn)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攝進(jìn)來,前面擺著多少事物,就攝取多少形象。……畫家應(yīng)該研究普遍的自然,就眼睛看到的東西多加思索,要運(yùn)用組成每一事物的類型的那些優(yōu)美的部分。用這種辦法,他的心就會像一面鏡子真實(shí)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就會變成好像是第二自然。”達(dá)·芬奇所表達(dá)的藝術(shù)真實(shí),就是以直觀形相表現(xiàn)的神圣思想和對象特質(zhì)的統(tǒng)一,也是科學(xué)真實(shí)的源泉所在。正如藝術(shù)史家貢布里希所說:“總之,《繪畫論》證明,建立繪畫科學(xué)的基礎(chǔ)……是一個(gè)以幾何學(xué)方式分析事物形相的理性頭腦。”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另兩位藝術(shù)巨匠拉斐爾和米開朗琪羅,他們的“風(fēng)格主義”藝術(shù)思想也一直影響后人。拉斐爾風(fēng)格的古典現(xiàn)實(shí)主義不僅為藝術(shù)理論提供了典型,而他創(chuàng)作所表現(xiàn)的無限優(yōu)雅和創(chuàng)造力,以及他的姿態(tài)的旋律性和筆觸的精致性都會給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記而值得研習(xí)。而米開朗琪羅開創(chuàng)的雕塑藝術(shù)不僅影響了后來的雕塑藝術(shù)本身,也對其他藝術(shù)門類,特別是繪畫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他的藝術(shù)思想也表現(xiàn)為對過去模仿自然說的繼承和發(fā)展,因?yàn)樗谀7聜鹘y(tǒng)中注入了強(qiáng)烈創(chuàng)造精神的美學(xué)觀,他認(rèn)為如果繪畫不加選擇地照摹自然,這一類畫風(fēng)就見不出理性、見不出偉大。西方文藝復(fù)興尤如藝術(shù)的寶藏,而對它的研究和挖掘,不僅反映了美術(shù)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也不斷為后人指明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路徑。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唯一可與三位大師名列的非意大利人——丟勒,不能不提,恩格斯曾贊揚(yáng)過他,歌德贊揚(yáng)他可與偉大意大利藝術(shù)家等量齊觀。他與達(dá)·芬奇一樣,有自己的藝術(shù)思想留世。他的藝術(shù)思想主要表現(xiàn)為對比例學(xué)說的深入研究,他認(rèn)為這是繪畫的科學(xué)基礎(chǔ),也為后人提出了以幾何透視學(xué)作畫的原理。而作為藝術(shù)思想發(fā)展的最高理論化,莫過于藝術(shù)美學(xué)的巨大成就和高峰,那就是德國的古典美學(xué)時(shí)代。這個(gè)時(shí)期出現(xiàn)了兩位美學(xué)巨人——康德和黑格爾。康德的藝術(shù)美學(xué)思想在他的名著《判斷力批判》中,黑格爾的藝術(shù)美學(xué)思想反映在他的三大卷《美學(xué)演講錄》中,然而他們的藝術(shù)思想博大而精深,后人從不同的視角進(jìn)行研究,也作出了不同的闡釋。但是,他們都認(rèn)為藝術(shù)應(yīng)該是美的,從而給出了藝術(shù)作品最基本的判斷。康德認(rèn)為:“審美的藝術(shù)作為美的藝術(shù),就是一種把反思性的判斷力、而不是以感官為準(zhǔn)繩的藝術(shù)……在美的藝術(shù)的一個(gè)產(chǎn)品上,人們必須意識到,它是藝術(shù)而不是自然。”而黑格爾在他的美學(xué)演講錄一開始就已明確,“這些演講是討論美學(xué)的;它的對象就是廣大的美的領(lǐng)域,說得更精確一點(diǎn),它的范圍就是藝術(shù),或則毋寧說,就是美的藝術(shù)。”而演講錄第一卷都是討論藝術(shù)美的,如藝術(shù)的概念、藝術(shù)的理念等。當(dāng)然,在這一時(shí)期,還出現(xiàn)了費(fèi)希特、謝林、席勒、歌德、費(fèi)爾巴哈等一大批思想家和藝術(shù)家,他們對藝術(shù)美學(xué)的探討也深有見地,作為古典美學(xué)高峰不可或缺的資源。19世紀(jì)后,藝術(shù)開始進(jìn)入多元的時(shí)代,各種主義、風(fēng)格、流派紛紜,思想繁雜。“主義”有:新康德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悲觀主義、實(shí)證主義、唯美主義、表現(xiàn)主義、形式主義、存在主義,等等,以哲學(xué)的視角來探索藝術(shù)的本質(zhì),從而形成各種學(xué)派的藝術(shù)思想。創(chuàng)作流派有:新古典主義、印象主義、拉斐爾前派、后印象、后現(xiàn)代、立體主義,等等,以不同的技法方式來創(chuàng)作,從而形成各種流派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也蘊(yùn)含著一定的思想光輝。特別是抽象主義代表人物康定斯基把通過心靈的激蕩所產(chǎn)生的內(nèi)心感受或“內(nèi)心需要”所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稱為真正美的藝術(shù),也稱為藝術(shù)中的精神,對于20世紀(jì)視覺藝術(shù)的變革產(chǎn)生過深遠(yuǎn)的影響,即使在當(dāng)代,對于豐富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手法、拓寬藝術(shù)的審美領(lǐng)域,也具有借鑒的意義。
3.大量優(yōu)秀的藝術(shù)經(jīng)典需要漫長的臨摹與消化
作品是藝術(shù)的載體,臨摹和鑒賞藝術(shù)大師的作品既是一個(gè)學(xué)藝的過程,也是一個(gè)傳承的過程,特別是在繪畫藝術(shù)中,更是一個(gè)技法訓(xùn)練的必經(jīng)過程。就藝術(shù)的整體而言,千百年來有大量的優(yōu)秀藝術(shù)作品流傳下來,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后人進(jìn)行鑒賞、學(xué)習(xí),甚至臨摹訓(xùn)練,才能把傳統(tǒng)的真諦和精髓傳承下來;就個(gè)體而言,要真正繼承前人的偉大成就,僅憑少量的作品,無法把握藝術(shù)的全貌和演變的進(jìn)程,更談不上繼承與發(fā)展了。據(jù)傳,我國著名藝術(shù)大師張大千先生年輕時(shí)曾有“三個(gè)一千”之誓愿,其中之一就是要至少臨摹一千幅畫,可見他不僅用功之深,而且他要借鑒更多不同風(fēng)格的傳統(tǒng)。為此,他說:“我國有悠久的繪畫藝術(shù)傳統(tǒng),歷代大家遺留下來的許多名跡。他們在不同的社會里,用了一生的精力,積累了許多經(jīng)驗(yàn),我們要把這些豐富的經(jīng)驗(yàn)學(xué)到手。”同時(shí),他還指出:“切忌偏愛,因?yàn)槊抑嫸加衅溟L,學(xué)習(xí)的人都應(yīng)該吸收采取;但每個(gè)人的筆觸又天生有不同之處,故學(xué)習(xí)的時(shí)候不可只專學(xué)一人,也不可單就自己的筆路去追求,要憑苦學(xué)與慧心來汲取名作的精神。”因此,臨摹、學(xué)習(xí)乃至消化更多的古人名跡,特別是具有經(jīng)典性的作品,是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一項(xiàng)重要條件。如大書法家趙孟頫先苦臨了王羲之書法,領(lǐng)會了筆畫神韻,后以顏體楷書為范本練習(xí)用筆,兼學(xué)其他初唐大師,同時(shí)又對李邕、黃庭堅(jiān)等多位前代名家進(jìn)行了研練,終于在傳承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立了一種新書體。
中國書畫藝術(shù)源遠(yuǎn)流長,以筆墨紙硯為工具,以線條造型為手段,利用筆墨技巧和抒情寫意的審美意趣,發(fā)展出中國獨(dú)特的書畫藝術(shù),至今仍經(jīng)久不衰,留下了大量的優(yōu)秀作品,在美術(shù)史上作為典范的作品就達(dá)數(shù)千幅。中國書畫自晉以來,始構(gòu)建體系,創(chuàng)造經(jīng)典。王羲之確立了書法審美的基準(zhǔn)坐標(biāo),顧愷之開創(chuàng)了生活藝術(shù)時(shí)代。隋唐在人物、山水樓閣、鞍馬走獸等畫科方面相繼繁榮,如閻立本、展子虔、韓混等的名作恢弘富麗。唐楷確立了漢字用筆規(guī)范,影響深遠(yuǎn)。五代兩宋山水、人物、花鳥等繪畫更趨完備,崇尚寫實(shí),精能高雅,也是文人畫始。宋元書法在繼承的前提下個(gè)性張揚(yáng),賦予了深厚的文化內(nèi)涵。宋元出現(xiàn)了“宋四家”、“元四家”和鮮于樞、趙孟頫等為代表的風(fēng)格流派。明代書畫是承前啟后、流派濫觴的時(shí)代。在繪畫上先有粗獷縱肆的“浙派”、“院體”風(fēng)格主導(dǎo)畫壇,后有清雅淡麗的“吳門四家”替代了宮廷“院畫”,而陳淳、徐渭的寫意花鳥畫創(chuàng)作豐富了繪畫的表現(xiàn)和內(nèi)涵,特別是晚明的董其昌集文人書畫風(fēng)格大成,影響深遠(yuǎn),同時(shí)“松江派”在晚明也平添一色。明代書法創(chuàng)立了“臺閣體”風(fēng)格,后又?jǐn)[脫了它的束縛。清代書畫傳承與創(chuàng)新并存,名家輩出,流派紛呈。在書法上,王鐸、傅山等承襲明末書風(fēng),雄奇跌宕;劉墉、翁方綱等力追晉唐,帖學(xué)興起;鄧石如、伊秉綬等以金石入書,開碑學(xué)風(fēng),至晚清碑學(xué)興旺,何紹基、吳昌碩等最負(fù)盛名。繪畫上,“四王吳惲”以摹古集大成而居主流;“四僧”、“金陵八家”及“黃山畫派”等師法自然,開辟山水境界;宮廷繪畫融合西畫技法以豐富中國畫表現(xiàn)形式;“揚(yáng)州畫派”以張揚(yáng)個(gè)性而注入活力;“海上畫派”、“嶺南畫派”以融入現(xiàn)代性而走向近現(xiàn)代。
對于西方藝術(shù)而言,也同樣有大量前人的作品摹臨和研習(xí),這既是傳承的需要,也是發(fā)展的需要,更是創(chuàng)作創(chuàng)新的需要。藝術(shù)史家昂納在贊揚(yáng)魯本斯時(shí)說:“沒有畫家比魯本斯更勤奮、更專注地研究過意大利大師們的作品:他臨摹了數(shù)百張的草圖和素描。雖然他的臨摹是為了嘗試不同繪畫再現(xiàn)的方法,但呈現(xiàn)出的強(qiáng)烈的感官表現(xiàn)和豐沛的想象力,使這些臨摹之作和他的其他畫坊作品一樣具有強(qiáng)烈的個(gè)人特色。”魯本斯就是一個(gè)具有把傳承古老的民族傳統(tǒng)藝術(shù)與當(dāng)時(shí)風(fēng)行的人思想結(jié)合起來的美術(shù)代表人物,形成了色彩豐滿、運(yùn)動(dòng)感強(qiáng)的獨(dú)特風(fēng)格。而在西方藝術(shù)理論中,一個(gè)最重要的理論就是模仿學(xué)說,不僅要模仿自然,更要學(xué)習(xí)模仿前人的經(jīng)典作品。他們具有善于把留存的優(yōu)秀作品展現(xiàn)給后人觀摩、鑒賞和學(xué)習(xí)的傳統(tǒng),因此,西方很早就開始興辦博物館、美術(shù)館、藝術(shù)館和展覽館,在這些館里,人們可以看到不同時(shí)代、不同風(fēng)格的真實(shí)作品,給人一種震憾、感受和體驗(yàn)。正如藝術(shù)史家詹森所說:“只有當(dāng)你看到原作,你才會擴(kuò)展對這些作品的認(rèn)識。……我們希望你能去博物館參觀原作;但要記住,觀看藝術(shù)并感受它全部的影響需要長時(shí)間反復(fù)觀看。偶爾,你也許會對某件作品作深入的解讀,這需要精察細(xì)節(jié),需要追問它們?yōu)槭裁闯霈F(xiàn)于此。”作為歷史的藝術(shù)經(jīng)典應(yīng)是藝術(shù)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傳統(tǒng)藝術(shù)的一個(gè)重要支撐,不能離開作品而空談傳統(tǒng)。因此,對大量的經(jīng)典的學(xué)習(xí)和消化是一種傳承的重要方式,它決非輕而易舉之事,同樣需要艱苦而不斷地進(jìn)行。
三、當(dāng)前藝術(shù)創(chuàng)作存在的幾種傾向
當(dāng)前,對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來說,是一個(gè)繁榮發(fā)展時(shí)期,藝術(shù)學(xué)已成為一門學(xué)科,探索藝術(shù)規(guī)律已成共識。現(xiàn)在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無論是專業(yè),還是業(yè)余;也無論是意識的創(chuàng)作,還是自娛自樂,創(chuàng)作都處在亢奮的階段,從人員到作品,其數(shù)量都是前所未有。但滄海橫流,大浪淘沙,真正具有藝術(shù)性的作品卻極少,這是由于除了藝術(shù)評論界忱于贊揚(yáng)而趨利外,還與當(dāng)前藝術(shù)創(chuàng)作存在的幾種傾向有較大的關(guān)系。
1.形式化的過度摹仿,失卻傳承的真諦
任何藝術(shù)一般都是從摹仿開始,并且東西方藝術(shù)思想中就有“模仿學(xué)說”,有了摹仿才有了傳承。對中國書畫創(chuàng)作而言,摹仿則更為重要,而大凡藝術(shù)家都認(rèn)為這既是學(xué)藝的起步,也是創(chuàng)作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他們都有許多摹仿的名作傳世,如董其昌仿黃公望的《江山秋霽》、張大千臨董源的《江堤晚景圖》、沈尹默臨《鄭文公碑》字帖等。因而,董其昌在《畫旨》中稱:“初以古人為師,后以造物為師。”而張大千對書畫摹仿的重要性也多有提起。他說:“學(xué)習(xí)繪畫,臨摹是必經(jīng)的一個(gè)階段。……臨摹有了深厚的根基,才能談到創(chuàng)作。”而如何通過臨摹把原作的特征和優(yōu)點(diǎn)承繼下來,為自己在創(chuàng)作中所用,他有著精辟的論述。他說:“臨摹必須擷取各家之長,摻入自己的心得,最后要化古人為我有,創(chuàng)造自我獨(dú)立之風(fēng)格。而對于書法來說也是如此,沈尹默先生在強(qiáng)調(diào)臨帖的重要性時(shí)說:“臨帖可以從帖中吸取前人寫字的經(jīng)驗(yàn),容易得到他們用筆和結(jié)構(gòu)的繩墨規(guī)矩,便于入門,踏穩(wěn)腳步,既入門了,能將步子踏穩(wěn),便當(dāng)獨(dú)立運(yùn)用自己的思考去寫。”即使對創(chuàng)作來說,不時(shí)的臨帖也同樣受益,因此,他又說:“經(jīng)常還得要取歷代法書仔細(xì)研玩,隨時(shí)還可以得到一些啟發(fā),這于自寫時(shí)有很大幫助。”因此,摹仿無論對于藝術(shù)初學(xué)者來說,還是成熟的藝術(shù)家來說,都是需要的,因?yàn)橹挥胁粩嗟哪》聦W(xué)習(xí)才能不斷地從藝術(shù)的傳統(tǒng)中汲取營養(yǎng),也才能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風(fēng)格。正如高居翰教授所說:“前人的風(fēng)格或構(gòu)圖是可以變成畫家創(chuàng)作的據(jù)點(diǎn)的。跟那些不標(biāo)榜溯古,而且看起來像是直接取材于自然,或是無拘無束的自創(chuàng)(事實(shí)上,并沒有藝術(shù)作品是可以完全不受拘束而自創(chuàng)的)作品相比,這類以前人畫風(fēng)為出發(fā)點(diǎn)的作品,同樣也可以達(dá)到高度創(chuàng)新的目的。”
然而,真正的藝術(shù)摹仿或者說以模仿作為自己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一種源泉卻決非易事,所以高居翰教授認(rèn)為這種“仿”是一種創(chuàng)意性的摹仿。他說:“有能力在古人的畫件中,看出這些結(jié)構(gòu)上的特征,并且引為己用——這正是創(chuàng)意性‘仿古的最基本要求,而且也是豐富個(gè)人畫風(fēng)的一種手段,有益于增長個(gè)人的創(chuàng)造力。”因此,所謂的“仿”,主要是針對過去藝術(shù)大家的風(fēng)格、技法而已,或者是針對它的某一個(gè)特別畫作,而這畫作又具有代表性的意義,以此加以自由摹仿,而對于形似并不特別在意,主要是在于能否與藝術(shù)大家進(jìn)行“神會”。因?yàn)樽龅搅恕吧駮保憧擅摲f為大家的“代言或代表”,而他所傳達(dá)的當(dāng)然不是藝術(shù)大家的形式,而是他們的思想或藝境而已。如中國書法藝術(shù)而言,書家自古以來就一直主張,自由摹仿易于神會,它高于亦步亦趨的形式臨摹。對此,唐太宗在《論書》中說:“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xué)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以此可以反映他并不刻意去摹仿其“形勢”,而是去探索那書法的“骨力”本質(zhì)。而對中國繪畫來說也是如此,元代大家趙孟頫留下了一些仿古名畫傳世,后人常常從中讀出他對更早的大家的心領(lǐng)神會,而他自己經(jīng)常在自己仿古畫作的題識中自謙稱能力不逮,難以重現(xiàn)古人的“原貌”,而這原貌正是大家藝術(shù)畫作真正的特征。而明朝董其昌在仿古畫作中,常常凸顯甚至放大古畫中能真正表達(dá)前人畫中的藝境和某一特征,而不是全面地“復(fù)制”。
而對于當(dāng)今一些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來說,并不是從本質(zhì)上去創(chuàng)意性地摹仿或傳承前人留下的藝術(shù)傳統(tǒng),而是刻意地追求形式上的相像。譬如中國的書法創(chuàng)作,應(yīng)該從筆劃的“骨力”、字形的“結(jié)構(gòu)”等本質(zhì)特征去追尋前人,而不是過于或一味從形式上去攀仿。如有一種現(xiàn)象,在作品中蓋上許多印章,以模仿古人留下的書法作品,以為是在視覺上可以表達(dá)一種藝術(shù)特征,其實(shí)這純屬是一種誤讀。留下的一些古書法作品里,之所以有許多印章,它反映了一種歷史傳遞和社會現(xiàn)象,因?yàn)檫@些印章除了作者的以外,有一部分是收藏者的,還有一部分是鑒賞者的,各具特色的印章匯集在一件作品中,能起到一點(diǎn)視覺上的效果,但決不是書法藝術(shù)的真諦。還有一種現(xiàn)象,在理論和實(shí)踐歷來都有一些爭論,那就是對碑字的臨摹。一些書者為了體現(xiàn)碑字的所謂特點(diǎn),把字中的石記印、斧鑿印,甚至風(fēng)化痕也摹寫出來,這完全誤讀了碑字。其實(shí)這是碑字的一種現(xiàn)象,是石書、斧鑿石刻或風(fēng)化所造成的,而不是書法本身的特征,為此,章太炎先生作了《論碑版法帖》一文,就碑字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論述,并且文中最后他對臨碑字者提出了忠告。他說:“專求形似,體貌愈真,精彩愈遠(yuǎn),筆無已出,見誚諸城。后之習(xí)者,筆益蹇劣,至乃模寫泐痕,增之字內(nèi):一畫分?jǐn)?shù)起,一磔珠為數(shù)段,猶復(fù)上誣秦相,下詆右軍,則終為事法帖者所誚已。”(《論碑版法帖》)而當(dāng)代大書法家啟功先生也警告說,莫把碑字中殘渝痕跡也當(dāng)作古人用筆來攀仿。所以,人們認(rèn)為臨寫碑刻要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把刻本還原為墨跡,因?yàn)槟E反映了書法的藝術(shù)特征。
而對于繪畫創(chuàng)作來說,也同樣存在著過于形式化模仿的情況。當(dāng)今一些創(chuàng)作者缺乏對傳統(tǒng)中國畫的深入研究,具體表現(xiàn)為:一是缺乏對古代畫家所用材料的研究;二是缺乏對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技巧研究;三是更加缺乏對畫家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及其文化和道德修養(yǎng)的研究,并由此導(dǎo)致對他的風(fēng)格研究缺乏深入。而這三者又是相互作用的,軍事上有句名言“技術(shù)決定戰(zhàn)術(shù)”,而用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那就是“材料決定技巧”,也就是什么樣的材料就有什么樣的藝術(shù)技巧,材料對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來說意義十分重要,正如王季遷先生在談到中國繪畫的重要材料之一的筆時(shí)所說:“有時(shí)候材料影響了藝術(shù)家,有時(shí)候則是藝術(shù)家發(fā)明一些材料來制筆。”在西方藝術(shù)史上,藝術(shù)家們特別注重材料的使用,使材料與技藝并重,以表達(dá)作者想要的藝術(shù)思想和時(shí)代精神。藝術(shù)史名著《詹森藝術(shù)史》中,著名藝術(shù)史家詹森對不同時(shí)期不同風(fēng)格和流派的藝術(shù)在“材料與技法”方面作了系統(tǒng)的研究,并開辟章節(jié)進(jìn)行了論述和介紹。我國歷代卓有成就的大畫家也都特別注重材料與技巧的使用,在他們的畫論中偶有散見,如張大千等,而現(xiàn)代著名畫家錢松喦先生的《硯邊點(diǎn)滴》對此作了系統(tǒng)的論述。但是,對于歷代不同的畫家、不同的風(fēng)格、不同的流派,他們用什么樣的材料以及配合什么樣的技巧而來表現(xiàn)什么樣的藝術(shù)精神和思想,對此進(jìn)行系統(tǒng)的研究,在我國藝術(shù)創(chuàng)作界卻遠(yuǎn)遠(yuǎn)不夠(鑒藏界則比較注重,這就是為什么一些藝術(shù)大師往往也是一流的鑒賞家的原因之一)。特別重要的是,一個(gè)藝術(shù)家總在一定的文化歷史氛圍和生活環(huán)境中成長進(jìn)步和發(fā)展的,有著時(shí)代和文化的烙印,也有著個(gè)人成長的印記,而這一切在他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中必有反映,而這種風(fēng)格又是要通過一定的材料和藝術(shù)技巧來反映的,如果不對此進(jìn)行過仔細(xì)深入的研究,就難以理解他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思想。而當(dāng)今由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對上述三者缺少研究,在傳承的創(chuàng)作中,就存在著生搬硬套、作品過于形式化的現(xiàn)象,如以紙代絹或材料與技巧的錯(cuò)位使用,忽略真正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或?qū)︼L(fēng)格的錯(cuò)誤解讀,等等,因此,對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傳承和再創(chuàng)作,需要對傳統(tǒng)進(jìn)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2.變異的創(chuàng)新,使藝術(shù)創(chuàng)作走上岐途
任何藝術(shù)門類都有其自身存在和發(fā)展的緣由、條件和規(guī)律,它的發(fā)展過程雖然伴隨著創(chuàng)新的過程,但是如果不遵循它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一味人為地求異求新,那必然會使藝術(shù)創(chuàng)作走上岐途,而造成的結(jié)果不是使藝術(shù)走上末路,就是使藝術(shù)會重新回到原點(diǎn)。人們之所以喜歡經(jīng)典,經(jīng)典經(jīng)久不衰,就在于經(jīng)典符合人們的審美情趣,它已融入到人們的心里,產(chǎn)生了審美共鳴。因此,當(dāng)人們贊揚(yáng)一個(gè)藝術(shù)家時(shí),常會說他的作品像古典的某個(gè)作品那樣好,這充分說明他的作品中含有經(jīng)典里最有意味的成分,而經(jīng)典中最有意味的成分就蘊(yùn)含著藝術(shù)的規(guī)律。貢布里希說:“我們現(xiàn)代的觀念是一個(gè)藝術(shù)家必須‘創(chuàng)新,……過去大多數(shù)民族絕對沒有這種看法。埃及、中國和拜占庭的名家會對這種要求迷惑不解。中世紀(jì)西歐藝術(shù)家也不會理解為什么在老路子那么適用時(shí),還應(yīng)該創(chuàng)造新方法來設(shè)計(jì)教堂,設(shè)計(jì)圣餐杯,或者表現(xiàn)宗教故事。”由此可見,藝術(shù)的創(chuàng)新并不是隨意之事,它是由諸多的條件和因素決定的,如習(xí)俗、文化、審美、程式、材料,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以中國的書法藝術(shù)為例。作為中國書法藝術(shù),歷經(jīng)了三千多年,已形成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規(guī)律。著名美學(xué)家宗白華先生曾總結(jié)說,中國人寫的字能成為藝術(shù)品,有兩個(gè)主要因素,一是漢字,因?yàn)槌橄蟮狞c(diǎn)畫表現(xiàn)出物象之本,而漢字的結(jié)構(gòu)又表現(xiàn)出物象之關(guān)系。二是中國人用的筆,“它鋪毫抽鋒,極富彈性,所以巨細(xì)收縱,變化無窮”。但從書法藝術(shù)的特點(diǎn),可以進(jìn)一步升華和發(fā)展這個(gè)理論,一方面,作為漢字,它是書法的基礎(chǔ)和首要條件,離開漢字就談不上中國書法,而漢字現(xiàn)已發(fā)展成一種文化生態(tài)和文化認(rèn)同,它具有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性,因?yàn)檫@穩(wěn)定的結(jié)構(gòu)里蘊(yùn)含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性,而改變和獨(dú)創(chuàng)漢字的結(jié)構(gòu)而進(jìn)行的書法創(chuàng)作,違背了書法創(chuàng)作的軌道和規(guī)律。另一方面,是中國的筆,而更進(jìn)一步地講,應(yīng)該是筆寫,尤其是用毛筆寫更能體現(xiàn)。因?yàn)闈h字是一筆一筆寫出來的,而不是畫出來或用其它方式表現(xiàn)的,書法中的特有用筆所寫出的一筆一劃,它可以表現(xiàn)出天地萬物,也表現(xiàn)出中華文化,而其它方式是不可替代的。王季遷先生說得好:“筆墨或水墨是由中國毛筆所畫出,而具有無限的多樣性,在歷史中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它的重要性。……中國人到唐代時(shí)就已敏銳地知道了筆墨藝術(shù)無限的潛能。如果你不看一個(gè)畫家基本表現(xiàn)潛能之揮(即透過筆墨),那么你就看不到中國畫的精髓。書法就更不用說了。”
而當(dāng)今書法創(chuàng)作有一些傾向,一是把漢字過于形象化。雖然漢字是以象形起始的,但隨著漢字的發(fā)展并不是所有的漢字都是象形的,也不是所有的漢字都可以用形來表達(dá),即使有一些漢字是象形的,如果用萬物之形來表達(dá),那它不是一種書法藝術(shù)而是一種畸形的繪畫了。縱觀書法幾千年的歷史,前人留下數(shù)以萬計(jì)的書法經(jīng)典,無一以萬物之形“畫”字的,而是追求結(jié)構(gòu)的美觀和筆劃的內(nèi)蘊(yùn)。二是以他物代替筆劃放在漢字中。有些書者為增強(qiáng)書法的視覺效果,把人體或線形的物體作為筆劃納入漢字中,想以人體之美或其它物象之美來襯托或反映書法之美,這完全背離了書法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規(guī)律,也并未使人們感受到書法的美蘊(yùn)。三是藝術(shù)成了雜耍。一些人為了表現(xiàn)自己的才能,用左手寫、雙手寫、腳寫、口寫、發(fā)寫,等等,大書畫家張大千在多年前曾對此痛斥為“雜耍”而不是真正的藝術(shù),他呼吁“要藝術(shù),不要‘雜耍”。他說:“這是誤事誤人,你們可千萬不能去學(xué)這一套!更不能被其表面現(xiàn)象所迷惑!我們這些天天同書畫打交道、準(zhǔn)備一輩子以書畫為職業(yè)的專業(yè)畫家都深有體會,我們就是正正經(jīng)經(jīng)、認(rèn)認(rèn)真真地用右手去畫,都還常嫌沒畫好,更不要說是去用什么左手畫,或者雙手同時(shí)開弓,甚而至于用腳畫了。用那些個(gè)手法弄出來的所謂‘作品,只不過是花哩胡哨地炫耀‘技術(shù)而已,而并非藝術(shù)。用這些個(gè)東西湊點(diǎn)熱鬧、開個(gè)玩笑還可以,但絕非是藝術(shù)作品。”由此可見,作為一種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它有著自身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規(guī)律,必須嚴(yán)格地加以遵循,而不是隨心所欲。
而對于繪畫來說,也有類似之舉。作為主要藝術(shù)形式的繪畫同樣也有藝術(shù)規(guī)律可循,特別是中國畫作為傳統(tǒng)藝術(shù)流傳至今,經(jīng)久不衰,它包含了一種真正的美及民族審美情感,伴隨著中國人的審美歷史,它不因時(shí)代的變遷而流失。而當(dāng)今一些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總認(rèn)為過去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已經(jīng)過時(shí)而不合當(dāng)代審美,一心想走創(chuàng)新之路,并認(rèn)為對傳統(tǒng)藝術(shù)的認(rèn)知和傳承易于保守,甚至想完全撇開傳統(tǒng),另辟溪徑。其實(shí)這是不可能也是不現(xiàn)實(shí)的,因?yàn)槿魏嗡囆g(shù)都不是從天而降,不論多么的“現(xiàn)代”或者“當(dāng)代”,都有其歷史的根源。法國著名藝術(shù)批評家克萊爾借用了沃爾夫林的觀點(diǎn),深刻闡述了這一問題。他說:“風(fēng)格的發(fā)展是藝術(shù)史的內(nèi)在現(xiàn)象相連,還是取決于外在的現(xiàn)象?沃爾夫林認(rèn)為,如果沒有‘圖像對圖像、形式對形式的持續(xù)的影響的內(nèi)在因素,風(fēng)格的發(fā)展是不可解釋的。在他及后來的馬爾羅看來,一件藝術(shù)品的起源不是在生活中,而是在一件先前的藝術(shù)品之中。”因此,如果無視中國畫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任憑自己的性情隨意繪畫,終究不會走得太遠(yuǎn)。
3.借鑒缺乏融合,創(chuàng)作表現(xiàn)不倫不類
藝術(shù)要發(fā)展,必須要借鑒,既要向其它藝術(shù)門類借鑒,也要向其它民族借鑒。在藝術(shù)借鑒中,既有借鑒表現(xiàn)手法,也有借鑒藝術(shù)技巧,使其相通相融。如對于中國畫來說,它歷來注重借鑒,如借鑒書法藝術(shù)中的筆墨技巧,筆墨既是國畫基礎(chǔ),也是中國書法最為重要的技法,因此,許多習(xí)國畫者都要練習(xí)書法,以便掌握繪畫中的筆墨功夫。同時(shí)中國畫也向文學(xué)借鑒,借鑒它的表現(xiàn)手法,特別是中國的詩詞藝術(shù)在表現(xiàn)萬事萬物時(shí),有一種意象性,也就是人們所認(rèn)為的寫意、喻意、象征等等,而中國畫借鑒了這種表現(xiàn),使畫作表現(xiàn)了一種特有的意境,而這種意境卻是建立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只有在理解中國文化的情景下,才能理解或闡釋詩或畫的意境所表達(dá)的心靈感受。所謂“詩情畫意”、“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正是反映了一種相互借鑒的關(guān)系。正如宋代著名畫家、理論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說:“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余因暇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之事,有裝出目前之景。”而美國學(xué)者高居翰也認(rèn)為,中國畫的這種意象性表現(xiàn)手法具有特定的功能,它隱喻了作者所表達(dá)的深刻含義。如傳米芾曾作《云山》圖,題款詩為“天降時(shí)雨,山川出云。”它隱喻了一個(gè)高尚的人格,猶如挺拔的高山,不為浮云所蔽;猶如旱后的甘霖,愿為人類造福。因此,高居翰說,中國畫“藝術(shù)家創(chuàng)造了可以鼓勵(lì)觀者去視覺性地探查圖畫空間并更深地進(jìn)入畫景的圖畫。通過暗示出所見物之外的深度,從而為當(dāng)時(shí)興起的對物質(zhì)世界的系統(tǒng)性探索提供了一個(gè)圖畫對等物。”而這種在繪畫中所表現(xiàn)的隱喻或暗示等手法,正是從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尤其是詩歌藝術(shù)中借鑒的。這種向書法、文學(xué)詩歌等借鑒的方法,自文人畫產(chǎn)生以來日益興盛,常常是三位一體,完整融合,增加了藝術(shù)的感染力和審美性。而中國畫向西方繪畫借鑒,也早已被藝術(shù)界所認(rèn)可,如素描寫實(shí)基礎(chǔ)、明暗對比與空間透視表現(xiàn)的立體感、圖示比例所顯示的遠(yuǎn)近感,等等。中國畫借鑒西方藝術(shù)技巧,據(jù)高居翰認(rèn)為,早在晚明時(shí)期就已開始。后隨著西學(xué)東漸,一些畫家受到西方藝術(shù)法則的影響,創(chuàng)新出了一套不同舊統(tǒng)的形式與習(xí)性,如畫中表現(xiàn)一種全新的空間遼闊和空曠感,利用明暗與光影表達(dá)事物的立體感等,給中國畫增添了一種新的活力,隨著西方技法的融合,這種影響與時(shí)遷移,最后也成為眾所認(rèn)定的法則,現(xiàn)當(dāng)代許多著名畫家都借鑒了西方繪畫技巧,創(chuàng)造了獨(dú)具風(fēng)格的藝術(shù)作品,如徐悲鴻、林鳳眠等大師的作品。
但是,借鑒的核心在于有機(jī)融合,而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是牽強(qiáng)附會,而融合的關(guān)鍵就是找到一個(gè)契合點(diǎn),而不是一切都可以融合的。而當(dāng)今一些繪畫,卻表現(xiàn)出了缺少一種融合,使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不倫不類的狀況。特別是20世紀(jì)以來,西方繪畫產(chǎn)生了眾多的藝術(shù)流派,此起彼伏,既有影響深遠(yuǎn)的,也有曇花一現(xiàn)的。原有一些從事傳統(tǒng)繪畫的創(chuàng)作者,為了體現(xiàn)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性,也欲借鑒西方的各種流派,想注入他的國畫創(chuàng)作中,而由于他缺少對西方繪畫思想及其技法的深入研究,特別是在材料與技法相互作用方面沒有熟練掌握,使得這種借鑒缺乏融合,使畫作在藝術(shù)審美上難以被人們所接受。如一些畫家在畫作上為體現(xiàn)印象派的特點(diǎn),在色彩上過于激烈,而有的甚至在畫上莫名地加上一些色塊和色條,也有的以西方繪畫的具象手法來想反映中國的意象世界,結(jié)果讓人不知所云。即使是同一文化背景的藝術(shù),如果借鑒不當(dāng),也易造成美觀的缺失,如書法過于借鑒繪畫,最后就不是書寫而是畫字了;反之如畫借助書法題字點(diǎn)睛,如果書得過分繁多,就成了喧賓奪主。
四、藝術(shù)范式的多元并存與藝術(shù)革命
“范式”是美國科學(xué)哲學(xué)家托馬斯·庫恩創(chuàng)立的一個(gè)重要概念,原為論述科學(xué)領(lǐng)域中的科學(xué)革命而創(chuàng)立,由于這一概念的精辟、獨(dú)到和深刻,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而廣泛的影響,不僅在科學(xué)技術(shù)界,而且在人文科學(xué)乃至藝術(shù)領(lǐng)域也常常被使用。有意思的是,庫恩理論被一些追隨者生搬硬套機(jī)械地用到藝術(shù)領(lǐng)域,遭到了藝術(shù)史家貢布里希的微詞,他為此寫下了《為多元論辯護(hù)》一文。作為庫恩本人對這種過于的牽強(qiáng)附會也頗不以為然,寫下《論科學(xué)和藝術(shù)的關(guān)系》一文,進(jìn)行了辯解性的論述,文中卻贊譽(yù)了貢布里希關(guān)于藝術(shù)和科學(xué)區(qū)分的觀點(diǎn),但同時(shí)也肯定了科學(xué)與藝術(shù)的某些相似之處。而科學(xué)社會學(xué)家黛安娜·克蘭在她的名著《無形學(xué)院——知識在科學(xué)共同體的擴(kuò)散》中,卻把他倆說到了一塊。而我認(rèn)為,庫恩范式是作為一個(gè)重要的科學(xué)元理論概念,雖然遭遇了一些具體而不同的學(xué)科實(shí)踐,但是有它的辯證適應(yīng)性。因此,范式理論對于包括藝術(shù)學(xué)在內(nèi)的人文學(xué)科應(yīng)有一定的指導(dǎo)作用。
1.藝術(shù)范式與藝術(shù)共同體
作為重要概念的“范式”究竟指的是什么?這一頗為含糊而又極富岐義的概念,曾引起廣泛而持久的爭論,這使得庫恩不得不為此進(jìn)行一番論述,并最終定義為一種“學(xué)科基質(zhì)”。他認(rèn)為,“學(xué)科”為一個(gè)專門學(xué)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財(cái)產(chǎn),而“基質(zhì)”由各種各樣的有序元素所組成。而學(xué)科基質(zhì)由四種最重要的成分所構(gòu)成:一是基本定理,也稱為“符號概括”,為團(tuán)體成員無異議地使用;二是信念,也稱范式的“形而上學(xué)”,是成員們共同承諾的一種信念;三是價(jià)值,它是在團(tuán)體行為中起決定性的因素,尤其是作為人文科學(xué)的繪畫藝術(shù)有著最重要的意義;四是范例,不僅增進(jìn)對定理的理解,而且提供如何運(yùn)用它的方法。由此,范式是一個(gè)綜合性的概念,它蘊(yùn)含著復(fù)雜而深刻的含義,它對共同體成員有一定的包含和凝聚作用。相反,建立或接受一種范式,也是一個(gè)共同體必須遵循的重要條件。作為科學(xué)研究來說,有了范式的指導(dǎo),研究就有了規(guī)律性的認(rèn)識,從而就會使研究能夠更加深入細(xì)致,更加具有目標(biāo)和方向。如克蘭認(rèn)為的那樣:“一個(gè)范式通常指明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為要解決問題應(yīng)該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想要觀察的現(xiàn)象的類型是怎樣的。沒有這種指南,科學(xué)家是不能做出那些相關(guān)的和積累起來的發(fā)現(xiàn)的。”因此,庫恩在構(gòu)建他的科學(xué)革命結(jié)構(gòu)時(shí),特別重視范式的功能作用,把它視為科學(xué)研究和解決難題的核心或樞紐。他說:“范式既是科學(xué)家觀察自然的向?qū)В彩撬麄儚氖卵芯康囊罁?jù)。范式是一個(gè)成熟的科學(xué)共同體在某段時(shí)間內(nèi)所接納的研究方法、問題領(lǐng)域和解題標(biāo)準(zhǔn)的源頭活水。”
從庫恩范式的概念定義來看,藝術(shù)中也應(yīng)有一定的范式,藝術(shù)家們遵從或選擇它,而藝術(shù)范式在藝術(shù)中應(yīng)有相似的作用,它對藝術(shù)活動(dòng)也有著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正如克蘭所說:“生產(chǎn)非科學(xué)思想的創(chuàng)新者群體,也一定是由類似的思想所指引的。”作為從藝術(shù)中確定的藝術(shù)范式,應(yīng)該涵蓋藝術(shù)的眾多元素,包括藝術(shù)思想、創(chuàng)作主題、風(fēng)格特征、價(jià)值觀念、審美情感、技術(shù)工藝、創(chuàng)作材料、示范文本(如字帖、畫譜、經(jīng)典作品)、藝術(shù)楷模,等等,都有可能成為藝術(shù)的一種范式,相比之下,比科學(xué)范式更為繁復(fù)多變。就書畫而言,中國的書法藝術(shù),書體上就有秦篆、漢隸、唐楷、宋行等,藝術(shù)表現(xiàn)及風(fēng)格上有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態(tài)等,筆法上更是千姿百態(tài),如挺拔、勁瘦、渾厚、秀麗等,呈現(xiàn)出不同時(shí)代的主體特征,正如劉熙載在《書概》中所言:“秦碑力勁,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金石略序》云:‘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fēng)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諒哉!”而這些書體、風(fēng)格、特征等都為后世藝術(shù)創(chuàng)作提供了示范作用。而作為繪畫就更為復(fù)雜了,就中國畫而言,題材表現(xiàn)上有山水、人物、花鳥等三大類別;技法上有工筆、寫意、綜合等大技法,有各種皴法、水墨法、色彩法等小技法;而表現(xiàn)風(fēng)格上,更是豐富多彩,在不同的時(shí)期、不同的地區(qū),由于藝術(shù)家們具有相同的時(shí)代及文化背景,相同的地理環(huán)境,相同的價(jià)值、審美和相同的筆墨技法,以及相互之間的交流和影響,從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風(fēng)格,如以畫寄情、文人寫意、追思古典、追神寫真、墨趣禪心、筆墨濃厚或清晰,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畫范式的重要內(nèi)容。而西方繪畫也同樣精彩紛呈,作為范式意義的,既有地區(qū)性的風(fēng)格,如羅馬藝術(shù)、希臘藝術(shù)等;也有宗教性的特征,如基督教藝術(shù)、拜占庭藝術(shù)、伊斯蘭藝術(shù)等;還有時(shí)代性的烙印,如中世紀(jì)藝術(shù)、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藝術(shù)、現(xiàn)代藝術(shù)以及后現(xiàn)代藝術(shù)等。而最具典型意義的范式,是各種具有表現(xiàn)手法的風(fēng)格性藝術(shù),如哥特式藝術(shù)、洛可可藝術(shù)、巴洛克藝術(shù),以及各種“主義”命名的流派藝術(shù)。而縱觀中外藝術(shù)史,凡處在范式幅射下的藝術(shù)家群體無不受到它的影響,也無不在范式指導(dǎo)下進(jìn)行藝術(shù)活動(dòng)或藝術(shù)創(chuàng)作。如克蘭所指出的那樣:“藝術(shù)家群體,與科學(xué)家群體一樣,在群體內(nèi)部對于工作有共同的方向。風(fēng)格概念代表著一個(gè)時(shí)期革新的最后結(jié)果,正象庫恩所指出的,它類似于科學(xué)中的理論。藝術(shù)家處在發(fā)展一種新風(fēng)格過程中,此時(shí)他是被關(guān)于藝術(shù)、繪畫或者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具體作品重要性的一致看法所指引的,這種一致看法代表著這個(gè)群體努力要去表達(dá)出來的思想。”
科學(xué)范式的社會學(xué)意義就是擁有相同范式的科學(xué)共同體,庫恩認(rèn)為:“一個(gè)科學(xué)共同體由同一科學(xué)專業(yè)領(lǐng)域中的工作者組成。在一種絕大多數(shù)其他領(lǐng)域無法比擬的程度上,他們都經(jīng)受近似的教育和專業(yè)訓(xùn)練;在這個(gè)過程中,他們都鉆研過同樣的技術(shù)文獻(xiàn),并從中獲取許多同樣的教益。”作為在相同藝術(shù)范式指引下的藝術(shù)共同體,與科學(xué)共同體極為相似,他們或許受同一美學(xué)思想的熏陶,或許有著同一師承的關(guān)系,或許受著同一古典風(fēng)格的影響,也或許有著相同的人生經(jīng)歷或?qū)徝狼楦小R虼耍@樣的藝術(shù)共同體也有著他們自己的共同主題,包括理論、風(fēng)格、價(jià)值、審美、技藝,甚至材料等等。共同體的成員把自己看作、并且別人也認(rèn)為他們是具有一個(gè)共同的觀點(diǎn)或追求一個(gè)共同的目標(biāo)。如庫恩所認(rèn)為的那樣:“一個(gè)藝術(shù)流派的成員具有共同的風(fēng)格和美學(xué)觀點(diǎn),他們也以此共同觀點(diǎn)而被人識別。”藝術(shù)共同體也是多層次的,在含義最廣的層次上,是所有藝術(shù)的共同體,當(dāng)統(tǒng)稱為藝術(shù)家。而在稍低層次上的主要藝術(shù)團(tuán)體,有畫家、書法家等的共同體,而中國畫家又可分為中國山水畫家、中國花鳥畫家等,以及由這些畫家組成的藝術(shù)社會團(tuán)體,如各種學(xué)會、研究會、協(xié)會等。如果當(dāng)以風(fēng)格作為范式來劃分,又形成了多種多樣的藝術(shù)流派或畫派,如人們所知的宋代文人畫派、元四家、吳門畫派、吳四家、虞山派、院體、浙派、揚(yáng)州八怪、金陵八家、新金陵畫派,甚至包括董其昌所定義的南北宗。藝術(shù)共同體與科學(xué)共同體一樣,也具有“無形學(xué)院”的多項(xiàng)功能,包括凝聚藝術(shù)人才、交流藝術(shù)創(chuàng)作、研討藝術(shù)理論、傳播藝術(shù)理念、培養(yǎng)藝術(shù)人才,等等,正如蘭克在她的著作《無形學(xué)院》中說的那樣:“對于科學(xué)中研究領(lǐng)域的社會組織的分析已經(jīng)指明,社會圈子中有無形學(xué)院,無形學(xué)院對于統(tǒng)一研究領(lǐng)域和為領(lǐng)域提供凝聚力和方向是有幫助的。這些重要的人物和他們的某些合作者由直接的紐帶緊密相連在一起,他們發(fā)展了有利于在成員間形成道德原則和保持積極性的團(tuán)結(jié)。這兩種類型的群體在藝術(shù)和文學(xué)中都能找到。”
2.藝術(shù)從歷史中走來
庫恩論述科學(xué)與藝術(shù)最大的不同就是如何對待自身的歷史。他認(rèn)為作為科學(xué)過去的已經(jīng)沒有什么價(jià)值而言,頂多只能提供史家去研究新發(fā)現(xiàn)的緣由,而只有新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才能真正推動(dòng)世界前進(jìn)。而相反,現(xiàn)在乃至將來的藝術(shù)總是沉浸在過去的影子中,而且經(jīng)典的藝術(shù)作品和藝術(shù)思想總是激勵(lì)當(dāng)今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他說:“過去藝術(shù)活動(dòng)的成果仍然是藝術(shù)舞臺的一個(gè)重要部分。畢加索的成功,并沒有把倫勃朗的繪畫擠進(jìn)藝術(shù)博物館的地下儲藏室。近古與遠(yuǎn)古的藝術(shù)杰作在形成公眾的藝術(shù)趣味與啟導(dǎo)藝術(shù)家走上專業(yè)道路。……然而只有歷史學(xué)家閱讀古代科學(xué)著作。在科學(xué)里,由于有了新的突破,昔日在科學(xué)圖書館里占據(jù)重要位置的一些書刊突然過時(shí)了,被扔到倉庫的廢紙堆里。……與藝術(shù)不同,科學(xué)毀滅自己的過去。”按照他的范式理論,在科學(xué)中,原有的范式隨著科學(xué)革命的到來已經(jīng)廢除,而代之以新的范式指導(dǎo)新的科學(xué)活動(dòng)。而作為藝術(shù)恰恰相反,過去在藝術(shù)活動(dòng)中創(chuàng)立的范式,現(xiàn)在乃至將來都有可能一直起著重要作用。人們常常用“典雅”來形容藝術(shù),它表明了藝術(shù)中蘊(yùn)含了經(jīng)典和古雅之意,以一種古典的藝術(shù)范式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為當(dāng)今的人們所贊賞。法國藝術(shù)批評家克萊爾有個(gè)精彩的表述:“古代是始終現(xiàn)今在場的范式,而現(xiàn)代性是在古代范式上打上時(shí)代的獨(dú)特印記。”縱觀中外美術(shù)史,盡管從前有許許多多的藝術(shù)家都畫過什么,但今天的藝術(shù)家依然有沖動(dòng)或激情去畫這些,仍然去追求屬于自己的藝術(shù)的完美。克萊爾繼續(xù)說道:“即使這么多年以來,這種完美已經(jīng)達(dá)到,但這樣的重新記憶、這樣的重復(fù)、這樣的工作不屬于死亡本能。”藝術(shù)之所以成為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它能夠在歷史中延續(xù)和傳承。
貢布里希說:“藝術(shù)具有歷史……自然的表現(xiàn)不可能由任何未經(jīng)訓(xùn)練的個(gè)人獲得,無論他具有多大天才,沒有傳統(tǒng)的支持則一事無成。”而這種訓(xùn)練和支持,正是歷史的藝術(shù)范式所起的指導(dǎo)作用。貢布里希認(rèn)為,這個(gè)歷史形成的藝術(shù)范式是一種圖畫的“公式和經(jīng)驗(yàn)”,離開了它的作用,而直接去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是不可想象的。他說:“沒有一種媒介,沒有一個(gè)能夠加以塑造和矯正的圖式,任何一個(gè)藝術(shù)家都不能模仿現(xiàn)實(shí)。”因而,創(chuàng)作者只有在熟練掌握構(gòu)成物體的物像時(shí),他才能走到外面的世界中觀察他所希望描繪的那些物體,而只有到了最后他才應(yīng)該畫出一些區(qū)別性特征,但首先是掌握該物體的一般特征,其次才能創(chuàng)作藝術(shù)家想要表達(dá)的特征。中國畫傳統(tǒng)練習(xí)的畫譜和當(dāng)今西方傳入的素描練習(xí),都是這種歷史的藝術(shù)范式的導(dǎo)引作用。貢布里希對于中國畫譜的指導(dǎo)作用,認(rèn)為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由于長期的畫譜練習(xí)使人們心里有了一種“存念”或“底蘊(yùn)”,而這種“存念”和“底蘊(yùn)”可以賦予一種創(chuàng)作靈感的心境。他說:“中國藝術(shù)家今天仍然作為山峰、樹木或花朵的‘制作者。他能把它們想象出來,因?yàn)樗懒岁P(guān)于它們的存在的秘密,但是,這樣做是要記錄并喚起一種心境,而這種心境深深地植根于中國關(guān)于宇宙本質(zhì)的觀念之中。”作為西方繪畫基礎(chǔ)的素描,它的范式引導(dǎo)作用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貫穿于西方繪畫史,甚至于整個(gè)西方藝術(shù)史。因?yàn)樗孛栀x予了人們親近現(xiàn)實(shí)、認(rèn)知整體事物的精神構(gòu)想,是對自然景物的一種真實(shí)捕捉,是感覺世界中那種模糊的東西就有了一種物質(zhì)感,而這些對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來說,就有了一種對所要表達(dá)的事物的基礎(chǔ)和把握。克萊爾說:“從12世紀(jì)起,是素描在‘教導(dǎo)輪廓和色彩,很久以后繪畫才敢面對這兩點(diǎn)。從13世紀(jì)末,還是素描,以水墨的形式,帶來對空間和光線的征服,打下了繪畫即將獲取的透視和價(jià)值情感的基礎(chǔ)。在一個(gè)畫家的獨(dú)特活動(dòng)中,每當(dāng)他的藝術(shù)遭遇障礙時(shí),都是素描突然出現(xiàn)或重新出現(xiàn)。……素描在這個(gè)世紀(jì)末,對于藝術(shù)的普遍命運(yùn)就像對于藝術(shù)家的獨(dú)特演變,提供了一條可能的出路。”由此可見,作為歷史意義的藝術(shù)范式,它的指導(dǎo)作用與科學(xué)范式,就是永遠(yuǎn)存在,這也是藝術(shù)從歷史中走來的真正緣由。
作為中國畫的藝術(shù)傳承更具有這種“藝術(shù)即歷史”的意義。我國現(xiàn)代大畫家潘天壽對這種歷史的藝術(shù)范式在中國畫創(chuàng)作中所起的作用曾作過精辟的論述:“文藝上的形式風(fēng)格,是脫不了歷史傳統(tǒng)輾轉(zhuǎn)延續(xù)的影響的。例如中國繪畫的表現(xiàn)技法上,向來是用線條來表現(xiàn)對象的一切形象的。因?yàn)橛镁€條來表現(xiàn)對象,是最概括明豁的一種辦法,是合于東方民族的欣賞要求的。因此輾轉(zhuǎn)待續(xù)地直到現(xiàn)在,造成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高度明確概括的線條美。反過來說,沒有歷史相互延續(xù)的積累,也無法完成中國繪畫在線條運(yùn)用上充分發(fā)展的特殊成就。其余如用色方面,透視方面,構(gòu)圖方面等等,都與歷史傳統(tǒng)輾轉(zhuǎn)待續(xù)有分不開的關(guān)系。即便是西方繪畫大統(tǒng)系的傳統(tǒng)技法風(fēng)格,也是許多代畫家研習(xí)的結(jié)果,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中國傳統(tǒng)繪畫是文史、詩詞、書法、篆刻等多種藝術(shù)在畫面上的綜合表現(xiàn),就更和整個(gè)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變革緊密地聯(lián)系,這是很自然的。”
因此,方聞先生認(rèn)為中國的繪畫就是一部中國藝術(shù)歷史,在后繼的中國畫中可以看到先賢大師畫風(fēng)的影子,也就是有一種歷史的藝術(shù)范式在起著作用。他說:“在東方,審讀中國繪畫史往往需要遵循譜系性范式并從典型風(fēng)格傳統(tǒng)的角度出發(fā),故而可見每一筆線條均襲于主流的先賢大家,并由后人的傳摹而余緒綿延。”所以,即使用現(xiàn)代的目光,中國古典藝術(shù)的精華也將作為淵博而深厚的文化資源被挖掘出來,也會重新融入現(xiàn)代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之中。
3.風(fēng)格的回歸與藝術(shù)創(chuàng)新
藝術(shù)上有一種風(fēng)格回歸的現(xiàn)象,這是藝術(shù)為尋求變革而常常走的途徑,是繼續(xù)以古典范式指導(dǎo)而導(dǎo)致的一種創(chuàng)新。著名哲學(xué)家馮友蘭認(rèn)為,一個(gè)變革發(fā)展的熟悉模式是隨著多次復(fù)古運(yùn)動(dòng)的成功更新而來的。劉勰也認(rèn)為,追求通變要多從古圣賢中尋取。他在《文心雕龍·通變篇》中說:“練青濯絳,必歸藍(lán)蒨,矯訛翻淺,還宗經(jīng)誥,斯斟酌乎質(zhì)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同時(shí)進(jìn)一步指出,“參伍變化,通變之?dāng)?shù)也。”也就是說,要錯(cuò)綜變化,在繼承中有創(chuàng)新,才有真正的變通。因此,對于許多力求創(chuàng)新的藝術(shù)家而言,追求風(fēng)格的回歸是一條通往原創(chuàng)活力的重要路徑,這不僅開啟了原創(chuàng)之路,同時(shí),這也為他們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種歷史性的證明,特別是中國藝術(shù)家更加重視正統(tǒng)范式的指導(dǎo)和傳承。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風(fēng)格回歸不僅是一條藝術(shù)創(chuàng)新之路,也是藝術(shù)不斷發(fā)展的軌跡,藝術(shù)家在汲取古典藝術(shù)營養(yǎng)的同時(shí),也融進(jìn)了自己的創(chuàng)造,從而使藝術(shù)生命得以生息不止、延綿不斷,同時(shí)也成就了自己。正如方聞先生所說:“古代典范在非歷史性延綿中擁有其地位,隨歲月而來的后代大師們在其中通過與古代典范的會心共鳴,取得了自身的實(shí)現(xiàn)。與其說他們是古代典范的追隨者,還不如說同樣是典范。”
縱觀中國書畫的發(fā)展史,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風(fēng)格回歸及再創(chuàng)造的歷史。劉勰在其文論《文心雕龍·通變篇》中,道出了只有對古代各種風(fēng)格和原理通曉的情況下,才能達(dá)到求變的狀態(tài),也才能以回歸古典風(fēng)格創(chuàng)新出未來的審美水平。作為中國的書法藝術(shù),每個(gè)學(xué)書者都喜歡臨摹古人,尤其是從臨摹“二王”的書法入手,而大凡卓有成就的書法家又都是在傳統(tǒng)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自己別具一格的個(gè)人風(fēng)貌來。書法史上許多具有承前啟后、開一代書風(fēng)的大家,無不在學(xué)習(xí)前人,特別是在“二王”風(fēng)格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書體來。如宋蘇東坡贊顏真卿時(shí)說:“顏魯公平生寫帖,惟《東方朔畫贊》為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yuǎn)。其后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于書未易為言此也。”而對于智永、虞世南、歐陽詢、禇遂良等也是如此,《續(xù)書斷》記載:“初浮屠智永學(xué)逸少書精極,名重于陳。世南從學(xué)焉,盡得其而有以過之。……詢師法逸少,尤務(wù)勁險(xiǎn)。……(禇遂良)其書多法,或效鐘公之體而古雅絕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馀,至章草之間,婉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朱長文《斷書斷·妙品》。而作為書風(fēng)集大成者元代的趙孟頫更是如此,他臨帖《蘭亭序》無以計(jì)數(shù),甚至對其中每個(gè)字進(jìn)行放大,對每個(gè)字的每一筆都心領(lǐng)神會,他在《蘭亭十三跋》中對臨帖學(xué)古提出了獨(dú)到見解:“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然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jié)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與此同時(shí),他還學(xué)習(xí)了顏真卿、褚遂良等的用筆,最后終于創(chuàng)造出一種嶄新的筆法語匯。所以方聞先生說:“作為稔熟古代書體的大師兼新楷書風(fēng)格的創(chuàng)造者,趙孟頫追求傳統(tǒng)儒家集過去‘大成的志向,他是以歷史的搶救者與仲裁人面目來把握文化道統(tǒng)的。”
而中國的繪畫史也同樣顯現(xiàn)出風(fēng)格的不斷回歸繼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歷史過程。世界著名中國藝術(shù)史家、哈佛大學(xué)藝術(shù)系教授羅樾認(rèn)為,中國的繪畫是一個(gè)不斷再現(xiàn)的藝術(shù)。他將中國繪畫的發(fā)展分為四個(gè)主要階段:周朝以前的原始再現(xiàn)性形象的裝飾藝術(shù)、漢代至南宋的再現(xiàn)藝術(shù)、元代的超再現(xiàn)藝術(shù),以及明清的以傳統(tǒng)風(fēng)格作為主題的歷史性東方藝術(shù)。每個(gè)階段的發(fā)展都是以風(fēng)格的回歸作為起源,掀起了一股股復(fù)古運(yùn)動(dòng)和浪潮,也推動(dòng)了繪畫藝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到了明代以后尤為顯著。蘇東坡借用佛教的四相“生、住、異、滅”,來闡釋他的藝術(shù)理論,可以看出北宋末以后的許多藝術(shù)家都依靠返歸古樸的風(fēng)格來更新藝術(shù)。以至后來成功的藝術(shù)創(chuàng)新無不依賴于對古代藝術(shù)風(fēng)格的回歸和復(fù)興。因?yàn)椋诜鹿胚^程中,杰出的藝術(shù)家總比他人更有意識、更善于吸收地考察和研究古代的藝術(shù)典范,而且以一種隱喻或以此為出發(fā)點(diǎn)來使用這些范本,同時(shí)在創(chuàng)作中為表達(dá)和實(shí)現(xiàn)自身,以形成自己獨(dú)特的技巧與構(gòu)成方式來“變”化范本。因?yàn)椤昂蟠嫾也皇窃僭旃糯L(fēng)格,而是通過自己時(shí)代的視象結(jié)構(gòu)與組合方式對古代風(fēng)格進(jìn)行變革和演繹。而形式諸要素、技法和單個(gè)母題可能被復(fù)述,而視覺上有機(jī)的宏觀結(jié)構(gòu)與藝術(shù)家運(yùn)作手法的微觀組成這兩者更微妙的形式關(guān)系確實(shí)是無法重演的。”對此,方聞先生進(jìn)行了深刻的概括,他說:“歷代藝術(shù)家通過掌握表現(xiàn)技巧,堅(jiān)定地朝前征服了繪畫的深度與自然運(yùn)動(dòng)的幻覺,表現(xiàn)規(guī)范中的結(jié)構(gòu)變革,也有明確的步驟獲得了進(jìn)展。在世界藝術(shù)史上,惟有中國的繪畫藝術(shù)呈現(xiàn)出生機(jī)蓬勃的圖繪性傳統(tǒng),它可以連續(xù)不斷地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時(shí)代的遠(yuǎn)古淵源。”
在西方藝術(shù)史上,歷來以創(chuàng)新出奇而著稱,但在藝術(shù)家感到迷茫或需要?jiǎng)?chuàng)新變革的時(shí)候,也常回歸古典風(fēng)格。以便為他們提供參照和方向。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許多藝術(shù)家為藝術(shù)變革就常常借用古典來激發(fā)自己的靈感或豐富自己的創(chuàng)作技巧,如三巨匠之一的拉斐爾在繪制人物時(shí)就借鑒了古羅馬的雕塑,他運(yùn)用古典藝術(shù)更直接的例子是他所設(shè)計(jì)的雕版畫《帕里斯的裁判》,作品參考了古羅馬藝術(shù)中的某雕塑藏品。他闡釋了原型而不是簡單模仿,強(qiáng)烈的輪廓線與明暗對照法清晰地構(gòu)成雕塑般的人物,作品為后輩藝術(shù)家傳承了古典藝術(shù)。最為典型的莫過于18世紀(jì)新古典主義的形成,藝術(shù)家們常常直接觀摩古代藝術(shù)品以及文藝復(fù)興和巴洛克時(shí)期的藝術(shù)珍寶,從中得到啟發(fā)、靈感和技法,古典風(fēng)格所表現(xiàn)的平面性和線性、樸素而細(xì)致的畫法,以及古典式人物及主題,都在新古典主義風(fēng)格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新古典主義者從古希臘杰作中看到了那種“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的特征,并以此作為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格。到了20世紀(jì)后,人們的觀念與價(jià)值觀雖已發(fā)生了新的變化,西方藝術(shù)的各種流派和“主義”仍在繼續(xù)盛行,但一些流派的藝術(shù)也越來越讓人感到一種迷茫和失望,因而一些藝術(shù)家及藝術(shù)評論家提出了“回歸”的理念,重申藝術(shù)要回歸到古典主義的風(fēng)格。如畢加索于1914年至1915年開始轉(zhuǎn)向古典主義,之后他經(jīng)歷了一個(gè)多樣兼容的階段,依次是安格爾式、準(zhǔn)學(xué)院式和如畫式的風(fēng)格演變過程。特別是法國著名藝術(shù)批判家讓克萊爾對當(dāng)代藝術(shù)進(jìn)行了猛烈的批判,在他的重要著作《論美術(shù)的現(xiàn)狀——現(xiàn)代性之批判》的最后,他引用了奧地利表現(xiàn)主義畫家的一句名言:“藝術(shù)不可能現(xiàn)代,藝術(shù)永恒回歸起源。”
4.范式的多元并存與藝術(shù)革命
根據(jù)庫恩的范式理論,當(dāng)科學(xué)范式發(fā)生了改變,要引起科學(xué)革命,同樣當(dāng)藝術(shù)范式發(fā)生了改變,藝術(shù)也要發(fā)生革命。正如庫恩所說:“藝術(shù)家與科學(xué)家一樣,也會碰到許多頑固棘手的專業(yè)問題,必須通過改進(jìn)自己的技藝去加以解決。”但不同的是,當(dāng)科學(xué)發(fā)生革命后,原有的范式將被廢棄,而代之以新的范式指導(dǎo)科學(xué)活動(dòng),并且人們喜歡新科學(xué)的到來而拒絕舊的科學(xué)。但對于藝術(shù)來說,一方面,當(dāng)藝術(shù)革命后,新的范式并不取代舊的,而舊的還將繼續(xù)起著作用;另一方面,人們并不都喜歡新的藝術(shù)形式,而喜歡舊的藝術(shù)卻大有人在,他們甚至排斥新的藝術(shù),認(rèn)為它不是真正的藝術(shù)。如庫恩所說:“公眾拒斥藝術(shù)卻是拒斥一種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而贊賞另一種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現(xiàn)代藝術(shù)根本不是真正的藝術(shù);讓我看那種描繪我們能夠賞識的主題的繪畫吧。”因此,新的范式不斷涌現(xiàn),而舊的范式仍然存在,顯現(xiàn)出多元藝術(shù)范式并存的局面。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風(fēng)格、不同的傳承同時(shí)并存,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藝術(shù)發(fā)展或增長的重要特征。正如庫恩在論述藝術(shù)這種現(xiàn)象時(shí)說:“一個(gè)藝術(shù)傳統(tǒng)的成功并不能使另一傳統(tǒng)變成不正確或謬誤,藝術(shù)遠(yuǎn)比科學(xué)易于容許好幾個(gè)互不相容的傳統(tǒng)或流派同時(shí)存在。根據(jù)同樣的理由,當(dāng)傳統(tǒng)已經(jīng)改變,有關(guān)的爭論通常在科學(xué)中遠(yuǎn)較藝術(shù)中更快得到解決。……在藝術(shù)中,爭論結(jié)束只意味著新傳統(tǒng)被人接受,而不是舊傳統(tǒng)的結(jié)束。”
藝術(shù)革命與其它革命相比,更為繁雜,有時(shí)革命不斷,流派紛紜,而有時(shí)卻要經(jīng)過漫長的時(shí)期。作為中國藝術(shù)的書畫來說,每個(gè)時(shí)代都有著不同的時(shí)代特征和風(fēng)范,這些特征和風(fēng)范都經(jīng)歷相當(dāng)長的時(shí)期。如書法藝術(shù),它有篆、隸、真、行、草等字體,每種字體都有著嚴(yán)格的規(guī)范或范式指導(dǎo),而每一種字體范式都有一個(gè)長期的形成過程,同時(shí)舊的字體仍然存在,形成了多種字體并存的局面。而對于書法風(fēng)格來說,自晉以來,個(gè)性化風(fēng)格開始凸現(xiàn),有“二王”、歐、顏、柳、趙、米等藝術(shù)風(fēng)格,而風(fēng)格的繼承、創(chuàng)新或革命、回歸、再創(chuàng)新或再革命,促進(jìn)了不同風(fēng)格的變換,也促進(jìn)了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形成了書法藝術(shù)史。而中國的繪畫藝術(shù)范式變換及其引起的藝術(shù)革命則更為復(fù)雜。我國著名畫史論家張彥遠(yuǎn)對中國繪畫史進(jìn)行了結(jié)構(gòu)性的分析,他認(rèn)為中國的繪畫經(jīng)歷了一個(gè)“簡淡”、“細(xì)密”到“完備”的過程,涵蓋了一個(gè)漫長而緩慢的變革,跨越了多個(gè)不同時(shí)代。如對人物畫的表現(xiàn),被喻為一個(gè)藝術(shù)奇跡或藝術(shù)革命,它把人物從各部的簡單組合變革為舉止自如的有機(jī)結(jié)合。而對于山水畫來說,變革的歷程就是從二維空間的畫面上表現(xiàn)摹擬的山水景象到創(chuàng)構(gòu)有三維空間和整個(gè)圖象的意象空間。正如方聞所說:“他們先通過表面抽象探索構(gòu)圖的無限可能性,以后又用簡潔的筆墨程式窮究有活躍的書法式構(gòu)圖的‘寫意山水畫。”也是他所認(rèn)為的中國山水畫“狀物形”與“表吾意”兩種范式的建立。特別是那些學(xué)養(yǎng)深厚的藝術(shù)家為了尋求藝術(shù)的變革之路,他們逐漸擺脫自然主義的形似,轉(zhuǎn)而回歸圖式化的更高復(fù)古境界,充分反映了中國畫創(chuàng)作的名言:“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由于中國畫創(chuàng)作過程中不斷地回歸與創(chuàng)新交織在一起,藝術(shù)革命在藝術(shù)史上也是頻繁發(fā)生,從而形成了多重流派和多重風(fēng)格并存的現(xiàn)象。以晚明山水畫為例,畫派林立、風(fēng)格各異,尤如高居翰所說:“明代最后幾十年間的山水畫創(chuàng)作,分散中國各地且多彩多姿,很難加以整齊地分類。”
對喜好變革或革命的西方藝術(shù)來說,藝術(shù)史就是藝術(shù)革命史,藝術(shù)革命波瀾壯闊。只要翻閱一下任何西方藝術(shù)史的著作,甚至瀏覽一下它的目錄,都可看出藝術(shù)革命的洶涌,如“從文藝復(fù)興到洛可可”、“從浪漫主義到實(shí)證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印象主義與拉斐爾前派”、“進(jìn)步與無止境的渴望:后印象主義、象征主義與新藝術(shù)風(fēng)格”、“走向抽象:現(xiàn)代主義革命”、“從戰(zhàn)后到后現(xiàn)代”、“從現(xiàn)代主義到后現(xiàn)代主義”,等等,目不暇接,甚至為了藝術(shù)能夠徹底革命,他們用一種“非藝術(shù)”的形式來革命那些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如達(dá)達(dá)主義、立體主義等。貢布里希稱立體主義“這一運(yùn)動(dòng)甚至比康定斯基實(shí)驗(yàn)的表現(xiàn)主義的色彩和弦更為徹底地脫離了西方繪畫傳統(tǒng)。”把藝術(shù)革命類比于科學(xué)革命的藝術(shù)史家貢布里希勛爵就是把西方藝術(shù)史作為一部藝術(shù)革命史來論述的,看一看他的《藝術(shù)的故事》,感覺與庫恩的《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卻有許多相似之處,如偉大的覺醒、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藝術(shù)的危機(jī)、傳統(tǒng)的中斷、持久的革命、尋求新標(biāo)準(zhǔn)等。因此,他說:“已經(jīng)證明在一切藝術(shù)中繪畫對于徹底的革新反映最快。如果你喜歡潑色,你就可以不用筆;如果你是個(gè)新達(dá)達(dá)主義者,也可以拿一點(diǎn)廢品去展覽,看組織者敢不敢拒收。……西方世界的確應(yīng)該大大地感激藝術(shù)家們互相超越的野心,沒有這種野心就沒有藝術(shù)的故事。”
藝術(shù)和科學(xué)一樣,也經(jīng)歷著進(jìn)化和革命的過程,但是什么引起藝術(shù)范式的變化而導(dǎo)致藝術(shù)革命呢?在庫恩看來,與科學(xué)一樣,同樣是由于原有的范式不能解決新的問題而導(dǎo)致的,對此黛安娜·克蘭、克羅伯等也持相同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原有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或技術(shù),它的可能性消耗殆盡時(shí),革命性的變革必然發(fā)生。克蘭說:“在藝術(shù)中,有什么東西是和科學(xué)家所使用的解難題方法能夠相比擬的呢?大概詳細(xì)檢驗(yàn)藝術(shù)家在不同環(huán)境中使用材料的方法,可以揭示出某種類似的東西。”但對于貢布里希來說,他認(rèn)為,“藝術(shù)家的手段,他的技巧,固然能夠發(fā)展,但是藝術(shù)自身卻很難說是以科學(xué)發(fā)展的方式前進(jìn)。某一方面的任何發(fā)現(xiàn),都會在其他地方造成新困難。”也就是說,在藝術(shù)中雖舊的問題得到解決,但會由此有新的問題替代它,并不像科學(xué)那樣累積性、邏輯性的發(fā)展。因此,他進(jìn)一步指出:“藝術(shù)跟科學(xué)技術(shù)之間存在著怎樣大的差異。藝術(shù)史有時(shí)確實(shí)可以追蹤一下某些藝術(shù)問題的解決方法的發(fā)展過程,但是在藝術(shù)中我們不能講真正的‘進(jìn)步,因?yàn)樵谀骋粋€(gè)方面有任何收獲都可能要由另一個(gè)方面的損失去抵消。”
由此可見,藝術(shù)革命的緣由并不是一種完全累積性的效應(yīng),除了外在的因素之外,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者個(gè)體的感受和動(dòng)因是不可忽略的,有人稱之為“非累積性”或“非連續(xù)性”的。正如普賴斯認(rèn)為的那樣,“在文化領(lǐng)域中,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xiàn)都是獨(dú)一無二的屬于個(gè)人。如果從來沒有米開朗基羅和貝多芬的話,他們的作品就會被完全不同的貢獻(xiàn)所取代。但是,如果哥白尼和費(fèi)米從未出現(xiàn),總有人會做出本質(zhì)上完全相同的貢獻(xiàn)。因?yàn)椋茖W(xué)家的貢獻(xiàn)不是他所獨(dú)有的,而藝術(shù)家的那些作品必定是舉世無雙的。”因此,對于藝術(shù)革命的緣因確實(shí)是一個(gè)有“爭議”的問題,但從藝術(shù)發(fā)展的歷史來看,高居翰的觀點(diǎn)卻頗有見地,他說:“藝術(shù)革命的原因可能比政治革命更難界定,但是若因此說沒有原因存在,也不盡然,變數(shù)總是來自藝術(shù)傳統(tǒng)之內(nèi)和藝術(shù)傳統(tǒng)之外,兩相激蕩而共同決定新的方向。”
以中國繪畫為例,元代的畫壇革命確是由當(dāng)時(shí)歷史和社會特征促成的,元代時(shí)期,由于業(yè)務(wù)畫家崛起,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級,不同的背景、理想與動(dòng)機(jī),導(dǎo)致了繪畫品味、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和主題偏好發(fā)生了改變,從而構(gòu)成了元代繪畫變革的基礎(chǔ)。作為對中國畫范式外來沖擊的,最早的就是公元1世紀(jì)佛教傳入中國后,印度和中亞的繪畫技巧,如明暗塑造法等,它有效形塑了畫面的立體感,在敦煌的佛教石窟壁畫中有所顯示。中國藝術(shù)家受到了極大的啟示,他們用自己的方式進(jìn)行了改進(jìn),用色調(diào)的變化、粗細(xì)有致的線描表示三維空間。因此,張彥遠(yuǎn)的《歷代名畫記》中認(rèn)為,這時(shí)期繪畫當(dāng)以南梁畫家張僧繇為代表,而他是受印度影響的凹凸法作畫著稱的。
作為藝術(shù)的創(chuàng)新或革命都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讓我引用我國大畫家潘天壽的一段體會作為結(jié)束語:吳缶廬曾與友人說:“不技拾人者則易,創(chuàng)造者則難,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畫家要?jiǎng)?chuàng)出自己的獨(dú)特風(fēng)格,決不是偶然俯拾而得,也不是隨便承襲而來。所謂獨(dú)特的風(fēng)格,在今天看來,一要不同于西方繪畫而有民族風(fēng)格,二要不同于前人面目而有新的創(chuàng)獲,三要經(jīng)得起社會的評判和歷史的考驗(yàn)而非一時(shí)嘩眾取寵。此之所以不容易也。(責(zé)任編輯:楚小慶)
①托馬斯·沃斯伯格著,李奉棲等譯《什么是藝術(shù)》,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
②康德著,鄧曉芒譯《判斷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46頁。
③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xué)》第一卷,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版,第4頁。
④同③,第5頁。
⑤[美]方聞《心印——中國書畫風(fēng)格與結(jié)構(gòu)分析研究》,陜西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⑥愛米·托馬森《藝術(shù)本體論》,[美]彼得·基維編《美學(xué)指南》,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頁。
⑦同②,第146頁。
⑧同②,第147頁。
⑨[美]約翰·杜威《藝術(shù)即經(jīng)驗(yàn)》,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版,第166頁。
⑩沈尹默原著、朱天曙選編《沈尹默論藝》,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頁。
同⑩,第41頁。
同⑤,第258頁。
門羅C.比爾茲利《藝術(shù)的美學(xué)定義》,Thomas E.Wartenberg編《什么是藝術(shù)》,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242頁。
王朝聞《審美基礎(chǔ)》上卷,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版,第19頁。
艾倫·戈德曼《評價(jià)藝術(shù)》,[美]彼得·基維編《美學(xué)指南》,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
同②,第159頁。
同③,第220頁。黑格爾說的呂莫爾,是德國藝術(shù)理論家。
同③,第220頁。
同③,第177頁。
同③,第220頁。
[英]貢布里希《理想與偶像——價(jià)值在歷史和藝術(shù)中的地位》,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41頁。
同,第149頁。
貢布里希用語,他說:“藝術(shù)的奧林匹克山,像神話中的奧林匹克山一樣,有各種級別神明的位置,從卑微的精靈到使人敬畏的大神。”
[英]柯律格《中國藝術(sh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同,第151頁。
[英]貢布里希《藝術(shù)的故事》,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08年版,第600頁。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shù)的法則》,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頁。
同,第143頁。
同⑩,第52頁。
徐小虎《畫語錄——聽王時(shí)遷談中國書畫的筆墨》,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
徐建融編《潘天壽藝術(shù)隨筆》,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76-77頁。
修·昂納等著《世界藝術(shù)史》,北京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同,第293頁。
同,第316頁。
葉子編《黃賓虹山水畫論稿》,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
同,第129頁。
葉朗《中國美學(xué)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頁。
方聞《超越再現(xiàn)——8世紀(jì)至14世紀(jì)中國書畫》,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王朝聞、鄧福星總主編《中國美術(shù)史》第6卷,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頁。
同,第433頁。
達(dá)·芬奇《筆記》,朱光潛譯,伍蠡甫、胡經(jīng)之主編《西方文藝?yán)碚撁x編》上卷,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頁。
[英]貢布里希《萊奧納爾多論繪畫科學(xué):評〈評繪畫〉》,李本正、范景中編選《文藝復(fù)興:西方藝術(shù)的偉大時(shí)代》,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0年版。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頁。
同③,第3頁。
張大千著、葉子編《張大千畫訣要論》,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頁。
同,第37頁。
同,第573頁。
[美]H.W.詹森著、戴維斯修訂《詹森藝術(shù)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3頁。
同,第39頁。
同,第39頁。
同⑩,第77頁。
同⑩,第77頁。
[美]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繪畫1570-1644》,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42頁。
同,第142頁。
同,第11頁。
同,第163頁。
宗白華《藝境》,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頁。
同,第7-8頁。
李永翹編《張大千藝術(shù)隨筆》,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5頁。
[法]讓·克萊爾《論美術(shù)的現(xiàn)狀——現(xiàn)代性之批判》,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頁。
范景中、高昕丹編選《風(fēng)格與觀念:高居翰中國繪畫史文集》,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頁。
同,第172頁。
[美]庫恩《必要的張力:科學(xué)的傳統(tǒng)和變革論文選》,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頁。
[美]黛安娜·克蘭《無形學(xué)院:知識在科學(xué)共同體的擴(kuò)散》,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頁。
[美]庫恩《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8頁。
同,第127頁。
同,第95頁。
同,第127頁。
同,第128頁。
同,第159頁。
同,第334頁。
大約1645年,在最早的科學(xué)共同體——英國皇家學(xué)會起源的時(shí)候,曾作為會員的著名科學(xué)家羅伯特·波義耳在信中把它稱為“無形學(xué)院”,直到今天仍以此聞名于世。
同,第129頁。
同,第336頁。
同 ,第72頁。
同,第72頁。
同⑤,第258頁。
[英]貢布里希《藝術(shù)與錯(cuò)覺——圖畫再現(xiàn)的心理學(xué)研究》,湖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頁。
同,第110頁。
同,第68-69頁。
方聞《兩張董元——早期中國山水畫“狀物形”與“表吾意”兩種范式的建立》,上海博物館《翰墨薈萃:細(xì)讀美國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頁。
同⑤,第9頁。
老水番編著《宋代書論》,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
同⑤,第109頁。
同⑤,第10頁。
同⑤,第23頁。
同⑤,第11頁。
同,第581頁。
同,第209頁。
同,第334頁。
同,第335頁。
同,第340頁。
同⑤,第11頁。
同,第114頁。
同,第160頁。
同,第570頁。
同,第614-617頁。
同,第129頁。
同,第262頁。
同,第617頁。
同,第122頁。
[美]高居翰《隔江山色:元代繪畫》,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2頁。
同,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