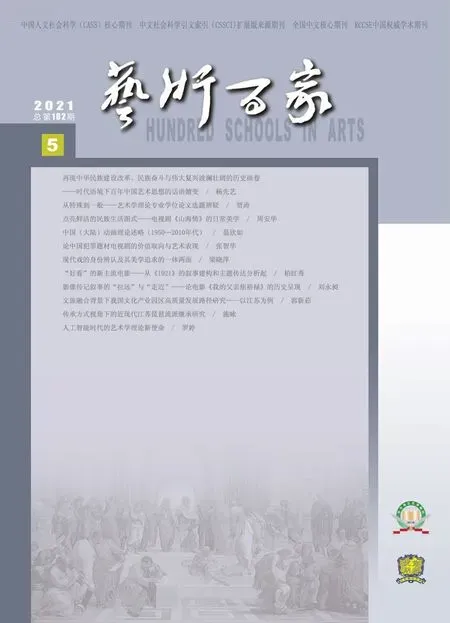現代性、日常生活與動漫亞文化的社會學考察
萬江
摘要:本文主要討論的是現代性、日常生活背景下動漫亞文化的興起,現代性與動漫亞文化之間的隱蔽關系。文章揭示了動漫亞文化特有的文化觀念和行為方式與自我認同建構的復雜意義,同時分析了動漫消費行為的被動性和被壓制性。
關鍵詞:動漫;現代性;日常生活;動漫亞文化;自我認同;審美文化
中圖分類號:J50文獻標識碼:A
Modernity, Daily Life and Sociology Study of Animation Subculture
WAN Ji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72)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媒介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國外卡通、動漫借電視媒體的“助陣”,開始大舉登陸中國市場,以此為背景,國內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漫畫、動畫、卡通消費群體,伴隨這種趣緣消費而來的則是具有鮮明的異于主流文化的動漫亞文化。作為中國后現代文化語境中重要的亞文化現象之一,動漫亞文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其中。它是一種體驗文化,人們通過諸如動畫、漫畫、網絡游戲、cosplay表演以及同人文學等表現形式展現個性,尋求快樂和滿足;它是一種社會文化,人們積極主動的在動漫行為上進行精力和情感的持續投入,與同行交流溝通,獲得精神的滿足的同時在這個虛擬世界中進行身份認同的建構;它還是一種經濟文化,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產業,人們在動漫產業結構中消費相應的產品和項目;等等。動漫亞文化作為現代社會高度工業化、都市化下的產物,是由一系列現代性進程和特征所催生的。因此,其存世的特定社會文化——現代性及其日常生活顯然是一個無法繞過的文化現實和理論視野。
一、現代性及其日常生活快照
現代社會是一個工業化的社會,其必然結果之一就是都市化的形成。人們逐漸脫離了鄉野大地而生活在人造的世界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都市的生活方式。齊美爾認為這種大都市生活方式的特征在于理性主義對生活各個層面的控制:金錢取代了土地,理性取代了宗教,文明取代了文化,世俗化急劇地膨脹起來,人們的日常生活結構及其價值觀念發生了重要變化。馬克斯·韋伯用“理性之鐵籠”的隱喻預示著現代人的命運。在他看來,現代生活乃是規章對人的規制,工具理性對日常生活的宰制無處不在,在理性主義的壓力下,個體屈從于各種科層化或官僚化的體制而無力抗爭,社會變得越來越等級化、程式化和法律化,生活越來越千篇一律或日復一日。失去了人文精神的人最終也變成了工具——自己是自己的工具,也是別人的工具。一言以蔽之,現代日常生活就是形式對生命力的抑制,感性的生活受到壓抑,生活失去了個性化的色彩。英文有一個傳神的詞來描述日常性的這個特性——routine,意思是“常規”、“例行公事”,或“排斥任何冒險和反常”的“墨守成規”,這正是現代性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
二、現代性與動漫亞文化凝視
1.現實的逃逸
每一種文化都承載著一種價值觀、一種生活態度。現代性日常生活的生存境遇,必然導致人們對于現代日常生活的膩味和逆反,激勵人們對于刺激和新奇感受的追求。人們往往通過對于非類化、非一般化活動的追求實現對日常生活重復性的抵制與顛覆。用齊美爾的話來說,就是個體有一種沖出這一鎖閉生活的冒險沖動,這種冒險的本質在于“從生活的連續性中突然消失或離去”。在韋伯的理論中,就是個體需要某種通過像審美和愛欲一類的活動來超越“鐵籠”的壓抑性的生活。學者們種種激進的表述深刻地觸及超越日常生活的內在沖動,這正是社會控制“有序之失序”辯證法的結果。在我看來,這一理論恰好指明動漫亞文化產生的第一個重要的現代性特征:“現實的逃逸”。
尼采、韋伯以來,從社會學到哲學,從美學到文化,一直有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藝術是作為日常生活局限的對立面而出現的。藝術是感性的張揚,是烏托邦。因此,無論是福柯所主張的“生存美學”,還是列斐弗爾對“游戲城”的向往,都強調以審美的感性來抵抗或擺脫日常生活的理性。動漫文化作為人類精神文化中獨特的存在形態,與其他藝術一樣有著自身的“修辭”,存在著同樣的審美體驗和特征。在我看來,動漫亞文化的產生為自我的“逃逸”提供了空間和手段,主體審美愉悅的獲得正是“動漫趣緣”這一亞文化群體“滋生”的重要的驅動力之一。
動漫亞文化現象作為人類文化活動中的活躍成分,豐富的幻想色彩是它吸引眾多現代人的法寶之一。當代動漫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故事發生在現實與奇幻世界的交叉,或是在完全的架空世界中,動漫之于現代人就如同面對一個全新的陌生世界。在動畫影像的視覺體驗中,人們往往通過動畫中的那種夢幻般的、轉瞬即逝的、新奇的審美感受來否定平庸的日常經驗;在cosplay角色的性格刻畫中,表演者通過“易裝”而化身他者,強烈的游戲色彩將現代人的目光從現實世界轉向一個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和情感的空間,滿足著種種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成就感、虛榮心乃至暴力欲望,也意味著自我意識的消失,其情感體驗作為對現代日常生活反省與批判的路徑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陌生化和震驚作用。顯然,動漫亞文化空間早已成為動漫迷們狂歡的“烏托邦”,在這里,僭越性的欲望可以得到暫時的表達和發泄,已建立的等級被片刻地顛倒了,而被禁止的快樂也被暫時的放縱了。動漫虛擬世界幫助個體實現了從原有的生活連環或連續性中暫時“逃離”出來,獲得某種超越日常生活的內在欲望的滿足與需要。它是人類非理性的一面從理性世界的偏離,是文化“自救”的空間。
2.認同的建構
工業化所導致的社會急速變遷加速了日常生活的進程,現代性雖然造就了對個體來說非常重要的生活機遇,但也為個體設置了風險和危機,使現代人的自我認同呈現出迷茫不定的狀態。自我認同源自自我身份感的確認,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在安東尼·吉登斯的理論視野里,自我認同根植于社會聯結,是與尊嚴感、自豪感和恥辱感等相關的價值觀和情感聯系在一起的。在吉登斯看來,伴隨現代性而來的是個性化價值追求與機器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工業社會、市場經濟的引入引發了物質利益的大追求,導致了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個體化,與這種利益追求相伴隨的是權力、地位在社會中極端重要性的突起。在這樣的背景下,“自我”紛紛逃逸,在正式組織過度合理化、科層化、社會麥當勞化以及人際關系利益化、制度化的縫隙中尋求發展的窄小空間。然而現代性的場景中,名利尋求充滿了艱辛與緊張,并不總依從于人們的期望或控制,真實的社會生活帶給現代人的往往是一種“欺騙感”、“挫敗感”,個體的精神世界因此變得焦慮、彷徨,感到本體性的安全受到威脅。endprint
布爾迪厄將文化描述成一種人們可以進行投資并積累資本的經濟。那些弱勢的、處于邊緣地位,缺乏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以及這些資本所帶來“自尊”的人群,由于無法實現建構自我理想的期望,就會投身某種亞文化空間,通過積累相關的知識來獲取某種非官方的資本,并且憑借該資本在群體中獲得“自我實現”。從這一意義上說,現代性給人們的自我認同帶來了困境,也帶來了更多建構的機會。在我看來,這一理論恰好涉及動漫亞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的現代性特征:認同的建構。
對于身處動漫亞文化空間的個體而言,現實世界中金錢和地位的衡量標準在這里意義不大,動漫亞文化空間中文化資本的獲得就成為了他們贏得別人尊重和肯定的重要因素。只要對動漫玩偶(手辦)收藏這一文化實踐的現狀稍加檢視就不難發現,收藏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其價值觀念及其典范效應通常是與所謂的“趣味”聯系在一起的。在康德那里,“趣味”是一種判斷力,代表了個體的價值判斷和文化選擇;布爾迪厄則指出“趣味”的一個重要功用就是“社會區分”。業界作品及其周邊衍生物的收集正是動漫趣緣亞文化群體內部建構社會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標記,收藏作為炫耀性消費的魅力在于被展示、被看見和被模仿,現代人對于動漫玩偶收藏的種種差異化訴求,實際上都是在傳達某種認同歸屬和追求優越的心理體驗及其滿足,這是一個個人的行為過程,又是一種社會性的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個體通過選擇,既獲得了一種身份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又產生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分享感,獲得了克服孤獨和社會交往的溝通感。從這一意義上說,動漫亞文化所賦予的認同感構成了日常生活中現代人幸福感和滿足感的重要指標。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人類正處于一個日益媒介化的時代,我們對自身文明及世界的認知和感受,都潛移默化地受到了媒介文化及其技術的強力制約和深刻影響,媒體和廣告,實際上就承擔了把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及其價值標準傳達給整個社會的中介功能。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和閑暇時間增多的條件下,動漫消費作為一種大眾消費行為,經由媒體的大肆炒作轉而形成某種公共壓力,這種壓力進而內化為公眾關于動漫亞文化的種種現代觀念,形成了動漫文化觀念及其行為方式對公眾的外在誘惑。或許可以略帶夸張地說,媒體的規訓正是動漫亞文化形成的又一個重要的現代性特征,媒體規定了人們對動漫亞文化行為的期待和滿足感,爾后的消費不過是這一規訓的實踐而已。
現代社會的發展以及都市化的形成,在為我們塑造了全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同時,也孕育了大眾對于動漫亞文化復雜的心理動因和社會需求。我們看到,作為人類擺脫理性中心主義的一種有效手段和自我表達的主導方式,當代動漫卸下了沉重的敘事負擔,重返社會現實和個人經驗,重新滿足大眾的閱讀期待。在我看來,這正是現代社會里動漫亞文化獨特的人文精神所在。(責任編輯:賈明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