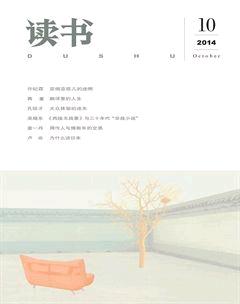夏衍在文化部
陳徒手
隨著毛澤東關于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先后下達,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文藝界刮起凌厲的整風運動,原本是領導機構的文化部黨組被中央高層點名痛責,狼狽不堪,很快就成了群起攻擊的靶子,至一九六五年初春,調整文化部領導班子,原黨組全班端掉。時任黨組副書記、主管電影的副部長夏衍一貫被視為右傾,自然成為此次運動的核心。
一
文化部機關向來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重災區,每一場慘烈的斗爭之后,總有若干部長被斗得灰溜溜地下臺。日積月累,文化部一逢運動總有自生的內部規律可循,大家多年形成的斗爭經驗總會得心應手地應用。
最大的經驗就是揪出一個斗爭的首要目標,傾倒所有的“污水”,狠斗一番,以圖整個黨組的安全生存和涉險過關。一九六四年整風一開始,夏衍就成了這么一個“斗爭拋出物”。文化部黨組上報一份《關于夏衍同志的主要錯誤的材料》,迅速定性,上綱頗高,內中稱:“夏衍同志是文化部這次整風運動中的重點批判對象。從現在已經揭發的材料看,夏衍同志是一個世界觀根本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作家。他在文化部工作期間,不是執行黨的文藝路線,而是實行一條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文藝路線。”
文化部廳局長們很快就看出揪夏的新動向,而且發現此次給夏戴的帽子顯得非同尋常的嚴重:
整風一開始,好像就是對夏衍同志來的。有位黨組成員就向我講過,叫我心中有數。后來聽七月二十日燕銘同志、光霄同志的動員報告也是講電影問題較多,其它方面談的很不具體。使我想起這幾年來文化部整風有個經驗,就是僅僅對某個人進行了批判,而對整個黨組問題通常就是滑過去了,好像就是那個人有錯誤,別人都沒有份似的。結果整風以后依然故我,整個文化部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見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藝術局長周巍峙同志在黨員干部批判會上的發言》)
夏衍自身存有一個回避不了、別的黨組成員所不具備的歷史問題,就是他被視為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的“祖師爺”,曾一度美化了上海黨的電影小組的領導作用,與官方推崇的四十年代延安文藝座談會有個明顯的時間差。這是眾人認為非常犯忌的大事情,直接冒犯最高領袖在文藝問題上的全能權威。劉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中央會議上談到兩種文化的性質問題,實際上已間接地把夏衍推到難堪的境地。陸定一在華東話劇會演的時候提到“遺老遺少”,對夏衍等三十年代活躍人物來說已是明確的警告信號,但夏衍后來檢查說,初讀“遺老遺少”段落的時候很震動,此時還沒有聯想到說的正是自己。
夏衍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日在文化部黨組做檢查時,才坦承自己近十天來進行了一場“很劇烈、很苦痛的思想斗爭”,因為要挖思想根子,必然會接觸到三十年代的問題。他說:“三十年代的文藝是什么性質的文化?我對它做了什么估價?它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的文藝有什么原則性的差別?……不把文藝座談會以前和以后的界線劃清楚,必然會把主席的文藝思想和三十年代的文藝工作混淆起來。”
他仔細講述了三十年代從事文藝工作的經歷,講到一批大革命失敗后從實際斗爭中退下來的知識分子和從日本回國的大學生如何冒險從事黨的工作,為配合政治斗爭寫出反帝反封建的作品,敘述謹慎而又平淡,多半以沉痛的口吻加以全盤否定,由此檢討自己:對于那個時期的文藝工作,感情上有留戀,背上很大的包袱,并沒下決心和這些舊東西訣別。
他在檢查中偶有幾句對自己成績的說明,但大都是嚴重自污,竭力接近中宣部定下的批判口徑:
我們都是非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世界觀沒有改造,沒有經過實際斗爭的鍛煉,當時的環境下又不可能和工農結合。我們從日本回來之前,正是日本福本主義(一種左傾機會主義)全盛時代,滿腦子“拉普”式的左傾教條主義。小資產階級急躁病,拼命主義……什么都有,這才會引起魯迅對我們的不滿。當然,在后期,我們也由于在實際工作中碰壁而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是,把當時的文藝工作估計得過高,顯然是錯誤的。
從當時的作品來看,盡管從反帝反封建的問題上,從力求配合政治斗爭這點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應該看到,三十年代作品的絕大部分,階級觀點很模糊,寫的都是小資產階級和城市貧民,而且我們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又深受十九世紀西方文藝的影響,但在創作方法上,卻又有公式概念、標語口號式的毛病。
夏衍已經覺察到自己頭上頂著一個隨時會引爆的“大悶雷”,就是“美化三十年代黨的電影小組”,好像在敵人進攻中,電影小組頑強不屈,“謹守”了黨的方針及瞿秋白的指示。有人還專門引了他文章中的話語來佐證那種“政治自負”:“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公司去當編劇,成立了黨的電影小組,這一年便成為電影向左轉的一年。”夏衍在檢查中特別強調此事不確,電影小組的事情并不像外界傳說的那樣:“事實上不完全這樣,就在我們領導電影工作的黨員中,有人被捕后變節,有人在困難時期消極而退出了陣地,也有人被資本家溶化了。”
眾人指責夏衍“迷戀三十年代”,夏衍只得慌亂地伺機解釋。他介紹說,由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電影事業的經營管理方面照搬了蘇聯的辦法,有許多框框不適用于中國的實際,以致在制片周期、耗片比例、人員分工等各個方面都造成很大的浪費。所以常常回過頭來,想從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面來吸取經驗。他說:“我不止一次說過,為什么抗戰時期的抗戰演劇隊三十來個人可以經常演出,而現在一個劇院有了三四百人還經常鬧劇本荒,不能演出新戲?因此建議他們總結一下過去的演劇隊的經驗。”(見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夏衍同志在文化部全體黨員和直屬單位負責干部會上的檢查》)這反而像是越解釋越混亂,更給自己的“政治罪狀”增添新內容。
文化部黨組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痛下“毒手”,不留余地,他們向上級明確地表示:“夏衍等同志把那時的上海說成已經有了一條完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已經解決了文藝工作者同工農兵結合的問題。他們特別頌揚瞿秋白同志個人領導如何英明正確。”報告中再三強調,這是否定延安講話的偉大意義,“用他們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來同黨的文藝路線相對抗”(見《關于夏衍同志的主要錯誤的材料》)。這實際上已經置夏衍于不堪的“死地”。endprint
二
由三十年代問題引發開來,夏衍被迫面對同僚們的一堆責問,對諸多事件像過山車一般來回交代、折騰。譬如六十年代初期曾內部組織觀摩十三部三十年代影片,中宣部領導得悉后大為惱怒,逼迫夏衍查問此事。夏衍只是把中宣部的指示批轉給影協、電影局處理,事后沒有進一步追查。中宣部認為這樣處理過于輕率,是放任自流的不負責態度。夏衍為此做了多次檢討,反復表白這樣的意思:“不考慮在國內外階級斗爭十分尖銳、黨在大力提倡表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現代戲的時候,放映這些三十年代舊片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在靈魂深處還有一個三十年代的包袱,相對的也就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東西沒有熱情。”
受一九六二年廣州會議精神的鼓勵,上海知名電影理論家瞿白音給《電影藝術》雜志寄來一篇論述“創新”的文章,影協、電影局負責人袁文殊、陳荒煤看后覺得不好決定,就送請夏衍審理。夏衍閱讀后也認為文章的氣味與當時漸變為嚴酷的政治環境不符,他就親自著手修補,刪去一些尖刻的話語,特意提到“講話”和“雙百”方針,加上了有關五十年代電影“工農兵成了銀幕上的英雄人物,這是劃時代的、根本性質的創新”等保護性的言辭。夏衍后來在檢查中承認:“實際上我不僅沒有擋住風,反而給他幫了忙。”事實上夏衍當時事后也曾布置《電影藝術》編輯部寫批評瞿白音的文章,但已于事無補。
夏衍為有政治問題的文章打掩護,不止瞿白音“創新”文章這一件,這就成了部內干部批判時最為憤慨的事例之一,認為為此類文章“擦了粉”,增加了政治欺騙性。看到夏衍焦頭爛額的模樣,副部長徐平羽在交心活動時還提意見,說夏對這件事做得不值得。
此時部黨組開會已被人稱為“渙散得實在不像樣子”。有一次與會者批評副部長徐光霄與有問題的劇作家孟超談話內容不妥,徐有點失控,回答時多有不冷靜。夏衍勸慰徐說,當時你就檢討一下,承認“走火”就算了,何以頂下去呢?黨組有人為此高調地指出,這是夏衍勸人“識相點”(上海方言),混過去算了,何必與人家爭論呢。夏衍身上的這種味道很不對,不是真正革命者的態度。
電影《早春二月》的問題更引發了大范圍的聲討,還為此在北影開了專題會,夏衍被迫接受批判。發言者指責他有濃郁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對創作人員施加溫情主義的影響,與三十年代的作品有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系。夏衍只好在別人批判的基礎上,承認自己“在重要問題上不能堅持原則”,“對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足”。
他交代道,當初討論《二月》分鏡頭劇本時,看出一些毛病,但沒有聯系當時階級斗爭的形勢,只是提出柔石作品有“小資產階級感情”、“當時看來也許問題不大,但今天看來就很不足了”等等意見,要求導演不要拘泥原作,可以比較放手地改,但并沒有指出原作根本性的錯誤和缺點。談及自己手軟的原因,他說:“因為我已經在上影否定了一部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在北影撤下了一部魯迅的《傷逝》和其他一些五四作品,因此覺得對《早春二月》只能幫他們修修補補,不要再堅持。”(見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日《夏衍同志在文化部黨組的檢查》)周揚看了影片的毛片予以激烈批評,夏衍深感吃驚,但也有一種“是否把問題看得太嚴重”的感覺,希望從“不浪費幾十萬元拍攝經費”的角度出發,對影片有所修改,以后在國內不放映,只作為對第二中間地帶國家輸出的片子。
在周揚批評影片《早春二月》不妥之際,影協袁文殊發現夏衍已經印好的“論文集”中有一篇談改編的文章,其中提到小說《二月》的改編,便好心地提醒夏衍是否要修改、刪除。一向自稱在具體事務上遲鈍的夏衍不覺得問題有多么嚴重,只是覺得那一段話是單純針對改編的角度而談的,生怕事后改文章給人以掩飾錯誤、逃避責任的印象。就是這么一疏忽,造成了周揚的不快和反彈,扣上“抗拒批評”、“犯有組織性的錯誤”的帽子。夏衍對此只好被迫做了這樣的表態:“這是一種舊社會的文責自負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日,夏衍在文化部黨組做了長篇檢查,他自以為一再“碰到自己最痛的地方”:“近來我一直在想,為什么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有那么多的顧慮?為什么柯老提出寫十三年就條件反射想到民主革命時期的題材還要不要寫?為什么電影題材比例中革命歷史題材少了一些的時候會那樣的憂心忡忡?為什么對五八、五九年的作品只看到缺點而不積極地肯定它的方向?這都是人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而思想感情還停留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具體反映。”這樣的檢查程度還是未獲中宣部領導的認可。
作為三十年代上海一起組織文藝工作的黨內老友,在惡劣的環境逼迫下,在自保和茍活的心境之中,周揚和夏衍由于一連串事件的發生而滋生裂隙,逐漸醞成了不念舊情的局面。
三
夏衍在文藝界有著深厚的人脈關系,錯綜交織,再加上在白區工作時習慣于個人單線領導,因而很多高層領導認為他是文藝山頭的“老頭子”,沒有經過嚴酷的斗爭生活鍛煉,自由散漫的積習非常嚴重,黨內對此意見頗大。早在一九五四年,周恩來就提醒他對過去文化界老友“團結多、批評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夏衍此后說話盡量謹慎,力求通過組織關系做工作。他對這段上海難堪的工作經歷做過這樣的檢討:“不警惕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利用我這個弱點,用拉老關系、奉承、迎合等等來對我施加影響,會用好像受了委屈似的可憐相來博取我的同情。”(見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日《夏衍同志在文化部黨組的檢查》)他在檢查中甚至用了“不寒而栗”作為回顧之感想。
五十年代初期夏衍在上海負責文化工作,整個狀態不盡理想,連續出了《武訓傳》、《我們夫婦之間》、《人民的巨掌》等挨批影片,對在上海的胡風、馮雪峰等又管理不力。他萬分苦惱,覺得自己政治上過于落后,擔負不了這么重大、復雜的工作,一再給周揚寫信,希望能把斗爭性強的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林默涵調到上海工作。
被內定為“右傾”、“溫情主義”的夏衍與上海市委的矛盾日見增多,市委要不斷強化對文藝界的斗爭,夏衍“和稀泥”的態度自然不能被容忍。他被調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長之前,已經處于極為狼狽的境地,離開上海已算是“幸福的解脫”。他離滬時,就聽到市委有人說,夏某人走了,上海電影界的事情可能好辦一些。endprint
上海市委對于夏衍領導文藝的幾年工作一直持有很壞的評價,認為他政治上過于軟弱,留下了一堆爛攤子。由于夏衍還處于領導全國電影工作的實權位置,他與上海市委的沖突還在以另外的形式繼續,這就使上海眾多的文藝界人士在文化部和市委的矛盾中屢屢受夾板氣,不知所措。有一次老演員趙丹問陳荒煤:“藝術上的問題,最后到底是誰說了算?”陳荒煤說:“當然是上海市。”趙丹認真地說:“我希望,你和夏公、和上海市的領導中間沒有什么問題,我們的日子就好過了。”趙丹所期盼的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景,上海的電影業幾年間就是在磕磕碰碰的沖撞中度過的,市委人士對夏衍的不滿和反感沒有絲毫減弱。
長春電影制片廠所在的吉林省委與夏衍及文化部多年沖突不斷,雙方在長影工作問題上時常意見相異。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曾向人惱怒地表示,電影方面的大右派在文化部電影局。又在一次會議中,公開稱陳荒煤與袁文殊都是修正主義者。宋振庭不便提及夏衍,但那種積累甚久的不滿意情緒顯而可見。
夏衍外受多個省市委的夾擊,業內又飽受下屬的埋怨,內心的煎熬無法比擬。一九六二年翠明莊會議,袁文殊按捺不住怨氣,批評夏衍說,你又是作家,又是內行,又是部長,但是歪風你不頂住。連溫和的陳荒煤都說出心里話:“有些事情你不出來頂一下,替我們說說話,我們也很難辦。”無奈的夏衍只好含糊地在翠明莊會上表態:“要出大氣,不出小氣。”此話后來被嚴厲地批為“想出中央的氣”。
一九六三年毛澤東關于文藝問題批示傳達之后,身感危機的夏衍曾寫信要求調動工作,自然是未能獲準。中宣部多次批評電影界有組織、有意識地捧老頭子,毫不客氣地說夏衍就是電影界的祖師爺。沒想到夏衍竟回應說,要消除這種影響,只有一改行,二撤戲,三開除黨籍。文化部黨組只能開會批夏衍的這種惡劣態度。會后匯報說,雖然夏衍承認態度不對,但他并沒有真正認識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性,而是繼續為自己辯解(見《關于夏衍同志的主要錯誤的材料》)。
夏衍后來在檢查發言中承認,“祖師爺”、老頭子的問題開始提出來的時候,震動很大,也很苦惱,也很抵觸。尤其是有人指出老頭子、祖師爺的地位不是客觀形成的,而是自己苦心經營所造成的,更是思想不通。苦惱之際,周揚代表組織與他談話,夏衍說,我自信不是一個堅持錯誤不改的人。周揚則回答說,要改正錯誤,先要認識錯誤。
在一九六五年初臨近整風運動結束之際,夏衍在黨員大會上做“深刻檢查”,認為自己思想根源在于自負:“美化三十年代的電影、文化工作,而且認為在領導工作、組織工作等等方面,都已經有了一套經驗。”這就造成工作上極其錯誤的局面:“近幾年來,文化部、電影局乃至影協不僅和地方黨委的關系很不正常,應該說對上、下、左、右的關系也很緊張,抵制黨對電影事業的領導。”“助長歪風,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甚至敵我不分,一任階級敵人來分化瓦解我們的隊伍。”(見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夏衍同志在文化部全體黨員和直屬單位負責干部會上的檢查》)
夏衍在會上表示,這次整風是黨對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畢生難忘的一次沉痛教訓。說者誠懇,聽者漠然。夏衍最終調離了文化部這塊凝聚工作心血,又匯集悲愴的傷心之地,在“文革”風暴到來之前就被打入冷宮。八十年代之后,論者多是籠統地說夏衍受盡“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公平而論,這次文化部整風運動,與“四人幫”沒有多少關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