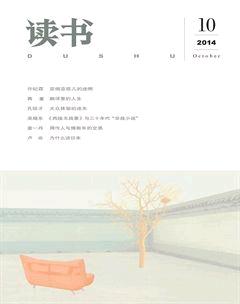中日關(guān)系中的誤解與錯(cuò)位
劉檸
中日兩國在相互凝視的過程中,會發(fā)生某種程度的焦點(diǎn)模糊、失真乃至錯(cuò)位,這是一個(gè)現(xiàn)實(shí)。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國家戰(zhàn)略的選擇結(jié)果,但在國民心態(tài)上卻表現(xiàn)為刻意視而不見;有些是源于信息不對稱,國民的知情權(quán)受到制約;有些則干脆是媒體的以訛傳訛,但背后仍透露出某種國民心態(tài)。
如人們通常以為,日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學(xué)習(xí)中國的結(jié)果。這固然是一個(gè)事實(shí),但也應(yīng)該做具體分析,因?yàn)樵诓煌臍v史時(shí)期,日本從中國文化吸收的強(qiáng)度是不同的,心態(tài)也不同。而日本心態(tài)的變化,客觀上也折射出中日兩國相對定位的變遷及文化的流向。大致說來,日本對中國的態(tài)度基本上可以用“前恭后倨”來形容:在漫長的古代,日本作為文化“下位”國家,對處于文化“上位”的中國表現(xiàn)出相當(dāng)?shù)木匆狻H欢搅私瑒t變得倨傲起來。到了現(xiàn)代(權(quán)且按照中國現(xiàn)代史的劃分),則開始公然蔑視中國。但在這個(gè)變化過程中,我們也看到文化的流向:從中國到日本,然后又從日本回流中國。到今天,則是雙向互動(dòng)。以語言為例,中文從日文拿來了“卡哇伊”、“違和感”等詞語,而中文的“電腦”、“微博”等詞語也登堂入室,進(jìn)入日語,并可望定型化。
檢討日本從中國的文化輸入及其背后的心態(tài),可以發(fā)現(xiàn):所謂“前恭后倨”,這“后倨”是成立的,但“前恭”其實(shí)并不像國人想象的那么“恭”—日人是謙而不卑,內(nèi)心仍放不下“矜持”。譬如,公元六零七年,圣德太子派特使小野妹子訪隋,遞交一紙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惹得隋煬帝大不悅,對臣子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fù)以聞。”
這則歷史記事,讓日人暗爽了何止千年!尤其是近代以來,日本史家爭相詮釋,論證早在圣德太子時(shí)代,島國統(tǒng)治者便已萌生與隋廷分庭抗禮的“二心”,旨在強(qiáng)調(diào)自身的“獨(dú)立性”。但其實(shí),至少在那個(gè)時(shí)代,“獨(dú)立性”云云似乎還無從談起,否則就難以理解同一則記事中的另一句話:“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我覺得,日人是以這種形式表達(dá)一種情緒—用日本哲學(xué)家內(nèi)田樹在《日本邊境論》中的表述,是“表面服從,內(nèi)心不服”。這正是所謂“邊境人”的顯著心理特征。而這種“內(nèi)心不服”的情緒,在不同的時(shí)期會呈不同的表現(xiàn),端賴自身的實(shí)力水平及與中心國家(中華)力量的消長。
日人素以認(rèn)真著稱,但在引進(jìn)中國的律令制度時(shí),卻似乎有“馬大哈”之嫌:他們引進(jìn)了諸般制度,從政治到文化,連文字都照搬無誤,卻獨(dú)落下了科舉和宦官制度,這事怎么琢磨怎么覺得蹊蹺。對此,內(nèi)田認(rèn)為,并不是說日本人經(jīng)過檢討之后,覺得這兩種制度存在不足,而是感覺這些制度似乎與其“本家的家風(fēng)”不大對路,于是便佯裝不知有這些制度的存在。但他們卻不會刻意反駁,只是悄然、低調(diào)地“割愛”。
對中國的典章制度如此,對儒學(xué)亦如此。作為深刻影響了日本文化的“外學(xué)”之一,儒學(xué)從來不曾成為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而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的整合對象。“和魂漢才”正如“和魂洋才”一樣,儒學(xué)充其量只被用作某種工具而已。
及至近代,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又呈現(xiàn)了一種日本對中國逆向輸出的景觀,我稱之為日本對中國的“文化反哺”。這一次,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赴日留學(xué)生和來華任職的日本教習(xí)。
自一八九六年首批留學(xué)生赴日以來,留日學(xué)生人數(shù)逐年增加,至一九零五、一九零六年間達(dá)最高峰(八千名左右)。美國學(xué)者任達(dá)在《新政革命與日本》中說:“粗略估計(jì),從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一年,至少有兩萬五千名學(xué)生跨越東海到日本,尋求現(xiàn)代教育。”與此同時(shí),大批日本人應(yīng)聘到中國內(nèi)地學(xué)校出任教師(稱為日本教習(xí)),或在各類政府機(jī)構(gòu)中擔(dān)任顧問(軍事、外交、教育、農(nóng)事顧問等)。除此之外,日人還在中國內(nèi)地開辦學(xué)校,派遣日本教師授課,在中國本土開展日語教育,培養(yǎng)留日預(yù)備軍。赴日留學(xué)生的增加與赴華日本教習(xí)、顧問派遣規(guī)模的遞增成正比,同消同長。
歷史地看,赴日留學(xué)潮無疑是現(xiàn)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運(yùn)動(dòng)。若用一句話來定性地加以概括的話,也許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九世紀(jì)九十年代兩國文化地位逆轉(zhuǎn)之后,日本對中國的“文化反哺”的話,那么包括我們此刻所談?wù)摰闹黝}在內(nèi),要么是“無從談起”,要么則需徹底變換形式(包括文體、文法及絕大部分學(xué)術(shù)專業(yè)名詞)。因?yàn)椋婕艾F(xiàn)代社會文化思想的一整套學(xué)術(shù)語言幾乎全部來自日語,諸如國家、政府、革命、自由、民主、人權(quán)、共和、憲政、政治、經(jīng)濟(jì)、商業(yè)、法律、文學(xué)、美術(shù)、戲劇、音樂、抽象、樂觀、形而上學(xué)、意識形態(tài),等等。試想,如果從一篇用現(xiàn)代行文表述的學(xué)術(shù)論文或講演詞中,把從日文中舶來的詞匯術(shù)語統(tǒng)統(tǒng)過濾并加以置換的話,意圖將何以傳達(dá),讀者或聽眾又如何接受呢?即使不是無從談起的話,不知所云怕是唯一的結(jié)果。
對此,從汪向榮的《日本教習(xí)》(三聯(lián)書店一九八八年),到美國學(xué)者任達(dá)的《新政革命與日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包括被認(rèn)為是該領(lǐng)域最權(quán)威著作的日本學(xué)者實(shí)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xué)日本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二零一二年)在內(nèi),均對日本的“文化反哺”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作用持正面、積極的評價(jià),甚至視為一樁絕對的好事。
但反思的聲音也并非沒有。如舒新城早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留學(xué)史》中曾發(fā)出過“軍閥如此橫行,留日學(xué)生自應(yīng)負(fù)重大責(zé)任”的慨嘆;五四運(yùn)動(dòng)史學(xué)者周策縱也曾注意到“留日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受軍事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較留學(xué)其他地方的學(xué)生所受的為多”的現(xiàn)象;王彬彬在《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文化反哺”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從日本輸入的‘西學(xué),已遠(yuǎn)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學(xué),而是被日本所刪節(jié)、改造、扭曲了的東西。”對于接受了如此強(qiáng)勁的“文化反哺”的中國,何以竟未能轉(zhuǎn)型為一個(gè)現(xiàn)代意義上的憲政國家的問題,他認(rèn)為:“……或許正因?yàn)槿毡镜挠绊戇^于強(qiáng)大,換句話說,或許正因?yàn)樵谥袊默F(xiàn)代化剛剛起步時(shí),就誤投了師門、錯(cuò)找了奶娘。”
也未可知。但正如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之不可逆一樣,真正的悲劇在于,即使這種“文化反哺”是“狼奶”(王彬彬語),我們卻已經(jīng)吐之不盡了。endprint
通過以上兩個(gè)例證(一古代,一近代),我們可以看到兩點(diǎn):一是日本在漫長的吸收、消化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并非始終是那種站得筆管條直、俯首帖耳的“好學(xué)生”,而是內(nèi)心有想法,有“不服”,且對老師的授業(yè)有自主選擇的學(xué)生;二是中日間的文化交流是雙向互動(dòng)式的,雙方各自給對方的都不算少,在文化上,應(yīng)該說都是慷慨的。對這個(gè)問題的評價(jià),兩國媒體其實(shí)都有不小的偏差。就中國媒體的報(bào)道而言,往往給讀者以一種兩千年來,中國文化始終在單向地、持續(xù)不斷地“喂養(yǎng)”日本,“有去無回”的錯(cuò)覺。
中日關(guān)系中的這種信息失真、意象錯(cuò)位的現(xiàn)象,還有一個(gè)奇怪的特征,就是越是晚近、現(xiàn)代的事體,反而越焦點(diǎn)模糊,云山霧罩,眾說紛紜。相比之下,對那些早期、古代的事情的描述和評價(jià),反倒相對清晰、準(zhǔn)確一些。
典型者,如所謂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戰(zhàn)爭索賠問題。一個(gè)眾所周知的說法是,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shí),毛澤東、周恩來出于對“日本人民”的體恤,放棄了戰(zhàn)爭賠償要求云云。這個(gè)說法流傳甚廣,隔三差五就會出現(xiàn)在微博上,具有極大的迷惑性。照這個(gè)說法,似乎是中日建交談判在先,在談判過程中,中國領(lǐng)導(dǎo)人寬宏大量,代表中國人民放棄戰(zhàn)爭索賠。可實(shí)際上,這個(gè)說法是經(jīng)不起歷史推敲的。中日兩國的外交檔案和眾多的史料,支撐的是另外一種歷史敘事。
首先,日本投降伊始,蔣介石即發(fā)表了著名的“以德報(bào)怨”演說,明言將放棄對日戰(zhàn)爭賠償要求。一九五二年四月,日本政府與臺灣當(dāng)局簽署了“日華條約”(全稱為“中日和平條約”及其“議定書”)。該條約承認(rèn)了前一年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中的原則,并在“議定書”的第一條(b)款中明確:“中華民國自動(dòng)放棄依據(jù)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a)1之規(guī)定,日本所應(yīng)提供之勞役利益,以作為對日本國民寬厚及善意之表征。”盡管對這個(gè)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予承認(rèn),認(rèn)為是“非法”、“無效”的,但國民黨最初的放棄原則,應(yīng)該說對大陸后來的相關(guān)政策決定發(fā)生了相當(dāng)?shù)挠绊憽?/p>
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訪華,并獲得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從七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周與竹入連續(xù)談了三個(gè)晚上,達(dá)成了十二點(diǎn)共識:主要是關(guān)于臺灣問題,其次是不謀求霸權(quán)、和平解決糾紛等問題;其中第八點(diǎn),即是“放棄戰(zhàn)爭賠款”。竹入把會談內(nèi)容做了筆記,被日本報(bào)界稱為“竹入筆記”。竹入其人,始終被中國和一部分日本媒體當(dāng)成是“田中密使”、“和式基辛格”,但其實(shí),他并不代表田中。直到兩國建交二十五年后的一九九七年,竹入才首次對新聞界披露了自己當(dāng)初是假扮特使,以私撰的政府談判條件訪華,取得了中方的建交談判草案后,作為“禮物”再呈送給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的幕后“秘辛”。
但無論如何,竹入義勝到底還是拿到了中方放棄戰(zhàn)爭賠償要求的“大禮”。當(dāng)竹入聽到周對毛的指示的傳達(dá)時(shí),竟禁不住戰(zhàn)栗。照日方當(dāng)初的估算,應(yīng)對與否另當(dāng)別論,如果要賠償?shù)脑挘瑢⒉坏貌荒贸鑫灏賰|美元的額度。“周總理的話,令我一陣熱流上涌—他讀懂了日本的心,看穿了即使日本方面有意支付,但只要中方端出賠償問題,自民黨將難以搞定的局面。”大平外相的秘書森田一則評價(jià)說:“如果(日本)被要求賠償?shù)脑挘菍⑹且粋€(gè)天大的問題,甚至到了將不得不對日中邦交正常化斷念的程度。”
得到了“竹入筆記”的厚禮,特別是關(guān)于中方放棄戰(zhàn)爭賠款的核心條件的“定心丸”之后,此前對是否應(yīng)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課題還搖擺不定的田中角榮首相才決定出訪北京,正式啟動(dòng)邦交正常化談判。所以,嚴(yán)格說來,中方放棄戰(zhàn)爭索賠,并不是邦交正常化談判的結(jié)果,而恰恰是談判啟動(dòng)的前提條件。
正因此,在談判過程中,當(dāng)日方實(shí)務(wù)主談人、外務(wù)省條約局長高島益郎從國際法角度,哪壺不開提哪壺地端出“賠償問題免談?wù)摗保ɡ碛墒鞘Y介石已在“日華條約”宣布放棄要求賠償?shù)臋?quán)利,而“一種權(quán)利不能兩次被放棄”)的時(shí)候,中方的憤怒可想而知(一說是高島被周恩來斥為“法匪”,但中方予以否認(rèn))。
回過頭來歷史而公平地看,這里其實(shí)也體現(xiàn)了雙方的相互不理解和對對方國情的誤讀,暗喻了日后兩國關(guān)系“晴間多云”的逆轉(zhuǎn):對中國來說,橫豎戰(zhàn)爭賠償我們已經(jīng)承諾放棄了,只是在《聯(lián)合聲明》中提那么一句,算是對歷史有個(gè)交待,怎么就一點(diǎn)面子也不給,連個(gè)臺階都不讓下呢?而對日方來說,《舊金山和約》是其結(jié)束戰(zhàn)爭狀態(tài),回歸國際社會的起點(diǎn),中方因人家不帶玩,可以轉(zhuǎn)過臉去,但日方斷不能輕言跨越這段歷史—這背后,也不無日人對中國國體不信任,怕中方“秋后算賬”的隱憂。
扯來扯去的結(jié)果,成了我們后來所看到的文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zhàn)爭賠償要求(《聯(lián)合聲明》第五條)。”這里,有兩點(diǎn)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是中方提議的原方案中,“……放棄對日本國的戰(zhàn)爭賠償要求權(quán)”中的“權(quán)”字被拿掉,從法律意味的語感上,變?yōu)榉艞壱环N中方單方面的主觀性要求,而不是一項(xiàng)客觀性的權(quán)利—這是日方堅(jiān)守的底線;其二,放棄的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不是“政府和人民”。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權(quán)利呢?文本中沒提—這為日后的扯皮埋下了伏筆。
上述第二點(diǎn)頗耐人尋味:對于先行簽署過《舊金山和約》的日方來說,對和約中“盟國及其國民”的措辭是不可能忽略的。而認(rèn)可《聯(lián)合聲明》中的方案,一方面是出于對“人民中國”政府的信任—政府全權(quán)代表人民;另一方面,也樂得模糊、曖昧。但對一心謀求對日邦交問題政治解決的中方來說,很可能只是一種單純的技術(shù)性失誤:首先,《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中國不是簽約國,它怎樣描述、規(guī)定,與我無關(guān);其次,在一九七二年的國內(nèi)政治環(huán)境下,有無國際法專業(yè)人士參與對日談判都難說,遑論法律文本的把關(guān);再次,在與外國簽署的法律文獻(xiàn)中需對“民意”有所回應(yīng),至少要考慮“民意”的存在,這種意識的成形少說也要到改革開放以后。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一部兩千年的中日關(guān)系史,其實(shí)中間穿插了諸多的誤解與錯(cuò)位。而且,往往越往后,焦點(diǎn)越模糊,誤解與錯(cuò)位越厲害。中日關(guān)系要想繼續(xù)朝前走的話,亦須從澄清這些事實(shí)關(guān)系,讓歷史回到客觀入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