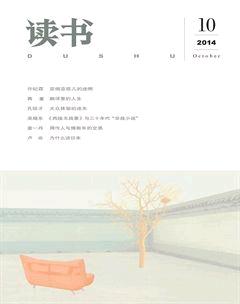謝肇淛的徽州之行
王振忠
一
“試問新安道,凄涼意若何。大都常業少,只是素封多。商舶年年出,倡樓夜夜歌。人情吁可怪,客子慎風波。”第一、二句頗感突兀,商旅往來、財富匯聚不息的“新安道”,何以在謝氏筆下竟以“凄涼”二字語出?
是青壯年大批外出,本土因人煙稀少而顯得有點落寞?還是野店風霜客路辛勞,秋天的景致讓謝肇淛倍感沿途之蕭瑟?抑或是其他什么緣故?或許,不假外求,《新安雜詩十首》的其他幾首詩中,就隱含了解讀的線索……
萬歷二十六年(一五九八)九月,謝肇淛從淮南鹽運中樞—儀真(今江蘇儀征)水陸兼行前往徽州。而他的《新安雜詩十首》,就是根據萬歷二十六年九、十月間徽州之行的所見所聞,生動地刻畫了皖南的社會風情,就其寫實程度而言,實可看作一組風俗詩。
《新安雜詩十首》的第七首指出:
水市居民少,山城長吏尊。
春寒稀出郭,日午未開門。
謁者真如鬼,功曹巧似猿。
禰生懷片刺,磨滅向誰言。
新安江穿行于皖南的低山丘陵,河谷深切地層,群山蜿蜒起伏,一府六縣依山傍水,留在當地的居民不多,天高皇帝遠,官員便顯得特別有權威。這首詩歌,狀摹了謝肇淛對徽州官府衙門的觀感。其中,最后兩句用了《后漢書·文苑列傳》的典故—東漢士人禰衡(此人即后世京劇中“擊鼓罵曹”的主人公),錐處囊中,常思脫穎。他從江南荊州來到人文薈萃的京師許都,為求進用,預先寫好了自薦書,打算找機會毛遂自薦。但因其人自視甚高,結果自薦書裝在身上,字跡都磨損得看不清了也沒派上用場。在這里,謝肇淛以禰衡自況,說自己未曾在徽州官府那兒打過秋風。
晚明時期,著名戲劇家湯顯祖曾有“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的詩句,意思是說,要見識富得流油的地方,就要到黃山和白岳去旅行。其實,明的是縱情山水,實際上是想在當地打秋風,這在當時稱為“黃白游”。而“黃白游”之舉,除了由好事的徽州富商接待之外,不少人還希望到當地官府那里夤緣關節。
其時,由于“黃白游”者紛至沓來,地方官疲于應付,有時因招待偶有不逮,秋風客踏上歸途后,便“惡稱歙游之涼也”(亦即指斥當地人招待不周)。由于有太多的文人墨客前往徽州做“黃白游”,寓客去留,游士來往,明末的傅巖對此顯然是不勝其煩,他遂公然聲言謝客:“徽有黃山、白岳之勝,向多游屐,恐浙接壤,停留指冒,遍示歇家寺觀,及刊刻啟言,或有過客造謁者,即令持啟阻回,起行概不接見,請謁以杜。”這位歙縣知縣的具體做法是—刊刻啟示,阻止各地的文人士大夫借“黃白游”之名前來徽州干謁。這雖然說的是明末的情形,但在此之前,謝肇淛顯然就碰到地方官府的冷面孔。從上揭詩歌來看,謝氏踏上徽州土地之前,可能也希望當地官府能盛情款待一下,可一經接觸,卻發現對方并不熱絡,見此情狀,謝氏亦不愿屈尊俯就,遂難免心存怨懟。故此,《新安雜詩十首》開篇所云:“試問新安道,凄涼意若何”,其間的一層意思或在于此。
另外,《新安雜詩十首》第三首的前四句還寫道:
白馬紫貂裘,朱門盡五侯。
貧因長聚訟,富為避交游。
此處說的是徽州當地有很多富商大賈、官宦人家,當地健訟之風熾盛,不少人因擅興官司而蕩析門戶。此外,在外來士大夫競逐“黃白游”的熱潮中,一些富商(如潘之恒等人)頗為熱衷,他們借此擴大交游,提高個人的聲望。不過,也有更多的富人卻害怕這種交游—因為與文人周旋,畢竟需要大筆的金錢花銷,所以謝氏才會有“富為避交游”之慨嘆。關于這一點,《新安雜詩》第五首又寫道:
比屋不知農,山村事事慵。
居民多習賈,市女半為傭。
日落催寒杵,溪流急夜舂。
相逢無好事,端不似臨邛。
臨邛,古縣名,治今四川邛崍。因秦時蜀卓氏、程鄭被遷至此,以鐵冶致富,后世遂以“臨邛”代指富商。在徽州,謝肇淛碰到的一些人并不“好事”,為人處世也完全不像他所想象的那類富商—這可能也是讓謝氏倍感新安道“凄涼”如許的另一原因。
二
謝肇淛是著名的旅行家,足跡遍及海內,他游覽名山大川,有相當獨到的體會。在《五雜組》中,他與讀者分享了自己的旅行心得:“游山不藉仕宦,則廚傳輿儓之費無所出,而仕宦游山又極不便。”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游山玩水不借助官府的幫助,那么,飲食車馬的費用就沒有著落,但倚靠官府旅行又相當不便,“侍從既多,少得自如,一也;供億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既殺風景,冠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這是從官員的角度來看,因為侍從眾多,游山時往往不太自由。另外,官府招待繁多,大吃大喝,彼此都心有不安,大概是招待之人難免嫌煩,而被招待者則過意不去,覺得欠了人情。游山之時前呼后擁,呵斥他人讓道,讓原本是雅事一樁的游山變得很煞風景。爬山爬熱了,總想脫掉上衣涼快一下,但為了保持官員的體統,卻又不好意思赤膊。而在另一方面,陪同之人更覺難過。例如,抬轎子及陪伴旅行之人,往往并不想走得很遠。那些作陪的和尚、道士,總是希望此種應酬及早結束。碰到崎嶇難走的道路,抬轎子的人就會罵罵咧咧。碰到很好看的風景,這些人就怕會成為先例,以后再來的其他人也要去游玩,招待起來不勝其煩,所以常常會將客人引到一般游客行經的線路。在這種情況下,“奇絕之景”往往難以看到。最后,謝肇淛總結說:“游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換言之,游山就必須找志同道合的黃冠緇素,大家提著拐杖隨興所至,踏盡落花。對于那些有錢又比較好事的主人,則要經常借助他們的力量。每逢一處風景,都要好好領略,并準備筆墨侍候,隨時記下,以備遺忘。這是謝肇淛游山的心得,其中詳細述及經常會碰到的各類情形,特別是旅行時招待方的情況:一類是仕宦(也就是官府),另一類則是富厚好事之主(亦即當地的有錢人)。而這兩者,也正是許多“黃白游”者的贊助方。
謝肇淛的徽州之行,全程由潘之恒招待。關于潘之恒,《小草齋集》中有《原上答景升》:endprint
丘壑空憐我,煙霞喜得君。
石樓曾望海,竹榻共眠云。
度嶺窮幽徑,摩崖識古文。
新詩與靈藥,滿袖碧氤氳。
景升即潘之恒,此一詩歌說的是潘氏與他步相隨、影相傍、語相通。對此,謝肇淛在《五雜組》中曾記錄一段趣聞:其時,黃山剛剛開辟不久,深山間有一處皆是積沙,人很快走過去便沒事,如果稍微遲疑一下,沙子就會崩塌。謝肇淛不敢走,而以“黃山東道主”自居的潘之恒遂自告奮勇,結果剛走上兩三步,沙就崩塌了,嚇得他大聲呼救,幸賴帶路的土人將他攙著往回走。而對面如死灰的潘之恒,謝肇淛調侃道:閣下差點做了秦始皇,駕崩于沙丘了……
根據方志記載,潘之恒為人“專精古人詞,工詩歌,恣情山水,海內名流無不交歡”。他出身于歙縣巖鎮的富商家庭,祖先都在江南儀真一帶從事鹽業。謝肇淛此行,就是從儀真前往徽州。可以說,他這一路上都是受到潘家的招待。潘氏是個才華橫溢的花花公子,曾入汪道昆的白榆社,又師事王世貞,后來與公安派的袁宏道亦過從甚密,在晚明頗有影響。謝肇淛此次到徽州,完全是由他接待—這可能是謝氏此行在徽州遇到的為數不多的幾位“好事”者之一。
前文提及,在晚明,士大夫之中風行“黃白游”,明的說旅行,實際上是到皖南打秋風。在當時,徽州富商中亦頗有好事之徒,他們對這些過往的文人好吃好喝招待,并陪同他們游覽境內的黃山、白岳,贈送現金、禮品等。有的徽商,還出資贊助文人學士刊刻書籍。例如,袁中道的《珂雪齋前集》刊刻于徽州府學,從首列校者姓氏來看,捐資助刻的友人或門弟子,絕大多數都是徽州人。而更早的一例子,則是于萬歷四十四年(一六一六)透過李維禎的推薦、由徽州出版商潘膺祉刊刻的《五雜組》。
《五雜組》刊刻的這一年(一六一六),在明史乃至明清易代史上皆是極為關鍵的一年。是年,建州女真努爾哈赤于赫圖阿拉建國稱汗,國號大金(史稱“后金”)。事實上,在此之前,謝肇淛在論及遼東形勢時,就極其敏感地預見到建州女真才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謝氏在《五雜組》中寫下此一預見時,距離一六四四年的“甲申之變”尚有二十多年,當時能有這樣的見解,非常了不起。不過,也正是因為這一扶傾救危的洞見,入清以后,《五雜組》就被軍機處奏請銷毀,以至于有清一代都不見《五雜組》的任何刊本。
不過,好在墻內開花墻外香,除了萬歷四十四年如韋館本之外,在明代還出現過另外一個刻本(今人稱之為“明刻別本”)。此本應刊刻于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之前,后輾轉流傳至東瀛,于日本寬文元年(一六六一年,當清順治十八年)覆刻。在江戶時代,《五雜組》在日本極受推崇,為諸多方志、隨筆、文集所征引。此“明刻別本”后來也一再翻刻,目前所知,至少還有寬政七年(一七九五)、文政五年(一八二二)的刻本。對照如韋館本,“明刻別本”的文字大同小異,最顯著的不同是全書增加了十六條的內容。而在這十六條中,有十五條都在卷十六的末尾(亦即位于《五雜組》全書的最后部分),可能為后來所補充。而且,這十五條基本上皆是根據前代筆記或前人編述的笑話加以改編,并無特別的史料價值。只有一條位于《五雜組》卷八的《人部四》,似乎特別突出,這一點顯然也與謝肇淛的徽州之行密切相關。
三
在《人部四》中,謝肇淛津津樂道于歷代的“妒婦”,其中談及當代時這樣寫道:
美姝世不一遇,而妒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為甚,閩則浦城為甚,蓋戶而習之矣。
在此處,這位福州才子從地域比較的視角來分析徽州的妒婦。他指出:當時漂亮女子不是很容易碰到,但喜歡吃醋、剽悍的女漢子卻隨處皆是,這主要是男人不爭氣的緣故。此種情形從地域上看,江南一帶以徽州最為嚴重,而福建則以閩北的浦城為其代表,幾乎每家每戶都是如此。
謝肇淛世居烏石山下,他從閩江北上出省,浦城為其必經之地,故對閩北的風俗應有所了解。至于新安(徽州),則是根據其人的所見所聞加以概括、提升。而這,讓人聯想到一篇在皖南廣為傳抄的《懼內供狀》。
伏為陰盛陽衰,巾幗之雄可畏;女強男弱,須眉之婦堪憐。秉坤而乃以乘乾,夫綱已墮;治內更兼乎治外,妻道何隆?風斯下矣!且世間多燕趙佳人,教且同焉,實宇內少昂藏之男子,慨往古而已然,嘆今人之更甚!
某本儒生,家傳閥閱,自信美如城北,豈期配在河東?號閫內之大將軍,自他有耀;怕老婆之都元帥,舍我其誰?……一言觸惱,分明太歲當頭;片語加嗔,儼似小魈破膽。……被罵總莫妙妝呆,動怒又何妨賠笑?……可駭者平時聲若洪鐘,到妻前不聞其響;可憐者縱爾勃然盛怒,入房中而忽改其容……更可悼者,立法尤嚴,設刑備至。大門閂使丈夫之驚魂墮地,小棒槌乃娘子之樸作教刑。馬桶蓋制就圓枷,儼似將軍之帽;裹腳布權為長鏈,竟同綿殮之尸。……欲討饒既慮鉆隙相窺,將高喊又恐隔墻有耳。無奈啞氣低聲,學吞淚(炭?)之豫滾(讓?);攢眉咬齒,等刺股之蘇秦……
它出自筆者在徽州民間收集到的一冊文書抄本。從中可見,這位自稱“怕老婆之都元帥”的一介書生,泣血稽顙,凄苦萬狀。文中字句惶惑駭怖,愁苦嗟嘆。其人平日雖然聲宏氣壯,但在悍妻面前卻似泥塑木偶不敢則聲。不過,他最后還是鄭重其事地聲明:“不敢書名,人各有妻,觀此莫笑,供狀是實。”言外之意,幾乎視全天下男子皆為懼內之同好,生得荒唐活著窩囊,大家彼此彼此,不必五十步而笑百步。類似于此的游戲文章,在徽州文書中尚不止這一篇。例如,徽州人還戲仿《滕王閣序》為文以贈懼內者,文中洋洋灑灑,同樣也是感嘆“雌強雄弱,威光射斗牛之墟;陰盛陽衰,夫主下床前之榻”。凡此種種,都說明徽州妒婦“比屋可封”的確源遠流長,懼內傳統在當地似乎已積淀而為一種民俗。對于此類的夫道不張,謝肇淛慨嘆道:
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不行于房闥,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于紅粉,俯首低眉,甘為之下,或含憤茹嘆,莫可誰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說—有的男人在外面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在家里卻很搞不定,這恐怕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啊!endprint
歷觀陳跡,遍窺時事,謝肇淛認為:“宋時妒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國朝則不勝書矣。”看來,對意識形態的重視時刻都放松不得,因為這首先關乎男人實實在在的幸福生活!接著,他又直呼王陽明、戚繼光、汪道昆三人之名,說他們都是著名的懼內之士。其中,一個是“內談性命,外樹勛猷”的知名官僚,一個是“南平北討,威震夷夏”的著名將領,另一個則是“錦心繡口,旗鼓中原”的文壇領袖,這三者在十六世紀算是最令世人艷羨的“成功人士”,不過,他們雖然在外面風光無限,外海內江莫大事功,但在家里卻沒有什么地位,竟被妻子修理得服服帖帖。
本來,寫到這里大概也就可以打住了。不過,謝肇淛博古通今,又是一位喜歡翻唇弄舌的大嘴巴。他到過徽州,與潘之恒等人過從甚密。而潘之恒恰是富家公子哥,畢生的著述便是“品勝、品艷、品藝、品劇”。所著《亙史》,將徽州當地的里巷瑣聞飛短流長編入小說(后來這也成為明清世情小說的素材而廣為傳播)。謝氏與他朝夕相處,在徽州逗留了一兩個月,對于“佳人有意村郎俏,才子無能美女狠”之類的傳聞似乎也特別感興趣。這位具有敏銳觀察力的有心人,在當地一定打聽到不少猛料,所以一時剎不住,接著又寫道:
汪伯玉先生夫人,繼娶也,蔣姓,性好潔,每先生入寢室,必親視其沐浴,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畢事即出。翌日,客至門,先生則以晞發辭,人咸知夜有內召矣。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嫗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見也。先生所以嚴事之,亦至矣。然少不當意,輒責令蒲伏,盛夏則置蚊蚋叢中,隆寒則露處以為常。先生每一聞夫人傳教,汗未嘗不灑淅也。先生有長子,稍不慧,婿于吳數載矣,一旦被酒,戲言欲娶妾。婦怒甚,伺其寐也,手刃其勢,逾月而死。先生令切責婦,幽之暗室,又數月乃自雉……
“少婦之見畏,惑床笫也”—在謝肇淛看來,老夫少妻朝歡暮樂最容易轉愛成畏。根據上述的說法—蔣氏夫人有潔癖,每次汪道昆前來高臥柔鄉之前,她都必須親自看其洗凈身子,讓侍候的老太婆用熱水從頭澆到腳;興云布雨之后,馬上就得離去。翌日,如果有朋友上門,汪道昆就以自己剛洗了頭發,需要曬干為由推辭(被發而干,即《離騷》所指的“晞發”),這樣,大家就心知肚明—老頑童昨夜又赴少妻處稱臣納貢撥雨撩云去也!平日里,蔣氏夫人對其管束極嚴,侍候的傭人,男子要超過四十歲,女的則要六十朝上。由于明代男風盛行,故而做女人必須嚴防死守—女小三自然無法容忍,但與此同時還必須防范男同志乘虛而入。謝肇淛描述說,汪道昆對太太非常小心謹慎,稍有拂逆,蔣夫人就讓他跪在那里,而且想盡辦法懲罰他—盛夏季節將其置身于蚊子很多的地方,寒冬時節則讓他裸身站在外頭,此種懲罰習以為常。所以他每次聽到夫人有什么吩咐,馬上就會直冒冷汗,相當緊張。
揆諸實際,汪道昆在文學史上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諸多史料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大致說來,汪氏生前享譽日隆,死后則非議蜂起,反差巨大。不過,無論如何,在十六世紀后半期,汪道昆與當時“后七子”之李攀龍、王世貞鼎足而三,成為其時的文壇領袖。因他官居兵部侍郎,以高官而得文名,聲名顯赫,故與同時的王世貞合稱為“兩司馬”。另就私人關系而言,汪道昆與介紹《五雜組》出版的李維禎關系莫逆,而接待謝肇淛的潘之恒等人,亦皆為汪氏之同鄉后輩和弟子。特別是在徽州,汪氏為當地的高門望族,汪道昆的門生故吏遍天下,族戚姻婭布徽州,社會關系可謂盤根錯節。汪道昆先后家居二十余年,在徽州文壇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就在謝肇淛前往徽州的三四年前,汪道昆還被宗人奉主入越國公祠,配享忠烈,稍后又奉祀為鄉賢。在當地人的心目中,汪道昆不僅為國家恃為棟梁,社會倚為砥柱,而且在私生活上,萬歷《歙志》的評價是“三配之外,絕無二色”,在男女關系上可謂一清二白。如此圣人般的人物,顯然容不得任何負面的八卦傳聞。
在此背景下,謝肇淛爆出的猛料,又焉能在徽人出版的著作中出現?雖然因史料不足征,我們無從確知謝肇淛交給李維禎的《五雜組》抄本之原貌如何,不過,“明刻別本”較徽州的如韋館本多出十六條,其他的十五條都分布在書的最后,只有有關汪氏父子二人皆懼內的八卦新聞位于卷八,似乎并非偶然的巧合。或許,萬歷四十四年謝肇淛交稿欲在徽州出版時即有所忌諱,那條八卦只是在后來的版本中才加以補充。或許,原稿中的確有這么一條,但被其他人所刪去。這當然只能是兩種推測,不過我想:即使當初有這么一條,也會被李維禎、潘膺祉等人毫不猶豫地刪去—這或許就是在徽州刊刻的如韋館本少了此一八卦的緣故。以往一些學者在研究《五雜組》時,雖然從校勘學上指出了如韋館本與“明刻別本”的區別,但卻未能解釋此種差異的原因所在。筆者以為,借由以上分析,或許可以找到部分的答案。
看來,盡管《新安雜詩十首》開篇即云:“人情吁可怪,客子慎風波”,不過,謝肇淛的此番徽州之行,還是不免在《五雜組》的魚尾黑口之間,泛起了一圈漣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