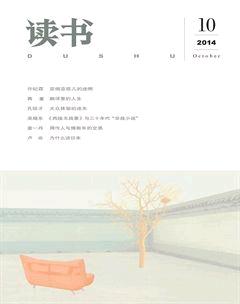也談齊如山與梅蘭芳
梁燕
《讀書》二零一三年第四期上有文《齊如山與梅蘭芳二三事》,作為關注齊如山近二十年的一個研究者,我想在此討論齊如山與梅蘭芳的關系等問題。
眾所周知,《齊如山回憶錄》和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是了解京劇史的兩部重要口述史資料,齊如山、梅蘭芳從各自的角度出發,敘述發生在他們人生過往中一些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無可厚非。即使談到同一件事情也會有不同的著眼點,敘述的輕重各異,詳略有殊。但是判斷《齊如山回憶錄》真實與否,僅以《舞臺生活四十年》作為衡量的標尺,顯然有失客觀公正。因為《舞臺生活四十年》在真實性上也不無瑕疵。比如說梅蘭芳“相公堂子”的出身在《舞臺生活四十年》里就沒有如實地記錄,而是經過了一定的“剪裁”,回避了曾經“典”“質”到朱小芬的“云和堂”做“歌郎”,后由京僚文博彥出“巨資”為其“脫籍”的事實。新中國成立后梅蘭芳已是聞名遐邇的人民藝術家,中國戲曲界的領軍人物,為尊者諱,發生在舊社會“堂子”之類的事兒也就不便再提。
《舞臺生活四十年》出版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那個時期的政治氣候對人的制約是可以想象的。齊如山在國共決戰時刻選擇去往臺灣,在大陸意味著什么,不言自明。梅蘭芳在書中多處用“集體創作”或列舉他人,既是一部分事實,也是一種迂回的辦法。
說起齊如山做導演、給梅蘭芳的新戲“按身段”的事情,有人質疑,筆者列舉民國時期三位戲劇界人物,他們當時的一些文字,或可厘清這個問題。一位是詩人、劇作家羅癭公,一位是理論家張厚載,一位是藝術家本人—梅蘭芳。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北平《晨報》"星期畫刊"第一二九號刊登劇作家羅癭公創作的一首《俳歌調齊如山》有云:
梅郎妙舞人爭羨,苦心指授無人見。……舞衣又藉齊郎授,共道前賢畏后生。
緊接羅癭公這首《俳歌》之后,《晨報》編者加了按語:“梅蘭芳之名,無人不知,而使梅之藉獲享盛名,實為高陽齊如山先生,則世能知之者鮮矣。梅所演諸名劇,劇本以及導演,胥由齊氏任之。癭公此詩,雖為游戲之作,真能發潛光也,不可不公諸世人。”
一九二八年七月戲曲理論家張厚載在“齊如山劇學叢書之一”的《中國劇之組織》序言中云:
劇界巨星梅畹華君,以《奔月》、《散花》等古裝歌舞劇震動國內外,一時男女名伶,竟起摩擬,成一時風尚……或謂諸劇身段穿插,均先生(齊如山)所手創。余初不信,先生亦未嘗為余言。其后余偶過綴玉軒,適梅君與諸伶排演《洛神》,先生指示動作,諸伶相從起舞,恰如影劇中之導演者,乃知先生于劇藝舞蹈,實負絕技。
一九三五年齊如山《國劇身段譜》問世,梅蘭芳在此書的前面作了一篇序文:
高陽齊如山先生,研求劇學已三十余年,梨園中老輩暨至后生無不熟稔,識力既高,又能虛心,逢人必問,故一切規矩知之極深,若紋之在掌。昔年與余談曰,中國劇之精華,全在乎表情、身段及各種動作之姿勢。歌舞合一,矩矱森嚴,此一點實超乎世界任何戲劇組織法之上。余深服其言。二十年間,余所表演之身段姿式,受先生匡正處亦復不少。近又將各種身段之原則,一一寫出,實為從來談劇著述中之創舉,我儕同業舊輩咸視為極重要之發明,深信國劇不至失傳,將惟此是賴。
梅蘭芳以他的人格魅力和藝術才華吸引了一批文人學者,特別是吸引了像齊如山這樣既有才干又很執著的人,成就自己走向藝術的巔峰,這說明了梅蘭芳的過人之處。梅蘭芳不平凡的一生中遇到了幾個對他產生重要影響的人,齊如山就是其中之一。齊、梅分手以后,二人的友誼依舊溫暖而澄澈。一九三三年齊如山為梅蘭芳創作了一出新戲《生死恨》,此劇后來被費穆導演看中,拍成了戲曲影片,《生死恨》也成了梅蘭芳后期一部重要的代表性劇目。一九三五年,梅蘭芳赴蘇聯訪問演出,為了宣傳之便,齊如山專門為梅蘭芳此行寫了一本書:《梅蘭芳藝術一斑》。一九四八年齊如山飛往臺灣,途中在上海轉機,還與梅蘭芳會面,梅夫人奉上兩套新衣褲,以解齊如山在倉促中的不便。齊如山到臺灣以后,每逢過年,梅蘭芳必去探望尚在北京、年事已高的齊夫人。
在齊、梅之間,關于誰幫了誰的問題,齊如山在回憶錄中說得很清楚:“我幫他的忙固然很多,他幫我的忙也不少。”“我所編的戲,好壞姑且不必談,但若非他演,恐怕不容易這樣紅,就是能夠紅,也不會這樣快,有幾出戲,已經風行全國,這當然是他的力量極大。”“他的名氣,固然我幫助的力量不小,但我的名乃是由他帶起來的。他的名氣到什么地方,我的名也就被彼處的人知道了。幾十年來,知道梅的人,往往就提到我,由這種地方看,豈非他幫助了我呢?”在梅蘭芳對自己產生的重要作用和影響的問題上,齊如山以上的分析也是客觀而懇切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