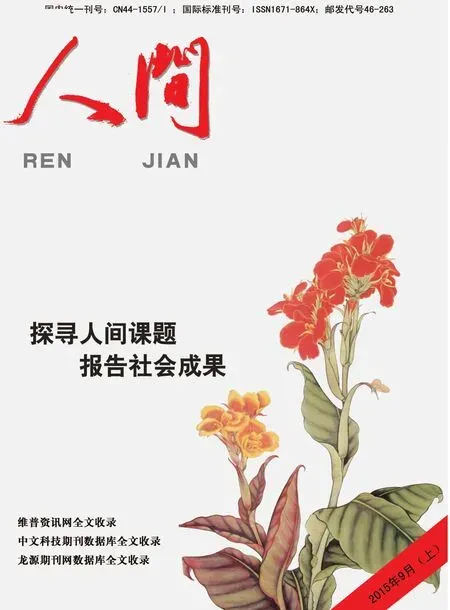重塑鄉土倫理
——淺談資本下鄉對鄉村倫理的影響
侯超
(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00715)
重塑鄉土倫理
——淺談資本下鄉對鄉村倫理的影響
侯超
(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00715)
在今日之中國,我國鄉村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生巨變,致使鄉村問題變得越來越紛繁復雜,國內學界如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學科也在鄉村與農民問題上展開了大量的研究,但倫理學界卻對中國鄉村社會并無太多直接的關注,在城鄉統籌建設開展得如火如荼的現在,這樣的一種缺失是不合理的。本文旨在從“新農村建設”與“城鄉統籌建設”中“資本下鄉”對鄉土倫理形成的影響作為切入點,來嘗試探索我國未來鄉土倫理變化之趨勢。
鄉土倫理;資本下鄉;城鄉統籌建設
偉大的無產階級導師馬克思曾有這樣一句話:“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①從鴉片戰爭打破我國鄉村的傳統經濟關系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鄉村經濟關系多次改變,鄉村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對整個鄉土倫理造成莫大的影響。
一、傳統鄉土倫理的崩壞
在中國傳統鄉村,農業生產占主導地位,農業的發展與土地是離不開的,以土地為中心的生產者必然被限制在土地之上,成為一種幾乎沒有人口流動的共同體,這便是我國傳統鄉村的“鄉土性”,但現在,圍繞土地生產不再是鄉村人口的唯一選項,鄉村勞動力開始大規模的遷徙,傳統的“鄉土性”已不復存在。從鄉村社會結構來說,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與快速工業化,鄉村大量的青壯勞動力進城務工,大量的鄉村共同體以老人、婦女、兒童為主,這樣一種人口構成,使鄉村社會這個共同體變得失衡與不完整,這樣一個不完整的共同體,其擁有的倫理道德也是不完善的。“差序格局”這一概念是指,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社會圈子按親疏遠近如水波紋一樣,一圈一圈蕩漾出去,越來越遠,但卻越來越薄。但在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三十年來的今日鄉村,隨著農民就業形式與收入來源渠道多元化導致的鄉村社會陌生化與疏離化,使得這種依托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會越來越難以支撐,外出到城市中工作的青壯年圍繞暫居地與務工單位形成了自己的社會圈子,鄉村的以血緣與地緣構成的社會共同體格局出現斷裂。“禮治秩序”的鄉村社會是什么樣呢?在這樣一個共同體里,禮是社會公認的合式的行為規范,禮和法律不同點在于維護其規范的力量。法律需要依靠國家機器來推行,而禮的規范力量來自鄉村共同體本身,費孝通先生概括了四種以“禮”為基礎的社會道德規范原則:橫暴力原則、同意權力原則、長老權力原則、時事權力原則。②但當鄉村社會已然不再是一個穩定封閉社會的情況下,共同體之外力量便得以對“禮治秩序”造成沖擊,法制性規范與契約性規范等多種規范交織一團,這樣一種原有的秩序逐漸崩潰,但新的秩序卻又還沒有建立起來,傳統鄉土倫理逐漸崩潰。
二、“資本下鄉”對重塑鄉土倫理的益處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③政策上的鼓勵與引導意味著高額的國家補貼、專業的國家技術指導和農業產業鏈的完善,可以預見的是,投資農業生產將變得炙手可熱,而大量外來資本的流入與產業化的經營模式,勢必會改變原有的以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為主鄉村經濟關系。
我認為我國大量的社會問題的產生,并不是因為城市化太慢,反而因其太快。城市化是每個國家走向強盛的必經之途,但這個過程中卻切忌一味的冒進,應當遵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適度原則,將速度降低到城市能夠消化的基礎上。“資本下鄉”的提出就很好的解決了這一點。城市資本在鄉村經營產業化農業,能夠有效的增加鄉村就業崗位,吸引一部分青壯勞動力留在鄉村,同樣也會吸引一部分城市富裕勞動力流向鄉村,形成城鄉人口雙向流動的結構,使得城鄉社會逐漸融合。對鄉村這個社會共同體而言,青壯勞動力的回歸使其不再是一個不完整的共同體,這個完整共同體能夠又回到那種“差序格局”的“熟人社會”狀態,“空巢”現象得以改善,避免了畸形的鄉土倫理的形成。再者,“資本下鄉”使得農民在一定規模上以土地、池塘、林地等生產資料入股變得可能,避免了鄉村居民資本缺乏的不足,改變了土地加勞動力等于收入的單一收入來源,形成一種圍繞生產要素所有權的新型的“鄉土性”。同樣,“資本下鄉”帶來的雇傭制度與生產要素合股等制度,使得法律與契約這兩種秩序能夠占據主要地位,進而改變鄉村多種秩序互相沖突的混亂局面。
這樣的改變同樣適用于改善新“愚”、“貧”、“弱”、“私”這四大問題。城市資本帶來的不僅是就業機會,也是學習機會,更加先進的生產方式與更有效率的管理模式,能夠改善鄉村原有的以家庭承包制為主體農業生產技術不高、效率低下等問題,利用市場競爭機制,又迫使鄉村原有農業生產不斷向其學習,這是一個“愚”變“智”的過程。同樣,城市資本資本的加入能夠做大農業這塊蛋糕,通過合理的分配方式,使“貧”變“富”。當然,在農業生產上,鄉村本土居民擁有的經驗優勢與城市資本擁有的理論優勢相結合,起到的絕不僅僅是一加一的效果,生產力以“弱”變“強”自然毫無疑問。在“資本下鄉”的過程中,鄉村集體所有的生產要素能夠在經濟上將整個鄉村共同體成員密切聯系起來,使個體能夠充分考慮到集體利益,增加了鄉村社會個體對集體的歸宿感,以“私”變“公”。
三、“資本下鄉”在重塑鄉土倫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鄉村社會生產關系的改變,自然會帶來如鄉土倫理這種觀念上層建筑的改變。但城市資本無論在資金、技術,還是市場資訊上的實力都不是鄉村本土農業生產所能企及的,在這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同樣可能引發鄉村社會一些與之相關聯的問題,在這一政策還未大規模實施的情況下,我們應當未雨綢繆,盡量考慮這些可能出現的問題,避免新鄉土倫理在重塑過程中再次走上歧途。
我國人口龐大,人均耕地較少,鑒于這種土地資源的稀缺性與國家糧食安全的必要性,應當限制城市資本大面積租種農戶承包耕地,避免在耕地經營權上的“土地兼并”,但更加現實的問題是,由于農業種植環節效益非常低,無論農戶還是企業,不規模化經營,便很難形成利潤,這邊關系到土地流轉的規模,應該在一個什么樣的范圍內才是“適度”的問題。再一個問題,企業化經營總會是有風險的,當種植規模化后,企業利益與農民利益捆綁在一起,如何解決風險問題,或者說,虧損責任應當如何分配的問題。再次,當農業產業這塊蛋糕做大后,企業與農民利益分配問題。最后,如何減少城市資本對傳統家庭承包經營農業利益的沖擊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優先級最高,因為其直接傷害到大部分農業人口的利益。
以上問題,如果不妥善處理好,那么城市資本不但不會給鄉村發展與城鄉統籌建設帶來好處,反而會加劇城鄉二元化,所有的道德問題的產生,歸根到底都是利益問題,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或不公平,將會造成城鄉之間、鄉村之間、單個鄉村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倫理道德上的沖突,孔子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④。只有建立起公平合理之分配制度,才能真正使鄉土倫理在重塑過程中走上正確的道路。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頁
②費孝通:《鄉土中國》,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年版,第54頁
③董峻:《中央一號文件鼓勵“資本下鄉”》,新華新聞網,2013年2月15日
④《論語·季氏》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2]晏陽初:《平民教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洛克斯(美):《城市化》,科學出版社,2009
[4]王露璐: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鄉土倫理研究及其方法,《哲學研究》,2007(12)
[5]張婷婷:市場理性與鄉土倫理:一項基于征地補償引發的家庭糾紛的社會學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學報》,2012(1)
C912.82
:A
:1671-864X(2015)07-0023-02
侯超(男)(1988.04.05-),四川省巴中市人;單位: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專業:倫理學;研究方向:管理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