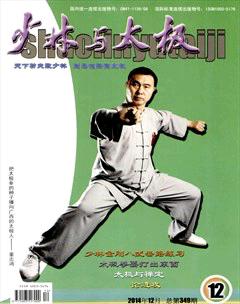淺議《水滸傳》中的“劫法場”
王建平
所謂劫法場,一般是指人們在法場上即官府執行死刑的地方用武力營救死刑犯的行為。它是一種公然以武力對抗官府的大膽行動,歷來為統治者所忌憚。在我國古代小說史上,有關“劫法場”的情節描寫并不多見。然而在元末明初的英雄傳奇小說《水滸傳》中卻有兩次“劫法場”的情節描寫,分別為第三十九回的“江州城劫法場”和第六十一回的“大名府劫法場”。作者用了兩回多的重要篇幅,先后對這兩次“劫法場”情節進行了生動細致的描寫。不但情節驚險生動、扣人心弦,有力突出了“劫法場”的梁山好漢李逵、石秀等人物形象勇猛無畏、重情重義的性格特征,反映了他們勇于反抗官府的斗爭精神,而且做到了同中有異、犯中求避,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藝術內涵,堪稱描寫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劫法場”情節的經典之作。正如清代小說評論家金圣嘆所說:“江州城劫法場一篇,奇絕了,后面卻又有大名府劫法場一篇,一發奇絕。”
一
筆者認為,《水滸傳》中之所以花費大量筆墨來描寫梁山好漢“劫法場”的情節,主要有兩方面的用意。其一是為了突出展現梁山好漢勇猛無畏、重情重義的性格特征,反映他們勇于反抗官府的斗爭精神。在第三十九回的“江州城劫法場”情節描寫中,作品重點描寫的人物形象是李逵。李逵在宋江、戴宗二人即將被官府斬殺的危急時刻,毅然獨自一人去劫法場,他“脫得赤條條的,兩只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手,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眾土兵急待把槍去溯時,那里攔當得住,眾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李逵為了搭救宋江、戴宗二人性命,完全不顧敵我力量極其懸殊的事實,不顧生死、不計后果地與官軍進行血腥廝殺,充分展現了他莽撞大膽、彪悍勇猛、忠義重情的性格特點。對此明代小說評論家李卓吾稱贊道:“真忠義,真好漢。”值得注意的是,李逵在劫法場時,只顧圖自己殺得痛快,不問官軍百姓一味追趕砍殺,連救宋江、戴宗脫離法場的主要目的都幾乎忘記了,則又暴露了他頭腦簡單、好戰嗜殺的一面。當然,在這一回中的情節描寫中,也寫到了以晃蓋、花榮、黃信等十七個頭領為代表的梁山好漢劫法場的情景。他們分別裝扮成弄蛇的乞丐、挑擔的腳夫、使槍棒賣藥的和推車的客商,巧妙地混入江州城中,從四面同時向官軍發動突然襲擊,終于成功地從法場上救出了宋江、戴宗。這充分地展現了他們機智勇猛、忠義團結的性格特點和勇于反抗官府的斗爭精神。
在第六十一回“大名府劫法場”的情節描寫中,主要描寫的人物形象是石秀。他在奉宋江命令去北京大名府打聽盧俊義消息時,意外得知盧俊義當天午時三刻將在市曹被斬殺的不幸消息。因來不及趕到梁山泊請來援軍,他決定獨自一人去劫法場以搭救盧俊義性命。在盧俊義即將被官軍斬殺的危急時刻,他首先故意虛張聲勢地大叫:“梁山泊好漢全伙在此!”以此蒙騙恐嚇官軍,然后趁著官軍因不知虛實而心慌意亂之際,突然“從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只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這突出表現了石秀精明機智、勇猛大膽、忠義重情的性格特點,李卓吾為此稱贊他“忠義包身,膽智雙絕。”
其二,用來串聯上下文相關情節。這兩回的“劫法場”情節描寫不但生動驚險、引人入勝,而且在作品中起到了承上啟下、串聯相關情節的重要作用。就承上而言,第三十九回“江州城劫法場”的情節描寫,是緊承第三十八回“得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中宋江、戴宗二人先后被江州知府蔡九抓入牢中的情節描寫而來。第六十一回“大名府劫法場”的情節描寫,則是緊承這一回前半部分中盧俊義因為遭管家李固陷害而被流放,途中燕青為救盧俊義而殺死公差,盧俊義被官軍抓住并被判處斬刑的情節描寫而來。這兩回的“劫法場”情節描寫可謂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就啟下而言,宋江、戴宗二人如果沒有這次梁山好漢集體劫法場的經歷,則自身性命早已不保,更沒有可能隨后上梁山泊聚義。同樣道理,如果盧俊義沒有這次石秀劫法場的經歷,也許早就人頭落地了。正因為石秀在法場上沒能救出盧俊義,自己也被官軍活捉,作品中才得以順勢展開后來第六十二回“宋江兵打大名城,關勝議取梁山泊”、第六十三回“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第六十四回“托塔天王夢中顯圣,浪里白條水上報冤”、第六十五回“時遷火燒翠云樓,吳用智取大名府”等一系列精彩生動的情節描寫。
二
《水滸傳》中雖然兩次描寫了“劫法場”情節,卻沒有出現雷同現象。作者巧妙地對其進行了藝術處理,使其各自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江州城劫法場”和“大名府劫法場”的背景與結果有所不同。前者是一場李逵的個人營救行動與其他梁山好漢的集體營救行動相結合的成功行動。早在第三十八回,吳用在突然發現自己偽造的蔡京給兒子蔡九知府的回信中因為誤用了諱字圖書而可能導致梁山好漢半路上營救宋江的計劃敗露之時,便已經緊急著手準備集體去江州劫法場了。從吳用預感宋江、戴宗二人可能被官府斬殺到梁山好漢動手劫法場,前后相距有六天時間,這使得他們得以事先為這次劫法場的重大行動做好精心充分的各種準備,因而最終取得了營救行動的勝利,成功地從法場上救出了宋江、戴宗二人。而后者只是石秀在突然得知盧俊義當天就將被官府斬殺的消息后匆忙之間被迫采取的個人營救行動,這是一次注定失敗卻令人贊嘆的悲壯行動。從他得知盧俊義將被殺的消息到其劫法場的時間不到一天,事情來得十分突然、時間顯得十分倉促,他根本來不及通知大批梁山好漢趕到大名府來協助自己,只得獨自一人勇闖法場救盧俊義性命。由于石秀只能單打獨斗、孤軍奮戰,他的這次劫法場行動最終因寡不敵眾而以失敗告終。他不但沒有救出盧俊義,自己也被官兵活捉了。
其二,在這兩次“劫法場”的情節描寫中,作者的描寫視角有所不同。在描寫“江州城劫法場”這一回的開頭部分,作者采用的是全知視角,用說書人的口吻來講述故事。而在描寫李逵和其他梁山好漢動手劫法場的關鍵性情節時,作者主要采用的是限知視角,如寫劫法場的李逵時,作品中起初并沒有直接交代他的姓名,只描寫他是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只手握兩把板斧。”寫劫法場的其他梁山好漢時,作品起初也沒有明確交代他們的姓名,只寫他們是“弄蛇的丐者”、“使槍棒賣藥的”、“挑擔的腳夫”和推車的客商。這其實都是從法場上與他們素不相識的圍觀者的視角來寫的,是一種陌生化的藝術處理,顯得富有懸念。而在描寫“大名府劫法場”情節時,作者主要采用的是全知視角,明確地指出劫法場的人是石秀。這兩回中之所以采用不同描寫視角,完全出于作品敘事的需要。因為“江州城劫法場”中李逵的外貌特征十分顯著突出,讀者從其外貌描寫就可準確推知其人。其他梁山好漢由于人數眾多,不便于一一具體交代,故在這回中主要采用限知視角。而在“大名府劫法場”一回中,由于僅有石秀一人劫法場,且石秀的外貌特征不太明顯,不便于采用限知視角,而以采用全知視角更為妥當一些。這兩種不同描寫視角是作者精心選擇的結果,可謂恰到好處,各臻奇妙。
其三,在這兩次“劫法場”的情節描寫中,作品描寫的文字繁簡程度和快慢節奏明顯不同。在“江州城劫法場”一回中,文字描寫十分豐富,節奏比較舒緩。作者“寫急事不肯少用筆”,“偏是急殺人事,偏要故意細細寫出”,不但生動細致地描寫了李逵和其他梁山好漢劫法場時與官軍激烈拼殺的場景,而且還分五個層次對他們當天劫法場之前的法場內外情況作了事無巨細的詳細描寫。在第一層中,主要寫牢外眾人為當天行刑作準備的情景。先寫江州知府蔡九早晨派人去十字路口打掃法場,飯后點起士兵和刀仗劊子五百人在大牢門前伺候,再寫巳牌時分獄官察請蔡九知府監斬,黃孔目呈犯由牌、判斬字,將犯由牌用蘆席貼起來。在第二層中,主要寫牢里眾人為即將押赴法場的宋江、戴宗作準備的情景,“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里把宋江、戴宗兩個編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發,給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絞子紙花。驅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吃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在第三層中,主要寫宋江、戴宗被押赴法場時的情景,“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后,推擁出牢門前來。宋江、戴宗兩個面面廝艦,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腳來跌,戴宗低了頭只嘆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千人。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團槍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兩個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在第四層中,主要寫法場上圍觀者眼中所見景象。先寫他們看宋江被押到法場上的情景,接著寫他們因未見監斬官到來而先去看犯由牌的情景,再寫他們看見監斬官到來時的情景。在第五層中,主要寫梁山好漢喬裝打扮后從四個方向混進法場并與官兵發生吵鬧時的情景。這些文字描寫顯得有條不紊、細膩生動,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
而在“大名府劫法場”一回中,文字描寫顯得十分簡潔,節奏比較緊湊。作者惜墨如金,雖然完整地描寫了石秀從正式動手劫法場到行動失敗、自己被抓的全過程,但寫得十分簡潔精煉,僅一百多字。在石秀正式動手劫法場之前的有關文字描寫中,也只寫了他到法場附近酒樓上喝酒吃肉,借機觀察法場周圍狀況,以等待時機解救盧俊義的情景。這些描寫文字也只有三百字左右,顯得十分簡明扼要。這一回的有關文字處理,可謂恰到好處,有效地避免了與“江州城劫法場”的文字描寫出現重復臃腫現象,做到了同中有異、犯中求避。
總之,《水滸傳》中“江州城劫法場”和“大名府劫法場”的情節描寫具有獨特審美價值和藝術內涵。它們做到了同中有異、犯中求避,可謂相得益彰、各臻其妙,充分體現了《水滸傳》作者精妙的藝術構思和深厚的文字功底,是這部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當今人們深入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