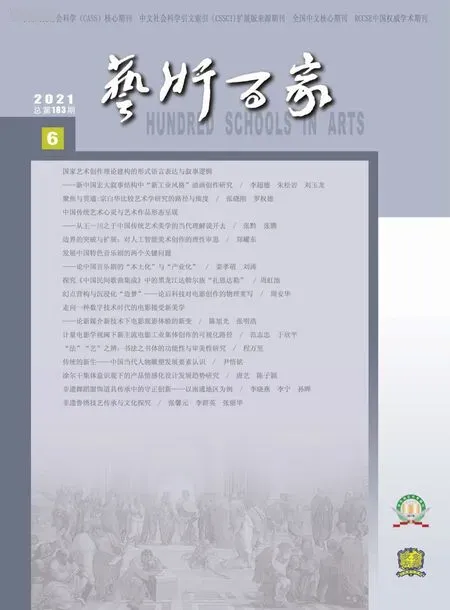一種文化的過剩模式
安燕+虞吉
摘 要:作為一種文化的過剩模式,良心主義成為指導中國早期電影創作的基本理念和原則。它是各公司生產經營的旗號,是電影刊物的辦刊宗旨,是導演創作的意識形態動機,是作品的根本思想訴求,也是中國電影主流敘事傳統的核心內構。文章從儒學良知論傳統開辟的德性倫理主義路線闡釋良心主義何以能夠成為中國早期電影創作的微觀權力政治,進一步觀察傳統與“五四”的深刻關系及“五四”自身的兩歧性。
關鍵詞:電影藝術;中國早期電影;藝術創作;良心主義;德性倫理;微觀權力政治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大學》八條目之“正心”是儒家心性文化傳統的根本,也是心性文化建構和變構而成的良心主義傳統的根本。良知的根本內涵即是“正心”而達于“至善”。在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上,良心主義不僅作為一種文化傳統而存在,也作為一種人格結構和文化心理結構乃至集體無意識左右著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循此,可將良心主義作如下理解:以儒家心性文化傳統的“良知”論為依據,以“正心”為價值內核,把人所具有的自然感情中那自明的向善道德心稱為良知,良知是人人內心都有的自明的、被視為天然合理的情感,也是道德的基礎,以之作為合理性基石可以證明道德規范以及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基于“良知”論在儒家文化中作為一種特定的學說體系或理論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及其強烈的價值傾向性,以及作為中國社會一種特有的道德心理結構和文化無意識,在知識學方法論上將其稱為良知主義或良心主義。在中國早期電影的歷史上,良心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的過剩模式,成為指導早期電影創作的基本理念和原則。良心主義不僅是各公司經營宗旨的表決,如聯華公司的宗旨是“提倡藝術,宣揚文化,啟發民智,挽救影業”,“提倡民族固有之美德,指示時代的正軌,以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①,“改良風化,箴砭社會,厥功甚偉”②。良心主義是電影刊物的辦刊宗旨,如《電影周刊》發刊辭:“二十世紀之電影事業,儼然成為一種勢力,足以改良社會習慣,增進人民智識,堪與教育并行,其功效至為顯著。”③良心主義是導演創作的意識形態動機,如鄭正秋說:“總之,取材在營業主義上加一點良心的主張,這是我們向來的老例,像藝術幼稚的時代,實在不敢太新啊。”④良心主義是作品集中表達的藝術思想,侯曜在描述《西廂記》中鶯鶯的內心沖突時說:“她又恍惚覺得她的良心從她的身上跑出來對她說,叫她去愛張生,叫她用愛情去醫治張生的病。她聽了良心的話,就決定了去酬簡。這兩段情節,是書上的《西廂》所無的。但是我為要表現原書中重要思想、精神的緣故,不得不表現在眼底的《西廂》里。”⑤良心主義是電影人對電影的基本藝術信念和信仰,鄭正秋談及有人批評他的影片教訓的氣味太濃厚,而他從不動搖良心主義的信念,“每一個片子里面,每插得進一分良心上的主張,就插一分,此種一貫的主張,還是始終不變。”⑥良心主義也是中國早期電影主流敘事傳統的核心內構,具“感人之情緒”,“且能表揚我國國民之良善特性”⑦的《孤兒救祖記》,“公映時候,卻出乎意外地為觀眾歡迎,輿論也一致擁護,并且因為它的賣座的特盛,竟奠定了此后中國電影的發展的基礎。”⑧良心主義對中國早期電影的全面介入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創作方法和藝術思想的來源,更是一種化為血肉的精神氣質和文化無意識,是一種中國人特有的面向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良心主義包孕著的文化慣習的強大力量在中國電影的歷史上從未中斷地延續到當下的創作中,以其溫和而堅韌的文化品格投射出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或文化無意識,也呈現出其自身生生不息的充滿歷史綿延力量的內在生命力。
一、德性倫理與良心主義
透視良知與至善、仁心、道德的不可分割的血緣關聯,完全可以說良知論傳統開辟的其實是一條以人的道德關注為核心的德性倫理主義路線,德性倫理的核心就是良知與道德。徐復觀認為,所謂的德性文化,指的是“中國文化所建立的道德性格,是‘內發的,‘自本自根而無待于外的道德”,這種道德靠的是內在的自覺而非“他力”,“是在每一人的自身發掘道德的根源,發掘每一人自身的神性,使人知道都可以外無所待的頂天立地底站起來”⑨。顯然,徐復觀對“德性”的理解走的仍然是傳統的內在超越之路。在西方文化中,德性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不獨指人的道德方面的品德,泛指使事物變好的所有特性和品德。無論是蘇格拉底的“知識就是美德”,柏拉圖的“善的理念”,還是亞里斯多德的“至善”觀,都可見出德性與理性不僅緊密相聯,而且德性來源于理性。蘇格拉底認為理性是知識與德性統一的橋梁,有德性的生活必然是理性的生活。柏拉圖說,一個道德的人,就是一個理性控制激情和欲望的人。亞里斯多德也認為,恰當的理性指導是養成善德的前提。西方傳統在表達德性時,指向的不僅是理性,也總是指向善。善是一切目的的規定性,是德性倫理的目標。麥金泰爾在其名著《德性之后》中指出,德性就是推動人們去實現積極的善,“一種德性就是人類一種后天獲得的性質,具有和運用它,會使我們能達到內在于實踐的那些善,而若缺少了它,則必定會阻礙我們達到任何這類善的東西”⑩。可見,在西方傳統中,善的行為即是德性的行為。與中國的德性先天具有不同,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哲人皆認為德性非天賦,要靠后天的訓練和培育才得以形成,較為注重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的典范,具有“以倫理組織社會”和“以道德代宗教”的泛文化功能,由此而有制度化的倫理儒學與超越性的德性儒學的不同層面。儒家自孔孟以來皆主張人是先驗的德性存在,仁心、仁性是自然而來天生具有的,“天生德于予”,人存在的價值就是實現道德的至善,德性之知即是良知呈現。而“仁”是超越個別具體德性的全體德性,是最高的道德規范和道德原則。從孔孟發展下來的整個儒學,都把至善作為最終的道德根源,朱子以天理代之,陽明以良知替之,從不同側面揭示了良知的豐富內涵。陽明明確指出:“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知乃德性之知,是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從本體的層面看,良知顯現為先天的理性原則;從德性的本原看,它構成了成圣的根據;從心物關系看,它是意義世界存在的根據。因此,本體的良知是先天的理性原則、德性的本原和意義世界存在的根據多方面的統一。陽明強調,就其為德性的本原說,它最初只是以潛能的形式存在,潛能只是為成圣提供可能,而并不是德性的現實形態。將善的潛能化為現實的德性,在邏輯上以良知的自覺為前提,在現實上則體現于“致”的過程中,在為善去惡的具體行為中實現:“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為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為;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于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于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此也。”B11良知本體決定了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惟有通過“致”之工夫,本原才能轉化為現實的德性,惟有將行善去惡落致實處,才能真正成為圣人。陽明師承陸象山,象山的“本心說”對人的內在德性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迷戀。他認為形上本體的心只有一個,通過日用常行表現出來。象山對本心形上形下合而為一的體悟對陽明體用不二的心學邏輯構架和“事上致良知”的著名思想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不管中西的德性觀如何不同,但都無可置疑地指向善,無論是西方較為寬泛的德性概念,還是中國較為專一的道德內涵,無論是先天還是后天,無論是超越還是事功,德性所蘊含的都是各種善端,都需要通過主體良知和主體的道德理性凸現出來,從而將道德理想和美德轉化為現實行為。然而,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則是,中國文化中的德性倫理因其內面的超越精神和道德理想主義的實質在中國的歷史上,在知識分子的人格結構和心靈結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以仁學為精神主旨、以道德理想主義為價值內核、以向善的追尋為動力結構的德性儒學作為一種替代宗教的精神超越資源,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巨大的象征性,和西方德性倫理的境遇是完全不一樣的,尤其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心靈結構,以及整個社會的烏托邦氛圍均產生了潛在而巨大的影響。即使在新文化運動全面顛覆孔教的倫理革命之時,也始終難以撼動蘊涵普泛人文價值的德性內核,面對儒學仁體禮用的倫理結構,激進反孔的啟蒙者,反對的也是倫理之禮,而非道德之仁,對儒家仁學的德性原則和人生理念反而多取認同態度。杜亞泉認為,道德之用可變而體不可變,舊道德之“仁愛”為古今中外一切道德的基礎,而具有普泛永恒的道德價值。B12吳宓、常乃德、蔡元培乃至新文化先鋒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皆莫不持此識見。思想史家張灝認為,雖然五四時期儒家德性倫理核心的“大學模式”遭受西學的侵蝕,但德性傳統中的道德理想主義對五四知識分子仍影響深遠。耐人尋味的是,這一影響竟從未斷裂,直到今天,它依然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現代生活,影響著現代中國人對事物的選擇和判斷,更深刻地影響著文藝創作的價值表達。
二、作為微觀權力政治的德性倫理
中國早期電影的誕生、初創與探索恰逢這樣的語境,許多人驚異于早期影像里為何殊難見到“先進”的新文化的影子,為何鄭正秋、朱石麟、卜萬倉這些受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電影人如此熱衷于家庭倫理、儒學德性、善善惡惡、現世報應之說?甚至侯曜這樣的在新文學的滋養中成長的新派知識分子為何在電影的表達上也總是難避陳舊和迂腐?更不必說天一公司定位于“舊道德”的整體創作。這種不由自主的選擇恐怕和杜亞泉們一樣,是對代表著普泛永恒的道德價值的德性倫理的認同和迷戀。鄭正秋的心態很能表達這種矛盾和糾結:“我做導演,往往喜歡在戲里面把感化人心的善意穿插進去的。……每一個片子里面,每插得進一分良心上的主張,就插一分,此種一貫的主張,還是始終不變。……電影應該有教育的意義的說法,已經大行而特行,我于是非常的痛快。不過我檢討自己過去的作品,對于有益世道人心的一點,卻還可以自信;不過,自己承認,言新不足,言舊有余而已。”B13在他因一味“教化”而遭人指責時,雖然面臨新文化、新思想的壓力,卻仍然“始終不變”,一來當然是因為他自己的個人趣味和對儒學道德之仁的熟悉與認同,他只能游走在德性的天空里展開創作,離開了這種空氣,他將無所適從;二來是考慮到當時觀眾的接受。他說:“我對于觀眾心理,比較的知道得多一點”,“我們以為照中國現在的時代,實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應當替大多數人打算,不能單為極少數的知識階級打算的。藝術應當提高,這句話我們也以為不錯,不過只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提高。”B14事實上,從鄭正秋對當時觀眾的估量以及當時觀眾對鄭正秋電影和崇尚“舊道德”的天一公司的影片的接受來看,雖經“五四風暴”的沖刷,中國下層社會仍是被儒家德性倫理主宰的社會,德性倫理是中國人最熟悉最親切的領域,道德之仁仍是整個中國社會共同的文化認同。因而崇尚良心主義的鄭正秋在談到中國電影的取材問題時,毫不含糊地主張按照中國的倫理習慣來行事:“因為中國男女有別,別得太厲害了,所以表演愛情的熱烈,就往往容易流入歐化。據我的意思,在這個中國影戲初創時期,與其多演不倫不類的愛情戲,不如換一個方向,多從男女之愛轉到親子之愛上邊去。……歐美的愛,是在一條水平線上的,是注重平輩得體的,可以說是橫的愛。中國的愛,是在一條直線上的,是從上而下的,有尊長在前,是不應當單講夫婦之親愛而丟掉長上的恩愛的,可以說是直的愛。”B15徐卓呆在評價《紅粉骷髏》時,也就中國電影的取材問題提出了“中國人情劇”的獨特見解,“制中國影片,選材料時宜掩護自己之短,竭力避去偵探劇……不如用‘人情劇做材料,把真善美三字來做吸引觀客的要素”B16,可見,一方面早期電影人對自身民族文化的魅力有著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們受德性儒學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即使后來因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而使中國電影走上“進步”、“革命”之路,在社會普遍價值發生轉化的宏大背景中,德性倫理不是退出而是推助良心主義世界觀向進步主義和政治理性主義世界觀轉向。因為德性倫理的核心是良知、向善、道德理想主義,而進步主義和政治理性主義皆是基于社會向善論的預設,當道德烏托邦完成向革命烏托邦的轉化,革命理所當然成為一種新道德,革命是有良知的中國人才會去從事的驚天偉業。事實上,中國早期電影的創作盡管紛紜蕪雜,其主導性的世界觀也各各不同,但德性倫理始終占據著一個重要的位置,它的彌散性、變構性和生成性使得早期電影的世界觀類型之間顯出對峙而又交合的結構張力。如墨子刻所言,儒家式道德理想主義傳統,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一再拒斥作為現代性基礎的經濟、政治、思想的多元主義,而親和烏托邦的深刻思想原因。乃至在“大公無私”、“克己奉公”、“犧牲小我”、“服從集體”的中國式共產主義道德中,也不難看出儒家德性傳統在中國深刻的連續性。因之,將德性倫理、良心主義理解為中國早期電影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一種微觀權力政治,實不為過。據福柯的研究,微觀權力政治并非通過國家機器和階級統治表現出來,它作為一種強力意志、指令性話語和普遍的感性力量,存在和作用于人類社會的一切領域,通過“真理的生產”塑造和宰制我們。在中國早期電影的歷史上,德性倫理恰如福柯所說的“真理的政治”,彌散于無處不在的關系網絡,它不僅是隱匿的,通常以文化無意識的方式表現出來,也是具有生產性的,一旦它與某一種具體的時代訴求結合,那種新生的世界觀不需佐證即能獲得正當性與合法性。
三、中國早期電影中的德性倫理與良心主義
德性倫理作為一種微觀權力政治,以其深刻的文化滲透力作用在中國早期電影的身上,聚焦為良心主義表現出來,無論是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編劇、導演的創作意圖,作品的思想旨歸,還是電影評論的價值標準,刊物的辦刊宗旨,皆體現出良心主義巨大的輻射性和彌散性。良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通過從善之心、同情之心、懺悔、主觀操持、人道主義等實現社會、人性的改良。對封建制度、社會現實的態度是改良而非激烈否定。張石川之妻何秀君在談到石川與鄭正秋的不同時說:“當時鄭正秋有改良主義思想,相信教育萬能,認為一切社會問題都可由勸善、教化、激發良心得到圓滿解決。所以,他寫的劇本都是先提出社會問題——主要是婦女問題,末了卻用妥協、調和的辦法,如辦教育、開工廠……解決,來個大團圓的結局。”B17鄭正秋自己也在很多場合多次談及“良心”,“大凡一種出品總要有一點意義,不問名字深淺,不問故事是悲是喜,第一重要的不要違背了良心上的主張,這是我向來的志愿。”B18“在這生死關頭,千萬千萬,替中國影戲多多的留一點余地,我們揭開窗子說亮話,我們也是將本求利,我們不要說為國為社會等等的好聽話,但是我們認為在貿易當中,可以憑著良心上的主張,加一點改良社會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豈不更好,可以挽回些外溢的金錢,豈不更好,可以發揚中國藝術,使它在世界上有個位置,豈不更好。”B19“總之,取材在營業主義上加一點良心的主張,這是我們向來的老例,像藝術幼稚的時代,實在不敢太新啊!”B20與鄭正秋同時代的的許多電影人皆發出過這種良心主義的感喟或呼喊,神州影片公司的創辦人汪煦昌不滿于當時中國電影界的粗制濫造之風,他說:“一片之出,其影響于社會人心者殊巨。蓋以其能于陶情怡性之中,收潛移默化之效。影片而良,人心隨之而趨上;影片而窳,世風因之而日下。”B21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周瘦鵑也較為理性地認識到,“影戲更因為是與我們的生活最密切的,有時他的功效還比教育來得大。在智識方面,為善方面,固然如此;在道德方面,尤其是為惡方面,更是如此。所以近代的影戲事業,并不是一種商業,乃是一種文化事業。……影戲對于一般人的影響,道德方面較之智識方面似乎更多。……從前只是迎合一般人的好尚,而現在卻要能提高一般人的好尚。所以此后的表演應當在正面,善的方面盡量發揮,在反面,惡的方面的表演愈少采用愈好。”B22更有甚者,痛心疾首大聲疾呼:“我久積不發的良心底吶喊聲,有大聲喊出的一日了!今后我要大聲吶喊,不時地吶喊,為影戲的前途吶喊!……我不顧一切,只知憑著我良心底命令來吶喊!……黑幕派……非但不能引導群眾,走向真善美的路去,反使無知者墮入淫邪的魔道!”B23經由德性倫理包裝的良心主義何以能夠如此正義凜然、堅不可摧?顯然,這是由孔孟開創至陸王而至王門后學所守持的一條以道德關注為核心的德性倫理主義在中國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所決定的。“良心”和“德性”成了中國社會最根本的大眾意識形態,成了社會得以穩固、運行、發展的合理性基石,成了左右人們對人與事進行判斷的基本價值標準和常識理性,也成了中國社會如空氣般無處不在的微觀權力政治。各影片公司的經營宗旨也相當集中地體現了良心主義的思想。聯華“本公司之宗旨及工作”規定“提倡民族固有之美德,指示時代的正軌,以抵抗外片之文化侵略”B24。民新影片公司“宗旨務求其純正,出品務求其優美,非敢與諸同業競一日之長短,欲勉為人類社會負慰安之使命而已。更有進者,中國固有其超邁之思想,純潔之道德,敦厚之風俗,以完成其數千年歷史上榮譽,茍能介紹之于歐美,則世界必刮目以相看。”B25明星公司則要求:“影片的題材,以發揚民族精神為中心思想,以倫理、教育、文藝等為影片之重要情節。”B26商務印書館鄭重宣稱其創作主旨,“沈信卿先生在本志第一號上面說:‘吾人應當辨別影片的內容,是否可以引起國民的良善性,是否可以矯正一般的壞風俗;果然能夠,我們便當借影戲為教育的一大助手了。敝館對于影戲價值的認識,正和沈先生一樣;而敝館制造活動影戲的主旨,也就在這一點。”B27天一公司更是毫不避諱因襲舊思想之嫌,公然提出“注重舊道德,舊倫理,發揚中華文明,力避歐化”。B28無論是提倡“民族固有之美德”,表現“中國純潔的道德”,發揚“民族精神”,“引起國民的良善性”,還是回到舊的倫理道德以抗衡西方,表現出了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電影人對儒家德性文化的高度認同和信任。這些電影人的態度再一次說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并非是一場全面否定傳統的運動,在這場激烈的反傳統運動中,需要更加審慎地來辨別傳統的不用層面,哪些確然遭到了否定,哪些卻又獲得了保留?否則,20世紀20年代剛剛經受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中國電影界何以表露出對傳統如此整一性的親近態度,實在難以解釋。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對德性倫理和良心主義的訴求一方面體現了影片在題材選擇和思想主旨上的單一,另一方面又強烈地印證了儒學德性傳統強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廣泛的文化滲透力。商務影戲部從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底一年半的時間里,由陳春生編劇、任彭年導演了《孝婦羮》《荒山得金》《蓮花落》三部長故事片,皆以傳統小說和地方戲曲為藍本,宗旨雖在教育,但在材料和內容的選擇、鋪排上顯現出濃重的倫理教化傾向,傳統道德文化的印跡相當濃厚。《孝婦羮》被“商務”宣傳為“描摹孝媳惡婆循環果報”,“實為中國家庭中警世、勸善勸孝、感化人心之第一影片”B29;《荒山得金》通過宋金郎和劉有泉善惡、義利的對比,突出勸人向善的主題;《蓮花落》講述了一個諷世勸善、浪子回頭的故事,著重電影的教化目的,制作也較嚴肅,因此評論認為“非誨盜誨淫者可比。”B30然而,有評者認為,該三部影片雖然符合當時普通市民觀眾的欣賞口味,但在傳統思想意識上卻缺乏選擇、創新,“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這三部影片所宣揚的教化人們的具體主題內容,如《孝婦羮》的‘教孝教慈,《荒山得金》的‘循環果報,《蓮花落》的‘諷世勸善,其實際的社會價值和意義都游離時代潮流而顯得陳舊了些。不能不說這是‘商務的‘為教育而電影在觀念和實踐上的一個致命弱點”B31。在五四轟轟烈烈的新道德、新文化運動過后,“商務”何以如此“不合時宜”,向“舊”而不迎“新”?是中國電影故事的講述與生俱來與傳統保有某種親近性?是教育、警世、勸善、世道人心的表達一定要在傳統道德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訴求?還是傳統舊道德經歷“五四”風潮依然保持堅硬的文化質地和旺盛的生命力?還是其德性倫理作為一種微觀權力政治和文化無意識早已深入人心,難以撼動?即使1926年掀起的古裝武俠神怪風潮出于投機牟利的目的,粗制濫造,但其所選擇的題材也少有不是關乎傳統舊道德的。各大公司競相投拍的影片要么取材于民間故事、傳說、神話,要么取材于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其思想主題不外“忠孝節義”、“善惡果報”。《中國電影發展史》對這些影片的批評是極其嚴厲的,指責它們充滿“封建毒素”、“惡俗不堪”,即使有制作較為可取的作品,如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美人計》,“雖然在藝術處理上比較嚴肅,較之同時期同類型的影片來,藝術質量也較高,但其思想主旨仍在于通過諸葛亮、孫權、孫夫人和趙云來宣傳所謂的‘忠‘孝‘節‘義的封建道德觀念”B32。本來是批評,卻從相反的方面印證了傳統舊道德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商業電影在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影響。以舊道德舊倫理為其拍片宗旨的天一公司更是直接將影片命名為《立地成佛》《忠孝節義》,宣揚人心感化、盡悔前非、忠孝節義、善有善報,并將之視為“集中國數千年來遺傳之美德”B33。于鄭正秋、包天笑等舊式文人而言,德性倫理既是他們的精神信仰,也是他們所深信不疑的市民社會價值合理性的源泉。《良心復活》的改編最能說明鄭正秋、包天笑對傳統德性文化和良心主義的體認。鄭正秋授意包天笑將托爾斯泰充滿基督教寬恕精神的《復活》直接改編成《良心復活》,以大團圓的結局突出了道德良知的意義,“從而使人們在良知被實現的結局中得到充滿倫理意義的撫慰。因此,《良心復活》完成的是宗教精神向道德訓誡的轉化”B34。時人評論《最后之良心》說:“它底價值能夠挽回社會的頹風,改良人類的心理,真是一劑很貴重的藥品啊!”B35“完滿的結束,在中國人的心理中大半贊成這種,這也是國民性的傾向”,因為中國人的理想便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和“有情人終成眷屬”B36。《孤兒救祖記》則“以母子之愛動人,其術甚智,且能表揚我國國民之良善特性”B37。《上海一婦人》更多呈現的是主人公愛寶的善良行為,表達妓女“不沒其本性之善”B38的意圖。《玉梨魂》“至于穿插本身的有無價值,只以有無良善主義而定。此片中的穿插,多有良善的寓意,如私塾媒婆之宜廢,學校之效力,誤解自由的笑柄等等,已經多數承認。”B39“江蘇省教育會電影審閱委員會”對各影片的審定評語更是體現以德性倫理和良心主義為基準的道德訴求B40:商務印書館出品的《好兄弟》“此片以父子兄弟之天性裁制男女之愛情,足以發揮東方倫理之精神。”大亞公司的《疑云》“此片柏玉霜女士以極純潔之思想行為……足以喚起一般人高尚潔白之思想,藝術亦精。”民新公司《玉潔冰清》“此片志趣純潔,描寫黃伯堅處勢利社會中獨能抱富貴不淫之精神,歷盡艱苦以與環境相抗,錢孟琪雖出豪家獨能不染塵垢,處處為伯堅謀為老父計,用心良苦,于二房東之厄于經濟時又能以恕道待人,尤足風勵末俗,藝術方面亦多可取。”明星公司的《好哥哥》“此片結構甚奇,末尾以慈善之思想成化莠之良之結果,大堪風世。”《馮大少爺》“此片為有財產而不能教育子弟者當頭棒喝,事雖平淡無奇,警世之意實深,藝術亦佳。”《盲孤女》“此片情節頗有曲折表演,品格高尚者之終有佳遇,于世教不無裨益。”《空谷蘭》“寫柔云之狡惡益足襯紉珠人格之高,前后結構完密,自然能引起觀眾善善惡惡之意。”大中華百合公司的《殖邊外史》“造意正大,足裨教化。……確合藝術家真善美之三要素。”天一公司的《忠孝節義》“此片事跡雖簡單而結構頗曲折,可增進社會道德法律觀念。”商務印書館《孝婦羮》“此片取材于《聊齋》,描寫舊家庭姑媳不安之狀態,實寓有教孝教慈之深意。”國光公司《母之心》“此片注重倫理方面,描寫母子之愛無微不至,藝術亦可觀。”上海公司《還金記》“此片意在懲惡,寫男女愛情頗純正,情節亦曲折奇險,攝影尤佳。”提倡“潛移默化”,頗有點“為藝術而藝術”的神州影片公司,從《不堪回首》《花好月圓》到《道義之交》《難為了妹妹》《可憐天下父母心》等,雖然貫注著“神州”以“情感”見長以“美”為依托的創作思想,但其主旨依然是“以倫理為軸心,勸人向善,提倡人要有同情心,有人道主義關懷”B41,根本上不離傳統的德性倫理。崇尚畫面古雅、唯美的但杜宇在《海誓》中講述了一個受虛榮誘惑的女子,后因“天良發現”而與窮畫師“終成佳偶”的故事。《古井重波記》雖然塑造了一個敢于為了愛情和情人私奔生子最后又能手刃仇人的不同于傳統寡婦的女性形象,但整個故事的講述旨在揭示青年寡婦最終何以能夠甘愿選擇“安貧受志以終”,從激烈抗爭到認同舊道德,由此肯定了后者的強大力量。自稱不信奉“任何主義”的歐陽予倩,雖然也在《天涯歌女》中揭露社會不平,鼓勵女性抗爭,但骨子里還是和鄭正秋一樣,不脫傳統倫理道德之念。因此《玉潔冰清》才會一再表現孟琪之善,并不可思議地讓壞人錢維德最終因幼子之死大徹大悟,棄惡從善。《三年之后》更是表現了浪子回頭,夫婦和好。候曜電影中的懺悔思想最終體現的也不過是倫理的覺悟、道德的覺醒。即使因“國片復興運動”而成績卓著的聯華影業公司,其所拍攝的12部影片也仍是以傳統倫理道德為題旨,要么反對、抗爭,要么提倡、贊美,顯示了較復雜的創作格局。其中,最受觀眾歡迎的是《戀愛與義務》和《桃花泣血記》。朱石麟編劇、卜萬倉導演的《戀愛與義務》中有嚴厲守舊的父母、守孝的女兒、良知激發的丈夫、“羞祖宗”“辱門楣”“不能見容于家庭”的情人以及最后令人欣慰的結局,整個影片的氛圍、人物設置、劇情、命運的逆轉,皆充滿了傳統德性倫理的威懾力。《桃花泣血記》《銀漢雙星》則通過自由戀愛和婚姻的失敗,印證了傳統倫理的強大。《恒娘》《義雁情鴛》表現了高尚的傳統道德,前者旨在讓隱忍、寬容的女性道德促成丈夫“良知”的“覺悟”;后者則贊揚了自我犧牲、克己復禮、兄友弟恭的家庭倫常。《愛欲之爭》《心痛》旨在勸善和宣揚寬恕、同情之心。《故都春夢》中的主人公朱家杰落魄歸鄉,向其妻長跪請罪,最能表現聯華“國片復興運動”以倫理的覺悟、道德的覺醒、良知的復得來“宣揚文化、啟發民智”的制片口號。鄭君里在《現代中國電影史略》中指出,中國“愛情片”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雖然也提出自由戀愛,反對封建包辦婚姻,“但它只允許在倫理的德性以內發生,即自由戀愛以對舊有的家庭關系妥協為前提。因此,我們雖然說過‘愛情片胚胎于‘五四思潮,但它卻沒有達到其先驅者所鼓吹的徹底的精神。……《人心》寫少年的自由結合為其父所否認,出謀自立,終因解救工人包圍父廠之厄而獲和解;《好兄弟》寫兄弟二人在三角戀愛中成為仇敵,終因手足情深,由兄讓步與別女結合;《采茶女》寫少年愛采茶女,父擬代擇配富家,后知茶女亦出身望族,乃成眷屬,都標榜自由戀愛,但都以為此種戀愛只有先與倫理的德性協調才能夠成立;《松柏緣》寫一對未婚夫妻因戰事分離,各秉忠貞的操節重獲團圓,這也是把以‘松柏為象征之從一而終的精神,貫入這新的戀愛關系的范疇里。”B42具有現代精神的自由戀愛,要么以向舊的家庭倫理妥協而獲得善終,要么以保全完善自足的傳統道德品性而獲得成全,這一方面見出新文化對讀書人的影響遠未深及根性,致使他們在價值觀和世界觀的選擇上難免保守;另一方面也見出傳統德性倫理根深蒂固的強大力量。有意思的是,在這一類返身回到傳統,對傳統德性倫理表現出無限文化鄉愁的影片中,往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女性尤其是身為人母的女性塑造成德性倫理的典范,《孤兒救祖記》《良心復活》中含辛茹苦撫養兒子成人的母親,《玉梨魂》中的梨娘,《空谷蘭》中的紉珠,《苦兒弱女》中的呂母,《母與子》中充滿母子情深的母親,《慈母曲》中養育兒女歷經千辛萬苦的老母,乃至《戀愛與義務》中獨自撫養孩子長大成人,卻不愿自己“不光彩”的身世連累女兒幸福而投河自殺的楊乃凡,都是典型的善良、隱忍、甘愿自我犧牲、歷經苦難的中國傳統女性形象。這一典型的女性形象以其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和藝術拓展力綿延在整個20世紀中國電影的歷史上,歷久不衰,生生不息。
四、結語
令人深思的是,傳統德性倫理和良心主義在中國早期電影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的歷史上如此濃彩重墨,包括后來走上“進步”之路的孫瑜、史東山等在內的每一位重要的創作者似乎都不能“幸免于難”,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現代性”似乎很難在這些作品里找到影蹤,五四運動激烈的反傳統之風似乎更難在這些作品里找到時代的呼應,何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儒學德性倫理和良知論傳統所具有的超越性品格和普世的道德理想,經“孔孟”、“程朱”、“陸王”尤其到王門后學的平民化運動,早已從士大夫階層深及民間和市民社會,作為一種文化自覺或文化無意識,深入到中國人的血液和靈魂中。事實上,自維新時期始,近現代中國人就已經開始探索倫理與道德的分殊,以此肯定道德的永恒價值。梁啟超在闡釋儒學改革的主張時,就認為倫理與道德不同,倫理因時勢變遷,道德則具有普泛和永恒的價值。如要君和多妻之倫理固不宜于現代社會,但忠之德和愛之德則通古今中西而為一。故中國傳統有缺弊而宜改革的,是其倫理而非其道德B43。維新思想家對儒家仁學的德性價值是極其肯定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時,對儒學也并非是不加區別對待的。蔡元培以儒家的“義”、“恕”、“仁”比附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B44。李大釗倡言立憲國民之修養,“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愛、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恃,以克己之精神,養守法循禮之習慣,而成立憲國紳士之風度,于是出而為國服務。”B45胡適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比之于基督教的“金律”和康德的“絕對律令”B46。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后期甚至對三綱倫理“忠孝節”的批評亦不無保留,主張對其進行倫理和德性的區分,“道義的本源,自然也出于情感,……但是一經落到倫理的軌范,便是偏于知識理性的沖動,不是自然的純情感的沖動。同一忠孝節的行為,也有倫理的情感的兩種區別。情感的忠孝節,都是內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純的;倫理的忠孝節,有時是外鑠的、不自然的、虛偽的。”B47此外,陳獨秀還力倡傳統美德“勤儉廉潔誠信”為中國之救國之道B48。他同時承認孔子德性原則具有普遍性道德價值,這些普遍的德性原則是人類道德的共相B49。顯然,“五四”知識分子普遍承認儒學德性原則的普世價值,尤其認可儒家的忠恕之道,而“忠恕”在孔子仁學中居于核心地位。由此,“五四”倫理革命就呈現出一幅充滿內在緊張的思想圖景:“在社會公共領域,作為啟蒙者的新文化人,倡言個人本位的、以‘利(權利、功利)為基礎的現代市民倫理;在個體精神領域,作為知識精英的新文化人,信奉的則是人倫本位的、以‘仁為基礎的傳統君子道德。這種立基于欲望的市民倫理與植根于德性的君子理想的價值張力,表征著五四啟蒙時期中西人文傳統的激蕩和沖突。”B50事實上,“五四”的反傳統完全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有著豐富矛盾的多元面向,在其中西文化沖突的內面,“欲望”與“德性”之爭也永難停歇。溝口雄三在論東西文化時指出:“圍繞人類的本性是貪求還是追求道德這兩個普遍性的命題,存在著永遠難解的意識形態上的對立。”B51欲望與德性之爭,利害與良知之爭,既是中國早期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電影的兩種意識形態,也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世界觀——良心主義與娛樂主義。不過,無論是選擇哪一種電影世界觀,“真善美”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論偏重藝術的、營業的、教育的,而真善美之三要素,不可不三復及之”B52。“真善美”正是構成德性倫理和良心主義的主要要素。由此可見,良心主義的電影世界觀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的創作產生的不僅是彌散性的影響,起到的也是決定性的作用,并對后來30、40年代電影世界觀類型的變構和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正體現了其作為微觀權力政治的強大生命力。然而,欲望與德性之爭,利害與良知之爭在一種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未形成之前,依然是相當激烈的。明星公司內部鄭正秋與張石川在電影創作觀念上的根本分歧便反映了良心主義與娛樂主義這兩種電影世界觀的爭奪。更為復雜的是,即使在個人的世界觀內部,也存在著不同態度的交合與沖突,最典型的如鄭正秋“營業主義加上一點良心”的主張,以及他在諸多場合從良心主義出發為營業主義所做的辯護,恰恰很能說明一個信奉“良知”的舊式文人在一個思想觀念紛亂的時代內心的困境,說明個人內心的德性與欲望之爭。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張石川、鄭正秋他們的“欲望”和“利害”來說,思想的源頭肯定不僅僅是基于個人本位的西學及其基于欲望的市民倫理,而更與中國傳統的“義利觀”、經濟倫理及其思想史變遷血肉相連。(下轉第46頁)(責任編輯:陳娟娟)
① 《聯華影片公司四年經歷史》,《中國電影年鑒》,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出版,1934年版。
② 黃漪磋《創辦聯華影業制片印刷有限公司緣起》,《影戲雜志》,1930年第1卷第9期。
③ 《電影周刊》發刊詞,《電影周刊》,1921年第1號。
④ 鄭正秋《中國影戲的取材問題》,明星公司特刊第2期《小朋友》號,1925年版。
⑤ 候曜《眼底的〈西廂〉》,民新公司特刊第7期《西廂記》,1927年版。
⑥ 鄭正秋《自我導演以來》,《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
⑦ 肯夫《觀〈孤兒救祖記〉后之討論》,《申報》,1923年12月19日。
⑧ 張石川《自我導演以來》,《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3、4、5、6期。
⑨ 徐復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民主評論》,1954年第5卷第8期。
⑩ 高國希《麥金泰爾對當代西方道德哲學的批判》,《倫理學(人大復印資料)》,1994年第4期。
B11 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頁。
B12 杜亞泉《國民今后之道德》,《東方雜志》,1913版10卷第5號。
B13 同④。
B14 同④。
B15 同④。
B16 徐卓呆《藝術上的紅粉骷髏》,《申報》,1922年6月14日。
B17 何秀君口述《張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中國無聲電影》,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2頁。
B18 鄭正秋《〈難為了妹妹〉是大好悲劇》,神州公司特刊《上海之夜》,1926年第4期。
B19 鄭正秋《請為中國影戲留余地》,明星公司特刊第1期《最后之良心》,1925年版。
B20 同④。
B21 汪煦昌《論中國電影事業之危狀》,神州公司特刊第2期《道義之交》號,1926年版。
B22 周瘦鵑《說倫理影片》,大中華百合公司特刊《兒孫福》,1926年版。
B23 辛漢文《為影戲的前途吶喊》,長城公司特刊《一串珍珠》,1926年版。
B24 同①,第73頁。
B25 予倩《民新影片公司宣言》,民新公司特刊第1期《玉潔冰清》號,1926年版。
B26 《明星影片公司十二年經歷史和今后努力擴展的新計劃》,《中國電影年鑒》,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出版,1934年版。
B27 《商務印書館的影戲事業》,《電影雜志》,1924年第3期,第19頁。
B28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83頁。
B29 閘北影院映演《孝婦羮》廣告,《申報》,1923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