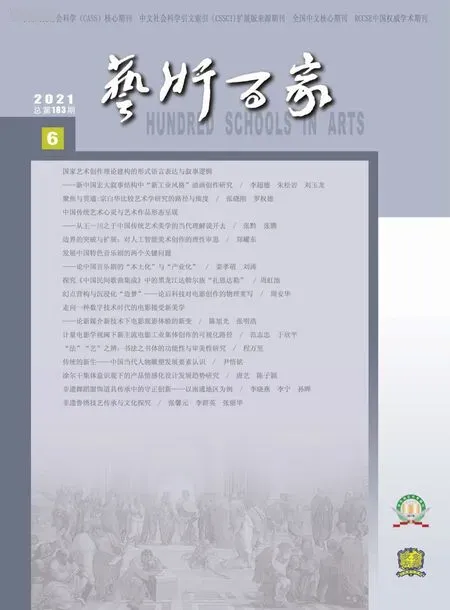論“價值無涉”思想影響下的烏爾姆設計觀
王敏
摘 要:“價值無涉”思想對烏爾姆設計學院的設計觀有重要影響,并體現在該學院的專業設置、規章制度甚至理論研究等諸多方面。文章從烏爾姆設計學院的設計主張、專業設置及影響等方面入手,分析了這種思想在烏爾姆設計學院出現的背景及表現方式。揭示了烏爾姆設計學院在注重產品的社會倫理、簡潔功能和實用性的表象下,謀求推動社會公共事業發展的一種政治愿景。烏爾姆設計學院強調設計知識的客觀性,抵制商業化、風格化和奢靡之風,在設計中以邏輯判斷取代價值判斷。最后指出“價值無涉”既作為該校奉行的一種設計觀的思想基礎,也是一種態度和信仰。
關鍵詞:設計藝術;設計思想;烏爾姆設計學院;價值無涉;馬爾姆;設計觀
中圖分類號:J50 文獻標識碼:A
“價值無涉”(value free)也被譯為“價值中立”。德國著名政治經濟與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進一步在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等人的基礎上,將此概念拓展為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核心內容。對于烏爾姆設計學院(HFG Ulm,以下簡稱“烏爾姆”)的設計觀而言,“價值無涉”意味著技術中立而不是價值判斷。如果說韋伯闡述的“價值無涉”為的是將(社會)科學從神學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烏爾姆所奉行的“價值無涉”則為的是將設計從手工藝設計傳統和屈從于商業利益的產業模式下解放出來,面向新的設計領域(公共交通等設施),服務于整個社會而不是私人或某個(特權)階層。因而,烏爾姆一方面潛心探索新的設計領域和科學設計方法,并在教學和設計實踐中予以檢驗;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要通過參與創建新的工業文化來實現自身的社會主張和價值。從文獻來看,這所學院是想“作為一種文化的促進劑。”[1](P.118)在1953至1968年短暫辦學時期,烏爾姆不僅在培養方法上形成了獨有的“烏爾姆模式”,也重新詮釋了“優良設計”概念。這時期,“價值無涉”在烏爾姆體現于專業設置、規章制度甚至是理論研究(科學設計方法)等諸多方面。值得關注的是,現有研究存在著對烏爾姆設計觀的誤讀甚至曲解的現象。如把烏爾姆設計簡單地歸為一種純粹的理性主義,并與“方法崇拜”和“技術至上”等極端傾向混為一談。此外,還將烏爾姆設計直接歸為是包豪斯設計的延續:“以為烏爾姆的理論框架,全然地取自于我們坐在室內討論的包豪斯。”[1](P.222)從早期馬克斯·比爾關于“從湯勺到城市”的普適性設計,到倡導科學設計方法論的階段,烏爾姆均堅持設計“去商業化”和排斥為私人服務的理念。研究“價值無涉”之于烏爾姆設計觀影響,一方面能夠全面客觀地認識烏爾姆的理想及社會主張;另一方面促進國內對德國現代設計歷史與理論的深入研究。正因如此,本文以“價值無涉”思想影響下的烏爾姆設計觀為題,旨在推動對這一問題的深層討論。
一、“價值無涉”思想在烏爾姆設計學院倡導的背景首先,“價值無涉”思想在烏爾姆得到倡導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這所學院始于1946年成立的社區學院(Volkshochschule),其主要的創辦者英格·紹爾(Inge Scholl)就是在1943年被納粹處決的抵抗組織“白玫瑰”(Die Wei e Rose)成員漢斯和蘇菲·紹爾兄妹二人的姐姐。從動機來看,這所學院的創辦其實一方面是為了紀念因抵抗納粹暴政而失去的親人;另一方面也是以推動西德戰后民主政治發展為目的。[1](P.28)正是上述原因,使烏爾姆的創辦得到了美國專員約翰麥克考伊(John J.McCloy)的幫助,并收到了來自美國及挪威方面的部分啟動資金。就這一點而言,至少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政治因素在初始階段就已經介入了烏爾姆的創建。美國方面也希望在西德建立起一所傳播民主政治的高等教育機構,雙方正是在共同政治利益的基礎上達成了一致目標——將烏爾姆創辦為一所推動德國民主化進程的高等教育機構。也就是說,烏爾姆無論是從早期的社區學院,還是后來改為一所設計學院,均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和傾向,并且不是將培養商業性(設計)人才作為其考慮的首要任務。不難看出,創始人英格·紹爾及其丈夫奧托·埃舍爾(Otl Aicher)應該是“價值無涉”思想在烏爾姆的最早倡導者。不過需要指出,他們也不可能因為政治的主張而完全持“技術中立”的態度,所以“價值無涉”在烏爾姆從開始階段就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可引以為證的是,在第一個時期[1](P.9-13)——即烏爾姆的(設計)教育思想的形成期,該學院是想成立一所:“致力于國民教育與民主的學院。教學課程為‘社會和政治科學。”[1](P.17) 盡管經歷了從早期馬科斯·比爾主持下的“包豪斯模式”階段,到奧托·埃舍爾和馬爾多納多等人對科學設計與方法論研究的不平衡發展展開批判等階段,烏爾姆始終沒有脫離對社會民主與政治問題的關注。其次,“價值無涉”思想影響烏爾姆的設計觀符合時代的需求:一方面,基于“二戰”后西德重建時期各領域對高素質設計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體現了新時代對設計師責任與義務的特定要求。眾所周知,在烏爾姆創立之前,德意志制造聯盟(1907-1934)及包豪斯(1919-1933)的設計思想,曾影響了德國乃至歐美等主要工業化國家的設計,并得到了廣泛認可——尤其是在推動功能主義設計思想方面。包豪斯甚至創造了現代設計史上一段烏托邦式的傳奇,并使“二戰”前的德國無可爭議地成為了西方現代(教育)設計的策源地。但必須看到,制造聯盟和包豪斯并不反對設計與市場,尤其是制造聯盟創建目的就是要提高德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一點,以前的設計明顯地與烏爾姆設計所追求的方向不同:其一,是烏爾姆崇尚科學實證與邏輯推理,反對藝術介入設計活動(將藝術排除在設計之外);其二,是烏爾姆將社會責任與設計教育相結合,目的是培養有責任感和民主意識的新型設計師。再次,專注于新興設計領域的實踐及科學設計方法研究,強調設計知識的客觀性,而不是以商業性的價值評判為衡量標準。與比爾時期不同,烏爾姆創辦者之一奧托·埃舍爾認為,包豪斯的缺點在于始終就沒有能擺脫自制造聯盟以來,藝術、手工藝與設計始終糾結不清的混沌關系,且僅滿足于傳統的手工作坊式設計模式,并沒有真正面向迅猛發展的現代化工業生產,走批量化生產的新型設計之路。因此,烏爾姆的辦學目的是“并不是想要成立第二個包豪斯,而是有意地想和該校拉開一定的距離。”[2](P.85)不難理解,在烏爾姆成立典禮期間(1955),當沃特·格羅皮厄斯(Walter Gropius)建議將學校命名為“包豪斯—烏爾姆”時,被奧托·埃舍爾等人婉言拒絕——二者間至少存在這樣的差異:其一,烏爾姆并不想延續之前的設計路線,而是試圖尋求新的方法及探索新的設計領域;其二,烏爾姆與包豪斯的歷史使命不同,包豪斯經歷了手工藝到機械化生產的轉變,烏爾姆面臨的狀況則是西德“二戰”后重建的現實,需要有專業技能和社會文化知識的設計師開展面向公共服務的設計活動。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工程設計領域興起的“設計方法論運動”以及“科學操作論”,影響到了烏爾姆的設計教育與理論研究。文獻顯示,烏爾姆在成立之初就因設計(教育)的發展道路出現過嚴重的分歧:該院早期創建者馬科斯·比爾(Max bill)的設計觀,與埃舍爾、托馬斯·馬爾多納多(Tomas Maldonado)和漢斯·古格洛特(Hans Gugelot)等人并不相同。對比爾而言,藝術在設計活動中占據主要的地位,藝術家的地位要高于技師。盡管他極力提倡烏爾姆的設計要致力于新文化建設,但他仍計劃將包豪斯作坊式的模式在烏爾姆復制,并且仍強調造型藝術在設計中的重要地位。埃舍爾曾對此這樣寫道:“在比爾的眼里,藝術保持著原樣,而同時我們卻開始把藝術看為是危及設計的事情。設計將從實際中發展它的道路。這個危險存在于設計正成為了一種實用藝術,并借助于藝術的解決方案。”[1](P.86)如馬爾多納多在1957年的一次新學年致詞中,就表露出了烏爾姆將與包豪斯走不同的道路:“要試圖延續原來的包豪斯路線,只能意味著回到過去。優秀的包豪斯人也會贊同如果這樣延續包豪斯(傳統),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對包豪斯的背叛。在現有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僅延續包豪斯進步和反傳統的態度,去推動社會的發展。因而,只有從這個意義來講,包豪斯的事業才能得以延續。”[1](P.22)這說明,烏爾姆只愿意繼承包豪斯的創新精神而非教育模式,并有意結合現有的條件將設計推向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可以看出,烏爾姆的規劃者當時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即科學與設計是否能夠較好地結合在一起,并最終要建立一個新的設計教育培養模式。在烏爾姆的教師中,除馬爾多納多對操作哲學推崇之外,古伊·彭西培(Gui Bonsiepe)也探討了科學(方法)對于設計的意義。在提倡科學、技術與設計三者結合的模式下,烏爾姆仍存在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其主要焦點在于“科學”究竟是“設計”的“工具”,還是決定未來設計品質的“主導”因素。一方面,因為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提高,能夠更好地為設計提供技術支持;另一方面,卻又將設計引入了工程領域,并可能限制了設計者創造力的發揮。不難看出,彭西培關于科學與設計關系的闡述,基本上反映了烏爾姆模式下設計者們所面臨的境地。事實上,烏爾姆內部關于科學方法論與實踐之間的爭論,從來就沒有真正停止過。可以肯定的是,烏爾姆的設計思想在學院成立初期,還是受到包豪斯提倡的藝術與技術相結合這一主張的短暫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烏爾姆所推行的科學操作觀及系統設計,與該校國際化的學術視野有密切的關系。尤其是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訪問學者,對烏爾姆的設計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英國學者布魯斯·阿徹爾(Bruce Archer)于1961至1962年在烏爾姆訪問期間,最早將設計的方法論介紹到了這里,而該方法論與馬爾多納多等人一直尋求的科學操作方式不謀而合,并最終在烏爾姆的教學及設計實踐中廣為提倡。此外,系統設計思想經過漢斯·古格洛特與布勞恩等企業的合作,在設計中體現出來,逐漸成為了烏爾姆設計的一個鮮明特點。眾所周知,系統設計思想最早出現在工程技術領域,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被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引入社會學系,被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用于哲學”。[3](P.46)系統設計表達了這樣的思想——個體的、獨立的產品設計,已經不能滿足使用者不斷增長的需求,而一些設計項目則需要設計師考慮到更為復雜的、相互關聯的整體。如成套的室內家具或廚房用具等要考慮整體的形態、比例和組合關系,單個椅子不但要考慮各個部件的色彩組合、可銜接性及可替換性,還要考慮成套擺放的效果和適用場所等。因此系統設計的思想并非出自設計師的靈感,而是來自項目實踐的需求,并在此基礎上成為了合理且有序的一種設計主張。可見系統化設計思想不僅專注于設計的合理性、協調性和整體性,同時更加注重對產品使用場所及其用戶的考慮。從上述論述中能夠發現,“價值無涉”思想在烏爾姆的出現基于其歷史背景和時代:其一,對包豪斯舊有模式的摒棄和批判。這一階段反映在比爾主導烏爾姆的時期(1955-1957),這一階段,烏爾姆一方面試圖擺脫包豪斯模式的束縛,另一方面在試圖尋找新的發展途徑;其二,科學設計方法的探求階段(1957-1960),在這一階段,烏爾姆開始試著調整課程設置和尋找科學的設計方法;其三,推行設計方法論及系統設計的主張,標志著其開始形成獨特的教育體系和設計觀。
二、“價值無涉”思想的具體體現烏爾姆的設計思想提倡在注重科學的方法論和產品的使用功能,也重視產品所包含的倫理價值。堅持將設計創新與嚴謹的方法論融為一體,形成了特點鮮明的理性主義設計思想。為其設計教育和產品設計模式提供了新的思維。烏爾姆設計觀中的“價值無涉”思想,首先體現在專業設置和培養目標方面。烏爾姆共設有四個教學系——產品設計、視覺傳達、工業建筑和信息系。值得一提的是,烏爾姆設置的并不是建筑系,而稱為工業營建系。這是因為工業營建,“是指在新型和現代社會的精神中重新設計建筑的工作。或許“工業營建”是一個較為恰當的稱謂”[1](P.197)。此外,烏爾姆也不開設室內裝飾設計和裝飾藝術等課程。因為該學院拒絕培養為私人住宅,或其他場所提供奢華或舒適性設計的設計師。從這個意義上講,時尚、風格和流行等概念是烏爾姆所排斥和避免的傾向。對此,曾長期在烏爾姆學習和工作過的林丁格爾曾這樣詳述了該院的設計(教育)觀:“從一開始我們不僅將藝術從教學中排除在外,而且還包括時尚及品味的內容,我們將自己從這些情感及非理性的活動特征中解脫出來。這樣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理性的領域之中,這也正是為什么烏爾姆人從不涉足裝飾及室內設計的原因所在。”[1](P.79) 可以看出,烏爾姆設計關注于產品的實用性與合理性,而非裝飾性或觀賞性,體現了明顯的理性主義傾向和信奉科技手段的烏托邦思想——這在科學、技術和設計三者相結合思想主導下的必然趨勢,又形成了潛在認識危機。不過能夠肯定的是,烏爾姆的這一主張,也體現在以團隊協作為特點的設計活動中:一方面,通過承接大型設計項目需要團隊通力合作;另一方面,是要培養面向工業化、批量化生產而不是作坊式的(個體經營模式下的)設計師。自此,設計被賦予了服務于工業化生產的使命,并被不斷地建立起新的標準和要求,賦予新的內容。因而,藝術創作中即興式的表現和主觀化的表達,不再為烏爾姆所提倡,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表達和實驗。除了開設一些自然科學類的課程外,烏爾姆在設計教育與實踐中尤其注重運用科學的設計方法,并不斷地灌輸這種“方法先行”的思想。再者,“價值無涉”在烏爾姆也體現為一種信仰,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種設計思想。烏爾姆有其區別于其他院校的“清規戒律”,比如師生們在校園內要求必須遵守某些規定。例如:“不允許騎自行車、任何人都身著黑衣、使其不得不扔掉短襪并且相互剪發。”[1](P.92)并且,在生活方式上也要脫離世俗生活(尤其是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如:“任何人在頭兩周內沒有拋棄中產階級服飾的痕跡的話,就會成為一個另類的人。首先是發型的改變,其次是襯衫和外衣布料的改變。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穿黑色衣服:因為當時最主要的想法是遠離中產階級(使用)的布料。”[1](P.92)其目的在于,要消除人們之間社會地位和經濟差異,而能夠平等地在學員進行學習和研究。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生活方式也會最終影響到這些未來設計師們的價值觀和設計實踐——以科學理性評判設計的價值,而不是出于市場營銷的經濟利益。此外,設計面向新的大型公共設施而不僅是室內日常生活器物,將設計對象拓展至新的領域,強調科學設計方法。在此基礎上,設計活動不再局限于創設日用品,更是面向社會性公共交通工具和生產企業廠房的設計等。在1957年比爾離去后,一種較為明顯的趨向主導著烏爾姆的教育理念,那就是探尋理性的科學方法論以解決設計過程中的各項問題。換句話說,理性的設計科學研究在烏爾姆不但取代了包豪斯教學模式,也明確了科學設計方法在設計活動中的重要性。馬爾多納多于1958年的一次演講,以“邁向更新的包豪斯”為題,分析了藝術與工藝的局限性。他提倡一種科學的操作主義(Scientific operationalism),理由在于:“知識的掌握將不再成為問題,重要的是對于知識的操作及控制。”[1](P.149)這種操作主義的思想,最初出自拉伯波特(Anetol Rapoport)在1953年發表的一篇題為“操作哲學”的文章,他認為操作哲學是一種行動引導目標的行為學。在馬爾多納多看來,在設計活動中引入操作主義的觀念,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因為理性的思考和嚴謹的科學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途徑來實現設計師的目的,而不再憑借偶發的靈感進行設計。最后,“價值無涉”還表現在以用戶為先的“優良設計”(Good design)主張中。烏爾姆設計采取以用戶為先的思想,有別于以產品(機器)為中心的設計思想。這里所指的用戶,不是以財富為標準劃分的不同消費能力的產品使用者,而是無階層差別的平等消費者。因而,烏爾姆立足于用戶的角度進行產品設計并對質量進行評價,目的在于使產品適應于人的使用需求,而不是使用戶被動地適應于產品。回顧德國工業設計的早期發展歷史,自制造聯盟以來的功能主義設計思想,主張追求產品的優良形式(Good form),并一直成為工業產品設計所追求的目標。烏爾姆顯然并未局限于優良形式的束縛,甚至開展了對已經形成模式化的產品造型形式予以了批評。如包豪斯幾何化的設計風格,在產品中業已成為了不實用的外在形式,設計師難免在思想上受其束縛并失去了創新的意識,對此現象奧托·埃舍爾給予了無情的批判。 在項目設計中,烏爾姆提倡追求產品的優良性能和使用價值的同時,注重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和不同使用目的,使產品更加符合使用者的具體需求,開始關注于使用者與產品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產品語義學的概念得到了發展,烏爾姆與布勞恩、克魯伯等公司積極開展項目合作,所設計的產品均獲得了使用者的好評,并成為了優良設計的代名詞。因此,從優良形式到優良設計的轉變,實際反映了從產品的表層要求上升到內部包含的倫理性因素,這反映了上述兩種截然不同設計思想間的差異所在。所以,以用戶優先的設計思想,既有著倚重社會倫理來審視產品品質的一面,也有對設計師自身素質建設和要求的一面,是現代主義設計中理性與倫理因素相結合的體現。烏爾姆設計中的這種思想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對文化的尊重,面向未來的工業發展,探討“城市化問題、技術和工業發展問題、人與技術的關系問題、人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問題、生態問題”[3](P.46)。在此基礎上,一些流行于國際的樣式(尤其是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流行的時髦設計),以及一些并不實用的設計方案,遭到了烏爾姆適時地批判和修正。在烏爾姆人看來,產品設計的過程中要進行必要的功能實驗,并強調在這一過程中遵循嚴謹的科學方法,表達產品所具有的語義并實現其使用目的,反對浮夸且無實用價值和以設計者自我為中心的設計行為。“價值無涉”在烏爾姆設計觀中的另一體現,是設計師與工程師的身份與地位平等,以及各種思想兼容并蓄的寬容度。在設計活動中,采取以批評為主且針對不同設計方案進行討論,以求獲得最優或相對優秀的結果。所以,在烏爾姆的設計實踐中,“設計師已不是個體的藝術家,變為了工業生產過程中平等的合作者,并更加關注于設計的過程而不是結果”[4](P.55)。正如烏爾姆的項目“研發團隊”(Developmentgroup)是以相互間批評為提高和參與競爭的手段一樣,烏爾姆的項目設計與教學中注重批評的作用和影響。在批評中,成員們不斷矯正方案的制定,從而將設計師與工程師等成員視為地位平等的參與者。事實上,烏爾姆同包豪斯較為相似的一點就是,始終充滿了爭論和批評。從早期奧托埃·舍爾和馬爾多納多等人對包豪斯模式繼承性的批評,以及1963年在期刊《烏爾姆》(第7期)中,馬爾多納多、彭西培等人對工業設計領域達達主義傾向的批判,均為再次調整烏爾姆設計的發展方向明確了目標——走科技與設計平衡之路。不過,也必須看到烏爾姆的科學設計之路,在馬爾多納多的帶領下曾偏離過創辦時的政治初衷。有研究者就指出:“從該學院的角度而言,馬爾多納多背叛了自己要為(學院)謀求政治利益的意愿。”[5](P.68)足見烏爾姆雖是以設計教育享譽世界,但其具有的政治愿景不容忽視。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價值無涉”影響到了烏爾姆的生活方式、教學與設計等不同方面。烏爾姆也正是在不斷的批評中避免了包豪斯的覆轍,并將“制造聯盟”以來始終未決的設計發展方向,堅定地走上了為工業化生產服務的科學設計之路。值得注意的是,烏爾姆創辦的初衷確實與德國的政治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價值無涉”思想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且貫穿于烏爾姆的教學與生活中。作為“二戰”后創辦的一所國際化的設計學院,烏爾姆不可否認地主動承擔了推動(西德)民主化道路歷史使命。而在這一過程中,“價值無涉”思想對烏爾姆設計觀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影響作用。endprint
三、“價值無涉”思想的影響及評析毋庸置疑,“價值無涉”在烏爾姆創辦初期體現為一種政治愿景,具有濃郁的烏托邦色彩。在烏爾姆擺脫了早期的包豪斯模式影響之后,雖然倡導科學的設計方法,但并不意味著該學院放棄了創建之初的社會理想。相反,通過與AEG、克魯伯(Krups)和布勞恩等公司的合作,烏爾姆提供了以高品質的設計影響了戰后西德的消費文化,而布勞恩公司也因與烏爾姆的合作成為了優良產品制造商的代名詞。從產品而言,以布勞恩公司的產品為例,基本遵循了如下設計理念:其一,依據使用者的需求、操作方式和新的技術開展設計;其二,滿足人體工學及心理的需求;其三,簡潔明了,合乎功能。上述三個特點,集中反映了烏爾姆當時的設計觀和審美思想。因此,正是通過產品生產企業、交通運輸公司和航空企業等與烏爾姆的項目合作,將烏爾姆的設計觀予以傳播。正因如此,林丁格爾甚至不無自豪地這樣寫道:“這所學校成為了一所卓越的設計實驗室和天才的聚集地。在被關閉了20多年之后,烏爾姆仍然被認為是繼包豪斯以來,歐洲最優秀的設計學院。”[1](P.1) “價值無涉”思想在烏爾姆還體現為一種消除了身份和經濟地位的平等:既存在于在日常教學與生活中;也體現在去除了以前設計師(或藝術家)在設計活動中地位高于一切的現象。這意味著在團隊協作設計的過程中,無論參與者的貢獻大小均作為設計決策的貢獻者。通過文獻可知,烏爾姆的“價值無涉”思想通過以下三個途徑進行傳播:其一,通過烏爾姆的項目設計,傳達了其設計的思想及理念;其二,通過媒體或學術期刊向外界表達烏爾姆的設計思想,如發表在學術期刊《烏爾姆》和“Georgy Kep”上的許多設計教育及批評性文章,成功地向外界傳達了烏爾姆教育者們的思想及態度;其三,在烏爾姆關閉后,其來自不同地方的師生們將其思想傳播到了世界各地。事實上,這所學校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傳奇般的辦學歷程,也不在于期間各種觀點的紛爭,而是在于創新的思維和科學設計的探索精神——正是在“價值無涉”思想影響下,烏爾姆出于“非利益性”目的,對新的設計領域進行研究。烏爾姆設計的可貴之處就在于,盡管前面已經有了包豪斯模式的成功和輝煌業績,但是仍堅持在批判的基礎上進一步地開拓創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創刊于1958年的《烏爾姆》季刊(共出版了21期),為烏爾姆設計思想與理論輸出的主要平臺和窗口。奧托·埃舍爾、馬爾多納多、彭西培和施奈德等人的文章正是通過《烏爾姆》表達了烏爾姆關于設計的態度、主張和立場——該刊現已成為設計界(尤其是設計理論領域)研究烏爾姆設計(思想)的重要文獻。從內容來看,《烏爾姆》關注于科學設計研究,及設計領域中出現的一些不良傾向和現象,經常成為烏爾姆教育者們評論的焦點。如在《烏爾姆》的第10期、第11期,曾發表過彭西培等人聯名撰寫的文章《科學與藝術》,目的是批評:“過分簡單地借用‘人體工學領域設計方法的行徑”。[1](P.151)對表面地套用人體工學的形式等現象予以了分析和評價,指出上述情況將會使復雜的科學設計活動被簡單的理解為程式化過程。在烏爾姆關閉以后,《烏爾姆》期刊及其他有關烏爾姆設計思想的文獻資料,隨著烏爾姆師生在世界各地的設計及教育活動而廣為傳誦。直至目前,這些烏爾姆的文獻資料仍作為國際設計界研究其設計思想的主要依據,并繼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上述兩個途徑對烏爾姆設計思想的傳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烏爾姆自創建伊始就有著國際化特點,這為其“價值無涉”思想的對外影響創造了有力條件。在烏爾姆的統計數據中,從1953至1968年間,烏爾姆“學生總數為640人。其中,工業設計系220人;視覺傳達系135人;工業營建系127人;電影系23人;信息系14人;基礎課程121人”[1](P.29)。這其中女生約占50%,有約一半的學生來自49個國家或地區,覆蓋五大洲的不同國家。在烏爾姆停辦以后,該校的師生們將烏爾姆的設計思想及理念,帶回到了世界各地的設計院校或企業中,使烏爾姆的設計思想開始影響世界各地的設計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在烏爾姆的學生中,有來自泰國、韓國、日本、印度和越南等國的留學生。如印度的國立設計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esign),就曾聘請古格洛特和林丁格爾為客座教授來講學,該校的教學計劃、方式和管理均受到烏爾姆的影響。設在孟買的工業設計中心(IDC),是印度另一家受烏爾姆設計思想影響的設計研究部門,該中心負責人Nadkarni同樣為烏爾姆的畢業生。這兩所設計教學與研究機構,仿效烏爾姆的模式開展教學和項目設計,在學校和企業間架起了實踐的橋梁,使烏爾姆的設計思想在印度得到區域化發展。在里約熱內盧的工業設計高等學校也同樣如此,他們的教員中如卡爾·海因茨·伯格米勒、亞歷山大·沃爾納等人都曾在烏爾姆學習,且作為烏爾姆設計思想的繼承者活躍在巴西設計界。[1](P.276)上述學校以烏爾姆模式為藍本,較好地將烏爾姆的設計思想與當地的工業設計教學與實踐相結合,均成為了烏爾姆在亞洲和南美洲的傳播中心。從史料分析,“價值無涉”思想對烏爾姆的影響并不是偶然,也并非獨例。究其原因,在烏爾姆奉行“價值無涉”的階段,正值“二戰”后(工程)設計領域科學方法運動的興起。例如,除烏爾姆對科學設計方法的研究之外,當時的設計研究者霍爾(Hall,1962),阿西莫夫(Asimow,1962)、亞歷山大(Alexander,1964)、 阿徹爾(Archer,1965)等人均投入到了該領域的研究之中。而戰后德國經濟重建需要求真務實的高素質專業人才以及新技術和材料的應用,這共同為烏爾姆設計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烏爾姆謀求通過科學的設計方法解答設計中所要解決的一切問題,崇尚嚴謹的邏輯推理而不是價值判斷,推行地位平等的設計團隊而不是以藝術的方式解決設計問題,這些均反映了一種明確的“科學主義”設計觀和社會態度。
四、結語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論述,不難理解“價值無涉”思想影響下的烏爾姆設計觀在一定程度上有著雙重身份和兩難的處境:一方面試圖去除世俗的地位與經濟因素,追求平等參與和社會進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抵制世俗生活與商業利益的誘惑,堅持在學院內部實施精英式設計教育與理論研究。烏爾姆不再作為包豪斯模式的翻版或延續,固然與“二戰”后德國重建的現實需求有直接關聯,但烏爾姆的政治愿景與設計教育相結合是客觀地認識該學院設計觀的重要因素。因此,可將“價值無涉”思想影響下的烏爾姆設計觀總結為以下三點:其一,政治愿景與設計教育相結合——民主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超過對技能訓練,設計師首先要有社會公共意識和責任感;其二,專業設置依據社會公共需求,排斥商業化、風格化和奢侈消費的設計追求;其三,烏爾姆強調設計知識的客觀性,崇尚科學理性的設計方法,以及設計研發團隊的參與者地位平等,在設計(研究與實踐)中以邏輯判斷取代價值判斷。可以認為,烏爾姆設計真正追求的并不只是“技術至上”及對科學設計方法的尊崇,以求解決設計中遇到的問題(盡管也出現了“方法崇拜”的錯誤),而更是對設計師社會責任的重視,以及推動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對于烏爾姆設計觀的認識,需要從“價值無涉”思想的視角加以審視。研究“價值無涉”思想對于烏爾姆設計觀的影響,一則是為了糾正先前對烏爾姆設計存在的誤讀與偏見;再則是為了反思當今影響設計決策的商業利益和它他非設計因素。筆者相信隨著國內對烏爾姆設計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對此內容會有更為全面和客觀的認識。(下轉第197頁)(責任編輯:陳娟娟)
參考文獻:
[1]Herbert Lindinger. Ulm Design[M]. Ernst Sohn. Berlin,1990.
[2]Otl aicher.The world as design. Ernst﹠sohn[EB/OL].1994.
[3]李樂山.工業設計思想基礎[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
[4]Markus Rathgeb.Otl Aither[M]. Phaidon.2006.
[5]Klaus Krippendor. Designing In Ulm and Off Ulm[A]//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al Papers (ASC) [C].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Year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