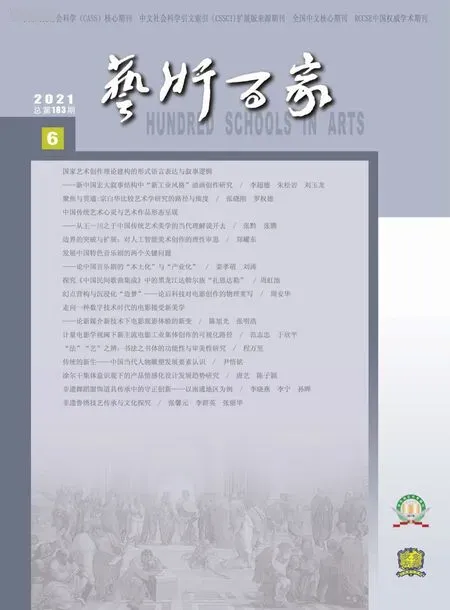敦煌壁畫中的民俗畫
馬楠
摘 要:敦煌壁畫中的民俗畫,是佛教故事、現實生活與藝術表現共同作用的產物,這些作品的創作初衷雖然是講佛教的故事,宣揚佛教的教義,但卻記錄下了當時的現實生活;雖然只是零星地散落于石窟的各個角落,卻閃爍著最具生活氣息的光芒,同時,也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藝術特點。文章就其題材選擇、表現手法及其藝術價值試做整理和分析。
關鍵詞:敦煌壁畫;民俗畫;佛教壁畫;壁畫題材;表現手法;審美價值;藝術特點
中圖分類號:J20 文獻標識碼:A
敦煌壁畫在描繪佛教經典圖像之余,有很多表現當時普通百姓亦即“庶民”生產生活場景的畫面,包括婚喪嫁娶、春種秋收、狩獵打漁等題材,令文字記載的歷史得以直觀呈現,并為歷史考古、民族宗教、社會民俗傳統學科提供了寶貴的圖像資料。關于敦煌壁畫的世俗化曾有多位專家發文論述,也有學者就“婚禮圖”、“射箭圖像”等民俗題材進行考古學和社會學的研究。但是,這些作品的審美價值卻未能引起相應的重視,本文欲就此試做整理和分析。
敦煌壁畫中描繪民俗生活的畫面主要出現在故事畫中,尤其是因緣故事畫與經變故事畫。因緣故事畫宣揚與佛有關的度化事跡,在早期流行的故事畫中,因緣故事的背景最為貼近生活,因而描繪普通百姓生產生活場景的畫面也開始在宗教石窟中有所展現。自隋代開始流行內容豐富的經變畫,在唐代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并在石窟中占據了主流地位。此時故事畫的內容開始減少,很多故事被組合在經變畫之中描繪出來。經變畫專指將某一部乃至幾部有關佛經之主要內容組織成首尾完整主次分明的大畫。其中的故事畫多位于主畫面說法圖的四角,或是以屏風畫的形式出現在主畫面兩側或下方。隋唐時期,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中外商業貿易繁榮的重鎮,經濟發達,社會生活豐富,也迎來了民俗藝術的鼎盛,經變故事畫中的民俗繪畫是敦煌壁畫中這一主題的杰出代表。另外,宣揚“五臺圣跡”的五臺山圖,全景式的構圖將人物穿插在山水之中,表現了不少民俗風情的場面。敦煌壁畫中的民俗畫,是佛教故事、現實生活與藝術表現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主題主要有:佛傳故事、善事太子入海緣品、維摩詰經變、福田經變、法華經變、寶雨經變、彌勒經變、楞枷經變、報恩經變、千手千眼觀音經變、五臺山圖等。這些作品的創作初衷雖然是講佛教的故事,宣揚佛教的教義,但卻記錄下了當時的現實生活;雖然只是零星地散落于石窟的各個角落,卻閃爍著最具生活氣息光芒,同時,也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藝術特點。
一、題材選擇
敦煌壁畫是依據佛經內容繪制,佛教為了吸引和教化信眾,佛經中的故事越來越貼近現實生活,尤其自隋唐以來,更成為僧俗共建的大乘佛教,是圓融各宗派的、社會化和世俗化了的‘入世佛教。有些經文中就直接講述現實生活,如《福田經變》的“廣施七法”。更多的是在經文中提到了相關的情節,而被畫工加以處理和發揮。如《彌勒下生經》中有云“女人年五百歲始出嫁”,據此短短一句經文所繪制的婚禮圖就達十幾幅,詳細地記錄了婚禮上宴飲、行禮、奠雁、樂舞、合巹等禮節。又如《楞伽經變》“斷肉食品”經云:“衢路市肆,諸賣肉人,或將犬馬人牛等肉,為求利故,而販鬻之。”在晚唐第85窟被描繪為備貨充足的肉鋪,屠夫一邊忙著手中的活計,一邊防備著不遠處虎視眈眈垂涎三尺的野狗。案板下還有一只待宰的肥羊,一派生意興隆待客盈門的場面,與佛經本意背道而馳。佛經中的只言片語,給畫工們提供了一個描繪現實生活的絕佳機會。對漢魏繪畫傳統的繼承,也在這些民俗畫中有所體現。例如對耕獲場景的關注與描繪,在兩漢魏晉藝術中淵源已久。在四川大邑安仁鄉出土的東漢弋射收獲畫像磚,四川彭縣三界鄉收集的東漢荷塘漁獵畫像磚,嘉峪關西晉六號墓磚畫耕作圖等,構圖雖有平面裝飾意味,但通過對各物體位置的安排,仍表現出了遼遠的空間,意境清恬,趣味盎然,敦煌壁畫多次出現的耕獲圖也大致承襲了這種感覺。另外出行、騎射也是壁畫中頻繁出現的題材。《太子學藝》《五百強盜成佛》《張議潮出行圖》《法華經變·化成喻品》等很多故事畫中都有對騎射、出行場景的描繪,或是浩浩蕩蕩的大片人馬,或為三五騎成群,雖然表現的故事情節各異,但畫工們都對人騎圖情有獨鐘,這也能在漢代繪畫中找到線索。河北省安平縣逯家莊東漢墓壁畫《君車出行》是出行圖中的代表性作品,其構圖方式、表現手法都能在敦煌壁畫中見到傳承。四川廣漢出土的東漢雙騎吏畫像磚,造型概括而富有張力,可以說是中國“人騎”圖像的典范之作,尤其是馬的造型,各種弧度的圓線組合成的軀干,配以頗具書法用筆韻味的四肢,奠定了后世馬匹形象的基礎,從北周的《佛傳圖》《五百強盜成佛》,到晚唐的《張議潮出行圖》,均能看出這種手法的延續[1]。地域的因素也影響著民俗題材作品的創作。敦煌地處西北沙漠,氣候干旱,《法華經變·藥草喻品》“佛法如甘霖,百草禾稼,均沾其惠”這句經文被描繪為生機盎然的“雨中耕作圖”,反映了百姓對天降甘霖的渴望。另外,敦煌建郡以前曾是游牧民族放牧之處,當地居民對牛馬駱駝等牲畜的偏愛也在壁畫的創作中有所體現。
二、表現手法民俗作品在壁畫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人物動物等畫面的尺寸相較于主體形象也顯得微乎其微,甚至一個庶民的“身高”還比不上本尊像的一只手的長度。同時,畫面的效果也良莠不齊,但技法成熟的畫作依然讓人覺得驚艷。小幅的畫面更要求對形象的高度概括,很多畫面現在看來只留下了剪影般的效果。如盛唐第148窟南壁“互拜成禮”,空間關系協調,新郎新娘分別在親友的陪同下對拜于帳外,長輩對坐在帳內的長桌兩側觀禮。人物坐立穿插,雖動作都比較靜止和單一,但前后關系明確,角度多樣,既營造了很強的秩序感,又不乏微妙變化帶來的生動性。雖沒有細節的刻畫,甚至線條都寥寥無幾,但每一個外形都能展現畫家深厚的造型素養,衣領的方向、飄帶的位置等均能恰到好處地暗示出空間關系,造型的嚴謹程度不遜于同時代的經典作品。賦色方面依然帶有濃濃的敦煌風格,石綠的背景主導了畫面,點綴著沉穩的深紅,重色以線、點的形式支撐起畫面的結構,節奏鮮明。盛唐第23窟北壁《雨中耕作》,描繪了三個場景。近處一片緩坡的背后,一家三口正圍食籃而坐,享用午餐。中景畫一農夫頂笠揮鞭,叱趕著犍牛扶犁耕地。遠處銜接背景的大雨滂沱,畫一荷擔急行的收獲者。畫面的顏色雖已部分氧化,但僅從人物的外形就能看出畫者對形體動態熟練的把握與輕松的描繪。背景的云、雨以線、點交錯結合,形式感強而別具天真意味。依據《彌勒下生經》“一種七收”繪制的榆林第25窟北壁西側的耕獲圖,描繪了“揚場”、“牛耕與播種”、“收割”的畫面。《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畫》:“其中的農婦形象,豐腴,健壯,頭束高髻,身著大袖衫、長裙、束帶大口褲、麻鞋,正是(唐)張籍《采蓮曲》詩中‘白練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釵梳妝淺的勞動婦女形象。” 表現手法以勾染為主,線條對形體的塑造精煉到位,不同于同期卷軸的工細,更帶有揮灑的味道。第85窟《樹下彈箏》描繪的是善友太子在經歷了種種遭遇之后,流落到利師跋國彈箏賣藝,看守果園,公主聽其彈箏而產生愛情。“善事太子入海求珠……描寫了一個優美的愛情故事。在佛教禁欲主義禁錮下,畫面上敢于正面表現男女戀愛私情,使這幅畫充滿了人間情趣。”[2]畫面構圖完整,整體的灰綠色調加上水墨氤氳的味道,讓人似乎能夠呼吸到果園中含著草香果香的濕潤的空氣。太子與公主相對而坐,太子的古箏斜放,似乎一曲終了,兩人仍沉浸在音樂的意境之中,抑或羞澀地低語心內的情愫,此情此景讓人為之動容。人物形象概括,姿態自然生動。同窟的佛像畫,同時代的卷軸畫,雖然描繪的對象一為純粹的宗教人物,一為純粹的世俗人物,卻在技法上有類似的特點——均為勾線染色之法,只是壁畫中是勾填法,而卷軸畫在勾線之后用三礬九染獲得了更為細膩精致的效果。再看《報恩經變》,在技法上的運用卻更為靈活自如,豐富多樣。樹木、地面用類似沒骨的技法加以渲染,全無勾線,讓人聯想到“米式云山”般朦朧的幻境。人物用爽利灑脫的線條勾勒外形和部分衣紋,間以平鋪的色塊,平面中隱約可見用筆的痕跡,雖然造型嚴謹,而筆墨卻非常放松,“筆才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三、藝術價值據《歷代名畫記》載,唐代畫家多擅長于佛像經變、綺羅人物、神鬼、鞍馬、山水雜畫等,只在《論師資傳授南北時代》中有一筆“田(僧亮)則郊野柴荊為勝”并《卷八·北齊》“田氏野服柴車,名為絕筆。”但畫跡已無可尋。其它畫史中較早出現的對世俗生活場景描繪的記載,見于《圖畫見聞志》:“(五代)梁駙馬都尉趙巖,善畫人馬,挺然高格,非眾人所及。有漢畫西域傳貴骨馬、小兒戲、舞鐘馗、彈棋、診脈等圖傳于世。”畫跡已無從追尋,但從記載之“彈棋、診脈”等圖,可以大膽地推想這應該是帶有民俗生活氣息的畫面。另,“(五代)李靄之……有賣藥、修琴、歸山圖、野人荷酒、寒林并山水卷軸傳于世。”可見隋唐五代時期風俗畫并未成為畫家創作的主要題材,敦煌壁畫中的民俗記錄,為兩宋風俗畫的勃興提供了難得的參照。寫意精神貫穿于中國繪畫史,但從狹義的“寫意”技法來看,一般認為寫意人物畫是以宋代石恪、梁楷為濫觴,或者按照“十八描”的說法,他們的作品是“減筆描”的起源和代表。但是,這種寫意技法在敦煌的壁畫中卻已出現端倪,而且能將工、寫、沒骨的技法融合在一件作品中,運用得渾然天成。(責任編輯:徐智本)
參考文獻:
[1]馬濤.張大千敦煌壁畫線描藝術探析[J].美術大觀,2013,(01).
[2]段文杰.敦煌石窟藝術研究[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