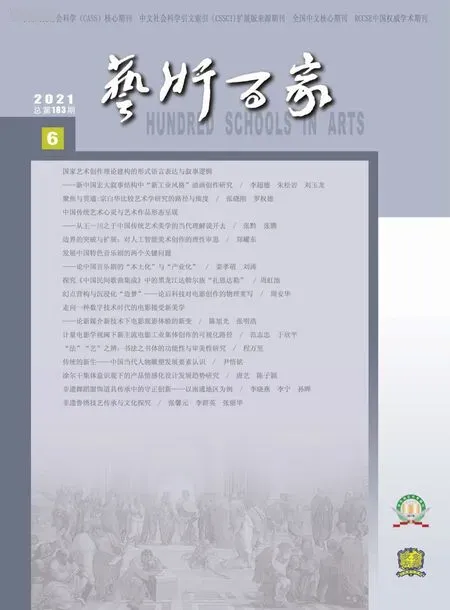微時代的審美風尚和生活的藝術化
摘 要:與全球化的新媒體語境相關聯的微時代,帶來了文化生態與審美風尚的變化。其以日常、感性、快餐、娛樂等為指征的消費效益原則,沖擊了以優雅、崇高、規范、秩序等為核心的經典美感風尚。以小生活、小人物、小情致等為代表的微風尚,不僅解放、豐富、沖擊著我們固有的感性能力、審美情致、生活樣態,也尖銳地展示了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技術與價值、藝術與生活之間的新的關聯域。唯此,在微時代,批判傳承生活藝術化的中西傳統,反思陶鑄適應新的時代需要的藝術審美品格與人生審美精神,抑或是抵御與超越美為生活吞噬、藝術為生存消解、人消費自我的可能困局的一種人文路徑。
關鍵詞:審美文化;微時代;審美風尚;生活藝術化;人文路徑;批判傳承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一微時代是和全球化的新媒體生態環境、高科技的新媒體生態平臺、開放式的新媒體傳播途徑緊密關聯的當下時代。微時代的文化特征與以大工業為基礎、科技文明為核心的現代文化特征不同,也不同于以傳統農業文明為基礎、手工業文明為核心的古典文化面貌。日新月異的新媒體技術、多樣開放的新媒體平臺、便捷發達的新媒體傳播,為新的文化樣態與新的生活風尚打造了直接而重要的技術支撐。而特別需要引起關注的是,這種技術的更替發展正逐漸展衍于大眾的生活,它改變的實際上已不僅僅是生活形式的某種“大”或“微”,也深入至生活的內里,包括人的精神心理。為此,我們需要關注這種伴隨新媒體而來的新文化特征與樣態。如果說,古典文化與現代文化,主要體現了以優雅、崇高、規范、系統、邏輯、秩序等為核心的“大”美感風尚,那么,新媒體時代,則以顯著的日常、多元、流動、平面、碎片、隨意、即時、娛樂等指征,呈現了一種“微”文化取向。在微時代,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過一種“小”生活。“百萬年蒙昧,數萬年游牧,幾千年農耕,幾百年工商,如今,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巨變,由工業時代邁向信息時代。”[1]信息時代的數字化生存,使虛擬現實成為現實。如果說,過去我們需要街巷、橋梁、鐵路、公路、會堂、廣場等串聯彼此,今天,個體與公共的壁壘,在新媒體信息高速傳播前,已經消弭。互聯網和移動平臺的結合,“教給我們這樣一個道理:我們既能成為一個龐大公共群體的一部分,還能夠保持我們的個性面孔”;“今后可能的情況是,在真實世界中曾經有的公眾和私人自我之間的那條本來明顯的界限會逐步被腐蝕掉,一點一滴地”[2]。足不出戶可以生活,隨時隨地可以享樂。新媒體造就了一個人生存的“男神”和“女神”。在微時代,我們也可以心無旁騖地做一個“小”人物。農業文明時代的英雄情結,工業文明時代的精英情結,在歷史腳步和時代風尚的蕩滌中,似乎已經讓位給了今天這個微時代的自由情結。我們似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隨性過。網絡的即演即唱可以即播即傳,不求經典,不尚完美,只要自己快樂與滿足,這是新媒體在微時代構筑的公共舞臺,私密的封閉打破了,自由、隨意、開放、互動,游戲、狂歡、感性、娛樂,活在當下,活出自我,活得舒服就是生活的目的。在微時代,我們還可以自由自在地追求一種“小”情致。曾經,我們肩負著種種群體性和社會性的責任。古典時期,“修身”是需要通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因此,屈原自然要把個人的美修與國家天下的未來相結合,個體的生命承載了巨大沉重的理性目標與理想意義。現代時期,雖然隨著資本經濟的發展,人本主義、個人主義思想萌發,個體、個性、人性得到了張揚,但這種張揚仍在群體社會理性目標的框架之內。因此,現代性的精髓,仍然是共同理性。“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則宣告了微時代“小我”的本色登場。“在網絡的虛幻世界中,沒有人知道我是誰,也沒有人在乎我是誰。只有那些往事,那些心靈的獨白,讓那些相識的、不相識的或似曾相識的人,在這里駐足。”[3]大理想未必人人實現,小情致可以自得其樂,你盡可以笑了、哭了、累了、痛了、困了、嗔了。零限制、交互性、受傳合一,使得思想霸權、話語統治,都在微時代接受著新媒體的挑戰。
二微時代的技術基礎和生態指征的變化,輻射著生活的各個層面,影響著大眾審美情趣的變遷。和傳統審美情趣相較,微時代的審美風尚日漸表現出平民化、感性化快餐化碎片化、消費化等特征。平民化是微時代審美風尚的首要特征。傳統審美情趣,需要一定的審美教育基礎,包括一定的審美知識、語言、技能、觀念等的基礎,甚至還需要一定的經濟支撐甚至一定的社會身份和地位的保障。比如說,中國的傳統戲曲,從秦漢時期的樂舞、俳優、百戲,到宋元以后的雜劇、昆劇、京劇等,沒有一定的唱念做打、生旦凈丑等相關知識的了解,就難以產生濃郁的欣賞情趣,難以領會其精妙。而這些傳統戲曲,依靠劇場演出,這樣就要受到場地、演員、成本等各方面的限制。同一場戲的觀眾,因為經濟基礎甚或社會地位的不同,觀劇的位置也可能不同,欣賞的效果也可能產生差異。而在“大家永遠在線,除了睡覺”[4]的微時代,小屏幕、短時間、快享受,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刷屏,觀賞與交流,不再備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欣賞的經濟成本也大大降低。那種劇場位置的差異,遠近、角度,都不復存在。而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審美也已經不是專屬于藝術的名詞。我們的建筑、商場、廣場、街道,我們的身體、服飾、飲食、日常用品,無一不被審美的因素裝扮著。“生活的藝術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平民化生活審美的一種憧憬、概括、表達。與平民化生活審美相呼應的,是微時代審美風尚的感性化、快餐化、碎片化等。這種審美風尚,直接來自生活,作用于生活,它的主體,就是平民與大眾。他們不想追求永恒,也不深究意義。他們在意的是當下的生活,是真切的自我。他們的審美感受,總是與身體感官密切相聯,是對色、形、音、味的直接感受。高度的感性化,也意味著即時的快餐式享樂和隨性的碎片性悅樂。電影《小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詮釋了這種快餐式碎片化的平民主義感性消費新樣態。眩目的人物活動空間,時尚的人物穿著打扮,扁平的人物個性形象,單薄的故事情節演繹,使得整部電影更像是一場“男神”與“女神”的時裝秀和感情秀。審美給現實和自我裹上了一層藝術的糖衣,漂亮、新異、時尚,骨子里仍然是享樂,但這種享樂早已不是原始的粗糙的享樂,而是以高度的技術、至上的個體、本質的效益,嫁接了曾經高雅神圣的藝術和審美所烹飪的一道道精致又隨性的快餐。消費化是微時代審美風尚的骨髓。一切物質、材料、技術的變革,一切生活環境、方式、樣態的變化,在本質上,都是傳媒、技術、資本的深度合謀,潛蘊著的是效益的靈魂。就連人自身,美發、美容、美甲、美體,自我包裝無所不涉,人墮入到物質、技術、材料的掌控之中。而這種掌控,恰恰也是美容資本產業的期待。人美化了自我,也消費了自我。美國學者韋爾施曾在《重構美學》一書中指出,現實中,越來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學的外衣,日常生活被塞滿了藝術品格。這種抽取審美和藝術中最膚淺的成分,然后用一種粗濫的形式把它表征出來的生活的審美化和藝術化,只是用包裝和形式給現實裹上的糖衣,它同樣也波及了人自身,由此出現了一種“淺表的自戀主義”者,他們對自己的身體、靈魂、心智都進行了全方位的時尚設計。而這種“日常生活與微電子生產過程交互作用”,所導致的整體現實生活的審美化,潛藏著的正是“服務于經濟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同美學聯姻”,“提高身價”,讓“甚至無人問津的商品也能銷售出去”[5]。微時代的技術革命和傳媒革命,實際上已將“無距離的美”推到了我們的面前。斑斕的色彩、迷人的外觀、眩目的光影日漸進入我們的生活,花園別墅、大型展會、高檔商場、明星選秀刺激和釋放著大眾的欲望和快感,不管在精神與價值的層面是否認同,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微時代的種種審美風尚已經相當典型地發展為某種泛審美化的日常生活情狀。其突出的特點是:審美化的形式,時尚化的設計,平面化的享受。如果說,理性和技術的進步,曾經是為了發明和探索,那么,今天,在微時代,消費和效益的絕對原則也借助新的電子傳媒,為物質和享樂的感性張揚鳴鑼開道。人依附于商品,必然退化為物。人只執著物質享樂,也將導致本能與存在合一。無處不在的淺表設計,讓人的審美感覺鈍化。一切以享樂為目標的革命,可能使人喪失自由的品性。當時間和空間不再是距離,身份和地位不再是障礙,大眾的狂歡,挑戰著我們曾經追求的多樣的感受力、豐富的幻想力、高度的創造力和深刻的反思精神。
三
維特根斯坦說,“一切都是對的,一切都不是對的”,“這就是你所處的境遇”[5]。當我們暢懷迎接一個新的事物的到來時,我們也必然會關注、疑慮、叩思這個事物的未來,這或許就是人文學者的宿命。在微時代,種種更為普遍日常的、感性細微的、流動多變的、開放互動的審美指向,正在解放、豐富、改變著我們的感性能力、審美情致、生活樣態。讓理想主義者和精英主義者憂郁的是,今天,我們還需要堅守美與藝術的傳統嗎?事實上,美和藝術,在不同的時代,從來不是僵死不變的。美和藝術,在不同的時代,總是從生活的土壤中開出絢爛花朵。不管美和藝術的形態怎樣變化,總是以它的理想照亮生活,以它的情致溫暖生活,以它的品格提升生活。今天,當我們面對微時代色彩紛呈讓人眼花繚亂的種種新藝術樣態和新生活情狀時,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和直面歷史和時代的發展所帶來的變化和進步,從中感受、體認這種新變帶給審美和生活的種種新活力和新情趣;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當微技術把高高在上的藝術、審美真切地帶到了我們每個人的身邊,變得觸手可及,不再那么神秘與神圣時,藝術與生活、美與丑的邊界也就不再那么明晰。生活、藝術、審美的交融,在微時代,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為緊密。而生活的藝術化和審美化,也必然成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需要研索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19世紀中后期,唯美主義的先鋒與代表,莫里斯、王爾德、佩特,曾“嘆息世間大多數的人只是‘生存而已,極少有真個‘生活的人”[6]。他們主張“生活是一種藝術”,倡導“以藝術的精神對待生活”,強調要使生活保持“強烈的、寶石般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狀態。他們認為,美是“人類生理化學反應達到暫時和諧時的感受”,因此,“美不能持久”[7]。人們應該抓住“美妙的激情”、“感官的激動”、“陌生的色彩”、“奇特的香味”來體驗生命中一切短暫美好的瞬間。由于把美主要理解為新異形式帶來的瞬間享樂,唯美主義最終走向了耽樂哲學。莫里斯熱衷于日常器物、居室環境等的審美改造,王爾德,也把自身作為生活藝術化的唯美實驗田,齊膝馬褲、黑色絲襪、鵝絨上衣、綢緞襯衫、紫紅手套,胸前別著百合花或向日葵,才華橫溢的王爾德最后留給人們的是迷醉官能享樂的“花花公子主義”的“紈绔子”形象。唯美主義本來試圖以藝術的純潔和審美的無功利,來反抗功利黑暗的現實,對抗平庸鄙俗的生活,但它卻構筑了自己的悖論。它對藝術純粹形式和審美感性官能的極致張揚,呈現了資本對審美的全面滲透,成就了人對自我的商品化膜拜和商業化展示。唯美主義展現了資本文化與審美文化之間的抗衡,它在世俗生活的浮夸、虛榮、物質主義、解構道德中演化為審美文化與消費文化的某種連接點,也為與消費文化緊密相連的感官欲望的全面登場開啟了某種通道。20世紀,日常生活審美化大潮洶涌而來。韋爾施將其稱為“美的泛濫”,是“表面的審美化”或“物質的審美化”,追求的是“最膚淺的審美價值:不計目的的快感、娛樂和享受”。因為“服務于經濟的目的”,即使“日常生活被塞滿了藝術品格”,“美的整體充其量變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了滑稽”[5]。如果說,唯美主義是從理想到媚俗,日常生活審美化則直接構筑了“無距離的美”與生活之同一。這種審美化,在實質上就是一種以個體享樂原則和經濟效益原則支撐的藝術實用化。以藝術的情懷體味人生,以藝術的標準提升人生,是中國文化固有的重要特征之一。孔子盡善盡美、內外兼修的追求,莊子逍遙自由、無待物化的理想,都相契于中國藝術的智慧和神韻。中國藝術是溫暖的。它不是神性的道路,很少有形式的道路,頗好性情的道路。如中國最早的音樂理論作品《樂記》,即提出“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但“音”如何成為“樂”,它沒有直接講,而是轉換了一個角度,講:“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音。”在這里,顯然把主體性情的養成,視為藝術審美活動的必要條件。同時,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也把顏回、曾點等為代表的仁樂之境,視為生命成就的至美之境。而道家的宗師老聃,以“無”立根,以“虛”立基,對文明社會人性的功利自私、貪得無厭等給予了極為深刻的反思與警示。后學莊子,則鐘情于以真人真性對抗文明的功利與虛偽,構筑了超越生命形體之千變萬化和生命界限之短長有無的逍遙理想。中國文化的源頭,非專論藝術與審美,但卻以深厚的人文情懷和高曠的精神理想,將藝術、審美與人生緊密地連接起來了,人生的理想憧憬內蘊了藝術的追求與審美的情致。這種人生審美的生活思潮,雖歷經變遷,包括孔莊后學的曲解、歷代文人的俗化,都難絕其韻。魯迅、宗白華都高度評價了魏晉名士的藝術式生活,盛贊其鐘情山水、超脫禮法的個性人格正是對淺俗薄情的反動。人生審美與藝術生活的思潮,在20世紀上半葉,納中西滋養,從古代到現代,被郭沫若、梁啟超、朱光潛、豐子愷等重新發現與塑造。尤其是以梁啟超、朱光潛等為代表,將藝術審美生活相關聯,要求以美的藝術精神為生命和生活立基,倡導創造與欣賞、小我與大我、物質與精神、感性與理性相統一的審美人生精神,倡導一種遠功利而入世的審美人生態度。20世紀30至40年代,這種審美人生精神和審美人生態度,逐漸聚焦為“人生的藝術化”命題,對中國現代文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8]。無論西方唯美感性的傳統,還是中國人生審美的傳統,它們所主張的“生活的藝術化”,本都不是試圖消解藝術與生活。但是,西方唯美主義和中國人生審美,最后卻走了兩個不同的路向。如果說藝術性大體體現為形式性、技巧性、精神性三種的話,那么西方唯美主義主要以形式性見長,并最終由精神的反抗走向了精神的媚俗。中國傳統的人生審美,在莊子那里,已有行為之游和心靈之游的區分,分別關涉了技巧性和精神性的因素,而以逍遙游為代表的無待的精神翱翔,早已成為中國藝術精神的杰出寫照。作為日常生活審美化思潮最為重要的研究者和批判者之一,韋爾施提出“感性的精神化,它的提煉和高尚化才屬于審美”[5],盡管這只是一家之言,但無疑,在任何時代,我們都不可能將審美和藝術局限于個體的人的純粹感性,也不應該有超越于人的價值向度的形式和技巧。如果說,在微時代,道德的和政治的立場,不再那么明顯于前臺,那么,形式與技巧的背后,自然有資本和經濟來粉墨登場。微時代,給予我們最大的挑戰,或許就是技術—精神、感性—心靈、欲望—情性之間的迷瘴,不僅有審美為生活所吞噬的困惑,更有人消費自我的焦灼。在生活和人性的深處,我們如何實現精神、心靈、情性的體味、提升、建構?或許,生活的藝術化,它所構筑的情感信仰和價值張力,正是實用和理想、感性與理性、技術和價值、物質和精神之間的一條可能的人文通道。(責任編輯:陳娟娟)
參考文獻:
[1]陸群等.網絡中國[M].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1997.48.
[2]博客里一般寫什么內容?[EB/OL].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876627.html.
[3]羅江南等.年輪網絡日記[M].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5.
[4]金瑩.微時代·微傳播·微電影[N].文學報,2014-06-26,(02).
[5]沃爾夫岡·韋爾施.重構美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9、7、16、6、18.
[6]豐子愷.豐子愷文集(第5冊)[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523.
[7]吳其堯.唯美主義大師王爾德[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11.
[8]金雅.人生藝術化與當代生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