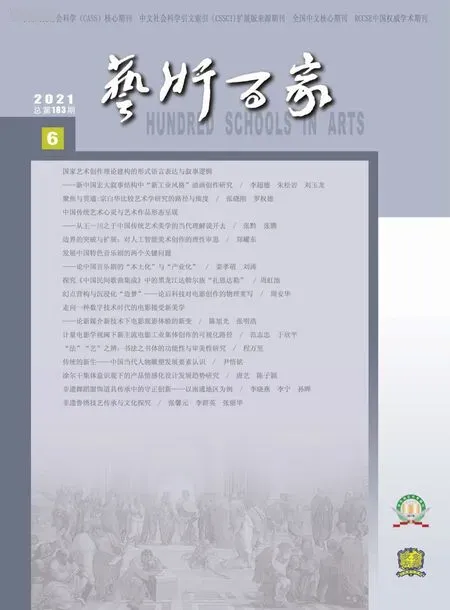藝術與歷史的奠基
郭文成+王廷信
摘 要:以現象學為切入點,海德格爾對藝術與歷史的追問可以理解為三個命題:首先,歷史作為形而上學史,這意味著歷史本性的遮蔽;其次,藝術作為形而上學的克服顯現為本性的歷史;最后,藝術為歷史奠基敞開了新的開端。以此,我們跟從思想的道路去深思當代藝術。
關鍵詞:藝術;歷史;海德格爾;藝術現象學;形而上學;真理;當代藝術;藝術思想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筆者近年來發表了數篇關于海德格爾的死亡現象學、技術現象學與藝術現象學思想的論文,其中關于藝術現象學的文章重點針對《藝術作品的本源》作了藝術與世界的關系的論述,其核心觀點在于把海德格爾的藝術現象學理解為世界性的,在此視域中藝術綻開于世界與大地以及真理的“之間”關系,由此,“藝術與世界、大地以及真理的親密關系得以描述,這構成了海德格爾獨特的藝術現象學思想。”[1]掩卷沉思之后,筆者深感所論及只是海德格爾藝術現象學思想的冰山一角,因此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在此,本文專門從藝術與歷史的“之間”關系來切入,試圖顯現海德格爾藝術現象學的歷史性維度。基于此種思路,文章將從三個方面展開:1.歷史的遮蔽;2.藝術的去蔽;3.藝術的終結與新開端。
一、歷史作為形而上學史對海德格爾而言,歷史是存在的歷史。存在的歷史不發生于思想的歷史之外,而是于其內。而思想的歷史自身表現為哲學的歷史,但是這樣的歷史只是形而上學的歷史。形而上學被理解為第一科學,因為它從事第一根據和第一原因。但是在海德格爾這里,形而上學既不是編纂學意義上的科學——即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也不是笛卡爾所講的哲學一個科目,即第一哲學;更不是我們通常所指的與辯證的、運動的、全面的相對立的靜止的、片面的、機械的思考方式和方法。同時也不是單指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即為存在者整體(physis)追尋根據、探求根據,尋找這個“元”(meta)。在海德格爾看來,形而上學是全部哲學和它的歷史,形而上學意味著:“存在的思想把于在場者和手前之物意義上的存在者作為為了向存在超出的出發點和目的,此超出同時又成為了回復于存在者。”[2](P.423)這里我們將從形而上學的基礎問題、基本樣式和基本立場三個方面思考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只是存在者而倒不是虛無存在?這是所有問題之中的第一問題。這個問題包含了形而上學思想的本性。因為“為什么只是存在者而倒不是虛無存在”的提問,它用這樣的一種方式思考存在者的存在,這種方式就是,思想從存在者出發,且超出此之外并又回歸于此。思想從存在者出發,這意味著存在自身已消失于視野。思想超出存在者之外,這意味著思想追尋著存在者的存在。思想復又回歸于存在者,這意味著,思想把作為第一根據和原因的存在者性說明存在者的根據。而這一事實是一切形而上學的思想道路——只思考了存在者,存在者的存在,而遺忘了存在自身——“形而上學以說明根據的設想來思考作為存在者的存在者”[3](P.374)。形而上學的基礎問題可以獲得形而上學的基本樣式:只要形而上學對存在者不僅以本體論的、神學的而且以邏輯的方式同樣本源地把握存在者的話。那么根據海德格爾,形而上學表明了它的“本體的—神學的—邏輯的”樣式。海德格爾也談到了形而上學的基本立場。一切形而上學的基本立場是由以下四方面得以規定的:“1.通過人作為人如何是其自身并且由此認識自身的方式;2.通過存在者向著存在的投射;3.通過對存在者真理的本質的界定;4.通過人在當時為存在者真理接受和給予‘尺度的方式。”[4](P.804-805)這四個方面說的實際上就是人、存在、真理及人與存在、人與真理的關系。古希臘的形而上學代表無疑是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的“ousia”,一般譯為“實體”,我們熟知的是他的“第一實體”和“第二實體”的區分,但是海德格爾將“ousia”理解為“在場性”,“第一位意義上的在場性乃是oti sein被表達出來的存在,即這樣—存在,實存。第二位意義上的在場性在ti estin中被追問的存在。即什么—存在、本質。”[4](P.1042)亞里士多德把第一位意義上的在場性理解為“實現”(energeia),這已經開啟了后來把“實存”看得高于“本質”的先河。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柏拉圖所思考的以觀念的方式存在的在場性就降到第二意義等級。無論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的分歧如何,他們由此奠定了后來西方形而上學的本性開端:“在場性的兩個方式。即觀念和實現,在它們的區分的交互作用中構成一切形而上學的基本結構,存在者本身的一切真理的基本結構。”[4](P.1045)當自然變為觀念時,邏各斯也變成了陳述。真理不再是自然的無蔽,而是正確性,即設想必須正確模仿作為原本和樣本的觀念。邏各斯不再相關于存在,而是相關于陳述。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笛卡爾進一步把真理解釋為確定性(Gewissheit),從而開啟了現代形而上學。對笛卡爾而言,形而上學的第一原理,一切定律中的定律即“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ergo sum)。海德格爾將笛卡爾的第一定律做了簡化:去掉了“故”和“我”,定律變成了:cogito sum(我)思想(我)存在。在此說的也不是“我思想”,或者是“我存在”,而是“設想”(Vostellen),“本質上已經向自身設想出來的設想,把存在作為已設想性,把真理作為確定性來設立。……設想的本性規定了存在和真理,但也規定了作為設想者的人的本性,以及這個標尺的類型。”[4](P.794)思想和存在的關系是思想和所設想的關系。在此不僅設想,而且所設想的必須被建立根據,因為這只是相關于根據的設想和表達。“根據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它必須送交給設想和思考的人。”[5](P.47)但是那思考的人在形而上學的歷史中,特別是在它最后的時代被設立為自我,自我自身說明根據和建立根據,于是自我獲得了它的絕對意義。“思想成為了我思。我思成為了:我本源地統一,我思考統一性(先行)。”[2](P.198)自我成為了所思的規定,也即設想規定了所設想的。笛卡爾的形而上學可以概括為:1.人成為唯一的主體(subiectum),成為一切設想和被設想者立足的基礎。2.存在性現在設想著主體的已設想性;3.真理與方法的改變,真理由正確性變為確定性,方法是對存在者的確保和征服行為的名稱;4.作為一般主體的人支配存在者整體,被建立為存在者整體的中心。[4](P.800-804)笛卡爾的哲學為人的解放奠定了形而上學的基礎。笛卡爾的定律確定了人的新地位,作為主體的人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由于這一轉變,歷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即現代。這個時代以人憑借自身的能力統治征服世界為根本特征。“什么是存在者”的問題變為關于真理的無條件的不可動搖的基礎的問題,轉變為真理的方法、道路問題。現代的真理即確定性,它確保一切存在者對主體而言的可設想性,把一切存在者確保為主體的對象。①
二、形而上學的終結與藝術的奠基形而上學是否有終結呢?海德格爾說尼采是形而上學的終結。盡管尼采曾批判過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但是“事實上,他與笛卡爾卻一致同意:存在意味著‘已設想性,即思想中的已設定性,真理意味著‘確定性。”[4](P.813)但是尼采不是簡單地重復笛卡爾,他以“權力意志”學說推進了笛卡爾的形而上學,并因此而完成現代形而上學。這是因為1.尼采把笛卡爾的“我思”追溯到本源的“我要”,把“求真意志”建立在權力意志的基礎上,因此,在尼采與笛卡爾的差異中,可以看到尼采在何種意義上被海德格爾稱為形而上學的終結。笛卡爾的主體是一般的思維主體,設想著的主體。但尼采的主體則充滿著欲望和激情,根本地講,是身體意義上的主體②。2.存在對笛卡爾而言意味著“已設定性”,可是尼采在存在之上設置了變化。變化高于存在,變化是權力意志的基本特征。盡管這樣,變化就其為權力意志所設定的生命提高的條件而言,仍屬于笛卡爾的“已設定性”。3.笛卡爾把真理理解為確定性,尼采認為真理就是信仰,信仰則是“持以為真”,“持以為真”是對變化的確定,此乃生命自身保持的必須。在方法上,尼采以身體為世界解釋的主導線索取代笛卡爾的心理和意識。4.對尼采而言,不僅已設想者是人的一個產物,而且每一構形和印痕都是人的產物和所有物。人成為任何類視角的無條件主宰。[4](P.821-822)從笛卡爾開始的現代西方形而上學,是主體性的形而上學。康德、黑格爾和尼采的形而上學都保持著這一基本特性。與笛卡爾、康德的有限主體相比,黑格爾和尼采建立了絕對的無條件的主體性,尼采將權力意志帶向無條件的有效性。因為權力意志的主體失去了任何限制,它本身就支配著任何限制和無限制。權力意志的主體性就是身體的主體性。尼采的“權力意志的無條件的主體性的形而上學”把現代主體性推到了它自身的邊界。因此,現代形而上學走向終結。在西方形而上學一般的意義上,當尼采把價值思考為使權力意志可能的條件時,事實上完全以柏拉圖的方式來思考存在。尼采以顛倒的形式顯示出他和柏拉圖的親緣關系,同時他也以這種方式完成自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形而上學。因為在海德格爾看來,尼采同樣形而上學地思考了“什么—存在”和“這樣—存在”的基本區分。權力意志說的是存在者“是”什么(was),同一物的永恒輪回命名為那個如何(wie)。通過顛倒,尼采賦予柏拉圖的變化以權力:變化比存在更有價值。從柏拉圖到尼采的形而上學圓圈就此合閉,合閉發生在這樣一個歷史瞬間,“在這一瞬間形而上學的本性可能性已經耗盡”[4](P.832)。但什么是形而上學的終結?終結并不意味著否定性的終止,也不意味著思想的徹底放棄或無能。“終結一詞的古老意義如‘地方一樣,‘從一個終結到另一個終結叫做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3](P.375)形而上學的終結指的是形而上學最大可能性的完成和聚集,“形而上學的完成之所以是一個終結,只是因為它歷史性基礎已經過渡到另一端。但這另一端并沒有跳離第一開端的歷史,并沒有否認曾有,而是回到第一開端之中,并且隨著這種回歸而接受另一種持存性。這種持存性并不取決于對任何當前的保持。它適應于對未來的保存。”[4](P.668)第一開端首先指的是西方歷史的開端。存在的歷史在第一開端發生為形而上學的歷史,在第一開端的歷史中,已經得到思考的是存在者、存在者的存在——什么存在和這樣存在。第一開端經驗和設立了存在者的真理,但是沒有追問真理自身,因為“作為為了自身遮蔽的”林中空地,存在者作為存在者必然性地超出一切,第一開端發生為存在的遺忘。但是第一開端,除了思想最后的可能性之后,還存在思想最初的可能性嗎?這最初的可能性就在開端性那里,只是這個開端處還是遮蔽的。因此,最初思想的可能的樣式是回歸。存在歷史的思想由此從形而上學處回歸。“回歸從形而上學移向形而上學的本性”[6](P.41)。此本性是第一開端中的開端性它表明為要去思考的,也即作為那在已思考中思考尚未思考的。如果思想要思考那尚未思考的且值得思考的話,那么它將開端性地思考并將從第一開端走向另一開端。而這個“另一開端經驗存在的真理并追問真理的存在”[2](P.179)。由此,第一開端向另一開端過渡,意味著另一開端不能簡單地揚棄和拒絕第一開端,相反必須把第一開端的歷史把握為曾有。曾有的思想和未來的思想聚集于思想的當前,憑借對存在者存在的思考,曾有的思想為向另一開端的過渡悄然準備了歷史性的基礎。另一方面,另一開端也不能重復和繼續言說第一開端的思想。唯有思想的歷史性的對話能從另一開端導向第一開端,這是從第一開端到另一開端唯一的過渡。這種過渡就是對形而上學的克服。克服形而上學意味著,不能憑一己意愿,因為“意愿知道始終是以自我意識遮蔽的狂妄,它基于自身制造的理性和它的理性性”[7](P.13)。它阻礙思想使思想變得不可能。思想應學習放棄,放棄形而上學的思考;同時采取“返回的步伐”,返回那值得思考的卻又遺忘了的存在。在此,藝術、詩與詩意語言的意義得以凸顯,因為它們是非形而上學的。因此,形而上學的克服一方面意味著存在遺忘的經驗,在此存在的遺忘中,自身遮蔽的存在沒有被思考;另一方面是真理的建立。在此,作為為了自身遮蔽的林中空地顯現于光天之下。此兩者完成于存在歷史的思想中。③但只要歷史是存在的歷史,是真理發生的歷史,而不是歷史學意義上的過去了的歷史事件,正如海德格爾所指出的歷史性不能從歷史學來理解,因為所有的歷史(Geschichte)都是此在的命運(Schicksal)的聚集,是存在之天命(Geschick)的派送(schicken)。人的行為之所以是歷史性的,就在于他應合了存在天命(Geschick)的派送。“這里海德格爾的命運與天命的同一與區分在于:它們都與此在的歷史性相關,命運側重于此在作為個體的本真生存,而天命是作為民族或人類的此在整體本真的生存。”[8]而藝術自身又是真理發生的諸方式之一,那么從存在的歷史角度思考藝術就是必然的。藝術與歷史的關系表現為藝術為歷史奠基。迄今為止,那已有的存在的歷史是形而上學的歷史,憑借于它只思考了存在者整體和存在者的存在,形而上學的歷史被海德格爾稱為第一開端的歷史。第一開端為另一開端的到來悄然地做著準備。在傳統形而上學終結的地方,思想準備著形而上學的克服,而形而上學的克服意味著思想由第一開端向另一開端的過渡,憑借于思想思考那已思考中尚未思考的而又值得思考的“存在”本身。④在存在的歷史中,藝術奠定形而上學歷史每個時代的本性;存在的真理自行設定于藝術作品中,憑借于藝術作品敞開了“為了自身遮蔽的林中空地”與遮蔽之間的爭端,藝術(偉大的藝術)為另一開端的歷史奠定基礎。在這里,沿著存在歷史的發生,我們將要追問的問題是:藝術如何為第一開端奠基?偉大的藝術如何為另一開端的將來奠基?海德格爾說:“思想之箴言唯有思想與箴言之所說的對話中才得到翻譯。而思想乃是作詩……存在的思想乃是作詩的源始方式。在思想中,語言才首先達乎語言,也即才首先進入其本性。……無論是在這一寬廣的意義上,還是在詩歌的狹窄意義上,一切作詩在其根本處都是運思。思想的詩性本質保存著存在之真理的運作。”[9](P.19)對海德格爾而言,偉大的藝術就是真理在作品中的顯現。比梅爾認為傳統的探討方式是在最后才把美與真理的關系問題提出來⑤,而在海德格爾那里則恰恰相反:規定藝術作品的出發點就是真理的發生,而藝術作品本身是用來說明這種發生的。[10](P.100) “吟唱和思想是詩作的相鄰樹干。”[11](P.85)思想和詩作是歌聲般的,因為它們是這樣一種東西,即它不僅只是擁有一聲音,而且不如說是它首先甚至必須唯一作為聲音而存在。因為“思考的詩作在事實上是存在的形態學,它給存在道說出其本性的地方”。[12](P.84)在此,思想和詩作、思想和吟唱同屬一體。由此,我們得以思考在存在的歷史中,也即在真理的發生中,藝術如何相關于真理?藝術如何為歷史奠基?我們將著重在第一開端的開端之處和終結之處思考藝術與歷史、藝術與真理的關系。海德格爾指出,古希臘的神廟單樸地置身于巨巖滿布的巖谷中,它包含著神的形象,正是神廟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關聯的統一體,同時使這個統一體聚集于自身周圍;在這些道路和關聯中從人類存在那里獲得人類命運的形態。這些敞開的關聯所作用的范圍,正是這個歷史性民族的世界。在神廟這個作品中敞開了什么?——世界、大地、自然和人類的歷史,即存在者整體的無蔽。鑒于此類似的作品,關于第一開端的歷史與藝術的關系,海德格爾做出了這樣的一般性的描述:“總是在作為存在者自身的存在者整體要求奠基以進入敞開性時,作為設立的藝術就進入它的歷史性本性。在西方,作為設立的藝術最初發生在古希臘。那是后來叫做存在的東西被決定性地設置入作品之中。”[12](P.76-77)當存在者要求進入存在者整體的無蔽時,藝術應合這個要求打開新的世界實現真理形態,并因此為存在者整體的敞開建立基礎,憑借提供存在者整體敞開的基礎,藝術獲得其歷史的本性規定。“在西方命運的發端處,各種藝術在希臘登上了被允諾給它們的去蔽的最高峰。藝術乃是一種唯一的,多樣的去蔽。藝術是虔誠的,是詩意,也即是順從于真理之運作和保藏的”。[3](P.315-316)而“從時代上思考,存在的劃時代的開端存在于我們稱之為希臘的東西之中。這一本身要在時代上得到思考的開端乃是從存在而來的存在之中的命運的黎明”。[9](P.27)在這個“存在命運的黎明”,設立入作品的是怎樣的真理呢?在前蘇格拉底時代,后來西方命運所系的“eon”得到決定性的思考并產生作用。它不僅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的箴言詩中而且還在荷馬史詩、索福克羅斯的悲劇中得以表達。在海德格爾看來,西方思想史上最古老的箴言——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談論的就是“多樣性存在者整體。”[9](P.20)這個存在者整體是一切在場者,以始終逗留的方式本性化:諸神和人,神廟和城市,大海和國家,飛鷹和長蛇,樹和灌木,風和光,巖石和沙土,晝和夜。海德格爾破除了對這一箴言后來流行開來的意見:亞里士多德認為的自然哲學、尼采認為的箴言與道德的、法律的因素相關。而從存在者整體的角度解說最古老的箴言,海德格爾認為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一切在場者的本性要素是“chreon”。海德格爾將之冒險地翻譯成德語“Brauch”,并將之解釋為把某物交付給其本真的本性,并且把作為這樣一個在場者的某物保持在保護著的手中。“Brauch”在德語中原指的是“需要、使用”的意思,Brauch需要并使用存在者,把在場者交付到它的在場中去讓其逗留于存在者整體的無蔽之地。Brauch讓在場者在其逗留中本性化的同時劃分并給予出在場者在其逗留中的份額。⑥可以看到,海德格爾借Brauch思考的是在場者與在場之間的關系,只是在他看來,阿那克西曼德的“chreon”對在場者與在場關系的思考只是暗示性,而且是模糊的暗示性的。阿那克西曼德并沒有清楚地思考在場與在場者的區分。前蘇格拉底的哲學中在場本身沒有與在場者區分開來,面對這種區分的未思是對存在與存在者區分的遺忘,支配了后來形而上學的本性。在“藝術在本性上都是詩”[12](P.75)的意義上,古希臘的藝術同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一道,作為開端性的作品,在場者整體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被設置入其自身的在場之中,作為詩作的藝術為這樣的開端奠基。endprint
三、藝術的終結與新開端據上述,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定律確定了人的新地位,與之相應的是形形色色的人類學思想產生。“人類學是這樣一種對人的解釋,它根本上已經知道了人是什么,從而從來不能追問人是誰”。[13](P.153)與之相應,美學和藝術隨著人類學的發展,“體驗美學”、“體驗詩學”紛紛出現,體驗似乎以人類學的思想所固定所要求的方式出現。“人體驗藝術的方式,被認為是能說明藝術之本質的。無論對藝術享受還是對藝術創作來說,體驗都是決定性的源泉。”[12](P.79)伽達默爾指出把美學建基于心靈能力的主觀性之上,卻是開始走上危險的主觀化之路。如果我們希望確定海德格爾對藝術作品本性的沉思的出發點,就必須清楚地記得,唯心主義美學,即賦予作品以特殊意義并將之當作絕對真理的非概念的理解法則的美學,已被新康德主義哲學掩蓋了很久。而在西方傳統中最完備的、最偉大的美學體系中,黑格爾宣告了藝術的終結,偉大的藝術迎來了它終結的時代:“在那個歷史性的瞬間,亦即在美學獲得其形成過程中的最大的可能高度、廣度和嚴格性之際,偉大的藝術趨于終結。”[4](P.91)那么,如何理解藝術的終結?藝術的終結中的藝術在此只能指的是偉大的藝術、真正的藝術(從藝術史來說,它偏重于指的是古典性的藝術),其并非意味著新的藝術作品和新的藝術思潮的終結,在黑格爾意味著藝術對我們的歷史性此在來說不再是決定性的真理的一種藝術和必然的發生方式。但是偉大的藝術的終結并不是人類學和美學的過錯,在海德格爾看來黑格爾的偉大正是在于美學思考并言說了偉大藝術的終結。藝術的終結源于藝術已經遠離了其本源。對此,海德格爾具體考察了希臘藝術與其本源的關系。在古希臘,一切藝術都源于Physis。在《形而上學導論》中,他指出這個詞“說的是自身綻開(例如玫瑰花開放),說的是揭開自身的開展,說的是在如此開展中進入現象,保持并停留于現象中。簡略地說, Physis就是既綻開,又停留的強力。”[14](P.16)按照海德格爾的詮釋,“Physis”在希臘思想中的本義是“涌現”(Aufgehen)、“出現”(Ent-stehen),是“生長”、“使成長”。這里Physis的本質特征被界定為出場與持續,后來此詞被譯為“自然”(Nature),但它的希臘原義仍是“存在”。因此可以說,希臘藝術源于存在,源于存在對人的言說。由此希臘藝術服從了存在的命運:建立世界與展示大地;從而為希臘人提供了歷史性生存的家園。因此,從歷史現象學的意義上說,海德格爾的“藝術是真理自行設入作品”意味著存在之真理是藝術的本源。然而,中世紀藝術的本源不再是“存在”,而是上帝的啟示;近代藝術的本源也非“存在”,而是理性;現代藝術的本源也不是“存在”,而是“技術”,其發源地是“技術世界”,因此現代藝術在根本上漂離了它真正的本源而成為技術世界的“文化工業”之一。在此,這些藝術不再是源于存在的真理的事情,從而也不再建立世界和展示大地,因而也不再是生存的歷史性本源。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認可黑格爾的一般藝術終結論:“我們不再認為藝術是真理獲得自我存在的最高樣式。……就其最高秉性而言,藝術對于我們而言是一種過去的事情。”[12](P.80)藝術的終結意味著貧乏時代與世界黑夜的到來。海德格爾認為,在貧乏的時代“里爾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詩意地經驗并承受了那種形而上學之完成而形成的存在者之無蔽狀態。”[12](P.98)面對貧乏時代的詩人的先行者荷爾德林的作品,海德格爾提出:“冷靜地運思,在他的詩所道說的東西中去經驗那尚未說出的東西,還將是而且就是唯一的急迫的事情。這是存在之歷史的軌跡。”[12](P.96)顯然,關于貧乏時代的藝術,對于海德格爾而言,僅僅把體驗看作是美學和藝術的死亡的根源是不準確的,因此他很嚴肅又慎重地指出:“一切都是體驗,但也許體驗卻是藝術死于其中的因素。”[12](P.79)需要注意的是“也許”并非就是“肯定”、“確定”,這意味著在體驗之外或許甚至應該存在著更深刻更本源地導致藝術死于其中的因素。那么這個藝術自身經驗到了的,而我們需要在“詩所道說的東西中”去經驗和思考的那“唯一的急迫的事情”是什么呢?“回顧形而上學史可以清楚地知道,近代形而上學將自柏拉圖以來的正確性真理進一步把握為確定性真理,而存在者經由特殊的存在者——人,被設定為可以通過計算加以控制和直觀的對象。藝術完成的是確定性真理的設置。藝術建立的真理乃是存在者整體的無蔽性。”[15](P.108)它沒有觸及到給出無蔽性的林中空地:“林中空地擁有其臨近樹林的邊界,此樹林環繞了林中空地的周邊。但海德格爾所說的這樣一個敞開的中心,從存在者方面來思考,它比存在者更有存在性。這意味著這個敞開的中心并不是真正的現實地就在存在者的中間,并被存在者包圍,相反這個中心像是我們所不知道的虛無是林中空地,這個發光的中心環繞著存在者。這里突出的是林中空地與虛無的關系。”[156](P.54)因此當存在者整體轉變為由主體設立的對象時,存在者真理達到最極端的可能性,由此偉大的藝術走向衰亡。后來的德國學者貝爾廷(Hans Belting)與美國學者丹托(Arthur C. Danto)也提出了藝術終結論:現代主義藝術終結了。丹托和貝爾廷共同看出,一個截然不同于現代藝術的新事物出現了:當代藝術。丹托在1984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藝術終結”(The End of Art)的文章,同樣指出,一向支持藝術史的敘述框架,到壽終正寢的時候了。藝術應該進入一個超越出這框架的“后歷史時期”——也就是去掉這敘述框架的時期。由此可見,他們的藝術終結論是藝術史式的,不是藝術哲學式的。在此,海德格爾的藝術終結論體現出現象學的歷史性透視。綜上,藝術的終結可以理解為藝術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藝術的終結指的是偉大藝術最大可能性的完成和聚集,藝術的完成之所以是一個終結,只是因為它歷史性基礎已經過渡到另一端。但這另一端并沒有跳離第一開端的歷史,而是回到第一開端之中,并且隨著這種回歸而接受另一種持存性。
四、結語在黑格爾所斷言的偉大藝術之終結時代,以及在海德格爾所稱的貧困時代,藝術何為?藝術還能否為將來的另一開端奠基?答案是:“真正說來,藝術為歷史建基;藝術是根本性意義上的歷史。”[12](P.77)但海德格爾的藝術思考沒有到此為止,他的深刻性在于:對于已思考的現代藝術而言,其中蘊涵著未思考的“未來藝術”因素。當然,“過去的藝術”(希臘藝術)已經死亡,現代藝術導致了時代的貧乏;但未來藝術的種子正在悄悄生長。“這種藝術從現代藝術而來,但又克服了技術構架的威脅,從根本上它是一種‘詩意藝術或者稱為‘詩;這種藝術使人與存在的關聯的重建有了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藝術的本性是詩,因為藝術不是被它的過去和現在形態所規定,而是被未來的形態決定:未來藝術必是詩,其使藝術成為藝術本身,由此藝術成為了生存的歷史性本源。”[17]然而在當下,海德格爾的藝術沉思是否還具有效性,即藝術現象學的思想仍可以解釋當代藝術?從當代藝術的實踐以及美學理論的發展來看,海德格爾的藝術沉思也只是現代性的,它具有其鄉愁性的限度。“而當代藝術的邊界是模糊的,這是由于藝術概念永遠在生成之中;當代藝術的邊界仍然有一個存在的基礎,這一基礎就是我們當下的生活世界。此生活世界是一個技、欲、道游戲的多元世界,由此我們說當代藝術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我們應該防止當代藝術成為‘技術主義、物質主義、虛無主義的俘虜,使之真正成為建設新的心靈的力量所在,從而給當代人的靈魂以居住的家園。”[18]綜上,正如筆者曾經所認為的“海德格爾的死亡現象學思想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它永遠在召喚有心人去傾聽死亡對于建構和諧生活的意義。”[19]本文的意義在于給出海德格爾藝術現象學的歷史性維度,召喚有心人去傾聽藝術與歷史的生成關系。(下轉第179頁)(責任編輯:陳娟娟)
① 威廉·巴雷特認為胡塞爾與在現代哲學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笛卡爾的觀點仍然一脈相承,而海德格爾思想的整個意義在于努力克服笛卡爾。參閱[美]威廉·巴雷特著,段德智譯《非理性的人》,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13頁。
② 從身體的角度,尼采必然談到笛卡爾意義上的主體的死亡,他稱“主體”是虛構并要求放棄“主體”、“客體”以及實體等概念。參閱尼采著,周國平譯《偶像的黃昏》,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
③ 羅蒂認為海德格爾克服形而上學是困難的。他說海德格爾只有一個主題:克服形而上學的需要。一旦這個主題變成似乎是自欺性的了,他就只能沉默不語了。參閱理查·羅蒂《哲學和自然之鏡》,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87頁。
④ 黃裕生認為可以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克服形而上學:一方面是消解作為存在者原則的“根據律”。另一方面是人放棄主體身份而成為會死之人。參見黃裕生《時間與存在——論海德格爾哲學中的時間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95頁。
⑤ 哲學史上由柏拉圖引起的藝術與真理之爭,可以參閱斯坦利·羅森《哲學與詩之爭》,英文本,紐約,1988年版,第一部分“哲學與詩之爭”。
⑥ 鄧曉芒認為海德格爾的這個理解是擬人化的翻譯,可以將它解釋為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與善。參見鄧曉芒《海德格爾“存在的末世論”的解釋學意義——〈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再解讀》,《哲學研究》,2006年第7期。
參考文獻:
[1]郭文成.海德格爾的藝術現象學思想[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5).
[2]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GA65)[M]. Indiana. 1999.
[3]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M]. Edi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New York:Harper&Row,1977.
[4]Martin Heidegger著,孫周興譯.尼采(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5] Martin Heidegger. Der Satz vom Grund[M].Frankfurt am main. 1997.
[6]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y and Difference[M].Translated by J.Stambaug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7]Martin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M].Translated by Peter D.Hertz.Harper& Row. Publishers. Inc.New York. 1982.
[8]郭文成:沉思高技術的挑戰——兼論海德格爾的技術現象學思想[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6).
[9]Martin Heidegger.Early Greek Thinking[M]. 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 1975.
[10] [德]比梅爾著,劉鑫、劉英譯.海德格爾[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1]Martin Heidegger.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GA13)[M].Frankfurt am main.1983.
[12]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M].Translated by Albert.Hofstadter.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ishing House 1999.
[13]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QCT)[M].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New York:Harper&Row. 1977.
[14]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