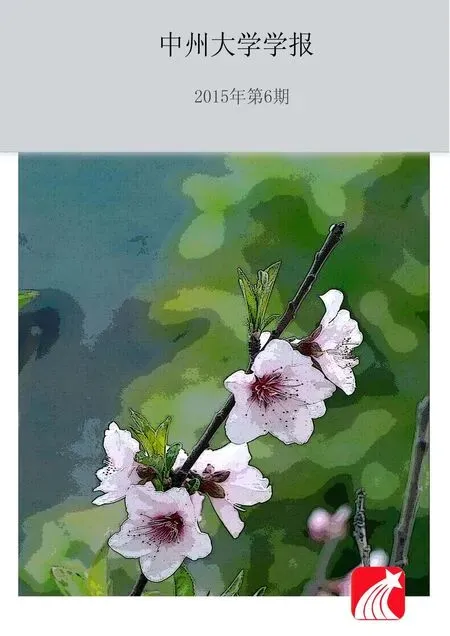簡析《白鹿原》中女性的生存境遇
惠 萍
(河南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1)
?
簡析《白鹿原》中女性的生存境遇
惠 萍
(河南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1)
《白鹿原》塑造了一大批生動活潑的女性形象,細致刻畫了傳統女性面臨的生存困境,同時也書寫出她們被忽視、被壓抑的歷史。她們或消極順從命運的安排或積極追求個性解放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但是結局都一樣悲慘,只有少數個別女性能夠善始善終。《白鹿原》既是一曲傳統女性的悲歌,也是一曲傳統女性的挽歌。
《白鹿原》;女性生存境遇;自我救贖;個性解放
隨著2012年9月同名電影在中國大陸公映,當代作家陳忠實的長篇小說代表作《白鹿原》再次引起人們關注。這部長達50萬字的作品初版于1993年6月,修訂再版于1997年,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在電影是否把一部史詩般的民族秘史改編成了一部“田小娥的情愛史”的一片質疑聲中,筆者再次捧讀修訂版的《白鹿原》,隨著翻動的書頁慢慢走近白鹿原,走近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男男女女。這部陳忠實準備死后“墊棺作枕”[1]33的書所展現出的厚重與悲壯足以引發我們方方面面的思考,本文僅就《白鹿原》中的女性生存境遇來談談傳統女性自我救贖的可能與尷尬。
一、《白鹿原》傳統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白鹿原那片綿延數千年的土地上,男權統治下的女人大都“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2]13-14,而在白稼軒父親的眼里,女人的價值略等于“一匹騾駒”[2]4。在這種普遍的集體無意識里,女人首先是繁育后代的工具和家庭事務的勞力,所以才有了白稼軒娶過七房媳婦六死一生傳奇婚姻的到來。白稼軒父親白秉德即將離開人世時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要白稼軒答應他去世后趕緊迎娶第五任媳婦。而母親則在父親去世后就催促,“不要等了,等也是白等,家里太孤清了;況且她一個人單是掃屋掃院洗衣拆被做飯都支應不下來,再甭說紡線織布等家務了”[2]11。白家得知孝義不能生育的消息后,甚至不惜偷偷讓孝義媳婦和兔娃借種生孩兒。其次,女人的另一功能是充當性工具。田小娥就是年紀一大把的郭舉人娶來滿足自己特殊需求的養生工具,還有土匪窩里的白牡丹和黑牡丹,地位也大抵如此。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地位顯而易見是被忽略、被輕視的。她們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過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生兒育女的生活,很少有人關心她們的尊嚴和幸福。她們中很多人都沒有自己的名字,嫁人之后隨夫姓加上自己的姓以及一個毫無感情色彩的“氏”字,如白趙氏、朱白氏、鹿賀氏、鹿冷氏等。書中顯示在白稼軒引以為豪壯的七房媳婦里只有第七房媳婦白吳氏仙草有名字,其余來自白鹿原附近東、西、南、北原的六房媳婦均沒有名字。在開頭長長的介紹這些媳婦們的敘述中,多是提到村名、家族姓氏和家庭經濟狀況,這些遠比女性本人更能決定有無與大戶人家白家聯姻的可能。頗有聲望的村醫冷先生的兩個女兒在書中也沒有自己的名字,她們一個是發了淫瘋病而被父親毒死的鹿冷氏,一個是不太機靈但還算能夠顧得住場面的白冷氏,大家口中的二姐。
即便在一般家庭里看似正常的女性也未必就能被關注,更談不不上與男子平等。比如,看似沉靜幸福的仙草。當她獨自在家生下女兒白靈后,碰巧回來的白稼軒趕緊給她燒水端水,以至于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因為這是她進這個門樓以后男人第一次為她燒水端水。而鹿三媳婦鹿惠氏(在第六章卻說是鹿張氏[2]80,也許是作者無心之失,但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作者也不甚在意鹿三媳婦到底姓啥,我們只要知道說的是鹿三媳婦就行了),在鹿三準備殺田小娥而磨梭鏢時問他干什么,鹿三沒有回答,她就不敢再繼續問下去,直到小娥托夢才端曉緣由,而且“鹿三說不進家門就不進家門……”
可以說,《白鹿原》中女性被忽略、被壓抑的歷史不是一兩個人的歷史,而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所有女性的不平等史。
二、遵從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孝文媳婦、冷家大女兒和孝義媳婦
書中涉及到的女性,不管詳略加起來有二三十個,其中絕大多數是遵循傳統禮教的普通女性,她們從生到死、生生死死,了無波瀾,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但還是有那么幾個,她們平靜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卻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比如孝文媳婦、冷家大女兒和孝義媳婦。
白孝文直到結婚前對兩性關系都懵懂無知,是孝文媳婦啟蒙了他。然而雖是初享云雨之歡的孝文不愿節制,孝文媳婦卻受到全家成人的側目,奶奶對她的口頭告誡不止一次,孝文媳婦難堪卻奈何不了孝文。更難堪的是,因孝文與小娥糾纏在一起,白稼軒讓小兩口另立門戶,孝文不但沒有改變,反而因少了父母約束更加肆無忌憚。分家后白孝文賣地賣房,她都不見分文。沒有糧食,兩個孩子被領到公婆處吃飯,而自己最后卻被活活餓死,臨死她走到白稼軒的面前控訴 :“爸,我到咱屋多年了,勤咧懶咧瞎咧好咧你都看見。我想過這想過那,獨獨兒沒想過我會餓死……”[2]318這是對白孝文的控訴,也是對以白稼軒為代表的封建家長的冷酷無情的控訴,更是對殺人不眨眼的封建禮教的控訴。
冷家大女兒鹿冷氏在嫁到鹿家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明白過來鹿兆鵬不喜歡自己,等她明白一些的時候卻又沒有足夠的勇氣沖破牢籠,既缺乏田小娥式的毫無顧忌,也缺乏白靈那樣的機靈和學識,只有在漫長的歲月中郁郁寡歡。沒有人關心她,也沒有人給她指點,即便是在這塊土地上以善解人們身體上的疾病痛苦而著名的父親也沒有給予她足夠的關心和愛護。最后,無可排遣的孤獨寂寞以及難以遏制的抑郁和情欲交織在一起促成了她的瘋癲。而此時婆家和娘家真正關心的不是她受傷的心靈以及她悲慘的生活現實,他們關心的僅僅是家族的面子問題。為了不讓她再發瘋說胡話,親生父親冷先生用藥結束了她的生命。臨死前由于藥物的作用,她說不出話來。如果能夠像孝文媳婦那樣說話,想必她會說:“想到過這想到過那,獨獨沒有想到會被親生父親毒死。”然而彼時的死亡,告別這個冰冷的世界對她何嘗不是一種解脫?
如果說孝文媳婦和冷家大女兒的鮮活生命被封建禮教所吞噬恰好對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古訓的話,那么孝義媳婦所受的“屈辱”也暗中對照“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教條下女性的悲慘命運。孝義媳婦是白稼軒迎娶到白家門里三個兒媳婦中最稱心最完美的一個。孝義媳婦模樣周正、落落大方。正是在娶孝義媳婦時,書中安排白稼軒這個白鹿原上的族長對女性之于家庭的重要性作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闡述:白稼軒“閑時研究過白鹿村同輩和晚輩的所有家庭,結論是所有男人成不成景戲的關鍵在女人。有精明強干的男人遇著個不會理財持家的女人,一輩子都過著爛光景;有仁義道德的男人偏配著個粘漿子女人,一輩子在人前頭都撐不起筒子;更不要說像黑娃拾爛菜幫子一樣拾掇下的那種貨色了,黑娃要是有個規矩女人肯定不會落到土匪的境地”[2]490。然而這個無可挑剔的媳婦進門后,讓白家人發愁的是沒有為白家添一男半女,最終弄清楚問題不在女方而在孝義,遂在家人的安排下向兔娃借種生下了孩子。孝義媳婦在這其中所受的屈辱書中沒提,但“無可挑剔”的孝義媳婦在這個問題上即使有怨言又何嘗能正常表達呢?
孝文媳婦、冷家大女兒和孝義媳婦,沒有一個不是“乖乖女”,遵父母之命、依媒妁之言,過著千百年來女性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普通生活。她們遵從封建禮教,相信救贖就在其中,因而沒有任何反抗,不承想封建禮教卻一次又一次讓平凡善良的她們“乖乖”地成為犧牲品。是啊,“這些女人用她們活潑的生命, 堅守著道德規章里專門給她們設置的‘志’和‘節’的條律, 曾經經歷過怎樣漫長的殘酷的煎熬”[3]49。
三、追求個性解放的先行者:田小娥、白靈和小翠
筆者不是那么在意電影版的《白鹿原》是否被改編成了“田小娥的情愛史”,因為在有限的電影表達時段里,要充分展現半個多世紀白鹿原的歷史畢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兒,但電影舍棄掉白靈這個女性形象還是有些遺憾的。《白鹿原》一書中個性比較突出、著墨最多的兩個女性是白靈和田小娥。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主動還是被動,她們是兩個走在追求個性解放前列的女性典型。事因難能,所以可貴。
田小娥和白靈都是反叛傳統、追求個性解放的先行者。但田小娥是迫于時世、源于本能的反叛,是不自覺的反叛。父母自顧把她許給郭舉人做小妾,而且也不受待見,主要的事情就是每天在郭舉人大老婆的監督下負責給郭舉人“泡棗”。而她的出場也是在這項不那么能見人的活兒被長工嚼舌頭根兒的“臥談會”上被帶出來的。直到遇上重情義的黑娃,田小娥才開始了自己對幸福的追尋。但命運一波三折:偷情被抓,被休回娘家;黑娃帶他回家,既不被祝福、也不讓進祠堂;村口窯洞寄生,短暫幸福生活因黑娃革命而中斷;為救黑娃被鹿子霖霸占,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被鹿三殺害,死后“報復”而被塔鎮骨灰。當她擺脫小妾的屈辱和黑娃自由戀愛過上“吃糠咽菜”也愿意的生活時,怎么也沒有想到后來會成為被白鹿原上人們所不恥的“婊子”。她委身鹿子霖一方面有為救黑娃被鹿利用的原因,一方面也有黑娃一時回不來而沒有經濟來源的考慮。后來跟孝文在一起可能有那么一點點感情的原因,但是也不能否認這里面的經濟因素:白孝文寧肯賣掉房子和土地也要把錢給她,與此對照的是白孝文的妻子被活活餓死(盡管一開始他不知道她會餓死)。盡管田小娥死后控訴“我到白鹿村惹了誰了?我沒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沒偷扯旁人一把麥秸柴禾,我沒罵過一個長輩人,也沒搡戳過一個娃娃,白鹿村為啥容不得我住下?”[2]462也不能否認她在追求個性、實現自我救贖的過程中只能利用自己的美色,在經濟不獨立的情況下以此作為對抗這個世界的唯一武器,但是她與命運抗爭了,即便沒有足夠的能力。
白靈則帶著先天的優越條件追求自己認定的幸福:出生的時候“一只百靈子正在庭院的梧桐樹上叫著,尾巴一翹一翹的”[2]76-77。她得到了全家人的鐘愛,被朱先生認為“習文可以治國安邦,習武則能統領千軍萬馬”[2]402。她是新學堂里走出來的女學生,是有意識地、自覺地追求個性解放:為了上新式學堂,不惜把刀架在脖子上逼白稼軒讓步;為了退婚,不惜和家庭決裂;發動學生起事兒,在大庭廣眾之下向反動者扔磚頭;和兆海私定終身,卻又因政見不同與兆海分手轉而愛上同黨兆鵬,全然不以兆海兆鵬的兄弟關系而掩藏自己的感情。她是“革命”的“寧馨兒”,是活潑的、生動的、福佑白鹿原的白鹿精靈。她去世時好幾位親人都夢到了白鹿,卻是委屈的白鹿,流淚的白鹿。她沒有被敵人投井或活埋、也沒有被敵人的子彈擊中,卻慘死在自己人手之中。她的追求給自己開了個玩笑:命運不但讓追求個性解放的她背叛自己的家庭,逃離了世俗的婚姻,也背叛了初戀情人;向往革命卻最終為革命獻身,成為革命的祭品。雖然她有鹿鳴這個孩子,應該說也算留下了希望,但事實卻證明:雖然她有追求個性解放的能力和資本,但自我救贖之理想的實現仍然極為遙遠和虛無。
書中還塑造了一個敢于追求愛情的小翠。文中對小翠著墨不多,但同樣驚心動魄: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小翠是一個木匠師傅的女兒,因為被人看到和喜歡的人的曖昧情景并報告給了夫家,夫家不動聲色地把她娶進門,第二天便到大街上羞辱她。夫家用自己獨特的方式狠狠地“報復”了這個天真女子的“不忠”。過門第二天,聽著外面的喧嘩,小翠在婆家上吊死了——僅僅因為一次“曖昧”,世間種種便都與她無關了。
田小娥、白靈,包括小翠們的反抗都可視為被封建禮教重重帷幕所包圍的女性試圖自我突圍的一種大膽嘗試,是沉沉暗夜所散發出的希望之光。她們是追求個性解放的先行者,以生命為代價向封建禮教進行了有力的控訴。她們悲慘的結局和遵從封建禮教的女性一樣令人唏噓。陳忠實“以她們的悲劇有力地批判了傳統仁義文化陰暗、殘忍的一面, 使人們對傳統文化產生質疑。小說以她們的反叛呼吁現代文明的發展和人們對新文化的追求。文化沖突讓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 也展示了文化進步的艱難”[4]89。
四、男權社會下的極個別善始善終者:白碧玉和高玉鳳
考察《白鹿原》傳統女性的命運,人們往往關注田小娥、白靈等個性鮮明的形象而忽略一些看似平常的人物,而這些看似平常的人物也是構成白鹿原女性生存圖譜的一部分,因而有著獨特的寓意和作用。比如白碧玉和高玉鳳,她們是《白鹿原》中男權社會下少有的能夠善始善終的傳統女性形象。《白鹿原》中有太多無名的女性,人們也許一下子還反應不過來這兩個人物到底是誰,她們分別是朱先生的妻子朱白氏和黑娃后來明媒正娶的妻子高老秀才之女玉鳳。筆者之所以把這兩位作為傳統女性的完美代表,是源于她們兩個都讓自己的丈夫在其有生之年想叫她們一聲“媽”,她們的名字中都有一個玉字,大概象征著她們的個性如白璧無瑕。
文中傳統文化的代表朱先生知道自己大限將至時,當著全家的面讓妻子給他洗頭,洗完頭后后臉貼在妻子的大腿上時說“我想叫你一聲媽——”當朱白氏非常疑惑而兒子兒媳也非常不好意思之時,朱先生又揚起頭誠懇地說:“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就盼有個媽!”[2]627-628說罷竟然緊緊盯瞅著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聲“媽——”兩行淚珠滾滾而下。而黑娃帶著高玉鳳回家認祖歸宗、進了祠堂之后黑娃謝絕了白稼軒為他備好的炕鋪,引著妻子走進自家那個殘破的敞院,深情地對高玉鳳說“咱們在媽媽的炕上睡一夜吧!”躺進破棉絮里。當他聞到一股煙熏和汗腥氣味,一股幽幽的母乳的氣味,顫著聲羞怯怯地說:“我這會兒真想叫一聲‘媽’……”[2]587玉鳳把黑娃緊緊摟住,黑娃靜靜在枕著玉鳳的臂彎貼著她的胸脯沉靜下來。這兩聲看似莫名其妙的“媽”的呼喚,而且是白鹿原上兩個最具自省意識的男性對著自己妻子深情的呼喚,忽然間讓我對白鹿原上生活著的眾多女性生存境遇有了新的認識。
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她們要么順從,在被侮辱、被戕害時也無力反抗,如前面提到的封建禮教的幾個犧牲者的代表;要么反抗,不管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如前面分析的田小娥和白靈,最后也不得善終,一個被壓在塔下,一個被活埋地下。還有小翠,前腳進了婆家門,后腳就離開了人世。那么什么應該是女性原本的宿命?書中沒提。但筆者從這兩聲“媽”的呼喚中似乎明白些什么,那就是還需要以儒家文化精神滋養的健康女性,既不甘于落后愚昧也不至于激烈反抗。碧玉是大儒朱先生的妻子,當初朱先生選擇白碧玉做妻子時主要是因為那雙眼睛,碧玉的眼睛“剛柔相濟”:男子眼里難得一縷柔媚,而女子難得一絲剛強。他見到碧玉時就斷然肯定,即使自已走到人生的半路上淬然死亡,這個女人完全能夠持節守志,撐立門戶,撫養兒女……而在他即將離世時妻子在他眼中愈見深沉愈見剛正,愈見慈愛了。碧玉本身品性高潔,加上在朱先生身邊耳濡目染,也更臻于完美。高玉鳳是秀才之女,婚后燒火做飯時還在看書,而黑娃就想找一個知書達理的媳婦管束管束自己的野性。玉鳳跟黑娃結婚的條件是黑娃必須戒掉吃“土”的毛病,否則將“以死抗婚”。她不計較他從前種種,只求今后表現良好。她沉靜地安排著自己和黑娃的生活,使黑娃感受到這個女性的全部美好和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安全和可靠。這兩個女性的丈夫在男權社會統治下的日常生活中忍不住想叫她們一聲“媽”,這不正是對傳統人性中母性的呼喚嗎?這更是對女性知書達理、溫柔敦厚的呼喚。
朱先生在深情告別碧玉后過世,完成了一個相對完美、自足的生命歷程。而黑娃在跟玉鳳結婚后真正成了鹿兆謙,回鄉祭祖不僅標志著被家族接納,也標志傳統文化反叛者黑娃徹底回歸到傳統文化的懷抱,他是自覺向傳統文化歸順,回鄉的時候甚至都沒有朝向壓著小娥骨灰的六棱塔方向張望一眼,他是徹底地告別了過去,從而真正從心底里“學為好人”。這些細節無不彰顯出傳統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朱先生也說自己最好的學生是曾為土匪的關門弟子黑娃,也標志著高舉儒家文化旗幟,代表白鹿精靈的朱先生對儒家文化再一次發揮神奇的歸化作用的肯定,他告訴朱白氏自己內心“孤清”得很,何嘗不是對儒家文化逐漸式微的慨嘆。在他眼里鹿兆鵬和白孝文等都算不得“好人”,而革命就像鏊子,翻來覆去,沒有反正。不管時局如何變幻莫測,唯有儒家文化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就像朱先生起草而被白鹿原上人們世代傳頌的《鄉約》,雖歷經被毀、重修,始終見證和調整著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精神生活以及每個家族的繁衍生息。因為在“緩慢的歷史演進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為鄉約族規家法民俗, 滲透到每一個鄉社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族, 滲透進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結構”[3]50。
母親創造生命,母親給自己創造的生命以無可替代的靜謐與安穩,她們以柔弱之軀為孩子們構建起強大的精神家園,而傳統儒家文化正是支撐這個家園的精神支柱。白趙氏在白秉德去世后顯示出少有的剛毅和果斷,在兒子主事以前有條不紊地安排著白家的生活,而鹿子霖的媳婦鹿賀氏在鹿子霖被抓后,也迸發出少有的主見,變賣所有的家產只為保鹿子霖回家。這些一向隱忍的女性蘊藏著巨大的生命活力和決斷力,常常在一個個不可預料的家庭變故面前表現得異常堅強,因而使得家庭渡過難關。她們沒有文化,但同樣是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下的母親和擁有母性個體特色的偉大女性。
五、余論
如果說白碧玉和高玉鳳是傳統女性在現世生活中相對完美的典型,那么是不是可以說擁有儒家文化溫柔敦厚、剛柔相濟的“母性”特質,就是傳統女性實現在男權社會中自我救贖最為穩妥的道路之一?然而即便如此,男權社會對“媽”的呼喚,對“母性”的肯定和褒揚恰恰是建立在忽略了女性本來的“女人性”的基礎上,作為“女性”的個體在封建社會依然是被壓抑和遮蔽的。傳統女性自我救贖的可能與尷尬也在這里。
孝文媳婦、冷家大女兒、孝義媳婦何嘗不是對封建禮教所提倡的三綱五常亦步亦趨,卻也逃不過被封建禮教吞噬的命運;田小娥也是秀才之女,何嘗沒有親近過儒家文化,受詩書禮儀的熏陶?但還是被父親嫁到郭舉人家,而在郭舉人夫婦眼里,她只是個工具而已,黑娃冒險帶她回家,但帶不進自家的祠堂里……最終還是在父權、夫權和族權的重壓下走向了毀滅——肉身被戕、靈魂也被壓在塔下——成為一個生動的反抗者的典型。最終她是孤獨的,因為在儒家文化的感召下鹿兆謙帶著玉鳳走近祠堂時,田小娥終于失去了最愛她而她也深愛著的黑娃。白靈在自我意識非常強烈的愿望中游走在國共兩黨之間,感情也在鹿家兩個兄弟之間轉換。不管在身體層面還是在精神層面,白靈看似都是出離于父權、夫權和族權控制的自由而獨立的時代新女性。然而她卻因不見容于自己的組織,被自己人出賣而被活埋。或順從或反抗,這些女性多舛的生活際遇充分顯示出命運無常的魔力。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在白鹿原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大多數女性依然找不到自己的救贖之路?封建禮教作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經過了漫長的發展過程,一開始并不是“吃人”的。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卻變成了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有些方面反倒走到了它原本的對立面。傳統儒家文化孕育了男權思想,在男權思想統治下造成了一個個貞婦烈女,留下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陳忠實在他的《白鹿原》創作手記中寫道:“為她們(貞婦烈女)行一個注目禮, 或者說挽歌。”[3]49《白鹿原》中女性的命運說明無原則地遵從封建禮教或者刻意追求個性解放都不能善始善終,最終還是要回到傳統文化的懷抱尋找撫慰,不管是像文中朱先生那樣的“大儒”還是像黑娃那樣學為好人的“土匪”。因此怎樣理解傳統文化對女性的影響仍然是今天一個重要的課題。
“當成文形式的中國傳統作為現代中國的指南而大部分受到懷疑時,實際上中國的價值體系、個人相對于政府的地位、農村父系家庭制度的支配地位和中國生活的成百個特征卻表現了明顯的延續性。人們用各不相同的歌詞唱同一個老調子。人們自覺思維領域中的變化大于日常行為的變化。”[5]23陳忠實的《白鹿原》再次證明了這個道理。看來嚴復,這個19世紀向國人傳播“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著名思想家在遺囑中寫到的“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6]360是有著深刻道理的。《白鹿原》中傳統女性日常生存境遇告訴我們傳統文化依然在日常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容小覷,今天也是如此。“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審慎地評價也許是今天我們對待傳統文化最好的態度。
[1]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手記[J].小說評論,2007(5).
[2]陳忠實.白鹿原[M].北京:人民人學出版社,1997.
[3]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手記[J].小說評論,2007(4).
[4]沈遠川,馬筱蓉.從女性悲劇看《白鹿原》文化沖突的意義[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09(3).
[5]〔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6]王栻.嚴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責任編輯 許峻)
An Analysis of Women’s Living Circumstances inWhiteDeerPlain
HUI 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The novelWhiteDeerPlaindepicts the living predicament and an ignored and depressed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and portrays a number of female characters. Some of them yield to their destiny, and others pursue self-liberation and resist the feudal restriction. However, destiny leaves them no difference in the feudal society, and unfortunately only few of the female could obtain a good ending.WhiteDeerPlainis a lamentation as well as an elegy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WhiteDeerPlain; women’s living circumstances; self-redemption; self-liberation
2015-10-20
惠萍(1974—),女,河南社旗人,文學博士,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主要從事編輯出版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等領域的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6.008
I207.42
A
1008-3715(2015)06-0041-05
——兼談歐美游客儒家文化認知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