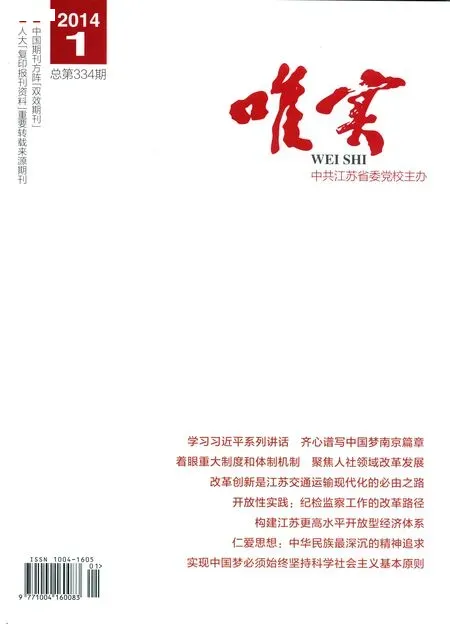用好重大機遇爭創江蘇經濟發展新優勢
王慶五+吳先滿+章壽榮
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和蘇南現代化建設示范區規劃“三大規劃”,早在黨的十八大之前就確定為國家發展戰略;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又創造性地提出了“兩帶一路”新的三大國家戰略。“兩帶一路”超越長三角,但起點或支點都在江蘇境內。因此,當前江蘇面臨實施六大國家戰略的重大疊加機遇。江蘇一定要用好這六大國家戰略機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爭創江蘇發展新優勢,譜寫輝煌美麗中國夢的江蘇篇章。
一、江蘇迎來六大國家戰略
疊加重大機遇的意義
六大國家戰略均與江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換句話說,江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迎來了六大國家戰略密集疊加的戰略機遇期。縱向看,江蘇之前從未有過。20世紀80年代,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內、對外開放,曾經給江蘇鄉鎮企業發展進而江蘇經濟的全面發展帶來重大歷史性機遇;繼后的90年代,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特別是浦東開發開放戰略,給江蘇外向型經濟大發展乃至江蘇經濟的又一次全面發展和水平提升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世紀之交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民營經濟蓬勃發展與創新性經濟發展,構成江蘇經濟發展的第三次重大機遇。而現在,則是六大國家戰略在江蘇密集疊加。橫向看,一些國家戰略在一些省市區集中實施時常可見,但像江蘇這樣一個地區恰逢六大國家戰略的集中實施,在全國其他地區尚未有過。因此,六大國家戰略在江蘇密集疊加,這樣的重大戰略機遇,對江蘇來說非常難得,必將對江蘇經濟的全面發展與質量提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六大國家戰略在江蘇集中實施,必將對江蘇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新動力。近年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未來一個時期的經濟運行,會呈現出中高速的新常態,經濟增長將保持在合理區間內。與此相聯系,近幾年江蘇經濟增長速度也在放緩,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江蘇積極參與并推進這“六大戰略”的實施,可以形成既有相當規模又有針對性,從而有質量效益保證的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強力拉動,借此可望保持江蘇經濟在中長期的持續較快增長。
六大國家戰略在江蘇集中實施,必將對江蘇省內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大而持久的推動作用,對進一步提升江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長期以來,江蘇省委、省政府持續實施區域共同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取得多方面的積極成果,在全國也是做得好的。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目前省內區域經濟差距還比較明顯,需要繼續調整、優化,省內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集中實施國家“六大戰略”,將對江蘇各區域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有利于各區域經濟的發展提升。實施蘇南現代化建設示范區特別是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戰略,將促進蘇南創新性經濟發展壯大;實施長江經濟帶戰略,將引導江蘇啟動新一輪即第三次沿江開發戰略行動,進而推動江蘇沿江八市的經濟發展再上新臺階;通過配套建設寧鎮揚同城化經濟圈、錫常泰經濟圈、蘇通經濟圈,必將加快沿江兩岸、蘇南蘇中跨江融合發展;實施沿海開發戰略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必將推動江蘇沿海地區經濟的加快發展和水平提升,實現其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崛起;實施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配合啟動現代蘇西經濟走廊或經濟帶的開發建設,將極大加快提升江蘇沿東隴海線經濟乃至整個蘇北經濟;積極參與長三角率先發展、一體化發展戰略,江蘇可以及時對接、復制、推廣上海自貿區的新成果于省內各地區經濟中,充分發揮這些改革開放“新火種”對面上經濟的激活效應與驅動力,通過沿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引的方向,處理好與滬浙皖的區域經濟關系,有利于重組、打造從而進一步增強江蘇經濟在長三角地區的新特色、新優勢。總之,融會貫通實施這六大國家戰略,必然促進全省各區域經濟在加快發展中縮小差距,增強協調性。
六大國家戰略在江蘇集中實施,必將對擴大江蘇經濟在國內外的影響,提升江蘇經濟在國內外的戰略地位和競爭力,同時增強江蘇經濟對全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產生深遠的影響。長期以來,江蘇經濟已經為全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歷史性貢獻,已經成為全國經濟的重要支撐點。現在六大國家戰略在江蘇的密集實施,必將顯著而又迅速地將江蘇經濟進一步推舉到全國經濟新一輪綜合改革開放與發展的中心地帶,進一步推舉到當代全球化經濟的前臺,讓全省經濟包括蘇北經濟、蘇中經濟和蘇南經濟,包括企業經濟和產業經濟直面復雜多變、瞬息萬變的國際、國內市場,全省各區域經濟、產業經濟、企業經濟,均可以幾乎零距離地接受國內外經濟輻射,均可以幾乎零距離地影響國內外經濟,參與新一輪的國際、國內經濟大循環,均可以在其中大顯身手、大有作為。
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
把戰略疊加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
抓住并用好“六大戰略”機遇,把戰略疊加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加快打造江蘇經濟升級版,江蘇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全力攻堅克難,全面貫徹落實國家“六大戰略”,統籌協調推進六大國家戰略在江蘇的實施,使得“六大戰略”在江蘇發展中無縫銜接、相得益彰。借“六大戰略”疊加優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拓展江蘇發展新空間,在對內對外開放中拓展江蘇發展新空間,在區域一體化發展中拓展江蘇發展新空間,在轉型升級中拓展江蘇發展新空間,形成全方位、立體化、綜合化的江蘇經濟發展新優勢。
擁近濟遠,拓展江蘇發展新空間。著重于省際開放、區域協作的長三角一體化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對江蘇來說,前者重在“擁近”,后者重在“濟遠”。“擁近濟遠”,有利于江蘇在沿長江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擴大江蘇發展空間的回旋余地。
首先,利用上海自貿區的溢出效應,增創江蘇發展新動力。上海自貿區是上海的,更是長三角的。江蘇要學習推廣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推進本省全面深化改革,釋放新的改革紅利。上海自貿區建設中體現出來的制度創新、政策優惠、貿易便利、金融自由、企業國際化,對于江蘇的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溢出效應即示范和帶動作用。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與政策創新的溢出,遠比企業、產業等實體性溢出更有價值。上海自貿區已經在可與國際接軌的市場機制上先行一步,由此來倒逼江蘇在行政、經濟等多方面的改革,釋放新的改革紅利,增創新的發展動力。江蘇要學習推廣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中形成的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和模式。江蘇要推進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促進長三角區域始終走在全國前列。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的溢出效應,將影響到整個長三角地區,從而加強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趨勢與進程。長三角各省市之間有較強的經濟互補性,要進一步加強分工與協作,江蘇要充分利用上海港口和金融中心的優勢,發揮自身在制造業上的比較優勢,實現產業融合發展。
其次,積極參與長江經濟帶建設,開拓江蘇發展新空間。從沿海黃金海岸率先發展到帶動內河縱深腹地崛起,是世界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一般規律。國家啟動新一輪長江經濟帶開發建設,為江蘇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機遇。“濟遠”就是江蘇要積極參與長江經濟帶建設,在產業轉移中支持中西部地區,以轉移促進轉型,在轉型中提升江蘇經濟發展的創新成分,實現產業轉移和轉型的雙贏;“濟遠”就是江蘇要與長江中上游地區協同構筑長江流域自主創新的產業鏈,并在沿江地區產業合理分工中推進自身向產業鏈高端轉移,共同推進長江流域現代產業體系建設。
揚長補短,實現省內區域協同發展。“六大戰略”機遇中,蘇南現代化示范區建設戰略重在“揚長”,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戰略重在“補短”。“揚長補短”,在蘇南現代化示范區建設中進一步提升先發優勢,從省內跨江融合發展中實現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協同發展。
首先,綜合運用“六大戰略”,推進沿江融合發展。從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視角,促進蘇中、蘇南融合發展。蘇中地區要充分利用長江黃金水道的天然優勢,承接重大項目布局,承接高新技術產業轉移。加快揚州跨江融合發展步伐,加快寧鎮揚同城化步伐,同時加快泰州新興產業的跨越式發展。長江口的南通市通江達海,既是沿江兩岸融合發展的關鍵連接點,也是江蘇沿海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撐極,加快陸海統籌,堅持江海聯動,努力打造“北上海”經濟圈。
其次,綜合運用“六大戰略”,推進江蘇沿海崛起。江蘇沿海地區練好承接和配套兩大“內功”,主動承接上海自貿區建設中對制造業的“擠出效應”,充分發揮沿海地區資源優勢與后發優勢,把承接與升級結合起來,形成適度、先進的制造業新產能,加快構建沿海現代產業體系。江蘇沿海地區要主動完善省內南北對接的通道。一方面,進一步加強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如交通、水利、通信等;另一方面,加強合作平臺建設,如物流、信息、金融等,選擇性接受蘇南產業轉移升級中的部分產業“移出”,以錯位發展實現合作共贏,共享蘇南現代化示范區建設的政策紅利。
陸海統籌,江海聯動,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著重于國際開放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戰略,前者沿陸路西進,后者涉大洋南下。兩大國家戰略必將提升江蘇對外開放新水平。江蘇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不僅要以新的理念、新的戰略加入國際大循環,而且要力爭取得國際大循環中的主動權、主導權。
首先,通過對內對外開放,提升江蘇經濟增長的質效。無論是“長三角一體化”,還是“長江經濟帶”建設,都為江蘇擴大對內開放提供了機遇;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戰略,則為江蘇新一輪的對外開放增加了新內容,提出了新課題。“六大戰略”把江蘇的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統合在幾個重要的節點上:南京、揚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蘇州太倉、南通啟東是長江入海口,連云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東方橋頭堡。顯然,蘇南、蘇中、蘇北都與“兩帶一路”有著天然聯系。
統籌運用“六大戰略”,要注重發揮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對江蘇率先發展的協同與互補效應。對于長三角地區和沿長江的區際開放而言,要注重區域市場的有效整合,促進產品和要素的跨區域自由流動,按市場機制決定資源配置可以降低產出損失和減少要素市場扭曲,同時可以促進不同區域之間的企業合作與交流、技術傳播與擴散,以進一步提高區域經濟的發展效率;對于國際開放而言,要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積極利用對外開放所帶來的技術與管理等“知識溢出”,進而促使生產要素由低效率組合轉向高效率組合,全面增強江蘇經濟增長的速度、質量與效益。
其次,通過資本雙向開放,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增進居民福祉。江蘇的第一輪對外開放,沿用“資本輸入—產品輸出”的開放模式,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僅獲得微薄的勞動報酬,大量剩余價值變為境外資本利得;江蘇的新一輪對外開放,要創出“資本輸出—利潤輸入”的新開放模式,實現資本輸入與輸出的雙向開放。這種“資本輸出—利潤輸入”的新開放模式,不僅可以實現資本與利潤的良性循環,而且可以實現江蘇經濟國際化從第一輪的初級開放階段,向新一輪的中高級開放階段的轉換。因此,江蘇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把先進的發展模式、制造技術、直接投資,輸送到陸上西向的絲綢之路與水上南下的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是沿途的中西亞地區、南亞地區與北非地區,以直接對外投資帶動一批跨國企業走出去。通過直接投資,幫助江蘇企業進入全球產業鏈的流通、品牌等高端環節,取得更高的資本增值,顯著提高江蘇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從而為全體江蘇居民創造更多、更大的福祉。
(王慶五: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教授;吳先滿: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章壽榮: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科研處處長,研究員)
責任編輯: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