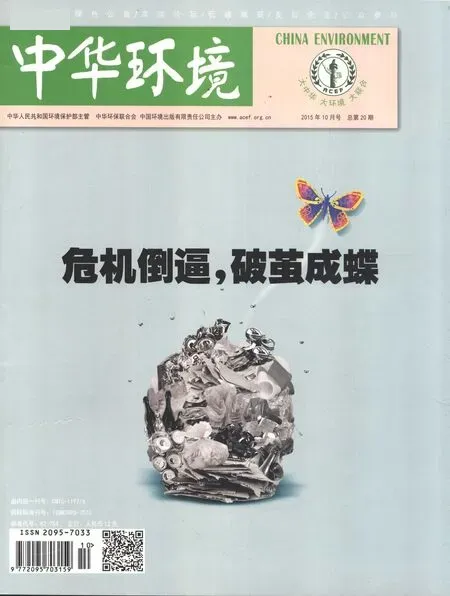誰來做環保產業這塊蛋糕
費米
誰來做環保產業這塊蛋糕
費米
有消息說,在國企進軍非洲之際,也有不少國人跑那里去賣山寨版的國產手機,原本在本土市場口碑不錯的華為、中興等品牌,在非洲不少地方都臭大街了。
中非關系來之不易,那是數十年的辛勤耕耘才收獲的。很多年前我們的醫療隊免費給非洲人看病,隊里的醫生都是國內各大醫院的業務尖子。我們的工人在那里修鐵路,工程質量據說比國內的都高。我有個親戚在坦桑尼亞修水電站,一去就是十好幾年,難得探親回一趟國,他老婆去接機,見面后打趣道:演《赤道戰鼓》都不用化裝了。
好口碑是需要努力付出的,一旦要毀了它簡直是太簡單了,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你之前修了再多的水電站和鐵路,二三十年后人家早忘了;你一部手機賣給人家用了不到倆月就壞了,人家能問候你祖孫三代好幾遍。因為大到電站小到手機,都是要老老實實用心去做的。
由此,國內的環保產業一直處于初級階段就比較好理解了。上世紀90年代初我去了江蘇宜興,那里據說是環保工業重鎮,不過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個手工作坊,設備簡陋不說,還沒多少人干活。我問其中的一個工廠主,為什么見不到工人在干活呢?工廠主的回答也實在的很:有訂單就忙,沒活做了就歇著。一套治污設備百八十萬,沒有哪家企業能痛痛快快拍板訂貨,所以我這里銷售人員幾乎跟工人一樣多,全國各地去推銷產品,賣掉一套掙得的錢,我跟他們倒四六分。
如此的分利,工廠主還有多少實力和興趣投入到產品的研發之中呢?能勉強維持工廠生存就很不錯了。這樣的企業能有多少競爭力就可想而知了,更別提什么技術創新了。靠這種技術粗糙、作坊一般的地方來帶動和推高中國的環保產業,近乎于癡人說夢了。
鄉鎮企業做不了領軍,國有大企業也好不到哪里去。素來與上海分析儀器廠并稱南北雙雄的北京分析儀器廠也奄奄一息,能賣的廠子賣了,能下崗的工人也下崗了,那些有技術有經驗正當年的工人跑河北拉來一車白薯在廠區外面叫賣:狼牙山白薯,干、面、甜。
也許,能撐起環保產業臺面來的企業在股市里?中國的股市向來不按市場的常理出牌,因此被人譏之為“政策股”“風向股”,環保股也沒能逃過這個宿命:上頭提倡清潔能源了,于是太陽能股、風能股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政策往節能減排上傾斜了,證券公司就猛給你推薦節能股、新能源股;霧霾到了人神共憤境地了,新法除塵除硫股開始大行其道。很難想象,那種一味揣摩圣意的經營者能有多少精力放在做大做強企業上。
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環保產業的支柱效益正在加速釋放。在我國進入“誰污染、誰付費”的時代后,各領域的資本力量都有了掘金環保市場的沖動。日前,環保部法規司司長李慶瑞公開表示,“十三五”期間,我國環保市場的總投資額有望達到17萬億元。這一數據不僅令政府為之振奮,更給環保行業打了一劑強心針,讓人們看到,那個常年與不賺錢、低利潤等詞匯掛鉤的環保產業即將“改頭換面”的希望。
在業內看來,過去多年,我國環保產業處于發展初期之時,環保投入一直處于被打了折扣的狀態,資本一旦進入這個市場,就像進入了一個“無底洞”,很難達到預期的投資效果。隨著排污標準的不斷趨嚴,迫切需要第三方企業來協助的將不再只有工業廢氣排放企業,還將拓展到污水治理、土壤修復、固廢處理等多個領域。當市場真正逐步放開以后,這個盤子里的蛋糕其實真的不小。
問題是,誰來做這塊蛋糕。由那些小作坊來做嗎?成天算計著跟銷售人員怎么分賬的管理者沒有遠大志向;還是碰到難處就把工人趕出去賣白薯的國企?不跟員工同甘共苦沒有絲毫擔當的企業沒有前途;或者,是那些將上意揣摩得很好的企業?這樣的業者擅長的是投機跟風,不具備現代企業家的素質,沒等蛋糕做得,他已經把蛋糕坯子給你吃個一干二凈了。
所以,環保產業要上一個臺階,就要重新洗牌,引進市場機制,讓那些有志向、有擔當、有堅守的企業家參與競爭,如此,環保產業這塊蛋糕方能做大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