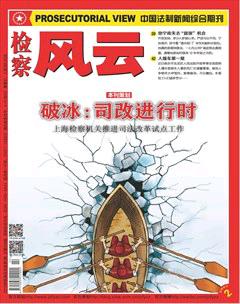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來報道法治新聞
楊金志
2014年12月1日,上海“復旦投毒案”二審開庭前夕,上海一家新聞網站刊發了一則報道《林森浩手寫道歉信跪求黃洋父母原諒》,文中摘錄了“道歉信”的部分內容,并稱:“由于無法向黃洋的父母當面道歉,林森浩便書寫了一封道歉信,希望通過代理律師轉交給黃洋的父母,但也遭到了拒收。”
這已經不是媒體第一次不恰當地、過分地介入“復旦投毒案”的審理。雖然報道本身沒有對案件審判提出明確“審理意見”,但是單方面傳遞涉案一方的態度、意見,所傳遞的內容并不在嚴格的法律程序之內,并且帶有較為濃厚的情感訴求。這里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林森浩一方的辯護代理人主動提供了相關材料。從某種程度上看,具有“媒體審判”之嫌。
事實上,近年來的一些熱點法治案件報道中,類似情況并不少見。由此可見,在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媒體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來進行法治報道,具有十分強烈的現實意義。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司法機關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規范媒體對案件的報道,防止輿論影響司法公正”。
對于這一部分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賀小榮曾撰文闡釋:“人民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尊重新聞傳播規律,有條件的法庭可以設立專門的媒體記者席,為媒體進行輿論監督、傳播司法信息創造條件。媒體也要尊重司法規律,特別是對未決案件的報道一定要恪守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等原則,尊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共同維護司法權威,防止輿論影響司法公正。”
“復旦投毒案”之所以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主要在于:第一,案件的被告人、受害人相對特殊的身份——復旦大學醫學院研究生。這由此又引發了社會上關于大學生教育問題的討論。第二,我國高校歷史上發生過疑似室友投毒的“懸案”。
而在“復旦投毒案”中,媒體的不當報道誤導公眾,主要存在于三個節點:其一,2014年5月,一些媒體刊發題為《復旦177名學子為投毒兇手求情》等報道,稱“林森浩之前幫助過的學弟學妹和林父共同找到律師咨詢,在律師的建議下,由學生執筆寫了這份求情信。隨后,學生們又找到了謝百三,希望由他倡導。在學生和老師的共同參與下,才有了‘177名學生聯名上書事件”,學生們的聯名信被寄往上海市高院。
其二,2014年7月,上海一媒體刊發題為《貴州教師為復旦投毒兇手求情》的大篇幅報道。報道稱:貴州省貴陽市退休教師劉鳳蕓(化名)只身前往四川自貢,懇求黃洋父母對林森浩網開一面,被拒之門外。隨后,她又只身飛赴上海,希望當面和上海高院院長溝通,以期免林森浩一死,又未能如愿。
其三,即文首提及的上海一家新聞網站于2014年12月1日刊登的《林森浩手寫道歉信跪求黃洋父母原諒》一文。
對于這些報道中涉及的“求情”,我們應該怎么看?對于一起公開審理的案件,任何公民都有權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發表看法。
但是,媒體是否報道、如何報道,卻需要斟酌。否則,就是放棄了大眾傳播“把關人”的角色,是對法治精神的無視。上述報道存在的明顯瑕疵在于:第一,報道不平衡。在大篇幅報道求情者觀點、訴求的同時,基本沒有受害人家屬的表態。事實上,在此類事件中,媒體即使去征求受害人家屬意見,要求其表態,本身也不符合新聞倫理。其次,對求情信的出籠,沒有進行審慎、深入的探究。從一些報道中的蛛絲馬跡看,這些求情信、道歉信可能并非來自求情者的自覺,而是來自一方代理人的“策劃”。第三,本案正處于一審、二審的法律程序之中,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媒體對涉案任何一方有傾向性的報道,應當審慎,原則上不應成為任何一方的“傳聲筒”;不能以“客觀記錄”為由進行“有聞必錄”。
類似“復旦投毒案”中出現的“不專業新聞”,在李某某強奸案、上訪人唐慧女兒被強奸案等法治案件報道中,同樣存在。面對進入法律程序的法治事件,新聞媒體首先需要的不是悲情、煽情,而是看似冷漠、消極、被動的冷靜,是對法治精神的堅守,是對依法裁判的尊重。
(上海法治聲音)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