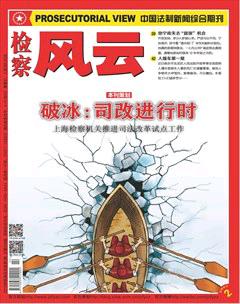校園里的表達(dá)自由
林海
汀克訴德梅因市校區(qū)案(Tinker v. Des Moines School District)是美國憲法史上的重要案例。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通過此案,重新討論了象征性表達(dá)的言論地位。此案之后,佩戴袖章這一象征性的表達(dá),被施予了第一修正案保護(hù)的言論自由的法律地位。法院還對校園管理是否能夠干預(yù)表達(dá)自由進(jìn)行了探討。最后的結(jié)論是,即使是學(xué)校這一“合格公民的培訓(xùn)場所”,也不得對表達(dá)自由進(jìn)行干預(yù)和剝奪。
13歲的反戰(zhàn)女孩
故事發(fā)生于1965年。當(dāng)時(shí)正是美國卷入越南戰(zhàn)爭、美國國內(nèi)反戰(zhàn)抗議進(jìn)入高潮的時(shí)期。13歲的小姑娘瑪麗(Mary Beth Tinker)是德梅因市(Des Moines)的中學(xué)生。她聽到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的演講,建議美國人佩戴反戰(zhàn)袖章,以示對越戰(zhàn)的抗議。瑪麗和幾個(gè)朋友商議之后,決定真的佩戴袖章去上學(xué)。瑪麗知道她這樣做有被學(xué)校停學(xué)的危險(xiǎn)。學(xué)校的教育委員會在兩天前以投票方式?jīng)Q定,佩戴袖章的學(xué)生必須停學(xué),理由是“產(chǎn)生混亂的影響”。她的代數(shù)老師曾警告學(xué)生,只要戴袖章來上課就會被開除。然而,1965年12月16日,決心已下的瑪麗和其他幾所學(xué)校的學(xué)生戴上了黑色的反戰(zhàn)袖章。據(jù)她自己描述:“那是個(gè)有自己活動內(nèi)容的青少年組織……我們決定戴黑袖章上學(xué)。那時(shí)候(1965年)反越戰(zhàn)運(yùn)動開始擴(kuò)大,雖然還遠(yuǎn)遠(yuǎn)沒有達(dá)到后來的程度,但全國各地有相當(dāng)一些人參加。我記得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激動;所有人都為這個(gè)了不起的信念攜起手來。我還小,但我仍可以成為其中一分子,而且仍然有重要作用。這不僅僅是成年人的事,小孩子也受到尊重:我們有話要說時(shí),人們注意聽。所以,那時(shí)候我們就計(jì)劃戴袖章上學(xué)這件小事。計(jì)劃在進(jìn)行中,我們沒認(rèn)為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完全不曉得會有那樣嚴(yán)重,因?yàn)槲覀円呀?jīng)舉辦過一些其他的小型示威,什么事也沒發(fā)生……我去上學(xué),整個(gè)上午都戴著袖章。同學(xué)們議論紛紛,但都很友好,沒有惡意。午飯一過,一個(gè)人來到教室門口說,‘瑪麗,你到走廊里來。然后他們把我叫到校長辦公室……校長態(tài)度相當(dāng)惡劣。之后他們就把我停了學(xué)。”
一共有六名學(xué)生被停學(xué)。他們對此決定不服,向街區(qū)法院提起了訴訟,指控學(xué)校的停學(xué)決定侵犯了他們的“言論自由”,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然而,街區(qū)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官認(rèn)為,校方的擔(dān)心并不是沒有理由的。因?yàn)楦鶕?jù)校方的說法,一名原來在該校上過學(xué)的學(xué)生,后來參加越戰(zhàn),在越南被殺。他的一些朋友現(xiàn)在還在學(xué)校上學(xué)。因此校方認(rèn)為,假如發(fā)生此類反戰(zhàn)抗議,可能會使他的那些朋友們卷入進(jìn)來,并使得事態(tài)難以控制。

于是,瑪麗等人上訴到該州上訴法院。上訴法院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支持瑪麗與其他學(xué)生,理由如下:佩戴袖章并未構(gòu)成對他人權(quán)利的侵犯,是安靜的和非暴力的表達(dá)方式。他們的行為應(yīng)受到第一修正案對于表達(dá)自由的保護(hù)。第一修正案所保護(hù)的權(quán)利,并不因?yàn)樘幱趯W(xué)校環(huán)境之中就應(yīng)受到限制,對于學(xué)生和教師而言,他們也有表達(dá)觀點(diǎn)的自由。在沒有證據(jù)表明瑪麗等人的表達(dá)方式會造成對于學(xué)校紀(jì)律的破壞或是對于他人權(quán)利的侵犯的情況下,校方對于他們表達(dá)自由的限制是不必要的,是違反第一修正案的。但是同時(shí),上訴法院也認(rèn)為,此案涉及法律適用的統(tǒng)一和憲法權(quán)利的解釋,或許應(yīng)當(dāng)交由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審理。于是,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下達(dá)調(diào)卷令后,于1968年11月12日開庭審理了此案。
象征性表達(dá)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hù)
178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又被稱為《權(quán)利法案》。該法案共十條,其中第一條即規(guī)定了對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會申訴權(quán)等民主權(quán)利與自由的保護(hù):“國會不得制定關(guān)于下列事項(xiàng)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jiān)干暝┑臋?quán)利。”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不需過多論證。對于個(gè)體而言,這是天賦的基本權(quán)利,也是體現(xiàn)和證明自身存在感的重要途徑。對于社會而言,言論自由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如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此案判決中所稱,言論自由是國家的力量、人民的獨(dú)立和活力的基礎(chǔ)。中國也有類似的古訓(xùn):“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個(gè)完善的社會結(jié)構(gòu)需要能夠自我修正與調(diào)整,而言論自由則確保不同的意見得以表達(dá),以避免這個(gè)社會結(jié)構(gòu)的僵死。
然而在此案中,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瑪麗等中學(xué)生佩戴黑色反戰(zhàn)袖章的行為,是否屬于某種“言論”而受到“言論自由”條款的保護(hù)?早期的西方社會里,表達(dá)(expression)一直被等同于言論(speech),因?yàn)楸磉_(dá)無非就是用說話、文字、印刷等方式來表達(dá)思想、意見等純屬觀念性的東西。而行為(conduct)從一開始并不被認(rèn)為是一種表達(dá)。布萊克法官認(rèn)為言論與行為應(yīng)該是兩分的,不能讓行為也享有與言論一樣的憲法保護(hù)。
然而,這種兩分法遭到了許多法學(xué)家的猛烈抨擊。他們認(rèn)為,那些具有表達(dá)內(nèi)容的行為,也同樣是采用另一種影響他人的、傳遞思想感情或觀點(diǎn)的形式。假如嚴(yán)格區(qū)分行為與純語言,并且不給予那些旨在表達(dá)并實(shí)際具有表達(dá)效果的行為以言論自由之保護(hù),那么仿佛是在向世人說明這樣一點(diǎn):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條所保護(hù)的言論自由,只是保護(hù)表達(dá)的形式,而非言論的實(shí)質(zhì)。聯(lián)邦最高法院接受了這些意見,在1970年原告將美國國旗卷成子彈形狀以示反對越戰(zhàn)的行為進(jìn)行了如下描述:“他是在進(jìn)行一種交流,也就是說,他想要別人知道,美國人是愛好和平的。他的行為不是毫無意義的,“他展示國旗一如國旗本身乃是展示一種信念的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他所表達(dá)的意思是很直接的,很容易為別人所理解,因而屬于第一修正案的保護(hù)范圍。”
對于聯(lián)邦最高法院來說,如果一項(xiàng)帶有表達(dá)愿望的行為希望被認(rèn)定為象征性表達(dá)從而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hù),它至少需要針對受眾,傳遞明確的信息。而在瑪麗等人的案件中,他們所佩戴的袖章是由一名名為Gerald Holtom的英國人早在1958年設(shè)計(jì)的反戰(zhàn)標(biāo)志:由海軍旗語N與D重疊而成(如上頁圖)。這一袖章在越戰(zhàn)之前就風(fēng)靡全球,成為通行的反戰(zhàn)徽章。因而,他們通過佩戴這一袖章,來傳達(dá)反戰(zhàn)的信息,無疑是明確且易于理解的。因而,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進(jìn)行了三個(gè)月的審理后,最終在判決中將這一行為認(rèn)定為象征性表達(dá),并納入了言論自由的范圍和憲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條的保護(hù)。
校園管理不能剝奪自由
瑪麗等人在實(shí)現(xiàn)“象征性表達(dá)”時(shí),遇到的主要“敵人”是學(xué)校的管理秩序。事實(shí)上,校方也是以“可能會引起其他學(xué)生的爭論、從而引發(fā)教室混亂”為由,禁止瑪麗等人在學(xué)校里以佩戴袖章的方式表達(dá)抗議。校方認(rèn)為,學(xué)校的主要作用是傳播知識。學(xué)生可以在課余時(shí)間或?qū)iT的政治討論場合表達(dá)自己對于越戰(zhàn)的反對,但在其他的、主要目標(biāo)是教學(xué)的情境中——比如代數(shù)課上,仍然佩戴袖章,就可能不太合適。這將干擾正常的教學(xué)秩序,也可能占用其他同學(xué)或教師原本應(yīng)投入到代數(shù)教學(xué)中的注意力或時(shí)間。盡管這些表達(dá)者一語不發(fā),還裝作認(rèn)真學(xué)習(xí)的樣子,但他們向周圍其他同學(xué)傳遞的信息卻已經(jīng)太過喧鬧以至于影響了正常的教學(xué)秩序。
然而,聯(lián)邦最高法院仍然堅(jiān)持,學(xué)生和教師在校園里仍然享有他們的表達(dá)自由。法院認(rèn)為,校園環(huán)境的特殊性確實(shí)應(yīng)納入考慮,但這并不意味著跨入校門就會進(jìn)入一個(gè)完全封閉的系統(tǒng),從而失去受第一修正案保護(hù)的自由與權(quán)利。當(dāng)校方在標(biāo)榜教育青少年的使命與教學(xué)的重要性時(shí),法院認(rèn)為需要警惕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成為限制青少年思想自由的借口。對于公民憲法權(quán)利和自由進(jìn)行限制時(shí),需要對限制的理由進(jìn)行實(shí)質(zhì)性的嚴(yán)格標(biāo)準(zhǔn)審查。
實(shí)際上,法院認(rèn)為,在全校18000名學(xué)生中,僅有寥寥幾人戴上袖章,校方并無證據(jù)說明,瑪麗等人的抗議已經(jīng)構(gòu)成了對于教學(xué)秩序直接而嚴(yán)重的破壞。當(dāng)僅僅是有“引起爭論從而造成混亂的風(fēng)險(xiǎn)”時(shí),校方即匆忙地要求他們停學(xué),這樣的限制是超過合理邊界的。因而,聯(lián)邦最高法院并不是認(rèn)為教學(xué)秩序不重要,而是認(rèn)為,當(dāng)校方以此為由限制表達(dá)自由時(shí),需要符合更加嚴(yán)格的實(shí)質(zhì)與程序條件。
法院還提出,學(xué)校無權(quán)強(qiáng)迫學(xué)生向國旗敬禮,也無權(quán)依據(jù)政治傾向正確與否而限制反戰(zhàn)抗議。因?yàn)椋瑢W(xué)校并不是培養(yǎng)一模一樣的思想的地方,相反,聯(lián)邦最高法院向?qū)W校提出的要求是:培養(yǎng)合格的公民,對于學(xué)生給予充分的公民訓(xùn)練。最終,法庭在判決中寫道,學(xué)校如果確實(shí)是培育公民意識的場所,就需要給學(xué)生機(jī)會,讓他們懂得,他們有權(quán)利表達(dá)不受歡迎的政治觀點(diǎn)而不受學(xué)校當(dāng)局的懲罰。就此,聯(lián)邦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了州上訴法院的判決,認(rèn)定校方的處罰不恰當(dāng)?shù)叵拗屏吮磉_(dá)自由,應(yīng)予以撤銷。塵埃落定,13歲的反戰(zhàn)女孩瑪麗勝訴,贏得了在校園內(nèi)表達(dá)其反戰(zhàn)抗議的權(quán)利。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