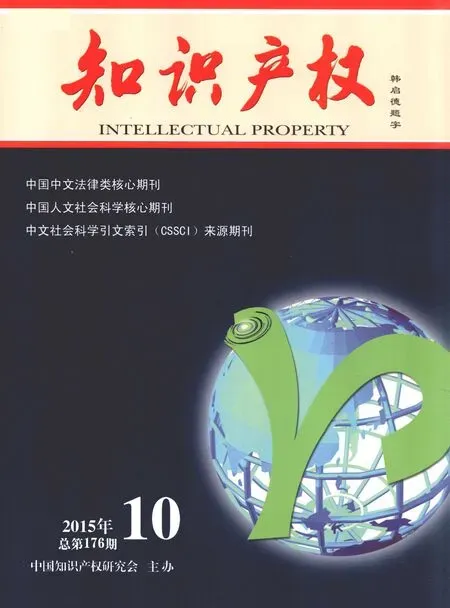也論民法典與知識產(chǎn)權
朱謝群
也論民法典與知識產(chǎn)權
朱謝群
內(nèi)容提要: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既是民法典圓滿其完整性、彰顯其時代性的需要,也是知識產(chǎn)權固本強基、良性運行的需要,更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將知識產(chǎn)權作為一個區(qū)隔于其他民事權利的封閉整體是現(xiàn)有知識產(chǎn)權立法模式設計中共同隱含的前提,但這一前提的理據(jù)并不充分。嘗試提出既不拔高、放大也不抑制、壓縮知識產(chǎn)權特殊性從而使之以本原、正常形態(tài)“融入”民法典的可能思路。
民法典 知識產(chǎn)權 民事權利 立法模式設計
上一次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圍繞著知識產(chǎn)權應否、能否以及如何進入民法典曾有熱烈的討論,其中不乏共識,分歧卻似乎所在更多。然而,隨著法典編纂的沉寂,無論共識還是分歧,大都漸漸淡出,只留下零星的回響。
2014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由此,民法典的制定被重新 “激活”,因而知識產(chǎn)權“入典”的相關問題也就必然再次浮出水面。本文不揣淺陋,嘗試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求拋磚引玉。
一、民法典中應否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
當前完全否認知識產(chǎn)權屬于一種民事權利的觀點不說沒有,至少也是十分難見。但是“知識產(chǎn)權法是民法的一部分,是不是意味著必然將知識產(chǎn)權法納入民法典呢?”①齊愛民:《論知識產(chǎn)權法的性質(zhì)和立法模式》,載《社會科學家》2006年第5期,第92頁。謝鴻 飛:《中國民法典的生活世界、價值體系與立法表達》,http://cclc.sdupsl.edu.cn/msyjxsqy/21517.jhtml.本文對此做肯定回答,并試圖在已有的贊同將知識產(chǎn)權法納入民法典的理由之基礎上,再做補充或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民法典作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就必須盡可能囊括產(chǎn)生民事權利義務的社會生活,并將其規(guī)范化”。①而在當今時代,隨著技術進步與經(jīng)濟發(fā)展,知識產(chǎn)權早已溢出特定人群“個別、局部”的生活場域,而是廣泛滲透于民眾生活的文化、商業(yè)、經(jīng)濟、科教、技術等幾乎所有領域,并仍或快或慢地鋪展開來,在“抽象普通人”之間的社會交往中成為常見、多見的元素與內(nèi)容,形成越來越寬廣、密集的權利關系網(wǎng)絡,甚至逐漸重塑著市民社會的行為方式。因此,如果知識產(chǎn)權在我國將要制定的民法典中不能得到足夠乃至前瞻的觀照、反映與規(guī)范,那么這部民法典的完整性顯然將存在缺陷。
第二,民法典作為“市場經(jīng)濟的基本法”,實際上也就是關于全部或至少是重要資源的市場配置機制最基本的“制度化表達”。反觀現(xiàn)實,我國目前正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戰(zhàn)略、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而“創(chuàng)新不是技術行為,也不是政府行為,而是市場行為”,①張志 成:《完善的市場經(jīng)濟是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根本》,http://www.m4.cn/space/2012-08/1176273.shtml.所以,在創(chuàng)新型國家建設過程中及建成之后,各種創(chuàng)新要素與創(chuàng)新成果必然成為我國市場機制所要配置的最主要對象資源之一。進一步看,經(jīng)由市場而配置創(chuàng)新要素和創(chuàng)新成果的最主要工具則非知識產(chǎn)權莫屬,因為知識產(chǎn)權的制度功能就在于通過市場促進各類要素向創(chuàng)新環(huán)節(jié)和創(chuàng)新部類流動、集中并進一步在市場上配置創(chuàng)新成果。近年來,知識產(chǎn)權運營的日益活躍以及反壟斷法對知識產(chǎn)權行使不斷升溫的“關注”,恰恰從正反兩個方面印證了知識產(chǎn)權在當前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中持續(xù)被抬高的重要地位。
據(jù)此而言,我國民法典如果不能充分反映知識產(chǎn)權在當前創(chuàng)新發(fā)展背景下的突出地位,恐將難以稱為“市場經(jīng)濟的基本法”。
第三,現(xiàn)代知識產(chǎn)權于我國無疑屬于“舶來品”,而且由于客體不同即導致權利不同,與建基于農(nóng)業(yè)社會和工業(yè)社會的傳統(tǒng)物權相比,知識產(chǎn)權確實具有“特殊性”,同時也更易于受到技術變革和國際形勢等其他因素的沖擊與影響。但是,知識產(chǎn)權特殊性再明顯、再突出也從未否定過其“私權”(民事權利)本質(zhì)(“知識產(chǎn)權是私權”恰恰是國際社會關于知識產(chǎn)權的普遍共識之一,所以才在TRIPS中被開宗明義地提出)。鄭成思教授就此曾明確指出:“知識產(chǎn)權本身,在當代,是民事權利的一部分——雖然知識產(chǎn)權的大部分來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權,它們與一般民事權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識產(chǎn)權法是民法的一部分,這在十多年前中國的《民法通則》中已有了定論。……傳統(tǒng)民法的大多數(shù)原則,適用于知識產(chǎn)權。知識產(chǎn)權取得后的最終確權、知識產(chǎn)權的維護,主要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在多數(shù)國家均是如此。在2000年之后修訂了主要知識產(chǎn)權部門法的中國,也是如此。世貿(mào)組織的《TRIPS協(xié)定》第41、42及49條,均指出了知識產(chǎn)權的保護(無論通過司法還是行政執(zhí)法),主要適用民事訴訟法的原則。”②鄭成 思:《民法、民訴法與知識產(chǎn)權研究——21世紀知識產(chǎn)權研究若干問題》,載《中國專利與商標》2001年第2期,第3頁。換句話說,知識產(chǎn)權之“特殊”是民法家族內(nèi)部的“特殊”,是民法這棵大樹上不同枝條之間的差異,而絕不是根基的“異類”,是與其他民事權利作為同類事物相比較而顯現(xiàn)出的差異。由此,也就尤其需要民法典將知識產(chǎn)權的“私權”本質(zhì)牢牢固定下來并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避免將知識產(chǎn)權在民法家族內(nèi)的“特殊性”放大到民法家族之外,從而使知識產(chǎn)權根基動搖,定位不穩(wěn),迷失方向,最終妨礙知識產(chǎn)權制度功能的正常發(fā)揮。
從一定意義上看,我國知識產(chǎn)權事業(yè)發(fā)展中的一些彎路(諸如馳名商標的異化、將授權量與政績掛鉤等)和爭議(如關于知識產(chǎn)權“私權公權化”、知識產(chǎn)權行政執(zhí)法的存廢等)不能不說是與民法精神滋養(yǎng)不足以致干擾了民法理念的貫徹有關。因此,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有利于彰顯知識產(chǎn)權的私權本性,克服欠缺私權意識的我國傳統(tǒng)法觀念以及一些過于強調(diào)‘社會化’的當代法理論對知識產(chǎn)權保護造成的負面影響,為我國知識產(chǎn)權制度設計與知識產(chǎn)權保護實踐提供重要的理念支撐。”③楊代 雄:《我國未來民法典中知識產(chǎn)權規(guī)范的立法模式》,載《上海商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第2頁。
綜上,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既是民法典圓滿其完整性、彰顯其時代性的需要,也是知識產(chǎn)權固本強基、良性運行的需要,更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知識產(chǎn)權立法模式設計的回顧與思考
(一)現(xiàn)有模式設計及理由
關于知識產(chǎn)權作為民事權利的立法模式,吳漢東教授指出:“曹新明教授在其博士論文中歸納了四種模式:一是分離式,即將知識產(chǎn)權法與民法典相分離,但無論是特別法典還是單行法,都是以民法典為其基本法,其立法例為法國《民法典》;二是納入法,即將知識產(chǎn)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之中,使其與物權、債權、人身權等平行,成為獨立一編,其立法例為俄羅斯《民法典》;三是鏈接式,即民法典對知識產(chǎn)權作出概括性、原則性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仍保留單獨立法模式,其立法例為‘我國第四次民法典草案’;四是糅合式,即將知識產(chǎn)權視為一種無形物權,與一般物權進行整合,規(guī)定在‘所有權編’之中,其立法例為蒙古《民法典》。”①吳漢 東:《知識產(chǎn)權“入典”與民法典“財產(chǎn)權總則”》,載《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15年第4期,第58頁。據(jù)此,將知識產(chǎn)權規(guī)定于民法典中的模式共有鏈接式、納入法、糅合式三種。
另外,還曾有學者建議過另外一種模式:“在民法典中單設一單元,可以是單獨一編,其位置應當在債權之后;也可以在民事權利部分單設一節(jié)。具體立法技術上,可以借鑒德國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將知識產(chǎn)權制度的一般規(guī)則納入民法典。……至于在民法典之外,是仍然存在作為民法特別法的知識產(chǎn)權單行法還是將各單行法編纂為知識產(chǎn)權法典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知識產(chǎn)權法典化并不排斥作為民事特別法的知識產(chǎn)權制度的存在,而是在知識產(chǎn)權制度與民法典之間建立有機的聯(lián)系。”②安雪 梅:《現(xiàn)代民法典對知識產(chǎn)權制度的接納》,載《法學論壇》2009年第1期,第51頁。相較于吳漢東教授提及的納入法,此種模式似可稱為“有保留的納入法”。
縱覽上述,可以看出,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的現(xiàn)有模式設計中除糅合式③此種 模式后文再議。外,其他各種模式在理念上存在共同的隱含前提:知識產(chǎn)權是一個“獨立板塊”,其實質(zhì)性的主干內(nèi)容務必保持一體,然后或打包封裝于民法典中自成一部分(編或章或節(jié))(納入法),或者整體游離于民法典之外而只在民法典總則中建立若干宣示性、象征性的鏈接點(鏈接式)。進一步看,這一隱含的共同前提顯示出上述鏈接式、納入法與“分離式”在本質(zhì)上其實極為接近,即均將知識產(chǎn)權作為一個區(qū)隔于其他民事權利的封閉整體,或明(分離式)或暗(納入法、鏈接式)地劃清與其他民事權利的界限和/或保持距離。
之所以建立這種區(qū)隔,歸納學者們先前的意見可知其理由主要如下:(1)知識產(chǎn)權易受技術變革和國際形勢的影響,顯現(xiàn)出多變性,從而與民法典的穩(wěn)定性有沖突;(2)知識產(chǎn)權內(nèi)容龐雜,既含有公法性規(guī)范,又含有程序性內(nèi)容,從而與民法典實體私法的性質(zhì)及“形式美”不合;(3)沒有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的成功立法先例;(4)我國知識產(chǎn)權研究儲備不足;(5)知識產(chǎn)權法的內(nèi)容已自成一體。④參 見吳漢東:《知識產(chǎn)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中國法學網(wǎng),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3769;袁真富:《論知識產(chǎn)權相對于民法的獨立性》,正義網(wǎng),http://revie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124403;齊愛民:《論知識產(chǎn)權法的性質(zhì)和立法模式》,載《社會科學家》2006年第5期;王崇敏、張麗娜:《論我國民法典總則中的知識產(chǎn)權保護規(guī)則》,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年第3期;楊代雄:《我國未來民法典中知識產(chǎn)權規(guī)范的立法模式》,載《上海商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滕銳、羅婷:《知識產(chǎn)權與民法典關系的思考》,載《科技與法律》2005年第3期;浩然、麻銳:《知識產(chǎn)權的結構與我國民法典立法體例結構》,載《河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以下將逐一分別討論。
(二)關于現(xiàn)有模式設計及理由的討論⑤文中 第5條理由,后文將專題商榷。
1.關于知識產(chǎn)權的多變性
客觀地講,知識產(chǎn)權的多變性確實存在,但如果仔細分析就不難發(fā)現(xiàn),“多變”的其實是知識產(chǎn)權的具體規(guī)則而非其“私權本質(zhì)”,亦非其與其他民事權利之間所有的共性。例如,隨著技術進步或國際形勢的變化,可能會產(chǎn)生新的知識產(chǎn)權客體或者新的知識產(chǎn)權權項,但是,知識產(chǎn)權排除他人擅自就特定客體進行使用、收益的核心效力并不會隨著新客體或新權項的出現(xiàn)而發(fā)生改變,否則知識產(chǎn)權就“權將不權”了。其次,民法典是體系化的構成,其基本的操作是“提取公因式”而非巨細靡遺、包羅萬象,否則就不會存在一系列諸多民事單行法。因此,只要知識產(chǎn)權的私權本質(zhì)存在,就必然存在與其他民事權利相同/相通的共性,也就必然具有能夠在民法典中提取出來的“公因式”;進一步看,只要知識產(chǎn)權的私權本質(zhì)不被否定,那么就意味著這些“公因式”不會消失或者說可以穩(wěn)固地存在。至少到目前為止,知識產(chǎn)權私權本質(zhì)還沒有被否定和推翻的任何跡象,那么,“提取公因式”的操作就是完全可行的。至于那些可能隨其他因素快速多變的具體規(guī)則,完全可以放到知識產(chǎn)權單行特別法中加以規(guī)范,這與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與其他民事權利之共性并無沖突。可見,真正的焦點其實并非知識產(chǎn)權的多變性,而是能否提取知識產(chǎn)權私權本質(zhì)中的“公因式”。
2.關于知識產(chǎn)權的公法性內(nèi)容和程序性內(nèi)容
事實上,民法典中并不絕對排斥公法性內(nèi)容和程序性內(nèi)容,顯例之一即為法人制度,①參見 鄭沖、賈紅梅譯:《德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二節(jié)。其中同樣涉及到公權機關的審查、審批等,卻并未破壞民法典的實體私法地位。可見,以是否含有公法性和程序性內(nèi)容來判斷一項制度能否被民法典所規(guī)定的觀點似不足取。
再進一步,關于民法典中的公法內(nèi)容,已有民法學者做出過比較深入的論述:“在我國,國家廣泛介入經(jīng)濟生活的范圍之廣、方式之復雜、手段之多,在立法技術不成熟時,已足以使民法典淪為公法私法耦合和交融的‘混合法’。……比較妥善的方式是民法典通過‘引致’等方式容讓公法,但并不納入公法的具體內(nèi)容。”②謝鴻 飛:《中國民法典的生活世界、價值體系與立法表達》,中國法學網(wǎng),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x?id=4310.由此,完全有理由認為,只要安頓得當,知識產(chǎn)權制度中的公法性因素和程序性因素也并不會妨礙在民法典中關于知識產(chǎn)權的規(guī)定。
3.關于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并無成功立法先例的問題
首先,這是一個守成與創(chuàng)新的問題。法國民法典制定之時并無先例可循,而德國民法典制定之時也未因襲法國民法典的先例,因而以有無(成功)先例來判斷能否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雖然不乏警示和參酌價值,但僅此就認為我國也不能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恐怕說服力不足。
其次,民法典是民族生活歷史的記載。雖然我國建立知識產(chǎn)權制度的歷史不長,而且并不具有現(xiàn)代知識產(chǎn)權的民族歷史基因,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管理體制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在建立知識產(chǎn)權制度尤其是入世后,又適逢數(shù)字技術的普及和互聯(lián)網(wǎng)絡的興起,知識產(chǎn)權制度其實已以卓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在我國法制史上烙下了清晰的印記,或者說知識產(chǎn)權已在我國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認知、生活經(jīng)驗與權利意識。這表明,當前我國市民社會關于知識產(chǎn)權的“民族”生活已經(jīng)為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而提供了素材,關鍵在于如何從中去“發(fā)現(xiàn)”和提煉。
4.關于我國知識產(chǎn)權研究儲備的不足
在我國上次民法典制定浪潮中,這個判斷或許不無道理。但是,上次浪潮退去之時,正是我國入世后官產(chǎn)學研各界遭受陣痛而開始正面直視知識產(chǎn)權之際。近十幾年來,《國家知識產(chǎn)權戰(zhàn)略綱要》的頒布、專利、商標、著作權單行法的主動修訂、相關司法解釋的不斷出臺與修訂以及諸多代表性、典型性案件的裁判等等背后,我國知識產(chǎn)權研究儲備量的增加和質(zhì)的提升之速度,用“空前”、“井噴”來形容或許都不為過。當然,儲備可能依舊不足,但是在民法典中提取知識產(chǎn)權與其他民事權利的公因式的能力顯然已有了長足進步——至少可以一試。
(三)關于“知識產(chǎn)權自成一體”
有觀點認為:“知識產(chǎn)權法在內(nèi)容上不僅包括人身權,如著作權上的精神權利(或者人身權利)、發(fā)明權、科學發(fā)現(xiàn)權等,而且包括財產(chǎn)權,如著作權上的經(jīng)濟權利(或稱財產(chǎn)權利)、專利權、商標權等;就知識產(chǎn)權法涵蓋的財產(chǎn)權而言,不僅包括財產(chǎn)權中的支配權內(nèi)容,表現(xiàn)為商標權的取得、專利權的實施等,而且包括財產(chǎn)權中的請求權內(nèi)容,表現(xiàn)為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專利權轉讓合同等方式……可見,知識產(chǎn)權法至少在內(nèi)容上,已自成體系,自成風格,有與傳統(tǒng)民法并駕齊驅的趨勢。”③袁真富:《論知識產(chǎn)權相對于民法的獨立性》,正義網(wǎng),http://revie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124403.至此,知識產(chǎn)權與其他民事權利的區(qū)隔可謂已“進行到底”。
但是,知識產(chǎn)權的特殊性真的已使自己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完整體系以致于可以脫離民法層級化概念體系的涵攝進而擺脫對民法的依賴了嗎?
事實上,“由于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像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tǒng)一的知識產(chǎn)權法律體系。”①吳漢 東:《知識產(chǎn)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 中國法學網(wǎng),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3769.“知識產(chǎn)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guī)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②黃勤 南主編:《新編知識產(chǎn)權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頁。轉引注釋。h換個角度看,知識產(chǎn)權的法律蘊含基本上都是通過民法術語來傳遞的,諸如人格、財產(chǎn)、合同、轉讓、排他權、請求權、停止侵權、損害賠償……等等,離開了民法的這些“概念構件”,知識產(chǎn)權幾乎無以完成自我表達。這不僅表明我們應當破除知識產(chǎn)權封閉自足體系的虛設幻象,而且恰恰相反,知識產(chǎn)權的研究與運用都必須緊扣其所使用的民法上諸種“概念構件”規(guī)范性、體系化的構造與機理,厘清各概念構件之間涵攝與關涉的關系,③這一點在很多時候非常必要,例如物權是具有排他性的財產(chǎn)權,但不能反過來將具有排他性的財產(chǎn)權都當作物權,二者的涵攝關系不容顛倒。文中上述的糅合式應該說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明確各概念構件在知識產(chǎn)權中的指向與“射程”及其在民法整體框架中的坐標,才能進而理順知識產(chǎn)權這個“總稱”名下的經(jīng)緯條理。正如鄭成思教授所言:“研究其(知識產(chǎn)權)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們抽象與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這才是真正學者應有的思維方式。”④同注 釋。d因此,知識產(chǎn)權應當找準自己在民法體系中的定位,經(jīng)由與其他民事權利之間的“公因式”,用自己的個性(特殊性)去印證、充實、拓展與其他民事權利之間不同層級的共性,在自我發(fā)育、完善的同時,也為民法的豐富與發(fā)展做出貢獻。
三、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的另一種可能思路
如前所述,在民法典中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的現(xiàn)有模式設計主要有鏈接式(對于鏈接點的選擇以及鏈接內(nèi)容的范圍存在分歧)、納入法等。⑤同注 釋。 i另,關于糅合式請見注釋。p就本文目前不成熟的看法而言,前者太過單薄,不足以充分體現(xiàn)知識產(chǎn)權的“私權”屬性;后者又確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民法典的體系構建使之“難以消化”,而且也面臨著如何與知識產(chǎn)權各單行法相互銜接的難題。
本文嘗試提出另一種可能思路,該思路的前置考量是將知識產(chǎn)權真正當作與其他民事權利平行的權利,賦予其平等地位,既不拔高、放大,也不抑制、壓縮知識產(chǎn)權的特殊性,使之以本原、正常形態(tài)“融入”民法典。不拔高、放大知識產(chǎn)權的特殊性,即破除知識產(chǎn)權已成為自給自足之封閉體系的幻象(同時也就免去了“肢解知識產(chǎn)權完整體系”的顧慮),不再自外、區(qū)隔于其他民事權利,而是盡可能通過公因式的提取以便在民法典框架中各個單元的不同層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借由公因式與其他民事權利的相應規(guī)則或者建立聯(lián)系甚至加以合并,或者在同一公因式的涵攝下與其他民事權利平行而立,在共性統(tǒng)合下展現(xiàn)自己的個性;不抑制、壓縮知識產(chǎn)權的特殊性,一是將知識產(chǎn)權旗下確實不能或基于特別原因而不宜規(guī)定于民法典的規(guī)則仍保留于單行特別法中,二是絕不能將其他個別民事權利的個性當作一類權利的共性進而生搬硬套于知識產(chǎn)權,或者說,在沒有公因式可提取之時,必須堅決維護知識產(chǎn)權自身的個性。
本文提出的思路是:將知識產(chǎn)權與其他民事權利最高層級的共性規(guī)定于總則,將知識產(chǎn)權與其他個別民事權利的共性規(guī)定于相應分則中的總則(或通則、一般規(guī)定),再將與其他民事權利不相容但卻屬于各知識產(chǎn)權(主要是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的共性在各相應分則中單列或至少給出指引,而不能完全不顧。當然,這只是一種思路,要具體實現(xiàn)則還有待于大量的進一步深入的識別與提取工作。試粗略描述如下以資說明。
(一)總則部分
第一,在法典總則中明確知識產(chǎn)權的權利類型相比較而言,直接給知識產(chǎn)權作出類似于現(xiàn)行《物權法》第2條第3款①《物權法》第2條第3款規(guī)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中給物權作出的定義的方式②例如可表述為:“本法所稱知識產(chǎn)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智力成果享有的(控制利用和)排他的權利,包括……。”略作說明如下:1、本文認為知識產(chǎn)權不是直接支配特定客體的權利;2、關于知識產(chǎn)權客體的表述可以再推敲;3、有文獻指出希臘民法典第60條曾做此表述,見 Koumantos, Georges ,1998.“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Kabel, Jan J. C. and Gerard J.H.M Mom, 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FORMATION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p.40可能最為理想,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是法工委草案中以界定外延的方式來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③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2002年《民法典(草案)》第89條規(guī)定:自然人、法人依法享有知識產(chǎn)權。本法所稱知識產(chǎn)權,是指就下列內(nèi)容所享有的權利:(一) 文學、藝術、科學等作品及其傳播;(二) 專利;(三) 商標及其他有關商業(yè)標識;(四) 企業(yè)名稱;(五) 原產(chǎn)地標記;(六) 商業(yè)秘密;(七)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八) 植物新品種;(九) 發(fā)現(xiàn)、發(fā)明以及其他科技成果;(十)傳統(tǒng)知識;(十一) 生物多樣化;(十二) 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智力成果。2015年4月公布的《民法總則專家建議稿(征求意見稿)》中雖未直接對知識產(chǎn)權定義,但以列舉對象的方式在第114條中規(guī)定:發(fā)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作品、商標、商業(yè)秘密等智力成果、商業(yè)標記和信息得成為民事權利客體。,理由在于第一種方式直接明確了知識產(chǎn)權的排他性,而后一種方式則可能仍需要對權利不可侵原則再做細化。排他性應當是人身權、物權和知識產(chǎn)權的生命線,目前有關知識產(chǎn)權的許多模糊認識大多與抵觸或試圖消減知識產(chǎn)權的排他性有關,因而在民法典中明確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的排他性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明確當前知識產(chǎn)權領域中熱門的“利益平衡原則”與誠實信用、公序良俗、權利不得濫用等民法基本原則的異同,如并無實質(zhì)差異或可被上述基本原則所覆蓋,則應以民法中上述已成熟的各基本原則為準;如果確有差異,則應在立法說明中說明并對利益平衡原則另作處理。
第三,在訴訟時效條目中,應當將基于知識產(chǎn)權的有關請求權列為不適用訴訟時效的除外對象。④參見 《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總則》(社科院草案)第197條。
(二)人格權部分(無論人格權單獨成編還是規(guī)定于總則中)
將著作權中的精神權利作為一個整體予以規(guī)定,作為與名譽權、隱私權等并列的一項獨立權利,由此彰顯著作權中的精神權利與每個自然人平等享有的普通人身權之間的區(qū)別,但同時肯定了著作權中的精神權利屬于民事權利。精神權利的具體內(nèi)容可以規(guī)定于著作權單行法中。
(三)“狹義財產(chǎn)權”⑤王衛(wèi)國:現(xiàn)代財產(chǎn)法的理論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第162頁。部分
此處的“狹義財產(chǎn)權”是指作為絕對權(對世權)的財產(chǎn)權。王利明教授指出,“在未來民法典的編纂過程中,是否有必要適應知識經(jīng)濟時代的要求,在民法典中確立一個超越傳統(tǒng)物權法和知識產(chǎn)權法的財產(chǎn)法總則,值得探討。”⑥王利明:《民法典的時代特征和編纂步驟》,載《清華法學》2014年第6期,第6頁。王衛(wèi)國教授也指出,“簡單地套用物權法的規(guī)則,不足以充分保護人們在智力成果上的財產(chǎn)權,也不足以有效建立知識產(chǎn)權的法律秩序。因此,需要在民法體系中為知識產(chǎn)權提供存在和發(fā)展的空間。”⑦同注 釋w, 第145頁。為此,建議設立一個包括物權、知識產(chǎn)權的財產(chǎn)權編,并將二者的共性(典型者如排他效力)提取出來列入該編的通則(或一般規(guī)定)中。
(四)債權部分
無論是否設立債權總則,都應當在債權部分對知識產(chǎn)權許可合同予以規(guī)定,具體內(nèi)容可以只涉及知識產(chǎn)權許可的共同含義、類型及相應效力、生效要件等。其次,對知識產(chǎn)權中可能涉及的無因管理、不當?shù)美劝l(fā)生債的原因也應有所規(guī)定或至少給出指引。
(五)侵權責任部分【略】
(六)親屬權部分【略】
(七)繼承權部分
無論是否對著作權的繼承作出具體規(guī)定,但至少應有所指引。同時,對自然人商標權的繼承也應有所規(guī)定,尤其是自然人商標權主體死亡后有多個繼承人的,如無指引將極可能引發(fā)爭議。事實上,我國一些關于老字號的商標案件在根源上就與商標制度同繼承制度的脫節(jié)有關。
The provi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civil code is not only the demand of realizing civil code integrity and highlighting the need of times, but also the need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omoting its benign operation. The provi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lso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country unde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a closed segment from other civil rights is the implicit premise of ex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islative model design, but the justifi cation of premise is not suffi cient. This paper tries to propose some possible ideas, which neither overstating, magnifying nor suppressing, compress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enable it to integrate into civil code in primitive normal morphology.
civil co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ivil rights; legislative model design
朱謝群,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文為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民法重述、民法典編纂與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法律制度的完善”(批準號14ZDC01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