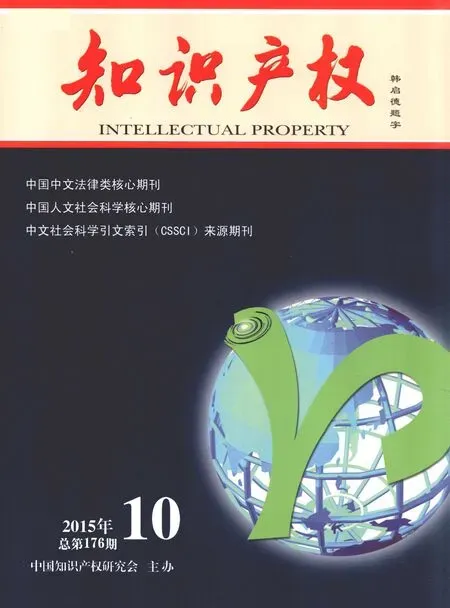論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
何煉紅 云 姣
論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
何煉紅 云 姣
內容提要:隨著大數據時代的發展,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進程已經無法繞開對大量孤兒作品的利用問題。由于相關立法滯后,我國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利用需要承擔高昂的經濟成本或巨大的侵權風險,致使孤兒作品資源被大量閑置。為了更好地平衡激勵創作與公眾獲取之間的關系,應當進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制度,將公共文化機構的特定利用行為納入合理使用的范圍,并明確其合理使用的方式和條件,以充分實現孤兒作品的文化價值。
公共文化機構 孤兒作品 合理使用 判斷要件
公共文化機構①公共文化機構主要包括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美術館以及其它具有類似性質和功能的數據知識庫,其共同特征是由政府等公共部門設立,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權利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具有非營利性和公益性。在大規模的數字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孤兒作品的利用問題已經日益凸顯。孤兒作品是指那些經過使用人勤勉盡力尋找,仍然無法被確認或無法找到權利人且仍處于版權保護期內的作品。如何更好地發揮孤兒作品的文化價值?如何在孤兒作品利用層面更好地實現激勵創作與公眾獲取之間的利益平衡?對孤兒作品進行合理使用無疑是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目前學界的研究主要關注孤兒作品的商業性利用及其集體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對于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問題鮮有論及。本文擬破解公共文化機構利用孤兒作品過程中所面臨的難題,探尋孤兒作品合理使用存在的制度根基,并明確其合理使用的判斷要件。
一、公共文化機構的大規模數字化進程對孤兒作品的利用提出挑戰
數字化技術和互聯網的普及極大地促進了公共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在這些技術的支持下,世界上大部分知識都將被數字化,并可供瀏覽,從而使人們更加便捷地獲取知識,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于數字圖書館或其他類似的公共文化網絡傳播平臺的建立。與此同時,自由開放、互動的網絡也使識別作者身份的信息能夠被輕易消除或丟失①何煉紅:《網絡著作人身權研究》,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3期,第70頁。,這就導致了孤兒作品現象在大規模數字化過程中尤為引人注目②GR EEN PAPER, Copyrigh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COM(2008)466/3.。當前,由于孤兒作品數量驚人,不論是商業使用者還是公益使用者,都在積極地尋找某種適當的方式來加大對孤兒作品的利用,公共文化機構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使用需求主體。
2012年的美國作家協會起訴HathiTrust一案③Au thors Guild v. HathiTrust, 1:11-cv-06351-HB, 156 (S.D.N.Y. 2012).,就充分反映了這種需求趨勢。HathiTrust是由5所美國知名大學的研究型圖書館聯合建立的一個共享型數字知識庫,它于2011年推出“孤兒作品計劃”,該計劃允許其成員大學的內部人員全文瀏覽和下載這些大學圖書館所確認并保管的孤兒作品。這種行為招致美國作家協會的起訴。美國作家協會認為,HathiTrust及其成員大學的圖書館對大量孤兒作品的使用沒有獲得授權,侵犯了版權所有者的權利。2012年10月審理法官哈羅德·貝爾卻做出裁決,認為HathiTrust具有非營利性和教育目的,其行為沒有造成對作品市場的損害,其行為屬于合理使用。美國作家協會不服此判決進行上訴,然而上訴法院仍然支持原審法院關于合理使用的觀點。④Au thors Guild v. HathiTrust, 12-4547-cv, 278-1 (2d Cir. 2014).該案表明,大規模的數字化活動刺激了孤兒作品的大量增加,并對孤兒作品的利用提出了挑戰,反過來,孤兒作品的版權問題又尤為關鍵地影響著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的進程,對孤兒作品進行合理使用,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
如何充分利用大數據時代的技術優勢,采取可行的途徑,使那些已經難以在市場上流通而被束之高閣的孤兒作品獲得重新面世的機會,從而令讀者能夠接觸到這些原本無法購買、借閱的作品,以最大化地實現孤兒作品的價值,將會成為大數據時代每個國家都面臨的問題。奧地利一家大學圖書館曾耗資15萬歐元將1925年至1988年期間完成的20萬份博士論文數字化,但因無法承擔高額的版權交易成本(約為數字化成本的20至50倍),以致現在都無法在線獲取。⑤翟建雄、鄧茜:《孤兒作品的數字化及利用:歐洲的立法與實踐》,載中國圖書館學會編:《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論文集2012年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2013 年初,英國由于一項改革法案被否決,使得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機構不得不預先為“孤兒作品”的使用買單,而這項支出將非常龐大。大英圖書館董事會會長泰莎·布萊克斯通(T.Blackstone)認為,這種決策對圖書館是“極具毀滅性的”。⑥秦珂 :《“孤兒作品”版權問題對圖書館數字化建設的制約與解決之策》,載《情報理論與實踐》2014 年第 3 期,第43頁。由此可見,公共文化機構利用孤兒作品的成本問題足以影響公共文化的發展進程。
我國盡管還沒有出現因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活動引發版權糾紛的典型案例,但我國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建設同樣不能繞開“孤兒作品”版權問題。比如,2012年,國家圖書館聯合國內文獻收藏單位,正式啟動“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劃”項目,以搶救、保護民國時期珍貴文獻⑦魯先 進:《關于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劃的思考》,載《圖書館建設》2012年第8期,第15頁。。該計劃的實施涉及文獻普查、海外文獻征集、整理出版等工作,自然無法避開孤兒作品的數字化等利用問題。再如,我國高校建立的CALIS項目(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即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其主要工作包括文獻信息服務網絡建設和文獻信息資源及數字化建設⑧耿靜 :《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體系建設研討》,載《現代情報》2006年第2期,第79頁。。可以預見,CALIS將憑借先進的數字技術手段為學術研究和創新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的文獻信息保障與服務。但如果沒有更完善的法律環境,孤兒作品的版權問題遲早將成為此類項目發展的阻滯因素。
二、公共文化機構合理使用孤兒作品是實現其文化價值的有效途徑
(一)孤兒作品具有文化價值
一般來說,孤兒作品大多是仍處于版權保護期內的絕版圖書,之所以變成孤兒作品,多數情況下是因為難以銷售出去,無法為版權人提供商業利益,因而版權人采取置之不理或不置可否的態度,在客觀上放棄了版權。也就是說,由于多數孤兒作品本身的商業價值已經在先前的出版行為中“耗盡”,權利人對其作品的“剩余商業價值”所抱有的期待遠遠低于普通作品權利人的期望值。
不過孤兒作品雖然因缺少商業價值而難以在商業市場流通,但其最本質的文化價值并不因此而滅失。比如,一部孤兒作品雖然可能由于時間推移等原因失去了廣泛的普通讀者,但它可能對于某個研究類似問題的學者仍有借鑒意義。因此,讓早已絕版的孤兒作品重見天日也是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建設的重大意義所在。也正因這些孤兒作品本身已沒有太多商業價值可供貶損,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使用是實現其剩余文化價值,并不會損害權利人的商業利益。
當然,盡管多數孤兒作品的商業價值極為有限,但不能排除其中一些作品仍有“枯木逢春”的可能。對于這一類孤兒作品,使用需求主體既有公共文化機構也有商業主體。商業使用的前提是看中了作品的盈利空間,因而甘愿付出相對應的成本,甚至包括侵權成本。而公共文化機構的公益性使用所關注的是作品的文化價值,其主體特性要求它不能從孤兒作品的利用過程中獲取商業利益,因此,相關法律制度應當區分孤兒作品的商業性使用和公益性使用。不恰當地對商業使用者和公益使用者一視同仁,要求二者為不同性質、不同目的、不同方式、不同后果的使用接受同樣的審查程序,并支付同樣的使用費顯然極不合理。法律為保護孤兒作品權利人的利益,設置一定的使用門檻,對商業使用者而言,其只需權衡成本與收益進而決定是否使用,但對公共文化機構而言,法律門檻的高低幾乎決定著當前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建設的成敗。
(二)公共文化機構合理使用孤兒作品是一種最佳的利用方案
公共文化機構如何利用孤兒作品,需要考量公共利益實現與高昂許可代價之間的矛盾所產生的利益平衡需求。以公共文化機構利用孤兒作品的便利程度由弱至強為標準,目前大致有加拿大1988年《著作權法》所規定的提存使用費模式,歐盟《孤兒作品指令2012/28/EU》規定的權利人出現后再付費模式和美國《2008年孤兒作品法案》規定的合理使用模式。那么該如何選擇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最佳利用方案?
加拿大1988年《著作權法》率先確立了由公共機構集中審查許可使用孤兒作品并預先提存使用費的制度①Cop yright Act , RSC1985, c. C- 42, section77 (1988).。即公共文化機構使用孤兒作品前須向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指定的機構申請并提存使用費。在該機制中,公權力機關的介入是解決孤兒作品利用困境的主要途徑。公權力介入的方式使得使用人在無法得到授權許可的情況下也可以直接利用孤兒作品,從而使得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具有很強的確定性,但該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推高了社會成本。②趙銳 :《論孤兒作品的版權利用》,載《知識產權》2012年第6期,第61頁。因為申請、審查和許可的過程,必然需要國家建立一套相應的制度和設施。由于孤兒作品本身著作權基礎信息的缺乏,導致公共機構實際上也無法做到高質量的審查,實質審查成本高昂。同時,由于孤兒作品權利人再次出現的概率較低,多數孤兒作品會因權利人客觀上無限期缺位而無付費之必要,而提存使用費則意味著將概率較低的付費可能變為一律付費。
歐盟2012年生效的《孤兒作品指令2012/28/ EU》,其適用范圍明確限于成員國內的圖書館、教育機構、博物館和檔案館③D irective 2012/ 28/ 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2 on Certain Permitted Uses of Orphan Work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299/5 (2012).,該模式的特點是 “先使用后付費”,即只有當孤兒作品的權利人再次出現后,公共文化機構才需對版權人給予適當補償。但考慮到公共文化機構預算有限,因此特別允許公共文化機構可以出于彌補向公眾提供 “孤兒作品”服務成本的“唯一”目的,從用戶的使用行為中得到補償④秦珂:《“孤兒作品”版權問題對圖書館數字化建設的制約與解決之策》,載《情報理論與實踐》2014 年第 3 期,第43頁。。這一機制較之加拿大1988年《著作權法》模式有了更大的進步意義,權利人出現后才付費的制度設計,有效避免了向永不出現的權利人付費的不合理現象。但缺陷在于仍然忽略了公共文化機構的非盈利性質。即便是對部分孤兒作品權利人予以補償,對公共文化機構而言仍會造成入不敷出的窘境。而令公共文化機構可以因這種使用向用戶收費的規定更會造成對公共文化機構公益性質的貶損。此外,《指令》當中規定“補償的具體規則由各國確定”,其結果無疑是這種具體規則難于確定,且缺乏可操作性。
美國參議院通過的《2008年孤兒作品法案》則涉及到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進行合理使用的問題。該法案中有一項重要規定:如果侵權者是一個非營利的教育機構、圖書館或者檔案館,或者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并且能夠以優勢證據證明如下方面,那么法院就不能作出要求侵權者為使用被侵權作品而支付合理補償的命令:1.侵權是在沒有任何直接或者間接商業利益之目的的情況下進行的;2.侵權行為在本質上是教育性的、宗教性的或者慈善性的;3.在接到主張侵權的通告之后,以及在誠意地對該主張進行迅速有效的調查之后,侵權者立即就停止了侵權行為。除非權利人證明并且法庭也認定,侵權者已經獲得了可直接歸結于侵權行為的收益,那么可歸結于侵權行為的收益的這一部分,應當判給此所有人。①韓瑩 瑩譯、支振鋒校:《2008年孤兒作品法案議案》,載《環球法律評論》2009年第l期,第158頁。盡管該法案最終沒有獲得眾議院的表決通過,但充分肯定了孤兒作品的“公益性使用免責”有其存在的價值。而美國作協訴HathiTrust一案的判決結果,更是說明美國在司法實踐已經開始認可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
一項法律制度立法模式的選擇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評價觀點,權衡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美國《2008年孤兒作品法案》所設定的公益性使用免責模式實際上是三種模式當中最合理、操作性最強、最有利于公共文化發展的模式。畢竟非營利性的公益使用不同于商業使用,沒有獲利空間,為兩種使用設定同樣或大致相似的使用條件不盡公平,亦會阻礙公共文化發展。因此,只有將公共文化機構從普通主體中抽離出來,對其非營利性的公益使用行為予以適當的法律傾斜,才能改變權利人缺位導致多數孤兒作品被棄置的不合理局面。
三、我國公共文化機構合理使用孤兒作品面臨的法律障礙
在我國,由于相關立法滯后,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利用需要承擔高昂的經濟成本或巨大的侵權風險,致使大量的孤兒作品資源處于被閑置的狀態。根據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22條的規定,“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為合理使用。《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7條規定:公共文化機構“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通過信息網絡向本館館舍內服務對象提供本館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數字作品和依法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報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間接獲得經濟利益。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前款規定的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應當是已經損毀或者瀕臨損毀、丟失或者失竊,或者其存儲格式已經過時,并且在市場上無法購買或者只能以明顯高于標定的價格購買的作品。”
可見,公共文化機構對館藏孤兒作品以陳列、保存為目的的復制行為屬于合理使用,并且對本館收藏的本身以數字化形式出版的作品和孤本作品的數字化復制版本也可以進行合理使用,但使用方式限于信息網絡,使用范圍限于本館館舍內。《條例》的規定在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方面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因為本身以數字化形式出版的作品、孤本作品的數字化復制版本都與孤兒作品存在一定的交叉,比如有一些孤兒作品屬于數字作品,還有一些孤兒作品已經成為孤本,有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必要,因此這兩類孤兒作品符合《條例》第7條的規定,公共文化機構可以對其進行合理使用。但該條規定的局限在于無法囊括所有孤兒作品,畢竟更多數的孤兒作品并非出版時即為數字作品,同時也并非為了陳列或保存有必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孤本。此外,對于立法沒有規定的內容,如對孤兒作品在局域網內提供免費全文瀏覽、允許下載等行為不在合理使用條款保護范圍之內,公共文化機構仍需對這一部分使用獲得授權并付費。而即便一些公共文化機構有尋求授權和付費的意愿,其又陷入另一個尷尬境地:即不知道向哪個組織取得孤兒作品的授權,如果貿然使用則面臨侵權風險。
我國2012年公布的《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采納了加拿大1988年《著作權法》所規定的提存使用費模式,即“對于孤兒作品,可以在盡力查找權利人無果的情況下向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指定的機構申請并提存使用費后以數字化形式使用。但具體實施辦法還需由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另行規定”。由于該條規定并沒有將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公益性使用作為其中的例外情形予以使用授權豁免,而是為孤兒作品數字化設計為“使用者勤勉查找+公共機構審批+付費使用”的制度安排,因此公共文化機構要實現其公益性、教育性目的,使其館藏的孤兒作品重見天日,就必須像其他商業使用一般,向指定機構申請并提存使用費。而這對于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共文化機構來說無疑是過重的負擔,進而將導致其選擇趨向于“不作為”,即寧可任由孤兒作品被閑置。此外,該條規定還存在原則性較強但可操作性不足的問題,如勤勉搜索標準、補償費用標準等仍未明確。“前款具體事項,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另行規定”的說法,使人們覺得關于“孤兒作品”條款的實施尚待時日①Schlesinger M:《國際知識產權聯盟對(著作權法〉修改及最高人民法院網絡著作權保護司法解釋的建議》,美國電影協會北京代表處譯,載《中國版權》2012年第5期,第18頁。。
綜上,我國由于相關立法滯后,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利用面對著一個兩難之境: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如果貿然將作品進行復制或數字化,就會構成侵權,當權利人出現時,可能承擔高額的侵權賠償費用;但如果放棄對這部分孤兒作品的收錄,又會面對巨大的資源缺失,阻礙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進程。即便在《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模式下,公共文化機構愿意積極尋求授權,也難以獲得更好的境況:或者將面臨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尚無另行規定而無所適從的窘境,或者待另行規定出臺后在審批和提存使用費的模式下承擔高昂的經濟成本。簡單的版權規則之后,大量重要作品、文獻資料因之而擱置,損害最大的無疑是這些作品資料公開傳播所能產生的社會意義②周艷 敏、宋慧獻:《版權制度下的“孤兒作品”問題》,載《出版發行研究》2009年第6期,第66頁。。法律作為社會的制衡器,關注更多的不是某個人或單個群體的一方需求,而是社會整體利益的調和。我國著作權法的立法宗旨正是在鼓勵社會創新的基礎上,促進知識的傳播和整個人類文明的傳承③何煉紅、鄧欣欣:《數字作品轉售行為的著作權法規制——兼論數字發行權有限用盡原則的確立》,載《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26頁。。因此,只有從立法上明確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規則,才能在根本上營造有利于孤兒作品文化價值最大化的法律環境,并更好地實現社會的整體利益。
四、我國公共文化機構合理使用孤兒作品的立法建議
隨著信息技術和數據時代的發展,公共文化機構要想最大化地實現其自身價值,就必須順應數字化的時代步伐,建立公共文化數據庫,而這一過程必然無法繞開數量龐大的孤兒作品。
本文建議,為了進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制度,我國《著作權法》應明確規定,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數字化復制、存檔、在局域網內提供免費全文瀏覽、允許下載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在此基礎上,為了確保該合理使用行為與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沖突、沒有不合理地損害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即符合作品合理使用的“三步檢驗標準”④《TRIPS協定》第13條規定: 各成員對專有權作出的任何限制或例外規定應限于某些特殊的情況,且不會與對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也不會不合理地損害權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在《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及相關配套措施中,還須對公共文化機構合理使用孤兒作品的主體、前提、對象和行為等內容進行具體限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一)使用主體
合理使用的主體是公共文化機構,包括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美術館以及其它具有類似性質和功能的數據知識庫。合理使用的主體強調非營利性和公益性,在此我們排除了商業性機構。以谷歌公司為例,雖然谷歌數字圖書館計劃對于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行為最終仍是輔佐于營利目的本身,此類公司并不能長遠地承擔學術研究、文化發展等社會責任,因此我們不能把學術研究的將來托付給谷歌公司一類的商業機構⑤John Wilkin, HathiTrust and the Google Deal, Library Journal, 2009, P 42-43.,而必須由公共文化機構擔負起搜集、整理、保存并為公眾提供文化作品的使命和重任。
(二)使用前提
合理使用的前提是通過勤勉盡力地搜索仍未找到或聯系到版權人。這一要件的設置一方面是為了明確所使用的作品確為孤兒作品,如果并非孤兒作品,則不屬于合理使用,使用時仍需向版權人支付報酬;另一方面也能夠反映出使用者主觀上是否為善意,如果沒有勤勉盡力地搜索版權人便擅自使用相關作品,無疑仍構成侵權。在勤勉搜索的認定標準上,較低的搜索標準容易造成使用者對搜索義務的懈怠,反之,如果認為只要通過“任何”方式能獲知著作權人身份和聯系方式,相關作品就不是“孤兒作品”,恐怕世界上也基本無“孤兒作品”可言了①王遷 :《“孤兒作品”制度設計簡論》,載《中國版權》2013年第1期,第31頁。。本文認為,可參考美國《2008年孤兒法案》的規定,對“合理勤勉”作以下要求:第一,使用人的搜索行為是合理的,并基于搜尋到的事實采取了實際行動;第二,運用了相關法律規定的最新和最優的辦法;第三,尋找是在使用行為之前一個合理的時間內進行;第四,使用人尋求了能夠得到的專家援助與技術幫助。至于勤勉搜索所能涉及的途徑,則包括直接聯系版權人,聯系作品出版單位;通過圖書館網站和其他相關網站公布擬使用作品的信息,征詢版權人;向版權信息庫提出查詢版權人的申請;通過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版權代理公司、版權登記機關,以及國家版權行政管理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查詢版權人;在全國性報刊上登載查找版權人啟事等②秦珂 :《“孤兒作品”版權問題對圖書館數字化建設的制約與解決之策》,載《情報理論與實踐》2014年第3期,第45頁。。
(三)使用對象
合理使用的對象是履行勤勉搜尋義務后所確定的孤兒作品,且該孤兒作品已經絕版或通常情況下不可能再回到商業交易市場。這個因素對于處理合理使用的現狀問題非常重要。③James Aaron, The Authors Guide V. HathiTrust: A Way Forward For Digital Access To Neglected Works in Libraries, Lewis & Clark Law Review, 2012, P8.因為假如該孤兒作品仍然在市場流通或極受市場歡迎,還有再版的可能,即說明該作品仍有現實的或潛在的商業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文化機構對該作品的使用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其市場價值。當然,這種影響可以通過對使用方式和范圍的限制而降到極低。但如果直接對使用對象的性質予以規定,即設置“已絕版或極不可能回到商業市場”的條件,則更能確保公共文化機構的合理使用不會擠占作品原有的商業市場。
(四)使用行為
合理使用行為僅限于公共文化機構對孤兒作品的數字化復制、存檔、在局域網內提供全文瀏覽、允許下載的行為,這些行為具有非營利性目的,且不得以任何方式收取報酬,否則不屬于合理使用。此外,對孤兒作品的合理使用都應以數字化形式使用,因為實體市場仍然是作品銷售、獲利的主要市場,將合理使用限制為數字化方式,使用范圍限于公共文化機構物理館舍的局域網和物理館舍所在的校園網,可以將使用行為對市場的損害程度降到最低。再次,公共文化機構合理使用孤兒作品時應附帶作品的版權信息標識,一旦版權人出現,公共文化機構應立即停止使用,由版權人決定是否可以繼續使用。使用機構對先前使用行為無需予以補償,但對后續使用應當支付報酬。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digital process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has been impossible to ignore a large number of orphan works. Due to the lag in legislation,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still confront high economic costs or huge infringement risk while they use the orphan works, which leads to the situation that orphan works resources are idle. The best approach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expand the explanation of fair use in Copyright Law. The behaviors of the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which conform to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should be treated as fair use. Only in this way, cultural value of the orphan works can be maximized in legal system environment.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incentive to create and the public access.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orphan works; fair us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何煉紅,中南大學法學院、中南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教授
云姣,中南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法碩士研究生
本成果系法治湖南建設與區域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平臺建設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