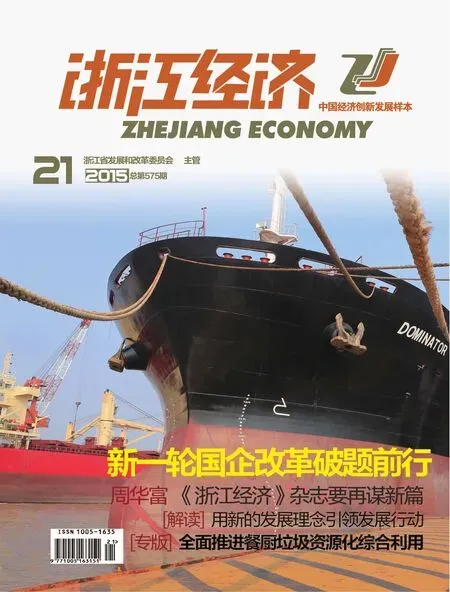客觀認識浙江產業向外轉移
張錢江 方曉
產業轉移是一個國家(地區)綜合成本,特別是要素成本上升后,自然出現的經濟現象。應采用市場化運作手段,加快培育信息、環保、高端裝備等高端制造業和新增長動力,把傳統產業轉移與轉型結合起來,延長和提升產業競爭力,避免出現產業空心
近年來,浙江低成本比較優勢逐漸弱化,產業向外轉移速度呈現加快趨勢,對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對此,政府相關部門應高度重視,堅持轉移與轉型相結合、政府引導與市場倒逼相結合,加速省內產業升級和傳統產業結構調整,避免產業空心化。
浙江產業轉移的基本情況
目前,浙江產業轉移主要集中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能源資源密集型產業,呈現出訂單轉移和產能轉移同步進行的特點,轉移目的地從周邊省份、東南亞擴大到東歐、非洲甚至美國,但產業鏈整體轉移尚未出現,目前對浙江產品出口的國際市場份額影響不大。
轉移進入加速期。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浙江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比較明顯的轉移,近年來向中西部及東南亞等地轉移明顯加速。一是產能轉移加快。據統計,浙江紡織服裝及鞋類產業境外投資,從2012年的1.5億美元增至2014年的2.8億美元,年均增長36%。二是訂單轉移加快。省商務廳的“外經貿運行調查監測系統”顯示,目前,浙江遭遇客戶訂單轉移的企業面達22.3%,其中10%的企業轉移訂單比重超過10%。
主要轉向東南亞地區。根據調查,目前浙江外向型產業轉移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向周邊的江西、安徽、蘇北等地及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轉移,據省商務廳“外經貿運行調查監測系統”調查,比例約在10%左右。二是向東南亞等新興市場轉移,比例約在30%左右。目前,企業更多的是向東南亞轉移,這與我國勞動力市場充分流動、地區工資差價不大(浙江與內地名義工資差價不超過50%)、物流成本及內地招商環境等有關。而目前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地區工資水平約是浙江的1/4-1/6,成本優勢非常明顯。
轉移主體從外資跨國公司擴大到國有、民營及中小企業。由于制造成本上升,外資跨國公司在金融危機后,就有意識地將訂單和投資向東南亞等地轉移,也帶動上下游關聯企業轉移。外資企業占浙江出口比重從2012年的28.1%下降到目前的21.4%。同時,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試探性轉移步伐正在加快,一些企業在一期項目達產后,馬上開始二期投資。
產業鏈整體轉移還未出現。從產業看,紡織服裝、鞋類、箱包及金屬加工等企業轉移較多,大多集中在縫制等加工環節,原料供應、研發設計、營銷管理等高附加值環節仍留在省內。
浙江產業向外轉移的動因分析
產業轉移主要原因是成本驅動,此外風險規避、資源整合、產能過剩等也是企業考量的重要因素。
成本驅動型轉移。隨著不斷攀升的綜合成本,浙江制造業的成本優勢,不僅與東南亞相比沒有競爭優勢,而且與美國相比差距也在縮小。如蕭山某紡織企業為化解成本上漲壓力,于2013年在美國南卡州投資紡紗工廠。雖然美國人工成本比國內高,但被更低廉的能源價格、便宜的棉花價格以及當地的稅收減免和補助政策所抵消,與國內相比,生產成本降低了許多:一是國內外棉花差價大。美國棉花比國內便宜3500元/噸,棉花成本占棉紡產品成本的70%,同樣的產能規模,僅棉花成本就比國內節省2.5億元。二是能源價格便宜,美國的電、天然氣等能源價格低于國內,電價僅為國內的1/2;三是美國人工成本較國內高很多。國內氣流紡噸紗用工成本約266元,美國用工成本約750元/噸。四是土地、稅收優惠政策等多,美國融資成本低,當地政府還給予多種稅收和政策支持。
風險規避型轉移。規避貿易壁壘是企業轉移的另一重要原因。如某銅材生產企業為應對來自美國、巴西等國的反傾銷稅,將產能逐步轉移到越南。此外,越南、柬埔寨等國使用進口原材料加工制成的紡織品、服裝出口歐盟的關稅為零。隨著TPP談判的達成,將有更多的紡織服裝企業轉移至越南等地,以確保其在美國等市場的份額。據海關統計,2014年,浙江對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這5個TPP發達成員國出口服裝112.5億美元,占全省服裝出口的33.8%,床墊及寢具出口12.7億美元,占比55.9%。
資源整合型轉移。東南亞、非洲等地自然資源豐富,進出口政策寬松。如豐富的木材資源,受家具、木地板等企業的青睞,豐富的礦產資源,吸引了浙江企業投資冶煉生產線。如某輪胎生產企業為規避貿易壁壘,同時實現原材料可持續供給,在泰國投資設立輪胎生產線,產品輻射東南亞市場。
產能過剩型轉移。部分產業因為國內市場日趨飽和,企業通過產業轉移來拓展新的市場空間。如面對國內水泥產能過剩,金華某水泥生產企業在緬甸等市場投資建設水泥生產線,產能輸出的同時開拓了當地水泥市場。
客觀認識產業轉移的影響
產業轉移一方面有利于緩解浙江要素資源供需矛盾,有利于企業整合境內外各類資源優勢,有利于拓展產業發展空間,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兩大疑惑,一是產業轉移是否會導致浙江產業空心化?二是產業轉移是否會減少浙江產品的市場份額。
產業轉移目前沒有造成浙江產業空心化。但目前浙江正處于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傳統產業轉移趨勢明顯,在新的產業尚未形成有力支撐之前,不能忽視產業轉移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如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從2012年50%下降到2015年上半年的46%,年均下降1.6個百分點。如近年來浙江制造業利用外資整體呈現下滑趨勢,年規模從2012年的64.1億美元下降到2014年的57.1億美元。
產業轉移暫時沒有對浙江出口市場份額造成影響。今年1-9月,浙江出口占全國比重為12.3%,比去年底提高0.6個百分點。根據WTO相關數據測算,浙江紡織服裝占美國市場份額從2012年的8.1%提高到2014年的8.6%,占歐盟市場的份額從2012年的5.6%提高到2014年的6.1%。但是,由于浙江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相對較高,占比達40.6%,我們不能忽視產業轉移今后對浙江出口市場份額的影響。今年以來,在國際市場需求不旺、傳統競爭優勢弱化、國外貨幣貶值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浙江紡織、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分別下降3.0%、2.9%、3.6%。
未來將在浙江與東南亞之間形成新的平衡。目前的產業轉移總體上仍不能動搖浙江的競爭優勢,但隨著時間推移,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東南亞等勞動力價格低洼地是趨勢,并會逐步帶動當地配套產業發展。但受到東南亞的經濟總量、社會穩定、宗教、員工勤勞程度、工作效率、基礎設施等因素影響,未來將會在浙江與東南亞之間形成一個新平衡(指成本、品質、貨期、服務的平衡,客商會采取搭配下單的模式。
相關建議
產業轉移是一個國家(地區)綜合成本,特別是要素成本上升后,自然出現的經濟現象。今后,應采用市場化運作手段(如鼓勵技術創新、提高落后產能運作成本等方式),加快培育信息、環保、高端裝備等高端制造業和新增長動力,把傳統產業轉移與轉型結合起來,延長和提升產業競爭力,避免出現產業空心化。
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增加專利等知識產權投入,發展信息制造、新材料、機器人等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將浙江的勞動力弱勢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擴大技術密集型產品與服務出口,從而拉動本省新興產業發展。如韓國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由于我國出口的增加導致紡織、服裝、制鞋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下滑,為此,韓國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增加研發支出,依靠創新發展,實現了以三星為代表的IT產業快速發展。如海康威視通過不斷加大軟件技術服務的研發投入,擴大整體解決方案業務,實現了信息技術服務外包的高速增長,出口市場遍布歐美、大洋洲、東南亞、中東等市場,今年1-9月,公司信息技術產品出口7.0億美元,增長60.4%。
推動傳統產業做精做深。紡織服裝等產業雖然增速下滑,但基本需求還在,沒有過時的產業,只有差的企業,只要注重創新、注重新產品開發、注重內部管理、注重升級換代,苦練內功的企業就會有出路,仍能獲得不錯的利潤。如前面提到的蕭山紡紗企業,國內工廠在淘汰“高能耗低利潤”的織造廠后,轉向附加值更高的環錠紡生產,通過機器換人、節能減排,有效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增加了效益。經測算,企業在人工成本、能耗成本及原料成本方面節省1000多萬。如紹興鼎記數碼主動加強內銷,內銷比重從2013年的30%上升到目前超過50%,同時外銷更加注重開發附加值較高的中高端類產品,企業出口下降24.3%,但總利潤同比增長了24%。
引導企業有序轉移。優先引導省內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強化與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合作,引導那些以內銷為主的紡織服裝企業往原材料資源豐富、內陸口岸資源豐富、鐵路運輸便利的內陸地區轉移。目前,制約東部沿海地區紡織業向西部轉移存在三大因素:一是2011年國家實施的棉花收儲政策造成剪刀差;二是運輸成本過高;三是區域貿易安排,如TPP協定的達成,使得紡織服裝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更有利可圖。為此,需要從國家戰略出發,提高對產能向西部轉移的重要性認識,依托西部如新疆等地棉花與人力資源優勢,依托浙江紡織服裝出口優勢,在新疆阿克蘇等地打造浙江紡織產業轉移示范基地,建設成國家西部面向中亞、歐洲的重要紡織品生產加工出口基地。同時,積極建議國家加強統籌引導,不斷優化中西部營商環境,實施差異化的優惠政策,對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西部給予更多土地、稅收等方面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