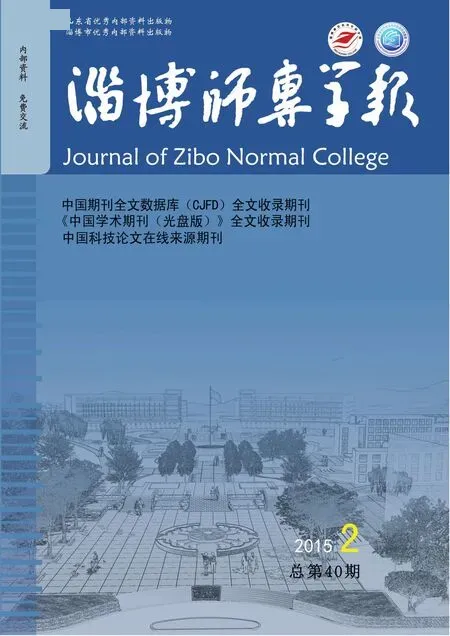情智共生的詩意生命
——論嘉男小說創作中的生態意識
李小凡
(山東大學(威海) 文化傳播學院,山東 威海 264209)
?
情智共生的詩意生命
——論嘉男小說創作中的生態意識
李小凡
(山東大學(威海) 文化傳播學院,山東 威海 264209)
在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日益緊張的當下,不少作家創作中體現出生態責任感。嘉男小說創作中的生態意識不同于其他作家生態理論的宏大高深,而是以女性博大的胸懷、富有詩意的語言展示著小城鎮的日常生活,在平淡真摯中透露出富有人性關懷的生態意識,構筑著“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狀態。這與其生態審美意識形成不無關系,在地理環境、文化熏陶及內心感悟潛移默化影響下形成的生態意識自然顯示出真實、親切、詩意之美。
嘉男;生態意識;詩意;天人合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人們的生活似乎充滿了太多令人炫目的因素,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諸多文學作品也急不可耐地追逐著物質市場。然而,在大氣污染熏眼嗆鼻,亂砍濫捕觸目驚心的生態背景下,那些都市狂歡化的文學留給讀者多是空虛和失落。人們期待在忙碌的旅途中找一個雅致的小亭暫歇腳步,期待一種富有情智的寫作,一種平和靈動的寫作。嘉男的創作正是如此,尤其近幾年的小說在敘述日常生活和女性經驗之外,更以悲天憫人的生態意識開辟出關懷萬物生存的新園地。她的文字溫情平和、娓娓道來、緩緩流入人心,卻又能在心靈最柔軟的地方給予理智深刻的一擊,讓人隱隱作痛,痛定深思。
一、生態破壞與人倫異化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鋼筋混凝土將人的生活空間分割成單元碎片,現代人以猜忌和防范維護著庇身之所。與此同時,城市化也將人類與自然的聯系切斷了,人類對自然的饋贈不再心懷感恩,肆意的攫取也沒有羞愧之情,如此導致的結果不僅是生態環境的破壞,還有人倫本性的異化扭曲。
嘉男生于黑龍江中俄邊境,現居威海,她的文學創作資源多來自于腳下的土地。她鐘情于小城鎮,創作文本多以濱海小城及北方邊境小鎮為背景。而小城鎮正是城市化的產物,從鄉村向城市發展的過渡。嘉男切身感受著城市化所帶來的生態及倫理問題,城市化侵吞了農田、樹木,曾經純熟精致的金黃麥田、高聳濃密的翠綠森林,如今都變成了方磚混凝土的灰色建筑。在伐木電鋸和拆遷卡車的高亢轟隆聲中夾雜的不是笑聲,而是利益紛爭的吵罵和失鄉人的嘆息。她目睹著城鎮的形成發展、自然的破壞消失,生態意識在文學創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嘉男小說創作中的生態意識在20世紀90年代創作的《前世今生》初見端倪,以“我”未喝孟婆湯帶著前世記憶投胎于今生20世紀中葉的荒唐敘事,展開對環境破壞后人類生存問題的深刻思考。在近幾年,其小說創作的生態危機意識愈加強烈。“多少個時代都被叫作小城,最近三十年,它像一個充滿欲望的怪物,到處長滿盛著欲望汁液的瘤子,四處瘋狂地擴散,吞吃了種糧食的土地、寧靜安詳的鄉村和多少人不愿舍棄的家園。”[1]張番薯這個懷舊的“瘋子”,他執著于寫詩,執著于捍衛村莊剩下的最后一面殘墻。在現代房地產業發達的當下,那面墻成為最后詩意的地方,成為村莊的象征,但最終也難逃被毀滅的命運。張番薯被弟弟送到了精神病院,那里有個詩意生態的名字“綠楊樓”。嘉男用溫和反諷的筆觸將現代人毀滅生態詩意、追求經濟效應的現實淋漓展現,閱讀開端輕松的微笑被深刻的結尾僵化,對張番薯之“瘋”的嘲笑,實質成為對社會經濟盲目發展的諷刺。《回鄉》中蔣云停多年后歸鄉,耳朵里充斥著火車的轟隆,鼻腔中忍受著刺鼻的化工氣味,絲毫沒有感受到老家的安詳。過去那個散發著香甜莊稼氣息的蔣家莊只能在夢中出現了,老人的去世也成為老家殘留本真的祭奠。曾經的蔣家莊是生態美好的寓體,在現代化工廠的侵占下,六百年歷史的蔣家莊永遠消失了,現代人住在樓房里以為過上了“幸福生活”。對生態破壞的痛心、現代人只顧眼前利益的批判,嘉男以動情而不乏理智深思的文字為讀者娓娓道來,令人回味的樸素詩意文字的背后,卻是對社會現象的當頭棒喝。生態意識潛化在其小說創作中,日常敘事的小片段也不乏深刻反思。守門的老人們看著電線桿上被電力人多次捅掉鳥窩卻依舊建巢的小鳥,感嘆鳥不長記性,不如人類。文字留白給讀者反思空間,人類真的聰明嗎?“生態大家”之不存,“人類小家”將焉附?
嘉男的自然寫作不僅著眼于生態現實困境,更著眼于深層人倫異化的事實。生態和人倫是相同交互的,生態破壞催化人倫的異化,而人倫的異化又加劇著生態的破壞。當鋼筋水泥割裂了鄰里互助的聯系,當建筑柏油路占據了人們曾經圍坐談心的樹蔭,人們變得冷漠、自私、孤獨。情感的灰色零投入使得人們停不下忙碌的腳步,去看看周圍逐漸褪去的青山綠水,只是顧自開墾、攫取、利用。如《上吊樹》中處境令人心寒的韋吉祥老人。因樓房分配兒女失和,老人決定自殺,他只求能夠在歪脖子樹上吊自殺以接近地氣,“那差不多是他親近大自然的唯一方式了”。可是這僅有的遺愿也在開發商的挖掘機下毀滅了。韋吉祥老人在城市化進程中生活看似富裕了,但只是“偽吉祥”罷了,其中真味留給讀者不少反思。又如在《大霧》中為生計奔波的出租車女司機夏芳茁,家中兒子卡在喉頭的手、丈夫暴躁冷淡的話,讓原本最親密的人倫溫情蒙上了一層阻隔的霧。家庭外的大環境更是被霧所籠罩,環境污染、災害頻發、人為災難不斷,少年為早熟的愛情冒險劫車,中年人為生計碌碌麻木,老年人為退休上訪焦慮……“那些研究氣候的專家說,跟大氣污染有關,夏芳茁覺得,跟人心也有關。”[2]當社會物質文明的發展使人類淪為逐利的奴隸,人們便喪失了自己的精神本真,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中失去平衡。
雖然嘉男對生態破壞和人倫異化的種種現狀痛心憂慮,但是并不以消極、無望的態度對待人類未來的發展,仍舊是充滿著溫情的期待。正如《漢字的戰爭》這篇寓言性的小小說,因戰爭失去了雙腿的“兵”和被轟炸變成了小丘的山,聯合成“岳”,重新變得完美。戰爭是現代化欲望的極端爆發,它付出的是生命喪失的慘痛、生態環境的破壞。而只有當人類與生態統一和諧起來時,才能在秀美環境中富饒生活。
二、敬畏生命與天人合一
在生態意識中最重要的便是對生命價值的肯定,中國古代生態智慧中有著“仁者愛人”、“人皆有不忍之心”的“貴生”思想,西方德國著名哲學家史韋茲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學思想。人與動植物共存于自然中,都有著生存的權利,而當下對動物的亂殺濫捕,對生態社會的肆意破壞是敬畏生命之心的喪失。這必將導致整個人類的生存危機,物種滅絕、生物鏈條斷裂正是災難的先兆。人類只有以敬畏生命之心來善待萬物,與自然和諧相處,才能達到“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存狀態。
在嘉男的小說創作中,敬畏生命的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萬物生命的關愛;二是對肆意殘殺生命的深惡痛絕。這種對生命意識的重視多體現在人與動物的關系書寫中。《花黃》是以一只貓的視角敘述的。流浪貓花黃被賦予人類意識,它默默地看著病床上的老太婆、為喪事籌備的兒女們、痛苦卻不善言辭的老頭兒,希望老太婆能夠好起來。而小說中老太婆沒有把花黃僅僅是當作人類的寵物,而是把這只流浪貓當成了自己的家人,和老頭一樣的親密家人。老太婆去世前還囑咐花黃不要跑出去,以后跟著老頭過,把這兒當成家。從此在山野小路上,前面走著一個老頭,后面走著一只貓,這是一副多么美好靜謐的圖畫。在嘉男的小說世界中,動物早已融入了人的生活與情感中,相依相存,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不再是馴化動物的主人形象,而動物也不再單純只是被利用的“他者”,有著主體感情和尊嚴。這種人和動物的和諧是一種生命和生命間的相通,在萬物平等的情感交流中體現出倫理情懷和敬畏生命的生態意識。《畜語》這篇小說則從對關愛動物的敬畏之情和虐殺動物的悲憤之感兩個方面來進行對比書寫,如此愛之深,責之切正是嘉男生命意識的體現。羊莊歷史上的傳奇人物小老羊,慈悲善良,聽得懂畜語,看到吃羊肉都會悲痛哭泣,動物們都與他親近。而羊莊現今的大老解承辦了養殖場,他不僅殘忍虐殺豬、狗,還活剝貂皮,用鐵锨和屠刀來對待動物。兩個人對待生命的不同態度在小說中得到了不同的報應:小老羊去世后是六只羊哀叫提醒了村長得以安葬,而大老解的養殖場被暴風雨摧毀后死于狗的撕咬下。這樣的小說結局設置是作家嘉男對于肆意踐踏生命、濫殺動物野蠻行經的無比悲憤和痛恨,也同樣凸顯出對生命的關愛和敬畏。生命意識是融于生態意識之中的,在嘉男筆下的生命不僅是在于人類,也包括世間萬物,人類要在地球這個生態圈中生存就必須將其納入到倫理觀照的范圍中來。
讀嘉男的作品,會給人留下“真摯和詩性的印象”,這詩性不僅在于其溫潤的文字,還在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想之中。她的創作多以城鎮社會生活為主,但在其中不乏承載著“天人合一”生態理想的人物形象。如在《太平家國》中一臉土腥氣的六十多歲小老頭沈老師,他暫住在芥子山,那里的樹木、河道、拱橋,讓人覺得脫離世俗,感到耳根清凈,心神寧靜。大自然被賦予神性,能夠蕩滌人們心中雜念,賦予人類本真的力量。沈老師感召自然,通過義務講道來平復世人被物欲煩亂的心,開啟安詳簡單幸福生活之道。沈老師的形象寄予本真心靈和自然生態融合的“天人合一”理想,使人想到萬物有靈、心即自然、自然即心的哲理。而受沈老師啟迪的丁萬家也看破金錢和物質的本質,在月色清涼中走向藍色海洋,將乘著白船去學道修行。小說結尾是丁萬家的豁然開朗和問道修行,倒不如說是嘉男對于世俗煩惱的豁達超然和對“天人合一”自然純真的美好向往。
三、生態審美取向形成的動因
生態意識在作家寫作時是一種自然地流露,作品中生成的生態意義需要讀者去感受和體味。從生態批評理論看,作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書寫與作家的文化背景、經歷是密不可分的。嘉男形成生態審美取向的動因也是多方面的。
美國學者托馬斯·J·萊昂說過:“對自然文學最初及最大的影響當然是這片土地本身。”[3]黑龍江中俄邊境廣袤的黑土地和濃密的樹林成為嘉男童年潛藏的記憶,也成為后來小說中北方“林城”的原型。而現居地威海——被譽為“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其大海的波瀾壯闊、空氣的清新純澈、山林的青翠可人,也滋養著其小說中的生態書寫。嘉男從林城,歷經多個地方,最終定居海濱小城,不同的土地給了她敏銳的自然感受力。自然是客觀存在的,只有人去主動擁抱自然,熱愛自然,才能領略到自然的千姿百態,才能憂懷生態的未來。關注嘉男的博客,不少博文和照片記錄著鶯飛草長、蟬鳴流云、落英秋葉的自然景色,可見其對于自然的喜愛之情。然而商業經濟的發展帶來的生態問題日益凸顯,尤其新世紀以來生態已經成為關乎人類持續發展的大問題。“灰天灰地,蒙蒙的霧,不是仙氣,是氣象預報上說的輕度污染。這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站在陽臺上能看見海的日子越來越少了。”[4]對自然一向敏感的嘉男面對環境的惡化,在寫作中便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對當下生態惡化的擔憂及對往昔美好生態的向往。
伴隨新世紀經濟的迅速發展,文化呈現多元繁復的景象,但嘉男的創作卻秉持著一種沉靜、簡樸的態度,透過物欲的“空氣污染”書寫平實的日常生活及生態理想。究其原因,她對傳統文化的自覺接受和認同是不可忽視的一方面,這也正是書寫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精神養料。如《太平家國》中沈老師講道放本心、求純真;《誰比誰幸福》中馮元秀學佛重修行、慈悲處事;《鮮花次第開》中鐘教授重儒學倫理,淡然處世;《安詳之道》中萬芬立意學佛,有意傳授傳統文化;《塵勞》中昔緣師傅心寬向善、放手塵勞……這些小說人物的身上所承載的儒學、道學、佛學的文化,正是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寶貴資源。儒學“仁者愛人”及“仁、義、禮、智、信”的智慧,對當下人倫異化、道德滑坡的社會現狀尤為珍貴而迫切;道學崇尚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強調人們只有效法自然才能夠順應人性,保持人性的本真自然,與大地萬物同生長共呼吸;佛學講求“慈悲為懷”,“萬物有靈”,人與自然萬物平等,敬畏生命。嘉男自身注重修行,堅持素食主義,更賦予作品由內及外的自然平和。道家崇尚自然與佛學慈悲之心,為她親近自然提供了內在的文化心理動因,使生態意識在創作中自然流露出來;而儒學中的人倫關懷內化在人類生存的博愛之中,生成人類社會和自然共態互生的理想。
一直以來,嘉男小說對“女性問題”的敘述得到讀者及評論家的重視,而近幾年的創作有意傾重生態意識,這與作家創作心態不無關系。在創作談中,嘉男說道:“反思自己,從前,我極不喜歡看描寫現實的小說,個人寫作也在一個狹小的天地里打轉,也許是年齡的原因,也許是現實到了無法回避的程度,我的筆終于有了方向。”[5]而這個方向便是面向社會現狀,面向生態問題,嘉男肩負起作家的社會責任感,通過真誠而平靜樸素的敘述,給讀者以深思,給社會以警醒。可貴的是,她的社會現實書寫并沒有流于說教,而是在曾經熟悉的日常生活書寫中將生態意識自然地融合其中。如在女司機夏芳茁家庭問題的主枝干上抽出生態及社會問題的新枝芽(《大霧》);在愛情婚姻糾紛的神秘水庫后帶著城市侵吞農田的一絲嘆息(《水底》)等。這也正是嘉男小說生態意識寫作的獨特之處,以日常敘述滲透生態問題,不僅使讀者感受到生態問題就是身邊的現實,又避免了反映社會問題的說教呆板。
[1]嘉男.人民的墻[J].青島文學,2013,(8).
[2]嘉男.大霧[J].時代文學,2013,(7·上).
[3]Thomas J.Lyon,ed.The Incomperable Lander: Abook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M].Bos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4]嘉男.隨感[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cc1a40102v02t.html.
[5]嘉男.身邊的現實[J].山東作家,2011,(4).
(責任編輯:黃加成)
For the increasingly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man and man, many writers’ creations show their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Different from the profundity of other writers’ ecological theory, Jianan’s novel creation displays the daily life in small towns with women's broad heart and poetic language, reveals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with human concern in the plainness and sincerity, and constructs the ideal state of life unifying man and nature. This is related to her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which is gradually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nurturing and inner feeling. Such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naturally shows a beauty of reality, kindness, and poetry.
Jianan;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poetic;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2014-12-28
李小凡(1990-),山東淄博人,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13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I041
A
(2015)02-00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