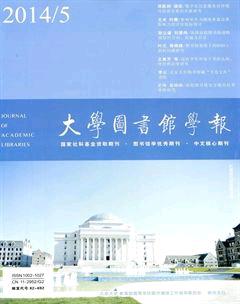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述略
李云
摘要 北京大學圖書館購入的“大倉文庫”典籍,在日本大倉文化財團大倉集古館以“大倉藏書”的名義保存了101年。這批書是1912年董康赴日本時將自己誦芬室部分舊藏和譚錫慶正義齋的部分典籍一并售與了大倉文化財團的創始人大倉喜八郎。這批典籍數量大、內容豐富、版本種類齊全,其中的善本典籍兼具極高的文獻價值、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可能是一批今后再也難得尋見的書藏珍品。
關鍵詞 大倉文庫 大倉藏書 北京大學圖書館 董康 誦芬室
2013年12月12日中午11時50分,九輛載有58個航空大木箱的中國郵政運輸車將留存在日本一個多世紀的931部、28143冊典籍順利運抵北京大學圖書館。按照2013年6月20日北京大學與大倉文化財團簽訂的《中國古籍善本轉讓合同書》相關內容約定,這批典籍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地庫以“大倉文庫”專藏的形式永久整體保存。2014年5月4日在文學苑,朱強館長為視察北京大學的習近平總書記展示了“大倉文庫”中的12部珍本。至此,北京大學圖書館歷時近兩年的收購日本“大倉藏書”工作告一段落。
本文將對這批典籍外流至日本的大致情況、書藏特征與價值作初步探討。
作為一個藏書集合,首先要考量“大倉文庫”形成的過程。
在對這批典籍實施收購的過程中,我們曾向大倉集古館理事長大崎磐夫先生和事務局長澁谷文敏先生了解當初這批書入藏大倉文化財團的情況,兩位先生的答復是在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中原本的大倉集古館建筑坍塌,相關檔案損毀了,幸運的是藏書的庫房沒有受到破壞,所以今天只知道是上個世紀初大倉文化財團的創建人大倉喜八郎先生從中國藏書家董康先生手中購買的。
董康,字授經,號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生于同治元年(1862)。26歲中舉,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授刑部主事之職。自此,董康開始了他的法務職業生涯。初往日本是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董康由沈家本保奏為法律館纂修兼京師法律學堂教務提調,并被派往日本調查司法,回國后任大理院推事。清帝退位后,董康曾應司法總長梁啟超的邀請,擔任司法編查會副會長,歷任大理院院長、修訂法律館總裁、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后被聘為上海法科大學校長,民國二十四年(1935)又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抗戰爆發后,民國二十六年(1937)12月,董康擔任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成漢奸。抗戰勝利后,董康被國民黨政府通緝入獄,民國三十六年(1947)死于獄中。
董康藏書始于得中進士進京為官之時,他經常流連于琉璃廠書肆搜訪古籍。由于官俸低,大宗書藏和價昂之書多不敢問津,但他鑒別能力過人,極具慧眼,常從書商認為毫無價值的書堆里發現珍本秘籍。他曾以八元的價格購入清法式善手抄《宋元人小集》八十冊,民國五年(1916)他再得宋本周密撰《草窗韻語》一部,這是數百年來歷代藏書家未曾提及的一部秘籍,當時書界人士稱之為“尤物”。董康后來將此書以二千元高價賣給了蔣汝藻,蔣如獲至寶,他的書閣也因此易名為密韻樓。由此觀董康聚書有兩個特點:零敲碎打、隨聚隨散。他一生聚書不多,有錢時購入,拮據時出售,成為一種常態。
“董康的書大宗出售有兩次,一次是在民國初年東渡日本時,售與日本巨富大倉氏,一次是在民國二十年(1931)售與北平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現藏有董康《誦芬室藏目》一卷,手抄本,只存甲部四集,共六十三種,大部分為明清刻本,每集后題一萬元,概為其賣書清單,但不知買者為何家。”
清末民初的法界精英有一部分有留日經歷,并由此形成了后來北洋時期法律界的東洋派,董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一生考察、游覽、訪書,往返日本共七次,后四次在他的《書舶庸談》中已有詳細的記載。前三次分別是前文提到的光緒二十八年(1902)和“光緒三十二年(1906),初夏至歲末,游日本,卜居東京小石川,與島田翰交,秋日同赴京都、奈良訪書”,“辛亥年至1913年因革命避居京都”。董康的部分誦芬室舊藏就是他在第三次赴京都躲避辛亥革命期間售賣的,“曾以部分藏書出售給日本巨富兼古籍收藏家大倉氏以維持生計”。
馬忠文先生曾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圖書館發現王國維的三封未刊信札,其中兩封是寫給繆荃孫的。在1912年1月9日致繆荃孫的第一封信中王國維提到,“誦芬室亦有來此之說,大約暫以售書為活”。
1912年7月15日《朝日新聞》第三版報道了日本財界巨頭大倉喜八郎購入中國董康的誦芬室藏書。
我們在對這批藏書進行編目整理中特別留意董康對這批典籍收藏過的痕跡。藏書印記是藏書家曾經遞藏典籍的直接證明,“大倉文庫”典籍中董康的藏印有“昆陵董氏誦芬室收藏舊槧精抄書籍之印”、“董康私印”、“毗陵董康鑒藏善本”、“誦芬室藏害記”、“董康秘篋”、“董康宣統建元以后所得”等,但加蓋了這些藏書印的典籍卻不到三十種。經仔細察看后發現,這些典籍與鮑氏知不足齋有關的十六種書中有十一種加蓋了董康藏印,其中五種可斷定為鮑氏知不足齋抄本,六種是經鮑氏批校遞藏之書。而加蓋董康藏印的明清抄本、刻本多也是由名家抄刻之典籍,如《耕學齋詩集》十二卷為清雍正元年(1723)文瑞樓抄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為清道光五年(1825)袁氏貞節堂影宋抄本,《唐書》二百卷為明嘉靖十八年(1539)聞人詮刻本,《陳忠裕全集》三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年譜》三卷為清嘉慶八年(1803)簳山草堂刻本。這一情況印證了董康由于經濟條件所限沒有能力廣聚宋元善本,于是他把精力集中在了對價格相對較低,且版本價值和文獻價值要高于普通典籍的名家抄本和名家刻本的搜集上。可以認為這些有著董康鈐印的“大倉文庫”典籍都是當年誦芬室的得意收藏。
我們在整理中還發現了有的藏書雖然沒有董康鈐印,但有證據能證明這些典籍曾是董康誦芬室舊藏。如宋人陳與義撰明初刻本《簡齋詩集》十五卷,書中鈐“守山同印信”、“同山眼福”、“拙盒經眼”、“白云紅葉盒藏書畫之章”、“海豐張守同印”、“大倉文化財團藏書”朱印,無董康印,但在書尾襯葉上有墨題“宣統辛亥八月從授經京卿叚觀。仁和吳昌綬記”并鈐“仁和吳昌綬伯宛甫印”朱印。由此可知,是書在被董康收藏期間曾為吳昌綬借閱。另外,明末清初抄本《南詞》四十二種四十九卷《附錄》三卷,首冊書首襯葉有乾隆癸卯蕓楣朱筆題記,《鳴鶴余音》后有光緒丁未吳昌綬校記二則。書中鈐“知圣道齋藏書”、“南昌彭氏”、“遇讀者善”、“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圖書印記”、“李之郇印”、“宛陵李之郇藏書印”、“伯雨”、“江城如畫樓”、“伯宛校勘”、“大倉文化財團藏書”朱印,惟獨不見董康藏印,但在《簡齋詞》、《樵歌》、《知稼翁詞》等卷末有光緒戊申董康朱筆校記。又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國家圖書館有《南詞》十三種十六卷,著錄“董氏誦芬室抄本”,據此可斷定是書為董康誦芬室舊藏,而國圖所藏是當年董康據其所藏抄撮而成。另,宋楊萬里撰、日本元祿間據宋端平刻本抄《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目錄》四卷,書中鈐“島田翰讀書記”、“大倉文化財團藏書”朱印,書衣背面題“影宋足本楊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島田翰奉贈授經先生以為他日券”,書內夾存島田翰致董康信札一通,由于這批書在大倉集古館一直處于封閉的保存狀態,因此我們確信該函即為董康生前夾于其中。此書當是董康第二次到日本時島田翰的贈與之物,為誦芬室舊藏。endprint
在“大倉文庫”中還有一部“四庫著錄”典籍,明周嬰纂、明崇禎十六年(1643)刻《卮林》十卷《補遺》一卷,書中鈐“周雪客家藏書”、“東山外史肖巖沈氏珍藏書畫”、“沈閬昆印”、“肖巖藏書之章”、“拜經樓吳氏藏書”、“曾經八千卷樓所得”、“詩家眷屬酒家仙”、“大倉文化財團藏書”朱印,在卷端及每冊書的首頁、末頁等正式鈐印的位置上未發現董康的藏書章,但在第二冊書的皮上卻鈐有長方形“董康私印”和橢圓形“課花庵”藏印各兩枚,向右傾斜縱向雙排列,左側依次為“董康私印”、“課花庵”、和“董康私印”,且前兩印重疊;右側為“課花庵”。從印跡的布局形式和所在位置上看當是董康順手隨意加蓋,也許董康生前就沒把在藏書上加蓋藏印當回事兒。
上述“大倉文庫”典籍中所屬董康舊藏的三種情況說明了董康只在他認為重要的藏書上加蓋藏印,而很多沒有留有董康印記的典籍應該也是誦芬室舊藏。但有一點應該明確,就是“大倉文庫”中的典籍并不都是經董康遞藏過的。
在整理“大倉文庫”過程中,有兩個人的印記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即譚錫慶和錢桂森,他們對捋清董康所售這批典籍的部分來源有一定的幫助。
如果按洪亮吉在《江北史話》中對五大類型藏書家的標準劃分,譚錫慶是屬于典型的掠販式藏書家,他聚書的目的就是賣。
譚錫慶,字篤生,河北冀縣人。《琉璃廠小志》記:“正義齋,主人譚錫慶,……于光緒二十五年開放(先于光緒十六年在文昌會館經營數年)后設肆于東路南,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訓之書。惟其作為往往以魚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欺騙,蓋仿舊抄本為其特長也。并藏有《長安獲古編》、《歷代人物年譜》等板,經營二十余年歇。后為孔群書社。”
馬忠文認為董康在日售書是和譚錫慶聯手經營。1912年11月王國維在給繆荃孫的第二封信寫道:“授經北方行未歸,聞以重價購得《永樂大典》十余冊,又購他書,共數千元,而老譚之款尚無著,渠自謂賠了夫人又折兵者,語或然歟?”“老譚”即譚錫慶。《王國維全集·書信》收錄了這年9月王國維曾致繆荃孫的一封信,“譚篤生忽患霍亂去世,授公與之尚有交涉未了,擬于二十后赴北京一行,一月有半返回。”將兩封信的內容聯系起來看,董康在譚錫慶去世后回京的目的是處理拖欠譚錫慶的錢款問題。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推斷,董康所欠譚錫慶的錢,是譚錫慶生前將正義齋的部分典籍交由董康同誦芬室部分舊藏一并出售給了大倉喜八郎,而所得書款在其去世前未能收的款項。
在“大倉文庫”中有37種書有譚錫慶的四種鈐印,“譚錫慶學看宋板書籍印”、“譚錫慶學看元本書籍印”、“畿輔譚氏藏書印”和“篤生經眼”。尤其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其中的17種四庫進呈本,這些典籍中沒有任何董康收藏過的痕跡。而在另外一種譚錫慶未經收藏的四庫進呈本《桂隱詩集》四卷《文集》四卷《附錄》一卷中則鈐有“毗陵董康鑒藏善本”朱印。清末民初,私人藏書家對四庫進呈之書的搜集趨之若鶩,這些曾為宮廷收藏的典籍因其極高的文獻價值和歷史價值在當時售價頗高。根據董康的聚書特點,他在如此重要的藏品上不可能不留下諸如藏印、題跋之類的遞藏痕跡,而從其一生的經濟狀況看他似乎也根本沒有能力購入這么大數量的四庫進呈本。因此“大倉文庫”中凡有譚錫慶收藏印的四庫進呈典籍應該是他生前委托董康出售的。
在譚錫慶收藏過的17種四庫進呈本中,11種書內同時又分別鈐有“犀盒藏本”、“教經堂錢氏章”、“錢犀盒珍藏印”、“錢氏犀庵收藏”、“海陵錢犀盒校藏書籍”等朱印,均是錢桂森的收藏章。錢桂森是“大倉文庫”中四庫進呈本流入譚錫慶手中,而后又被董康售賣東瀛的源頭人物。
錢桂森,字犀庵,江蘇泰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累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曾授業徐世昌。錢桂森生平藏書極富,藏書室名“教經堂”,其書大半得之翰林院,多四庫進呈本。趙萬里先生在《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中講:“《四庫全書》完成后,庫本所據之底本,并為發還范氏,仍舊藏在翰林院里,日久為翰林學士拿回家去,為數不少,前有法梧門,后有錢犀庵,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錢桂森從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及第直到咸豐七年(1857)才補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這七年間他一直擔任翰林院編修之職,可以非常方便地接觸到翰林院收藏的典籍。此時《四庫全書》早已編纂完成,對未經退還的進呈本(有一部分同是四庫底本)的管理遠不及乾隆時期嚴格,加之此前的法式善等人已開了“不告而取”的先河,翰林院官員將典籍采用隨身夾帶出宮的現象屢見不鮮。在這樣一種環境下,錢桂森有充足的時間和機會將四庫進呈本私自攜帶出翰林院據為己有。直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他去世后,這些典籍才流入社會。可以肯定,“大倉文庫”中凡加蓋了錢氏藏印的四庫進呈本都是譚錫慶收購的錢桂森生前從宮中盜出的“教經堂”舊藏。
在“大倉文庫”中有一部宮廷舊藏的來源尚待考證,即二十四函一百四十七冊一百四十四卷,一部完整的《大清世祖章皇帝寅錄》,其余的中國古籍都應該是董康當年出售給大倉的。根據上述分析,“大倉藏書”中的大部分是誦芬室舊藏,也有一部分是譚錫慶正義齋的藏書,而和刻本的大多數典籍則是大倉集古館自行補充的收藏。另有朝鮮刻本《增刪濂洛風雅》五卷,已改為四眼線裝,顯然是日本人所為,故亦不屬董康舊藏。
這批典籍從民國六年(1917)集古館落成后就一直保存在庫房中,世稱“大倉藏書”。大倉文化財團大倉集古館也因此成為日本收藏中國典籍數量較多的機構。
“大倉文庫”共有93l部、28143冊,其中古籍906部、28020冊,包括中國古籍715部、25432冊,和刻本190部、2576冊,朝鮮本1部、2冊,這一數量足以撐起一個中型圖書館的古文獻特藏規模。若把這些典籍按四庫分類,則經、史、子、集四部皆備,經部94部、史部193部、子部158部、集部412部,又有叢書27部,碑帖22部。其中集部典籍數量最大,這是中國傳統私家書藏普遍結構特征的反映。如果以版本歸類,其數量分布為刻本612部、活字本62部、抄稿本116部、鉛印石印本等86部、鈐印本5部、摹刻拓本3部、碑拓22部,覆蓋了典籍的各種版本類別。數量大、內容豐富、版本種類齊全是“大倉文庫”的總體特征。endprint
“大倉文庫”所屬715部中國古籍的精華部分當為宋元明刻本、活字本、抄稿本和四庫進呈本,下面對其價值舉例論述。
“大倉文庫”有中國古籍刻本479部,其中宋刻遞修本4部、元刻本9部、明刻本155部、清乾隆前刻本153部,清嘉慶至宣統刻本151部,民國刻本7部。刻本的善本比例達67%。在這部分典籍中以宋刻遞修本、元刻本和明刻本價值最高。
宋刻遞修本因其每次補刻特征明顯,因此對歷代遞修之源流研究十分重要,堪稱宋刻遞修之范本。
《宋書》一百卷、《魏害》一百十四卷,屬“眉山七史”系列中的兩部。南宋紹興年間,四川轉運使史景度在眉山刊行南北朝史七種,書板歷經元明清不斷修補印刷,清嘉慶年間毀于江寧藩庫火災。此兩書最晚遞修至明嘉靖十年(1531),為現存同類書中刷印較早的印本,也是保存宋刻特征最豐富的宋刻遞修典籍。
宋寶佑五年(1257)刻元明遞修本《通鑒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不但存有大量的宋代原刻版葉,又經毛晉、方功惠、陳希祖、張之洞等多位名家私藏,且尤以方功惠對其珍愛有加,為防蟲蛀,用萬年紅紙作襯將書重裝。足見此書價值之珍貴。
九部元刻本中雖有八部為后世略經修補的印本,但亦屬書品極佳的精刻精印本。其中的《春秋屬辭》十五卷為元至正二十年(1360)至二十五年(1365)海寧商山義塾刻本,該書字皆趙體,刻功甚精,用皮紙精印,清代通志堂本即據此翻刻。目前存世者僅寥寥數部,且多為明弘治六年(1493)高忠重修本,此本字體清晰、版式整齊,印制當在修版之前。
如果我們因為13種宋元刻本中多數是后世遞修補印之書而多少有些遺憾,那么155部明刻本的入藏則足能使我們的心境得到平復。由于這批明刻本中絕大多數是嘉靖以前的刻本,是明刻本中的精品,加之一次入藏數量較大,且不乏海內外孤本,所以得到古籍鑒定專家的一致認同。
如明弘治三年(1490)馮忠刻本《詩話》十卷為北平黃叔琳養素堂舊物,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此之前僅上海圖書館藏殘本一至七卷。又,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準石谷書院刻《唐十子詩》十種十四卷,天一閣原藏殘本一部,存常建、郎士元、嚴維、劉義四家,“大倉文庫”書則十家俱全,為孤本。再如明刻本《東坡先生往還尺牘》二十卷,現知此書是最早的蘇軾書信選集,在此之前僅知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孤本一部,經與此本比對,始知上圖所藏實為僅存九卷半的殘本,此本即為現存最早的一部全本,孤本。
即便是在普通刻本典籍中,也有難得尋覓的珍稀版本,如清道光十年(1830)錢唐瞿氏清吟閣刻本《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此書首先是出自名家刊刻,清吟閣曾因刻印宋周密的《絕妙好詞》和清朱彝尊的《詞綜》而聞名清代書界;另外書中有大量朱筆校及改刊印樣,是珍貴的古籍校勘修版實物;再者該書曾經清末著名藏書家楊繼振和李希圣遞藏,并鈐楊氏著名的251字長文藏印。
“大倉文庫”的中國典籍中有活字本59部,其中明木活字本一部、銅活字本14部,清木活字本43部、銅活字本一部。這些活字本中以明銅活字本最為珍貴。首先,明代銅活字本流存至今者已是鳳毛麟角,蓋因明代法律規定除宮廷、寺院之外,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鑄銅字排印書籍,所以存世至今的民間鑄印銅活字典籍的文物價值極高,另外,當初以銅活字排印的典籍所依底本多為宋版書,今若宋版散佚,明銅活字本就成了最早的版本,于校勘至關重要,所以又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因此其版本的珍貴程度也就成了下宋一等珍本典籍。北京大學圖書館能一次入藏如此數量的明銅活字本是絕無僅有的。
在14部明銅活字中11部是《唐人詩集》本零種。其中有《沈儉期集》四卷,唐人沈儉期詩文集于《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有十卷本,《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亦為十卷本,而《郡齋讀書志》和《文獻通考》則著錄五卷本。今該書宋本的十卷本、五卷本均佚,現存最早的版本當為明正德十三年(1518)王廷相所刻《唐沈儉期詩文集》七卷和唐銅活字本《唐人詩集》四卷本,即此本。之后又有嘉靖十九年(1540)刻《唐百家事》本《沈云卿集》二卷,明嘉靖黃氏刻《十二家唐詩》本《沈儉期集》二卷,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霏余軒刻《前唐十二家詩》本《沈儉期集》二卷,以及明刻《唐五十家集》本《沈云卿》二卷。就存世的沈儉期集的版本看,此銅活字本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另14部銅活字《唐人詩集》本零種的版本情況和《沈儉期集》的情況類似,均是同種書中最早的,或最早之一的版本。
明弘治年間無錫有華燧、安國兩家鑄銅活字印書,很是出名。華燧的侄子華堅更以蘭雪堂名號排印了一批為藏書家竟相爭藏的精品銅活字版典籍,“大倉藏書”就中有一部鑄字排印的《錦繡萬花谷》,被日本列為“重要美術品”。在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大倉文庫”中,華氏、安氏的銅活字本各有一部。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目錄》二卷,明正德八年(1513)蘭雪堂金屬活字本。《白氏長慶集》是元稹為白居易編纂的最早的五十卷本詩文集,當初因唐穆宗已去世,唐敬宗繼位,準備第二年改寶歷元年,為紀念長慶的最后一年,元稹便以此年號命名該集。之后白居易又在此基礎上不斷修訂,最終成七十五卷,并抄錄五部,分藏于廬山東林寺藏經院、蘇州南禪寺、東都勝善寺、侄子龜郎家、外孫談閣童家。雖然這五部書后來都毀于唐末五代戰亂,但白居易的這部詩文集的內容通過輾轉傳抄,除四卷在宋代亡佚外,其他七十一卷都保留了下來,成為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文人自編集之一。這部銅活字本的《白氏長慶集》是現存白氏詩文集中最早的明代版本。明代中期的金屬活字印本極其少見,保存完整更為不易,此本之外尚知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九十四卷,明錫山安國金屬活字印本。此書缺《外集》六十六卷。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國內藏有是書的僅四家,且均為殘本。其中南京圖書館藏三百二十四卷,《前集》、《后集》和《外集》全;天一閣藏二百十四卷,《續集》全;上海圖書館藏九十六卷,五集均有殘;國家圖書館藏九十六卷,五集亦均為殘。此四部典籍所存卷帙各有不同,四書相配,僅缺《別集》卷七至十二,而“大倉文庫”書之《別集》是完整的,因此五書相配可合為完璧,或“大倉文庫”書與南京圖書館所藏《外集》相配亦能成一部完整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endprint
清木活字本43部典籍的大部分是清乾隆時期的武英殿聚珍版,這類典籍雖于國內大型圖書館中多有所藏,然若要配齊一套是非常困難的,此次入藏的武英殿聚珍本典籍有他館所不藏者,從古文獻資源共享的角度講,這為國內公藏單位協作共享一套完整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向前推進了一步。
“大倉文庫”中國典籍中的另一大特色是111部抄稿本,其中多名家抄校、遞藏之書,孤本、全本疊現,抄寫精良,裝幀規整,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中精品典籍的一部分。
若論名家抄校本,這批書中當首屬九部鮑氏知不足齋抄校的典籍。知不足齋為清中期江南著名藏書樓,且以抄書校書享譽書界。第一代主人鮑廷博(1728-1814),不求仕進,喜購藏秘籍,常與江浙著名藏書家互相借鈔,廣錄先人后哲所遺手稿。所抄書籍流傳至今有名可稽的達一百四十余種。子鮑士恭、孫鮑正言、重孫鮑寅世守家風,亦抄校不綴。乾隆間開《四庫全書》館,詔求天下遺書,鮑士恭進獻626種,居私家進書之首。此次入藏明確為鮑氏知不足齋抄本的有:《溪堂集》十卷、《謝幼盤文集》十卷、《毅齋詩集別錄》一卷、《耕閑集》一卷、《古梅吟稿》六卷、《燕石集》十卷、《僑吳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友石山人遺稿》一卷《附錄》一卷、《贈朝列大夫云松巢朱先生詩集》三卷。其中可斷定為鮑廷博手抄者為《燕石集》《僑吳集》和《友石山人遺稿》三部,其他書中亦有鮑廷博批校手跡。
另一部可與鮑氏知不足齋并稱為名家抄校本的典籍則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抱經堂寫校本《唐律疏議》三十卷《圖》二冊。抱經堂為清乾隆年間大校勘學家盧文弨(1717—1796)的藏書室,盧一生校勘古籍二百多種,并將其中十余種鏤板刊印,匯成《抱經堂叢書》。此書即為盧文弨晚年的抄寫校過本。
在111部抄稿本中,有一部大型類書,明代藍絲欄寫本《文苑英華》一千卷,全書21函101冊。是書煌煌巨帙,綿延宋本一線之傳,首尾完整,字體拙樸,屬典型的明抄本風格,極具文物價值,深得專家稱道。
觀“大倉文庫”中國典籍,如果我們把著眼點放在書藏的遞藏關系上,就會有一批曾為清官舊藏的珍本典籍特別引人注目。這批典籍26部,從版本類別上包括了刻本和抄本(含寫本)。由于26部典籍已按版本類別歸類,故此數量不應在479部上重復累計。其中22部為四庫進呈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為編纂《四庫全書》而廣征天下遺書,此后各省督撫、鹽政購進、借抄遺書和私家進呈原書總計一萬三千余種,這些進呈本全部收藏于翰林院,每種書首葉鈐“翰林院印”或“翰林院典簿廳關防”滿漢文印,首冊書衣鈐乾隆某年某月某督撫某送到某家藏某書壹部計書若干本戳記,這些書稱“四庫進呈本”或“四庫采進本”。《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后,未經發還的進呈本一直存于翰林院,庚子之變時慘遭兵燹損失殆盡,目前存世僅近九百部,其中是四庫底本的有三百多部。在“大倉文庫”所藏鈐有滿漢文“翰林院印”的二十四部典籍,除有兩部存疑外,其他二十二部部確為四庫進呈本,這之中“四庫著錄”十二部,“四庫存目”七部,“四庫未著錄”三部;在十二部“四庫著錄”本中又有三部四庫底本,其中就有已近失傳而重現人間的孤本。如四庫進呈本、四庫著錄本、四庫底本的《字溪集》十一卷《附錄》一卷,是書為宋淳佑年間官至朝奉大夫的陽枋所撰,約明末清初散佚,世無傳本,此為館臣在編《四庫全書》之初從《永樂大典》中輯佚的謄清稿本,透過四庫館臣在上面的刪改痕跡,可比對該書與閣本之差異,亦可窺見《永樂大典》之原貌,以及四庫館臣校勘之得失和四庫館的謄寫之正誤。此本即成為《字溪集》現存最早的版本,孤本。
清宮舊藏中的另外兩部珍本,其一就是文津閣四庫全書本,一百二十卷、四十二冊的《南巡盛典》。此書各冊首葉鈐“文津閣寶”朱印,末葉鈐“避署山莊”朱印。書中鈐“所寶惟賢”、“大倉文化財團藏書”朱印。乾隆三十六年(1771)高晉等纂輯《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記乾隆四次南巡事。乾隆四十九年(1784)阿桂等重加纂輯,增記乾隆第五六次南巡之典,書一百卷,首二卷,遂將已收入《四庫全書》高晉的一百二十卷本抽出,替換為阿桂的一百卷本。此即文津閣《四庫全書》抽出之本。而《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一百四十四卷則是宮中舊藏大紅綾本。卷五至十六抄補,書衣用祥云紫綾。清代各朝實錄共繕寫正本四部、副本一部。正本有大紅綾本兩部,用于存檔,一部藏皇史成,一部藏盛京崇謨閣;小紅綾本兩部,供皇帝查閱,一部貯于乾清官,一部貯于內閣實錄庫。而作為副本的小黃綾本,是以備隨時查閱的,也存在內閣實錄庫。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時,《世祖章皇帝實錄》就是以藏在當時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小紅綾本為底本。此為正本中的大紅綾本。此兩部珍本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
通過上述分析論述,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首先,“大倉文庫”典籍珍善之本眾多。根據統計,“大倉文庫”善本總數為491部,約占其所含中國古籍總量的69%,且孤本、全本眾多,其部分刻本、抄本、名家批校題跋本、活字本、四庫進呈本,刊刻精良,抄錄批校精朗細密,品相舒展完好,多名家遞藏。這批典籍不僅具有較高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并且因其所承載的歷史印記而具有一種特殊的和極為豐富的文化內涵,進而也具備了極高的文物價值。所以“大倉文庫”可能是一批今后再也難得尋見的書藏珍品。
其次,“大倉文庫”的人藏有助于從數量和品種上補充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古文獻所缺。經初步查詢比對,“大倉文庫”典籍中的51.2%為北京大學圖書館所未藏,從而提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為教學與科研服務的古文獻保障力度。另外,“大倉文庫”的購藏不僅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自1939年李氏書入藏之后,第一次成批地整體購入逾萬冊的善本典籍,也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有收藏機構首次最大規模地回購留存在海外的我們自己的典籍,具有里程碑的意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