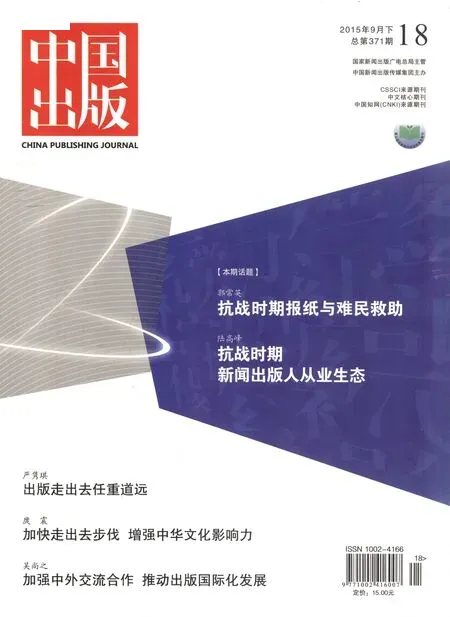抗戰時期報紙與難民救助*
□文|郭常英
抗戰時期報紙與難民救助*
□文|郭常英
抗戰時期,中國報界在宣傳和動員民眾積極抗戰的同時,也在發動社會開展難民救助、扶貧濟困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報紙有效的信息傳播、輿論引導和輿論監督,使抗戰期間的難民救助與之前有了很大不同。報紙輿論關注社會民生、倡行社會救助、營造關愛落難人群的社會氛圍,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與官方話語并行且相制衡的輿論空間,體現出“社會守望者”與“民聲傳感器”的媒體角色,發揮了報紙作為文化傳媒的特殊作用,也是近代報紙發展的歷史見證。
抗日戰爭社會動員難民救助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中國盧溝橋駐軍發動進攻,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軍隊在中國各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犯下滔天罪行,“日寇的炮火所到,日寇的鐵蹄所到,不僅我們那里的男女同胞,或萬、或千、或百、或無數的生命,橫遭慘酷無倫的毀滅、屠殺和奸淫……”[1]這場戰爭歷時8年,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不盡的屈辱,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流離失所的難民無數,其中包括許多“失學、失業、流浪”的文人學子,他們也深刻感受到侵略者的罪惡與落難者的凄慘。在抗戰開始之后,眾多報刊大力宣傳愛國救亡,鼓勵民眾團結抗戰,在民眾動員方面形成壯舉。與此同時,報界對戰時民生狀態的關注則顯示出與以往戰爭時期不同的特點,救助戰爭難民的問題成為報紙內容中一個重要主題,形成具有時代特征的社會現象。筆者對此試作探討。
一、積極有效的社會動員
在近代中國,各種戰亂與紛爭幾乎從未間斷,戰亂必然帶來難民問題。不同時期大大小小的戰爭,都會導致多重社會災難的發生和戰爭難民的出現,構成困擾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歷史時期,政府和社會都會對難民問題給予關注。然而,在抗戰期間,社會民眾對于難民的關切和救助,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廣泛與深入。從材料所見,無論是從難民問題的提出,還是到各種救助方案的實施,均能顯示社會各界的重視與參與,救助難民成為不少民眾投入抗戰活動的自覺行動。
民眾的積極參與還有力地改變了當時政府在難民救助方面的不足。抗日戰爭是由日寇大舉侵華帶給中國的一場全面戰爭,這場大規模的戰爭歷時較久,造成的難民傷員數量眾多。由于戰爭帶來的資金緊張、物資匱乏等困難十分嚴重,當時政府的難民救助工作很難做到及時、到位和完善。此時民眾的救助不僅募集了一定的資金和物資,還營造了對難民熱情關愛的社會氛圍,構成了政府與民眾共同推動社會救助的態勢。而這一局面的出現,是與當時報界的有效輿論宣傳分不開的。各種報紙在難民救助問題上表現出的同情心和責任感令人感動。
1.發布消息引發民眾關注難民救助
抗戰開始后,流離失所逃亡到上海的難民處境堪憂。《申報》曾載文發布1937年11月的有關情況:“近日本市天氣突轉寒冷,各收容所及沿街流浪難民,受寒凍死者,日漸增多,尤以南市難民區難民及災童,因此死亡者,日有十數人,最足驚人……切望各界熱心人士,慨捐衣被,火速予以救濟”。[2]另有報道稱:“難民區現有難民四萬余人……糧食斷絕,兩日不獲裹腹,生命頻于危殆。”[3]關于難民生存的惡劣狀態,不僅《申報》記者所關注,此類消息在戰時報紙中比比皆是,由此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與同情。
在敵寇入侵、戰爭來臨之時,國家安危、民族存亡成了最為突出的問題。但同時,人們正常的社會生活遭遇重大沖擊,民眾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危害,難民中挨餓受凍的兒童、孤弱無助的老人、作戰負傷的傷員等,都成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給政府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日寇大舉入侵之下,嚴峻的戰場形勢、國力不足的困境,形成多種難解的社會問題,使本已窘困不堪的國民黨政府,在面對戰爭難民和傷員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和矛盾交織——亟須解決難民問題,而又無力妥善解決,甚至是難以顧及。政府也曾為難民救助問題發出號召、作出部署,但“底氣”不足,很難在救助難民問題上有實際作為。此時,報刊反映民情與民意的作用與社會發動的功能凸顯出來。
報紙還登載義演廣告進行難民救助宣傳。1937年11月2日,《申報》登載“名票名媛演劇籌款救濟難民”廣告。此次演出由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上海市分會舉辦,由于門票收入用于救助難民傷兵,受到社會各界的贊譽。[4]1939年5月25日,《申報》(香港版)登載中國救亡劇團舉辦義演廣告,這場演出更轟動一時。廣告顯示,此為該劇團“第七四二次大規模義演”,“為香港各界賑聯會籌款救濟傷兵難民”,從5月25日至27日連演三晚,分別演出《臺兒莊之春》等三部抗戰史劇和國防名劇。廣告宣傳稱,三場義演有“偉大的劇本”“精湛的演技”“宏麗的布景”“奇異的燈光”,吸引人們對演出的關注,有助于募捐活動的順利進行。[5]
報紙是當時社會的主要媒體,它關注戰爭時期的社會民生問題,著眼社會公益與慈善救助事業,倡行對難民與傷員的關愛與幫助,形成積極的社會影響,既在媒體傳播界營造起反映民間疾苦、影響社會生活的聲勢,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與官方話語并行且相制衡的公共空間。同時,在中國尚未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情況下,媒體影響下所形成的社會效應意義深遠,一方面促進社會對中國救助事業的關注,另一方面也為戰時民眾生活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
2.以輿論引導民眾參與社會救助
輿論引導是報紙作為媒體的重要功能之一。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社會和民眾帶來巨大的災難,在民族危亡之際,特別需要全體民眾的動員。報紙刊文鼓勵民眾參與抗戰,并呼吁民眾積極參與戰爭傷員救護與難民救助,所載文章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使人們認識到,參與傷員和難民救助,也是對國家做貢獻,是支援抗戰的有效方式。
《申報》曾刊文講述救助活動與抗戰關系:“一般人常常把救濟難民,僅看作是慈善事業,與抗戰并無多大關系。若干熱血青年,且以為出錢救濟難民,似不能表示其熱心為國的精神。他們總希望自己捐出的錢,都能作政府買槍炮之用,打退侵略者出中國。這單純的心情,我們極能理解,且表示無限欽佩。但確也太過單純一點。抗戰的第一個目的,即在求民族的生存,而所謂民族的生存,就是人民大眾的生存的集合。如其在抗戰期間,這些難胞的生存,不予相當的顧及,那就根本談不上抗戰……救濟難民,本質上和抗戰是有相同之點的。”文章還提出,“負槍前驅,為國效命,人人固須有此大決心;而站定崗位,量力而行,人人更須此大毅力。政無大小,事無巨細,均須奔赴于抗戰建國這個大目標。”[6]當時報紙刊載此類文章非常多,起到民眾思想動員與正面教育的效果。這一時期,上海各界人士以救助難民與傷員為宗旨,組織發起“節約救難運動”。這項活動得到上海各階層、各行業人員的熱烈響應,參與難民救助活動的人數也很多。
在抗戰時期,報紙還將救助傷員難民與“救國救家救自己”的道理聯系在一起,使人們認識到,參與難民救助工作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大公報》在武漢以救助傷員一事刊文告知社會:“現在的武漢,人口的眾多,商業的繁華,都是靠著前線戰士的拼命苦斗。我們不要因為現地的安穩而忘記了國家與個人的危險,同時更不要忘記了在前線為我們拼命的戰士……我們還不應該出些錢救助我們的戰士嗎?本報為負傷戰士募救助費,承各界踴躍輸捐,不勝感激。凡是大公報讀者,都是愛國者,他必然不忍坐視負傷的戰士而不救。望諸君盡力輸捐,俾戰士早痊,重返前線,為國殺敵!”[7]媒體將救助負傷戰士與“抗敵救國”“社會良知”等民族大義問題連結在一起,以其特殊的社會角色發出呼吁,觸及人們的心靈,激發民眾的情感,產生出一定的社會動員作用。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長期與外來侵略者的抗爭中堅強了意志,也在與西方列強侵略與壓迫的斗爭中積累了經驗。雖然日本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在這一時期,國家和民眾遭受的損失比中國近代以來任何一次外敵入侵所造成的損失都要慘重,[8]但是,抗日戰爭已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場全民族的戰爭,中華民族集百年“救亡圖存”、奮爭民族獨立的經驗,已逐步形成舉國動員、團結抗敵、一致對外、誓奪全勝之勢。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報刊媒體積極發揮輿論引導作用,呼吁社會民眾組織起來開展難民救助工作,也是中國社會的這種進步與發展的反映。
二、傳媒作用的發揮與受眾的認同
在上世紀30年代,刊載社會新聞的媒體仍是報紙,此期報紙還是重要的輿論工具。特別是《大公報》《申報》《新華日報》等大報要聞,不僅刊載人們所關注的戰爭消息,評論世界各國對戰爭的態度,對戰爭形勢和發展走向進行評析,同時還及時通報戰局與社會民生狀況。這樣的報道使民生狀態以及難民的痛苦與不幸能夠為社會所知曉,有助于引發民眾對戰爭難民問題的關注,喚起對落難百姓的同情與關愛。報紙期望通過媒體的呼吁和幫助,解決集聚在城市中的社會難民問題,以使團結抗戰有堅實的基礎和后方,也使前線將士能夠英勇地殺敵報國。許多上聯國勢、下接地氣的報道,成為各階層所關注的聚焦點。
就報紙與社會的關系而言,除了讀者的訂閱之外,社會對報刊的關注度和讀者與報刊交流的參與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報紙的公眾影響力。社會民眾對于一種報紙的信任與認同,常體現在讀者與編者交流和互動中,如向報刊提供信息、反映問題,受報刊影響參與有關社會活動,還有委托報刊表達或代辦事務等。類似情況在抗戰之前并非沒有,但往往時無時現,而在抗戰期間,這種報紙與讀者的互動情況則相當集中而明顯。此一現象反映出報紙主辦者關注國家安全和社會民生,圍繞救助難民與傷員問題,從傳播信息、引導輿論、輿論監督等一系列環節上履行報紙的社會職能,體現出其媒體的“社會守望者”的角色。
隨著抗戰時局的變化,戰事局面日益復雜,加之辦報經費緊張等原因,許多報刊被迫停辦或一度停辦,也有的報紙發行量逐漸減少。但是,我們從《大公報》《申報》和《新華日報》等主要報紙所刊載的內容來看,其中有關救助難民傷員的消息依然較多,社會各界對報紙主張的難民救助措施認同感也較為明顯。
如《申報》以《援助被難同胞的義務》為題,指出自全面抗戰以來,戰區同胞在日寇的蹂躪之下,顛沛流離饑寒交迫者僅上海及附近區城已不下數百萬人。“我們全民族是一體的,在這次圣大的全民族抗戰中間,戰區同胞所受的災難,都是換取民族生存和民族光榮的代價……救助他們不僅是慈善,還是無可避免的義務。如果只顧一身一家生活上的享樂,而漠視著戰區同胞的流離失所,那就不能不受良心上嚴重的譴責了。”[9]
對于如何救助難民和傷員,許多報刊也紛紛提出各種建議和方案。如《大公報》(漢口版)在《難民傷兵》一文中,就妥善安頓傷殘官兵一事提出三條建議:“(一)辦理殘廢官兵調查登記,各按其殘廢的程度,利用其一手一足,片聰片明,分配與其所能負擔的工作。(二)一切公私社團均應酌用殘廢官兵,使其精神得所安頓,國家得其貢獻。(三)給予殘廢官兵榮譽證,使國民知所崇仰。”[10]《新華日報》的《怎樣安置難胞》一文,就救助戰爭難民問題提出了三條方案:一是開放新建起來的市房大廈撥作難胞的宿舍;二是迅速發放募捐得款,保證全數用于難胞身上,并要公開收支賬目,肅清貪污;三是除為難民介紹職業外,政府劃撥專款和土地安置流亡難胞,使其生產自給。[11]
還有一些報紙以媒體自身優勢和特點參與和關注救助工作,通過對社會捐款數量和走向的公布,或者抨擊有關部門賑濟管理過程中的弊端,有效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也贏得了社會和民眾的信任。如1945年1月4日的《新華日報》,刊登了《餓的還是挨餓,宿的還是露宿,難民站職員倒很安閑》一文,披露了陪都重慶的某個“賑濟委員會”的劣行,文章將其工作效率低下和不負責任的情況公布在社會民眾面前。文章還對其提問道:這樣能把事情辦好嗎?難胞們能得到救助嗎?同時嚴厲地指出:“這種麻痹和無效率的情形,用官僚機構的一套,來應付救火一般的濟難工作,實在是應該改革了。”[12]
民眾對報紙在救助難民工作中作用的信任,還體現在人們以報社為依托,借助報紙組織救助活動,或者由報社代收捐款等。如由上海國際救濟會中西會長共同署名,在《申報》刊登《上海國際救濟會征募難民御寒舊棉衣被》,為他們所辦各收容所中的難民募集不足之衣被。[13]1938年12月4日,《申報》登載了社會人士許孝格發動少年兒童為難民捐助的文章《向全滬小朋友勸募寒衣文》等。[14]筆者注意到,在《新華日報》的“讀者園地”欄目里,僅在1943年的2月和3月間,就刊登有多篇有關難民救助的文章,如《擴大救濟豫災運動》《為災民吶喊》《當前救濟事業之重要》等。[15]
委托報社代收代轉捐款是當時公眾救助難民的一個重要途徑,然而各個報社并非僅僅履行代為轉送這樣的義務,而是對歷次捐款的單位及個人,認真清晰地記錄和公布其名單以及捐款的額度。盡管有一些捐助者(如小學生)的捐款數額非常小,有時可能僅有一兩角錢,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們表達的是心情和愛意,其中能體現捐助人的真摯情意,這樣的事例,能夠喚起全社會對難民救助的熱情參與,也能使社會公眾看到報紙主辦者關注社會疾苦、以真情感動民眾的良苦用心。《大公報》屢次刊載代收節約捐款者的名單,僅在1938年11月2日到12月29日,兩個月之內,公布名單就多達46次。一些社會團體和個人委托報社代收捐款的情況還有很多,《大公報》《申報》《新華日報》等重要報紙都被社會各界所看重。可見,此時的報紙真正起到了文化中介的作用,為求助者和救助者之間架構起聯通心靈的橋梁。
在抗戰期間,《大公報》曾因日軍對各地的侵占,社址多次遷徙,最早由天津遷至漢口,又遷至重慶等地。在漢口時期,自1938年4月19日起,在報紙頭版頭條經常刊登同一啟事,告知讀者,該報代收救護傷兵醫藥捐款,也接收外地助募者捐贈的款項,并寫明了捐款的時間、地點及外埠捐助匯款事項等。報紙還堅持將每一筆捐款如數刊登公示,既張揚正氣、鼓勵捐助行為,又利于報刊的募捐管理接受社會監督,起到積極的社會宣傳作用。1938年10月17日是《大公報》在漢口出版的最后一天,至此該報在漢口已刊登76次捐款報告,公布各界人士和民眾通過該報為傷員捐款情況。該報當日發出最后一次在漢口的募款報告《本報代收救護傷兵醫藥捐款報告(七十六)》,公布76次捐款總額為“國幣十四萬六千七百零四元二角二分八厘”。[16]
《新華日報》被委托代收的救助捐款,既有香港歸僑救濟難僑的募捐,也有工廠員工們為遭受寇災落難同胞而募集的錢款,還有單個的工友為前方士兵和戰爭難民積攢的捐款。一位工友在送來自己的募捐同時,還表述了想發起一個救濟難民募捐運動的心愿,并通過報紙提出建議,希望政府部門和大的企業出面,組織全面的救助難民活動,認為上上下下都伸出救援之手,“可以救活無數的難民”,“是國家之幸,人民之幸”。[17]戰時報刊積極開展難民和傷員救助工作,受到了社會公眾的歡迎,也贏得了各界廣泛的好評。《大公報》(漢口版)1938年4月12日刊登《義教實小學生募捐》一文,內容反映了《大公報》社發起的慰問傷兵活動得到了社會響應,以至連小學生都是非常熱情地參與進來。該文為漢口義務教育第一實驗小學全體學生寫給報社編輯的信,信中寫道:“前幾天我們聽到臺兒莊大勝的消息,幾乎快樂得發狂,可是靜靜的一想,勝利了固然是快樂,但是這次的勝利,完全是那些英勇抗戰的將士們的生命和熱血換得來的。我們想到了這一點,并且得到了老師的同意,就和許多同學去募捐,為受傷的將士們作醫藥費,現在連我們的糖果錢合共六十元零五分,送交貴報。”[18]報紙在難民救助問題上以多種形式加強與讀者的交流與溝通,對推動抗戰救助工作是個有效促進,對擴大報紙的社會影響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不僅起到了傳遞信息的功效,而且有利于拉近編者與讀者的距離,真切地反映讀者的心愿與情意,從而能夠產生更好的親和力和感染力。
抗戰時期報紙媒體從事難民救助工作及取得的成效,使我們從中看到,它們在社會宣傳和民眾動員方面所做的努力,適應了抗戰事業的需要,不僅對于救助和安撫戰爭落難百姓、對于服務戰事和支援前線是個重要的貢獻,同時這些報刊擴大了在社會中的影響力,獲取了更多民眾對其的認同和信任。
三、結語
觀察近代百余年來中國報刊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如果說,其主要社會角色可概括為啟蒙、革命與追求國家現代化的話,那么抗日戰爭時期,報紙在抗戰救助方面的宣傳活動,則是將民族解放事業與關注民生、社會發動的實際運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幅“抗戰不分前線后方,萬眾一心報國救亡”的壯麗畫卷。新聞媒體特有的輿論導向功能和社會傳播作用,要求它是一個有力的“接收—發送”傳感器,能聽到公眾的訴求和時代的呼喚,能看到面臨的任務和肩負的責任,能想到承擔的使命和應有的作為,并能在此基礎上向公眾傳播正能量,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從抗戰之前報紙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歷程來看,它曾在思想啟蒙、救亡圖存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因當時社會發展及報紙自身發展條件等因素制約,它所涉及的受眾面是有限的,它所影響到的社會范圍也相對較小。而相比之下,抗戰時期報紙在民眾發動中所起到的作用,則是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僅從本文所述戰時報紙與救助難民問題而言,報紙此方面消息所占篇幅之多、內容之豐富、說理之深刻,特別是其大力倡行的“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救助難民也是神圣抗戰”等號召已經深入人心,并化為各個社會階層和大眾的熱情行動,這是中國社會歷史的進步,也是近代報紙在抗日戰爭時期取得新發展的歷史見證。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研究”(15BZS092)研究成果
注釋:
[1]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我們關于目前文化運動的意見[C].劉增杰等.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上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12-13
[2]難民凍死日增急盼捐助衣被,各界慨捐給養方可無慮,普善山莊征募棺木經費[N].申報,1937-11-27(5)
[3]難民區絕糧[N].申報,1937-11-12(7)
[4]廣告[N].申報,1937-11-2(5)
[5]廣告[N].申報(香港版),1939-5-25(2)
[6]略論節約濟難[N].申報,1938-10-20(4)
[7]向本報讀者呼吁[N].大公報(漢口版),1938-4-6(第1張-3)
[8]榮維木.近十年來抗日戰爭研究述評[J].教學與研究,2005(8)
[9]援助被難同胞的義務[N].申報,1937-11-12(5)
[10]難民傷兵[N].大公報(漢口版),1938-2-10(第1張-2)
[11]怎樣安置難胞[N].新華日報,1944-11-19(4)
[12]餓的還是挨餓,宿的還是露宿,難民站職員倒很安閑[N].新華日報,1945-1-4(3)
[13]上海國際救濟會征募難民御寒舊棉衣被[N].申報,1937-9-17(5)
[14]向全滬小朋友勸募寒衣文[N].申報,1938-12-4(16)
[15]擴大救濟豫災運動[N].新華日報,1943-2-6。為災民吶喊[N].新華日報,1943-3-3。當前救濟事業之重要[N].新華日報,1943-3-6
[16]本報代收救護傷兵醫藥捐款報告(七十六)[N].大公報(漢口版),1938-10-17(第1張-4)
[17]工友關心難胞士兵,捐款千元救濟慰勞,王清理君寄信本報,建議擴大募捐賑救難胞[N].新華日報,1944-12-11(2)
[18]義教實小學生募捐[N].大公報(漢口版),1938-4-12(第1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