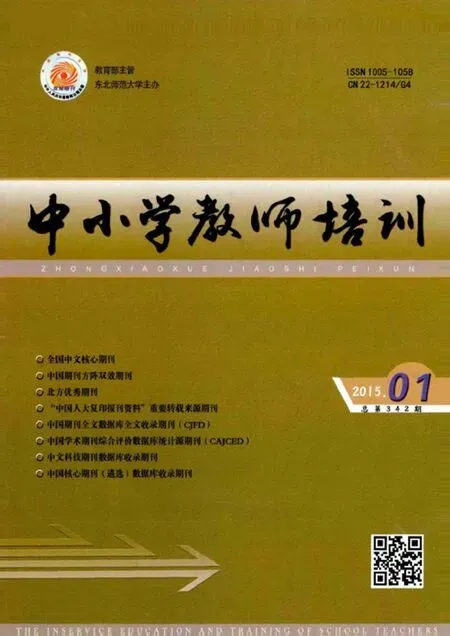從“靜聽—接受”到“研究—體驗”
——中小學教師培訓模式的變革
辛繼湘,李金國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湖南長沙410081)
在“國培計劃”的全面展開和推動下,中小學教師的培訓活動蓬勃發展,呈現出培訓范圍廣、內容種類多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新課程改革理念的傳遞和輻射,滿足了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需要。不過,在各類中小學教師培訓中,雖然培訓的內容比以往要豐富和新穎很多,但培訓模式卻仍以“靜聽—接受”為主,仍然側重于教育教學知識技能的單向傳遞,這使得培訓無法達到所期望的效果,有必要改進培訓模式,真正使每一位中小學教師在培訓中受益。
一、“靜聽—接受”培訓模式的特征與局限
“靜聽—接受”式培訓是指培訓者向教師傳授已有的教育教學知識技能,教師主要以靜坐聽講的方式加以接受的培訓模式。這種培訓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知識目的先行。學科專業知識的增長、學科教學知識的增進、課程改革理念的傳播等是當前中小學教師培訓的主要目標導向,而這些內容主要以知識形態呈現在培訓過程之中,知識傳遞居于培訓的核心,成為整個培訓為之努力的方向。
二是單向定論演繹。“靜聽—接受”培訓模式偏重于知識的呈現、認知的強化,熱衷于將已成定論的知識以演繹的形式單向度向參訓教師傳遞。
三是看重學習結果。知識目的導向決定了“靜聽—接受”式培訓必然采取結果性的評價方式,重視教師經過培訓后學科專業知識和教學知識的增長、教育教學技能的提高,并以此作為教師參訓效果的主要評價指標。
雖然“靜聽—接受”培訓模式對于增加教師的學科知識儲備、傳播新課程改革的理念、提高教師教學技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顯:
第一,培訓目的片面。在工具性、主知性教育觀念框架內建構的培訓活動,認為培訓就是為了讓教師掌握更多的專業知識以提升自身職業能力,培訓的重心在于知識技能的積累,忽視了教師的興趣、態度、情感、意志乃至生命的完整體驗。知識成為工具化的存在,變成與教師的情感、需要、意志和生活隔離的東西。而真正好的教師培訓,不僅要讓教師獲得足夠的知識和技能為后續職業生涯提供幫助和支持,還要在培訓的過程中引發教師理解職業發展的價值和意義,體驗培訓過程帶來的內心快樂和心靈敞亮,獲得精神上的關照、鼓舞與提升。
第二,教師主體性旁落。培訓者往往不考慮教師參訓前的狀態、存在哪些實踐困惑、有何專業期待和未來職業規劃等等,沒有顧及教師自身的主體性,參訓教師被動接受來自培訓者傳遞的知識,缺乏對知識的質疑與思考,缺乏對“定論”的探究體驗,也缺乏對培訓者課堂講授的積極回應,因而這些知識通常并不能真正融入教師的主體意識之中,也就無法對教師的教育教學產生富有啟發性的深刻影響。
第三,生命體驗缺失。“靜聽—接受”式培訓,教師以聽講、接受的方式進行,沒有相應的機會和途徑去經歷、體驗,不能融入自身經驗深刻領會知識背后所蘊含的多種意義,也不能在真實的教育教學情境下靈活地運用知識。正如杜威所言“如果所溝通的知識不能組織到學生已有的經驗中去,這種知識就變成純粹言辭,即純粹感覺刺激,沒有什么意義。”[1]如果培訓忽視了參訓教師自身的生命體驗,就會成為了一種枯燥、機械、沒有趣味、缺乏生機與意義的活動。
二、“研究—體驗”培訓模式的特征與優勢
“研究體驗”式培訓是指參訓教師與培訓者一起就教育教學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切磋、探究、體驗,從而獲得知識、技能、情感、態度、價值觀等完整生命發展的培訓模式,其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目的多元并重。“研究—體驗”式培訓十分重視教育教學知識背后蘊含的精神、文化、意義,以及參訓教師參與探究過程的前期經驗和內在體驗。培訓目的不再只是關注知識的簡單積累,還注重教師在經歷問題切磋、深層對話、合作探究等體驗活動后獲得情感、態度、意志及專業精神等方面的發展;培訓目的也不再是外在強加和設置,而是更多地基于教師在理論學習和教學實踐中自身的需求和期待,融入教師的生命意志和職業追求。
第二,多向交流對話。“研究—體驗”式培訓重視多主體、多層次、多向度的交流對話,它可以是培訓者和參訓教師之間的對話,也可以是參訓教師之間的交流;既包括培訓者和參訓教師的共同探究,也包括參訓教師之間的合作研究。這樣的過程不是已有教育知識的單向傳遞,不是培訓者高高在上的訓誡。它重視的是培訓者和參訓教師之間的民主平等,尊重教師對于教育知識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一種教師和學生之間互惠式而不是從前那種傳授式和控制式邏輯衍生的教學關系。”[2]培訓者與參訓教師在互為主體的關系中共享話語權,在相互交流和研討中共同發展。
第三,問題研究主導。在“研究—體驗”式培訓中,注重對教育教學問題進行探究,這些問題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參訓教師參訓前在理論學習與教育實踐中遇到的困惑;二是教師在培訓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切近教師自身的教育教學情境,具備教師自身教育經驗所具有的現實性,能更有效地激發教師對問題思考、研究與分享的愿望,從而讓教師在共同探究中深刻理解不斷生成的新知識,并能感知知識背后蘊含的精神價值和豐富意義。
“研究—體驗”式培訓的優勢主要在于:
第一,發揮了參訓教師的主體性。作為有意識、有目的地參與培訓活動的教師,具有在培訓過程中發揮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的可能。“靜聽—接受”式培訓限制和阻礙了這種可能,造成教師主體性的旁落。而“研究—體驗”式培訓中,教師可以對相關知識進行質疑,可以積極主動地與培訓者及其他參訓教師進行溝通、交流、研討并反觀自身的經歷,可突破現有的結論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思想,能夠不斷超越自身已有的認識而進行新的創造。
第二,形成了參訓教師共同體。“研究—體驗”式培訓注重發揮教師個體的主體性,也很看重參訓教師之間的交流合作,讓教師們在共同探討、互相學習的過程中獲取知識、發展能力,獲得更豐富的體驗。這種共同學習、探討的過程有利于互利互惠的教師共同體的形成,有助于教師在以后的理論學習和實踐困境中能夠相互理解與支持,在教育教學工作中攜手并進。
第三,提升了教師的創新能力。“靜聽—接受”式培訓,參訓教師從培訓者那兒接受現成的知識和技能,培訓過程中只有單純的“講”和“聽”,教師缺乏質疑和思考的空間;而“研究—體驗”式培訓基于教育教學實踐中的問題情境,參訓教師與培訓者共同探究,經歷質疑、分析問題、實踐檢驗、總結升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具有開放的心態,大膽想象、多方論證、樂于創新、敢于突破,其創新能力能夠得到很好的提升。
三、“研究—體驗”培訓模式的實施策略
教師職后培訓面對的是已經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較強認知能力、學習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成人,是對自身興趣需要、專業成長、生命發展有著獨立思考和見解的專業人員,“靜聽—接受”式培訓沒能很好地顧及參訓教師的這些特點,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助益十分有限,有必要改變培訓模式,讓教師通過“研究—體驗”的培訓模式,不僅能獲得新的教育教學知識與技能,還能感受到教師工作的意義和自我實現的價值。
(一)培訓目標:變知識主導為多維目標整合
如前所述,知識主導下的教師培訓將目標定位于學科知識及認知能力的提高,而忽略了參訓教師在培訓過程中的興趣、情感、態度、意志、價值觀等要素的確立和發展。而對于參與職后培訓的教師而言,由于在工作中常常面臨教育教學的困惑和職業瓶頸,后者對于教師的成長和發展其實更為重要,更貼近參訓教師的切身需要。因此設置培訓目標時,須改變知識主導的價值取向,在確立知識目標的同時,明確情感、態度、專業精神等方面的目標,并從整體上加以整合,從而引領教師們在知識學習過程中獲得多方面的發展,形成更強勁的后續發展動力。
(二)培訓形式:變單向講授為多向交流研討
教育教學知識的單向傳授易使參訓教師處于學習的被動狀態,而轉換為多向交流研討之后則有利于參訓教師在培訓中發揮自身主動性。具體而言,需要在培訓過程中改變“專家講座”為主的形式,可采用問題診斷與研討、教學觀摩與剖析、小組同課異構、“影子”教學實踐等互動交流形式,變單向知識傳輸為參訓者與培訓者、參訓者之間乃至實踐基地一線教師之間多向、多層次的交流研討,促進參訓教師主體性的發揮,以完整的生命主體共享知識與經驗,共同體驗研究的過程,感悟教育教學的真諦。
(三)培訓過程:變理論演繹為問題合作研究
“靜聽—接受”式培訓采取知識主導的理論演繹過程,窄化了培訓活動的目標與內容,簡化了培訓過程的復雜性,固化了整個培訓的流程。倡導由理論演繹轉向問題合作研究,是為改變培訓目的的片面性,從而豐富培訓過程的生動性和開放性。問題合作研究的過程以問題為導向,實現多主體間的合作、對話與研究,改變過去忽視參訓教師自身體驗的狀況,促使教師把興趣發展、情感意志、生命體驗融入培訓過程中,從而加深對教育教學問題的反思,升華對未來職業發展的期待。
(四)培訓場域:變課堂中心為開放培訓空間
“靜聽—接受”式培訓主要以課堂為培訓場所,固定化的場域阻礙了教學空間以及各種課程資源的開放程度,而“研究—體驗”式培訓場地不局限于課堂,還將空間延伸到中小學校教育教學現場、社區博物館、展覽館、圖書館、大學實驗室和微格教室等場所,參訓教師在培訓者引導下開展問題研討、小組合作探究、教學情景模擬、案例剖析、教學設計研究、課堂教學實踐等,實現培訓空間、課程資源的多元開放。
(五)學習評價:變結果性評價為過程性評價
“研究—體驗”式培訓注重過程性評價,將評價視野投向參訓教師的整個學習過程,而非單一的預設的學習結果。培訓過程中教師學習動機的激發、學習態度的展現、教學理論的運用、教學策略的嘗試等都成為評價的重要內容。當然,注重過程性評價并不意味著否定結果性評價,即評價在關注培訓過程中教師的學習進程、學習態度和研究體驗的同時,也不忽視不同學習方式下教師的不同學習結果以及經由培訓后跟蹤測評的學習結果,并把這些結果和培訓過程密切聯系起來,以此對教師的專業發展起到激勵作用。▲
[1]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05.
[2]大衛·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與后現代教育學[M].郭洋生,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