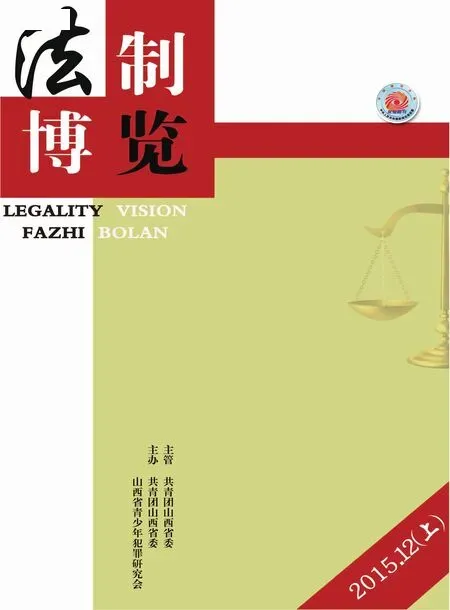從“公意”角度解讀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
從“公意”角度解讀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
王俊
中共婁底市委黨校,湖南婁底417000

摘要:“公意”思想是盧梭社會契約論的奠基,是構建國家政治合法性的有效來源。在盧梭《社會契約論》的論述中,契約體現“公意”這一思想貫穿始終。本文通過揭示盧梭的公意思想與社會契約之間的關系,來分析、評價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關鍵詞:社會契約;公意;盧梭
中圖分類號:B565.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5)34-0281-02
作者簡介:王俊(1962-),男,漢族,湖南婁底人,本科,中共婁底市委黨校,副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

《社會契約論》是18世紀法國工啟蒙運動主要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讓·雅各·盧梭)的代表作之一。公意是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最核心的概念,盧梭從公意思想的闡述出發,進而建構了他對于政權如何形成,國家如何運轉的近代民主政治理念,為國家權利和政府權力找到依據。
一、公意的政治內涵
《社會契約論》這本書中對公意的論述有很多處,大致來說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把握盧梭對公意理解。
首先,公意是相對與個人意志抽象的結合。公意來源于個人意志又超越于個人意志,個人意志和公意在本質上應該是一致的。盧梭說:“縱使個別意志與公意在某些點上互相一致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至少這種一致若要經常而持久卻是不可能的,因為個別意志它的本性總是傾向于偏私,而公意則總是傾向于平等。”[1]為了確保公意的公正不偏私盧梭認為社會契約的每個締結者應該將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權利全都轉讓給集體,也就是說由公意去保證公民的正當權利。為了更好的闡述這個問題,盧梭又論述了公意與個別意志、團體意志以及眾意的關系。公意不等于眾意,眾意可以演變成社會某個集團的利益,從而成為特殊利益,所以眾意并能不代表整個公民的共同利益。
其次,公意不能被代表。盧梭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只要選出了代表,他們就不再自由,他們就無足輕重了。”[1]只有由公民集體投票表決產生的意見才是公意,盡管公意不是每個人的意志,但它代表的是集體的最優選擇,代表的集體的利益。對于公意不是所有人的意愿這點,盧梭認為并不需要所有人同意才能形成公意,只要是多數人的意見就可以被稱作是公意,他確立了多數人同意原則以確保公意不被個人和小團體的意見篡奪。至于什么是多數人的意見?他確立了公意的投票比例數的兩條法則,“一個是:討論的事情越重大,通過的意見就應當越接近全體一致;第二個是:所涉及的事情越需要迅速解決,對立雙方的票數差額就應當越小,在必須馬上做出決定的討論中,只要一票的多數就行了。”[1]
最后,由公意產生城邦的絕對主權者。盧梭將公意抽象出來用“主權者”表示,主權者的意愿就是公意,所以主權者不會違背公意,主權者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證城邦中的個人幸福生活,主權已經是一個最高意志的存在,沒有任何權利能夠凌駕于他之上,而城邦中的各項事務都受他支配,根據公意可以確立城邦中的大小事務,立法權,行政權等權力只是主權行為,但不是主權者,公意才是決定主權者的唯一途徑。
二、“公意”思想對社會契約的作用
(一)“公意”思想是契約公正簽訂的基礎
在《社會契約論》這本書中,一開篇盧梭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人奴役人的強權社會,并多次駁斥格老修斯的觀點,分析這種強權壓制下社會的不合理性。那么怎樣一種契約就是合法的呢?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甚至是放棄自己的義務……這樣的一種棄權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為的一切道德性。”[1]所以,盧梭認為制定契約不是去束縛人類的自由,不是去剝奪人有自由的權利,相反契約是為了解放束縛而產生的,是為了打破人類不公正的束縛,是為了更進一步的實現民主,平等,自由。
(二)由“公意”產生法律保證人民的政治權利
社會契約首先是來自人民,由人民自己組成的政治共同體產生“公意”,由人民自己自由協議產生國家,這樣國家權力的運行就代表公眾利益,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公意”。光是從國家體制上設定還不能足以確保這一點,盧梭考慮到運用法律手段也就是國家機器來保證國家是自由和平等的。由于“法律是政治體的唯一動力,政治體只能由于法律而行動并為人感知,沒有法律,已形成的國家只不過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體,它雖然存在但不能行動。因為每一個人都順從公意,于是就出現了法律的必要性。”[1]法律的確立,不僅體現了公意,更保證了契約的穩定。
(三)將“公意”的統治轉為法律的統治,保證契約不可侵犯
“要使一個國家的體制能真正穩固和持久,就必須嚴格按照實際情況行事,使自然關系和法律永遠在每一點上都協同一致。”[1]作為人民意志的執行者,政府具體負責執行法律并維持社會的以及政治的自由,政府在對外和對內的許多事務中,有時可以代表國家,但是,從根本意義上講,它不是國家。“政府必須給人以法律上的自由,必須提供物質福利,消除財富分配上的重大不平等”[2],必須執行公意。一方面法律是公民的政治權利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政治權利以法律為限,必須服從法律的統治。人民的主權如果被篡奪,則公意必然蛻變成暴君的意志,政府如果失去了民心,則必然違背了人民的公意,也必然失去了公意,這樣的政府損害了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有權推翻它。
三、對以“公意”為基礎的社會契約的反思
盧梭的公意思想反映了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時期追求平等、為自由而戰的時代要求,為以歐美為主的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公意”導致集權或多數人的暴政
盧梭希望通過“主權者”的力量維護權利公民的利益,力保自由平等的生活,因此給予主權者一個極大的權威認同。公民與主權者訂立契約不但要將他的所有權利轉讓出來,更要無條件的聽從主權者的決定。“盧梭在否定了他人的極權主義的夢想的同時又走向了新極權的傾向,盡管盧梭認為人與人的約定是出于人的自愿的約定,沒有強迫的可能性,而實際是盧梭在這里就把人們的共同意志作為所有人的行為標準,在這里明顯地為我們的生存制定了一個新的權威。”[3]
(二)直接民主不是保證主權者永遠正確的可靠方式
盧梭從直接民主決策的公意中推出了主權者永遠正確的“真理”。然而直接民主卻不能保證公意的絕對正確。盧梭的社會契約中設想政治共同體是徹底的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它要求人民都理性的為他人著想為公共利益著想,要求政府完全按照公意行政,克服公意本身的弊端,要求行政人員沒有私心,秉公辦事,在盧梭構想的社會中,道德具有奠基石般的地位,沒有道德,一切都會不存在,而且這種道德要求非常之高。最終導致奠定在這種社會契約基礎上的只能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理想國。
(三)“公意”理論與民主體制的矛盾性
盧梭主張立法權與行政權分離,立法權由主權者控制,任何上升為法律的條列都來自公意,是全體人民對全體人民做出的規定。盧梭將公意與個人意志對立起來說,并要求每個人都要服從公意,是與他當時所處封建時代密切相關的,是對當時個人集權的壟斷統治的一種挑戰,但他反對個人專制時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另一種專制形式——資產階級專制。盧梭恐懼“民主政府”演變成為人民的暴政,在盧梭眼中以保障全民權利為目的的精英政府會不會演變成為一個由富人控制的代表這個階級利益的假民主政府,盧梭卻沒有考慮到。這也是盧梭在這個問題上的時代局限性。
四、結語
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把傳統自然法提高到新的高度,以自然法保障天賦人權,構建契約后又將契約精神上升到法律層面,以制度的形式確保人民的權利,對盧梭對平等和主權在民思想的不懈追求,使得這本著作成為18世紀最有研究價值的鴻篇著作之一,然后正是由于盧梭對公民政治權利近乎完美的最求也使得盧梭的“公意”思想頗具有爭議性,盡管如此,啟蒙思想家盧梭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抨擊,對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使得盧梭的思想閃爍在歷史的長河中。
[參考文獻]
[1]盧梭,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2]崔艷霜.盧梭立法倫理思想的研究[D].河北大學,2008.11.
[3]王碧英.論“契約”公正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解析[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05,20:83-84.